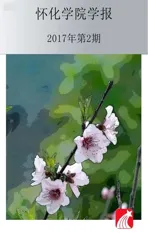论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三个向度
2017-03-10李青
李青
论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三个向度
李青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程颢在《识仁篇》中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可以从三个向度来理解:从仁之体的角度看,人与天地万物同禀一理、一气而生,因而能在“身—心”一体的基础上识自身痛痒并将此知痛知痒的心推扩出去;从仁之用的角度看,一体之心感通无碍,人便自然而然的对此“大身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具体表现为博施济众,立人达人;从仁之乐的角度看,仁者与万物一体无碍,人便能从这一体和谐中感受到心体的和乐安宁。这三个向度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人我关系、人物关系紧张的今天,程颢“与物同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与物同体;仁;一体之乐
程颢,字伯淳,后世多以“明道先生”称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首先提出了“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在程颢那里,“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1]33,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将天理生生不息之性与仁联系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以浑然与物同体来指点仁,并把此作为仁的最高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是程颢的代表性文字《识仁篇》中的一句,紧接着首句“学者须先识仁”。牟宗三先生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无物我内外之分隔,便是仁底境界,亦就是仁底意义了”[2]180。这里“与物同体”是识仁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浑然与物同体呢?这仅仅是功夫修养圆熟之后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还是有其本体论上的依据;是人在认识的基础上逻辑思辨的结果,还是在实践上切切实实的一种功夫?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主要阐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三个不同的向度:仁之体、仁之用和仁之乐。本文和以往关于程颢仁说的研究论文相比,从仁之体、仁之用和仁之乐三个向度全面阐述了“仁者与物同体”的涵义并论述了三个向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三个向度是通过一体之心的不断外扩而联系起来,较之以往更为全面和系统。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论述了程颢“浑然与物同体”思想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身—心”感通无碍与仁之体
如果说程颢以万物生生之意说仁是正面说仁的话,他以身体的“手足麻痹为不仁”来从反面对仁进行说明实乃一创举。俗语说“麻木不仁”,在明道先生那里,仁的一大特点便是感通无碍。在医家那里,不通便是身体的整体运作出了问题,是不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手足麻痹,不知痛痒,而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
医书言手足麻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想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1]15。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33。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1]74?
心体发用流行,而身体则是这一发用流行的承担者和实施者,也即种种道德修养都是以具体的可操作的身体为基础的。当手足麻痹时,“气已不贯”、“疾痛不与知焉”。身为人便没有不爱自己的四肢百体的,这是天性所在,进而会因为爱而生出对身体的责任感。不仅如此,程颢还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那么,现在的问题则是个体的小我如何才能做到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重要的,它不仅能回应“我为什么要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困惑,同时还关系到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问题。
其实,在程颢那里,人与天地万物是本来一体的,这也就是仁之体。这里,“一体”应该怎样去理解呢?牟宗三先生认为,“浑然与物同体”之体作一体解而不是作本体解。与此不同的是,蒙培元在《理学范畴系统》一书中提到,万物一体不是从形体上说,而是从本体之理说。要弄清楚一体的真正含义以及二先生的孰是孰非还需要到明道的话语中去看。人与万物同禀一气而生,这可以说是宋明儒的共识,因此,人与万物一气相连,这是程颢一体说中不可忽略的含义。“在其一体论的证成中仍然存在“气论”的预设。天地为一身,此身实在就是“一气流通”、“一气贯通”的大身子”[3]45。“否定或遮蔽气在一体证成中的地位,其结果往往是将儒学的“一体之仁”单纯的视为一种心灵境界,而丧失了存在论的向度”[3]45。除此之外,程颢有“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之说,人与万物都是从这“生生之谓易”的道理出去,也即是程颢所说的“只为从那里来”,天理落实在万物之中便为万物之性,人禀得此所以然而成为所当然。因此,二先生之说皆是明道一体之涵义其中的一个面向。
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那么,人在其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其实在儒家传统之中一直都有人是天地之心的说法,《礼记》中有“人者,天地之心也”。“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万物虽都是禀得生生不息之天性而来,然而人则能推,物则推不得。“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字在这里的作用显然是关键的,这也是人与物区别的关键。人与天地万物的感通无碍,如果从主动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人能推的结果。“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不仅是圣人,人人皆有此感通无碍之心,不必外求。此时,能与天地万物感通无碍的“我”,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体之身的小我,而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大我”。
程颢有“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之说,这里“不知觉”是说心对己身、对外物失去了感知能力,“不认义理”就是说不知道人与天地万物是同禀一理而生,本是一体的。从程颢对何为不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在程颢那里,仁的一大特点便是能够在“身—心”的结构下感通无碍,这种感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一体之身中,心作为孟子所说的“大体”,是整个身体运行的主宰者。心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便是知觉,“程颢所主张的作为仁的知觉并不是生理上的知痛知痒,而是在心理上把万物体验为自己的一部分的内在验觉。”[4]对个人身体的感通无碍是做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前提,因为如果连自己的麻木痛痒都知觉不到的人,我们又如何希冀他能够去知觉去关心他人的痛痒呢?
另一方面,当把人放到整个天地万物的大视域中去时,那么在仁者的眼中,整个天地便是人的大身体,而人则是天地之心。因此,将此一体之仁心不断向外推,那么天地万物都是与我息息相关的一部分,是包括我在内的痛痒相关的大身体。张载的《西铭》篇中作了详尽的发挥:“乾称父,坤称母;与兹藐然,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程颢评论说“《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此体便是仁之体,也就是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在此基础上,人自然而然的对天地万物有着关爱之情。这种对天地万物的不容己的关爱之情其发端便是人的恻隐之心,孟子已经指出这一点,“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其实早在孟子就开始用“痛感”来描述仁之体段。他认定恻隐之心是仁心的最重要的表征,是人禽之别的关键。“恻隐”二字即是痛感语,其义不外是伤痛之极。怵惕亦为恻隐用语,本是《内经》所载一症状。”[5]恻隐之心的最初发动仍然是离不开“身”的。可见,身与心一体想关,只有身心如一,整个生命体才能畅通。如同人四肢百体是自然感通,痛痒相关的,“拔一发则百骸为之震”,天地万物原本与我就是浑然同体的,因此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是主观的臆想,也不是逻辑的推理,既有本体论上的根据,也是实实在在的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以恻隐之心为发端,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推扩出去,首先是他人,然后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最后甚至是没有生命气息的瓦石土块。其结果便是视天地万物都是包括人在内的大身体的一部分,天下万物不是与我没有关系的“他者”,而是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对待他们就如同对待自己的手足四肢,痛痒冷暖能够时时观照留意,这也便是仁的境界了。“人之一体不容己之心是无限的,生动活泼的,所以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圈子,而遍润万物,周流四方”[3]226。
二、“两行之理”与仁之用
天地万物都是与我一体相关的一部分,这便是仁之体,人将此一体之仁心推扩出去,天地万物这个大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人自然而然要去解决,这落在现实层面上便表现为立人达人,博施济众,这也即是仁之用。“宋明儒者不断强调对最高境界的体悟和觉解,更重视仁者境界在人伦事务中的践履和发用,在日常事务中体现仁,而不是把仁作为一个空洞的教条”[6],程颢亦是如此。事实上,在程颢那里,已经可以看到理一分殊思想的落实,这是儒家“两行之理”[7]的体现。
在《识仁篇》中,程颢在“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后面一句便说到,“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因此,仁是全德,是其它四德的根据之所在,就如同牟宗三先生所说的,仁不为任何一德目所限定,但任何一德目足以表现仁。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1]14。
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体仁之体[1]15。
因此,在程颢那里,仁不是一个空洞的教条,仁就真真切切的体现在待人接物之中。也就是说仁之境界不是缥缈高远的,而恰恰就在日用伦常中见。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与行为指导,而上面的说法则是体现了以仁为体,以义、礼、智、信为用的倾向。“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识得此理应该就是识得此仁体,既已识得此仁体,则接下来要做的便是以诚敬存之。刘蕺山在《明道学案·上》中说:“程子首言识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识得后,只须用葆任法,曰‘诚敬存之’而已。”因此,即本体即工夫,体用不二是明道之学的精华所在。
程颢强调“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的天人一本以及对“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仁体的存养,因此其学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高妙圆融。朱子认为“明道说话浑沦,然太高,学者难看”,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的按语云:“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无所不入,庶乎所过者化矣。故其语言流转如弹丸。”程颢虽重视一体之仁,但他并没有忽视仁的具体发用流行的过程,如他所说的“义、理、智、信皆仁也”。而且,他在讨论手足麻痹为不仁时说: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遗书》卷二上)陈来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把仁者与万物一体作为”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内在基础,它是要落实到社会关系和忧患之上。后来,小程子提出“理一分殊”,朱子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发挥,他们和程颢的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大程与小程及朱熹的区别在于,对于理一和分殊,程颢更看重的是理一、浑然、一体,而对于分殊的说明相较小程及朱子而言则较少。
程颢自身也在践行着这一“理一分殊”的原则。明道先生在为官之时,爱民如子,据其弟子杨时记载,“明道先生坐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曰‘颢常愧此四字’。”(《二程外书》卷十二)其为政之道很好的践行了孔孟的主张。“在明道看来,学问的宗旨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治民,二是育德,成就事功与心性修养并举”[8]24。事实上,程颢十分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并积极想出对治方法,他在《论十事劄子》中便讨论了“师傅、六宫、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事、四民、山泽、分数”等诸多现实问题。横渠先生说:“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亦记得孰”。(《遗书》卷十,《洛阳议论》)因此,程颢自身便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践行者。在视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相关的基础上,将此感通无碍之心推扩出去,真正视民如子、博施济众,在识仁之体之后处处将仁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真正做到了成就事功和修养心性并举。
三、仁之乐与仁者境界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仅涉及仁之体与仁之用,它本身也是一种境界。仁者若是能够做到“浑然与物同体”,那么在此境界中自能体会到一体之乐。这里所说的一体之乐,是说在人在能够视天地万物与己身浑然同体之后,见人与万物欣欣向荣而自然从心底生发出的和乐。如果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是要学者们先识仁体的话,那么仁体是怎样和一体之乐联系起来的呢?这是我们讨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而程颢的“与物同体之乐”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从观天地生物气象而体验到的生机之乐以及自家的仁心能与万物之生意感通的体知之乐。其实,乐不必外求,一方面,人心若不为私意间隔而廓然大公,仁心冲扩无限,自能感受到胸中之乐源源不断随着仁心的发散而消长。阳明先生的一句话能较好的解释这个问题:“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乐和畅,原无间隔”[9]69。仁心若有私意,对外物生起种种计较之心,则“我”便与天地万物这个大身体有了间隔,就像肢体的麻木不仁会使周身血气不贯一样,人与外物的间隔也会让这个大身体周流不通。如此,乐则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就像手足麻痹时人自然不会有乐感一样,若将此心推扩出去,当天地万物这个大身体有诸多问题时,人自然与不会生出乐意。因此,在人意识到这个大身体的种种“病痛”之后进行积极对治,使万物重归和谐,当看到万物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时,心体自然有和乐之感。
总的来看,这一体之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便是说万物与我合一,而又能反求于自身之乐。这主要是继承了孟子的思想而来。此外,因见万物春意盎然,从“观天地生物气息”中感受到的生机之乐以及自身仁体能够与万物盎然生机感通的“体知”之乐。“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活”[1]152。不难看出,这“乐”都是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紧密联系的。“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可以说,与物同体正是一体之乐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体之乐和宋明儒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有相同之处。
和先秦儒家相比,程颢虽然也注重对“仁”的指点与发挥,但二者所体现的境界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在程颢看来,这样的仁学还不是‘仁’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博施济众只是仁的“用”(表现),还不是仁的“体”(根本)。仁在根本上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与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10]90程颢在对这种境界进行说明的时候,虽然也明确指出了“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但就像陈来先生所说的,程颢的仁学境界更多基于心理体验。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禀生生之性而来,因此与物同体是有存在论的基础的,但他并不从存在论基础出发去做分解式的讨论,而是从自身生命实践中那些真切的感受体悟来指点仁,用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言说仁。程颢以手足麻痹为不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四肢百体是人最能真切的感受到的,这也是基于自身体验的能近取譬了,是后世学者认为程颢说仁最为亲切的原因。
程颢先生本人便是体现这种仁者境界的极好的例子。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道:“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可见,一个人达到了怎样的境界,便会呈现出怎样的气象。但宋明理学家们不仅仅重视对这种仁者境界的体悟,他们认为如果达到此境界后便停留于此种状态,欣喜于此种状态而着力把捉,其结果则无疑是“玩弄光景”。因此,程颢先生“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后,紧接着便说“义、理、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仁包四德,是体,礼、义、智、信是用,博施济众亦是用,因此,恰要在用中去见体。孔子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达到仁者境界的人同样如此,义、礼、智、信不再是约束于我的外在的教条律令,人能够自觉的承担起天所赋予的道德使命并对自己完成这个使命的道德行为有极高的认同感和自觉性,对于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天地万物这个大身体有着发自本心的责任感,并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感受到精神的和乐。
结语
总体上来看,“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所内含的三个向度之间又是内在贯通的。从本质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万物同禀一气而生,皆是天命之性下贯落实的个体,一己之“心—身”结构向外推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天地万物视为与我息息相关的大身体,人便是天地之心,对于天地万物有着内在不容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现实生活的表现必然是爱民如子,博施济众。因此,“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是一种空悬而无着落的精神境界,而是儒家两行之理的重要体现,在此基础上,人与万物和谐一体,感通无碍,内心的自然和乐便自然而然的涌现,三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是一己之心不断外推最终实现本心的自然和乐的过程。
从先秦儒学到汉唐经学再到宋明理学,仁的内在涵义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孔子那里,孔子并没有给“仁”一确定的定义式的含义,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问题随机指点。总体上看来,孔子所说的仁是启发性的指点性的,为的是人真生命的挺立。到了孟子,仁可以通过恻隐之心为入手处来了解。牟宗三先生认为明道所说的感通义是总持并消化了孔子所指点之仁而真切的体贴出来的。明道以“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来论仁,是对儒家自孔孟以来的儒学思想的发展。陈来先生指出:“万物一体的仁学在这里虽然显现为主观的,但这一话语的形成及其在道学内部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为从客观的方面去把握万物一体之仁准备了基础,这是宋儒特别是程明道及其思想继承者的贡献。”[11]明道之后,杨时、吕大临、游酢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程颢这一思想。北宋以来,关于“仁”的讨论一直处于学者们关注的核心范围内,明代王阳明对于“仁”的探讨可以说也是在明道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他进一步强调了仁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总的来看,明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提出虽是受到了横渠的影响,但其思想内涵却并不等同于横渠,其以万物一体论仁,以麻痹不通为不仁,以一体之乐的境界描述仁,在中国古代仁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可见,明道先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思想在理学史上意义重大,不仅如此,因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中挖掘出对治现代社会弊端的良方。在人物关系、人我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关系紧张的今天,人不仅对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且在各种关系中也不能自我定位。而对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强调,使人能正确认识到“我—物”、“我—他”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外在的关系,而是一体与共,息息相关的。“人不是孤悬于天地万物之外的个体,人的自我理解、自我实现、自我创造,均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脉络”[12]30。个体的真生命必然不是与他人、与外物以及与世界隔绝孤立的状态,全然追求个人利益而漠视他人、世界的个体生命,或者说只顾及自身欲望的满足,动物一般的活着,那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不是孔子所谓的“真生命”。这种个人与他人、万物孤立隔绝的状态,正如程颢所说的,是身心的麻痹不通,是生命的病态,不是生命的本真样态。因此,重新审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以及拥有一种万物一体的博爱关怀无疑是重要的。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陈来.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J].河北学刊,2016(3):2.
[5]陈立胜.仁·识痛痒·镜像神经元[J].哲学动态,2010(11):32.
[6]赖尚清.程颢仁说思想研究[J].中国哲学史,2014(1):92.
[7]刘述先.理想与现实的纠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1.
[8]郭晓东.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0]陈来.宋明理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1.
[11]陈来.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J].河北学刊,2016(3):1.
[12]林月惠.诠释与工夫[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
On Three Dimensions of Chen Hao's Idea of the Benevolent is Undifferentiably One with Allthe Things
LI Qing
(Philosophical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Chen Hao's Idea of the Man of jen is undifferentiably one with all the things is proposed in To Recognize Benevolence,it could be understood in three dimensions.First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umenon of Benevolence,human beings is born from the same Li and the same qi with all creations,therefore he has the sensation of experiencing pain on the basis of unity of body and soul and can spring out it.Secondly,from the practice of jen,the unity of body has no obstacle to perception and naturally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the large body”,the implementation of it performs in bestowing and helping other people. Thirdly,from the pleasure of jen,the man of jen is undifferentiably one with all the things and has fun with all citizens,as a result,“the large body”will has not any pains at all and in harmony with our mind,which people can fell the pleasure and peace from it.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any more.Toda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and other things are in tension,this idea of Cheng Ha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nowadays.
the oneness of all things;benevolence;the happiness of the Unity of body
B244
A
1671-9743(2017)02-0058-04
2017-01-14
李青,1992年生,女,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