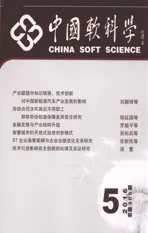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
2016-09-05黄卫东岳中刚
黄卫东,岳中刚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
黄卫东,岳中刚
(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究竟是以线上渠道替代实体零售,还是刺激了新增消费?本文从包容性创新视角提供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利用我国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信息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和普惠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从总量而言,信息技术普及率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显著为正;从结构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将从信息技术应用中获益更多。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实施“互联网+”战略促进消费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消费增长
一、引言
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供应链系统以及消费网络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并以电子商务的业态模式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毕达天和邱长波,2014)[1]。然而,交易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颠覆式改变,对于大众消费者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消费者而言,究竟是带来便捷渠道的“信息红利”还是拉动消费差距的“数字鸿沟”,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论。Bhavnani等(2008)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强化发达个体的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使落后个体进一步面临信息贫困与知识贫困的威胁。这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似乎并不能自动缩小数字鸿沟,反而可能扩大原有的差距[2]。如Shiu和 Lam(2011)采用1978-2004年中国22个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电信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循环关系仅发生在富裕的东部地区省份[3]。张红历等(2010)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信息技术发展的网络效应使得区域间逐渐形成紧密的空间联系结构,对缩小由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着独特优势[4]。大量基于亚洲、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手机、互联网及其融合发展的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给更多的人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带来福利的增加,是解决弱势群体需求的包容性创新(Jensen,2007;Conley和Udry,2010;李坤望等,2015)[5-7]。所谓“包容性创新”是指通过创新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本身的权利的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即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大多数人(George等,2012)[8]。Aker(2010)统计分析了西非国家尼日尔(Niger)2001-2006年谷物市场,发现移动电话普及率导致市场价格和价格离散度分别降低了4.5%和10%,而且市场效率提高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对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一种帕累托改善[9]。Qiang等(2009)实证研究了120个国家移动电话对人均GDP的影响,发现移动电话普及率每增加10%,将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0.8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则为0.60个百分点[10]。
近年来,随着网络消费方式的兴起,沃尔玛等欧美零售商通过“收缩门店”和“启动线上”打造全渠道零售平台来推动消费增长。我国也大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网+”战略促进线上线下互动的O2O消费(谭晓林等,2015)[11]。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络购物用户达到4.13亿,网民进行网络购物的比例达到60%;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达到了3.40亿,手机网民进行网络购物的比例由2014年42.4%提升至54.8%。在此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是否享受到了互联网应用所带来的“信息红利”?目前国内普遍关注互联网发展对实体零售的替代效应,而缺乏对居民消费总量“边际效应”的关注。此外,尽管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省间差异从1997年的3.37下降到2014年的0.24,但从CNNIC对全国城市O2O发展水平的测算情况来看,东部一线城市的综合实力、环境因素、应用水平、发展潜力方面均领先于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那么互联网的覆盖、手机的使用、O2O消费的便捷和低成本,是否更多地惠及了我国商业设施严重欠缺的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即信息技术应用是否具有包容性创新的“普惠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网络化与社会化购物方式的兴起与消费增长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购物方式的日益盛行,消费者的购物渠道从“线下”到“线上”的大规模迁移,使实体零售商陷入了“展示厅”的困境。所谓“展示厅”(showrooming),是指消费者先到零售实体店查看和体验意向商品,然后通过线上渠道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该商品的行为,即“先逛店后网购”,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零售服务的横向外部性”或“信息搭便车”(Shin,2007)[12]。根据麦肯锡2015年对中国不同级别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共计约6.3亿互联网用户的调查发现,实体店的展示效应对30%的消费者而言尤为明显,这些消费者会在店内浏览体验商品并同时用手机进行价格比对,最终只有16%的消费者会选择在门店购买此产品。“展示厅”困境反映了信息技术应用对实体零售店的冲击,也迫使其向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零售商转型发展,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消费选择。以全球最大的实体零售商沃尔玛为例,在中国市场推出了O2O服务平台“速购”,该平台包括手机APP、顾客自提货的门店“速购服务中心”以及线上线下多种移动电子支付方式,充分结合了线下实体店的现场提货优势以及线上购物的搜寻便捷优势。“阿里+苏宁”、“京东+永辉”等并购模式也反映了全渠道是零售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线上线下的效率互补效应既提升了市场覆盖范围和流通效率,也满足了众多消费者线上下单、线下取货的市场需求,这必将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
随着社交网络和购物行为的互动融合,使得社会化网络推荐成为影响我国大众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其消费流程也表现为“3S模式”:首先在社会化网络媒体(如微博、虚拟社区等)上分享(share)朋友或口碑推荐,然后通过搜索网站搜寻(search)商品信息,最后去实体零售店查看或体验(see)商品。201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中国网络零售市场的调查表明,无论是消费者熟悉的商品还是不熟悉的商品,网络评论对消费选择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分别有44.8%和34.7%的消费者受此影响,远超过商品价格、物流与售后服务、购物经验等影响因素。由此可见,网络评论已经成为潜在消费者了解商品或服务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企业了解消费者需求以及促进商品销量的营销媒介。Duan等(2008)认为,社交网络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知晓效应和推荐效应[13]。所谓“知晓效应”是指社交网络传递了商品存在的信息,使消费者知道、关注和选择该商品,而“推荐效应”是指社交网络可以塑造消费者对商品的态度和认知,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Trusov等(2009)比较了社交网络与传统营销对新顾客获取的效应,发现社交网络等口碑推荐的长期弹性为0.53,是事件营销的20倍,媒体营销的30倍[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充分利用这种从线上至线下的社交商务模式,借助庞大的社交用户人口构建数字化的直销网络,销售依赖口碑推荐的经验型商品如化妆品、服装、保险产品等。
综合上述分析,信息技术应用引致的网络零售不仅仅是实体零售的替代渠道,对消费增长产生了广泛的波及效应,表现为促使实体零售加快业态现代化升级,拉低整体零售价格以及提升整体消费规模等。根据麦肯锡研究院2011年对我国266个城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网络消费量较高的城市整体消费量通常更高,约有61%的网络零售是从实体零售商转移而来的消费,而39%的网络零售则来自于网络化和社会化购物方式刺激产生的新增消费。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发展,提升了消费市场的交易效率,进而促进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信息技术应用的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
与日韩、台湾地区相比,我国的线下传统商业体系发展并不完善,尤其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线下商业渠道不仅分布密度较低,更在价格、商品数量、品质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以每百万人拥有社区便利店铺数量为例,日本是388家,台湾地区是425家,中国城市平均为54家,而且中国城市便利店单店效率远低于日本和台湾。传统商业体系的发展滞后极大地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而构建在互联网之上的电子商务平台则具有跨区域、无边界的天然优势,将这些受到抑制的消费需求纳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专业市场或实体零售不同,电子商务平台突破了货架空间的限制,增加市场规模的边际成本基本为零。从市场效率而言,来自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均可以借助商务平台提供的智能搜索工具进行商品检索和筛选,增加了价格透明性以及提高了市场的匹配能力,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改善。根据阿里研究中心测算,网络零售的交易效率是实体零售的4倍,同样1元的投入成本,实体零售完成的商品成交额是10.9元,而网络零售完成的商品交易额是49.6元。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弥补中西部地区以及乡镇实体零售相对落后的局面,使这些区域的消费者获得与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同等待遇和机会,实现“无差别消费”。
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其便利性使我国中西部以及偏远地区的消费者跨越PC端电子商务,直接进入移动商务,加速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消费差异。2014年,基于移动互联网消费额增速最快的100个县域中,有75个来自中西部,其中较集中的省区有西藏(16个)、四川(13个)、云南(9个)、甘肃(7个)、陕西(5个)。麦肯锡发布的《2015年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互联网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普及率较低,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数字消费者都在使用电子商务,网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68%和60%。基于互联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市场分割问题,而且使得我国独具优势的大国市场效应显现,释放了庞大的内需消费潜力,尤其为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参与市场提供了统一的准入条件、交易规则、信用制度、信息服务等。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统计测算,电子商务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这些地区网络消费的57%是新增消费,远高于39%的全国均值。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信息技术应用的包容性创新效应为欠发达地区消费者参与统一大市场提供便捷渠道,释放和促进了这些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为了实证检验信息技术应用异质性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3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信息技术普及率以及物流配送等相关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以及待检验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的面板数据计量方程如下:
lnaretaili,t=α+β1ICTi,t+β2Logistici,t+β3Crossi,t+β4Controli,t+εi,t
其中,lnaretail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计量方程的被解释变量;ICT为区域信息技术应用程度的相关变量,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邮电业务量三个指标衡量;Logistic为物流配送的相关变量,本文选取交通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客运量、货运量等指标进行量化;Cross为相关解释变量与区域变量的交叉项,本文将区域变量界定为二维虚拟变量,参考我国统计分类标准,上海、广东、辽宁等11个省市为东部地区,其它区域为中西部地区,并将东部地区的省份设定为基准组,赋值为0;Control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作为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相关变量的选取与界定如下:
(1)被解释变量及测度。本文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总量的促进关系,为此选取了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衡量居民消费总量及其随区域与时序变化状况。
(2)解释变量及其测度。本文选取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以及与电子商务配套的物流配送发展状况。目前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分的扩散和应用过程,为此本文用各省市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邮电业务量来测度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居民消费所依托的商业基础设施有三个层次:交易技术、信息通讯和物流配送,网络零售的正常运作有赖于物流配送发挥其支撑功能。考虑到31个省份的区域差异,为了减弱指标选取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借鉴刘秉镰和刘玉海(2011)的处理方法,以交通密度即“单位面积的交通基础设施”反映区域内交通便捷程度,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反映物流配送可达程度,以客运量、货运量来反映区域物流总量状况[15]。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尽管消费理论经历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的变迁,但可支配收入一直是影响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考虑本文以区域为研究对象,为此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从微观层面反映该区域居民消费能力以及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考虑到不同变量水平值的巨大差异,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本文对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中移动电话普及率、客流量、货流量、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取了自然对数。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2的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人均邮电业务量(lnats)之外,计量模型的主要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譬如,互联网普及率(Rnet)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的相关系数为0.8918,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区域交通密度(Dtraffic)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的相关系数为0.6245,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于邮电业务量统计范围主要包括函件、固定电话等传统信息通信方式,与以互联网为主的现代信息方式相关性较弱,为此呈现负的弱相关趋势。

表1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方法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固定效应模型假定个体不可观测的特征与解释变量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则假定个体不可观测的特征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选取回归模型,若Hausman检验的P值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
(二)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
为了检验假说1,本文利用前面设定的计量模型,首先回归估计了信息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表3中模型(1)和(3)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1。模型(1)在有效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这两个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后,采用信息技术应用的相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Rnet)、移动电话普及率(lnrmobile)分别在5%和1%显著水平上对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有正向影响,传统的邮电业务量(lnats)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尽管形成了对实体消费的部分替代,但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
模型(2)检验了线上渠道高度依赖的物流配送发展状况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除客流量(lnpassger)以外的物流配送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为此,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3),综合估计信息技术应用以及物流配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Rnet)每提高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将增长1.76%,即二者的弹性系数为1.76;移动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将增长0.15%,这也说明了移动互联网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此外,物流配送的关键变量也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这意味着信息基础设施与物流基础设施共同支撑的线上渠道是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引擎。
(三)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普惠效应
为了检验假说2,本文采用Rnet×Mwest这一交叉项来衡量信息技术应用的区域差异对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的影响,用lngoods×Mwest来衡量物流配送的区域差异对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lnaretail)的影响。表3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与中西部虚拟变量交叉项(Rnet×Mwest)系数为0.66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一种包容性创新,消除了全国商业流通业布局不够均衡的问题,更多地惠及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从而验证了假说2。进一步将各省市网络平均购买水平排名与平均消费水平排名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见表4),云南、贵州、广西是两项排名差异较大的三个省份,2014年这三省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分别为第29位、30位和27位,但网络平均购买水平排名分别为第7位、第10位和第18位。这也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则从“供给侧”一端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消费能力的释放并带动消费的整体增长。然而,货流量与中西部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为-0.104,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物流配套的相对滞后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增长,而互联网改造下的消费经济必将从“需求侧”一端促进这些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形成消费增长与物流网络完善的良性循环机制。

表3 信息技术应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2004-2013)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表3中模型(5)和(6)分别对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进行面板回归,关键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及显著性水平和模型(4)基本一致,这反映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模型(5)中,移动电话普及率(lnrmobile)的系数为-0.0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模型(6)中该变量的系数为0.028,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通过个人电脑网络购物与智能手机网络购物的替代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受限于互联网接入,消费者进行网络购物更多地采用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因此移动互联网更大程度地惠及了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这一研究结论与麦肯锡发布的《2015年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报告》一致,该报告反映互联网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普及率较低,但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为这些地区的消费者网络购物提供了工具。阿里研究院发布2014年“双11”的统计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更倚重“手机抢购”,移动互联网成交额在网络消费总额中占比排名前十的城市全部来自中西部地区,前100城市里中西部地区则占据了76个。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为了分析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关系,进而挖掘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本文从包容性创新视角提供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利用中国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显著为正,且与物流配送形成O2O商业生态系统,共同促进消费增长;(2)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普惠效应,与东部地区消费者相比,中西部以及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将从信息技术应用中获益更多。这两点显著支持了信息技术应用对消费增长以及内需扩大的叠加效应,也显著地释放了这些地区的消费潜力。其深层次原因可归结为:
(1)电商应用的互动性提升了用户体验水平,也拉近了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用户需求,带动用户消费潜能增长;
(2)电商应用能充分展示产品的多样性,一方面加剧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多维度信息采集和设计理念的碰撞提升了产品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
(3)智能终端所蕴含的个性化,辅之以大数据分析,可以更深层次挖掘用户需求,加之交易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消费市场的效率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从而满足了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升级;
(4)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区域产品的特质在电商平台下可以低成本展示和营销,同时高便携性的终端为偏远地区用户需求的表达提供便利,有利于将数字鸿沟进一步弥平。

表4 典型省市居民网络平均购买水平与平均消费水平排名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括号内为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排名。
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在全球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统一而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成为释放大国市场消费潜力的引擎(李建伟,2015)[16]。而政策的有效引导,可以更好地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为我国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
从全国范围看,需要着力推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在扶持综合型电商平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同时,鼓励发展专业型平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以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商业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商业资源、创新商业服务,也极大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专业型平台有利于行业信息采集和运行趋势实时发布,影响国际市场产品定价权。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网上销售价格平均比线下价格低6%-16%,2011年网络零售将全国的平均零售价格拉低了0.2%-0.4%,2012年则拉低了0.3%-0.6%。平均零售价格的降低意味着相对购买力增加,进而刺激了消费增长,这种收入效应对消费的刺激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将更为明显。2014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预计,2013年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升GDP增长率0.3-1.0个百分点[17]。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不是一个靠刺激内需的短期投资思维,而是内生驱动的经济体,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新范式。
而东部和中西部由于信息化的不同影响特征,政策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从东部地区的信息化领先优势看,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整合优化行业资源、节省交易成本、促进市场需求与生产供给的“精准对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即成本集约基础上市场需求侧的增长。另一层面,信息化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加速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形成创新驱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据此,东部地区一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将加快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作为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快信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渗透速度,有效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挖掘和提升消费潜力,改变消费行为、企业形态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
二是加大互联网技术创新力度,引爆社会创新。通过税收和资金等政策,引导产品和服务创新;构建电子商务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创新产品;建立院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人才培养机制,为电商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通过电商带动信息化、网络化和大数据分析,从供给侧结构化变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三是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发展环境,促进企业电商应用和业务创新互动提升。引导企业从关注生产和销售转向更加关注用户需求和产品设计,以增强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支持企业的设计数字化、装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等智慧制造和智慧服务全过程,通过“互联网+”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而中西部地区则须抓住信息技术应用带来消费增长的普惠效应,结合区域特色以及资源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寻求产业分工中的合理定位。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鼓励依托资源和特色优势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甚至新的商业生态系统,进一步影响和加速区域传统产业的“电子商务化”,促进和带动经济整体增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有可能借助互联网经济实现东部和中西部的错位发展,实现“换道超车”,成为“网上WTO”规则的制定者。
据此,中西部地区则应注重:一是提高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这不仅对消费增长有较大的促进空间,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3.4部/百人,而中、西部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85.4部/百人和78.7部/百人,区域差距仍然较大。此外,尽管宽带和3G网络已遍布我国东部大城市,但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程度仍然参差不齐。2014年,我国家庭宽带渗透率仅为40.9%,远落后于美国(70%)和德国(61%)等发达国家。我国城市宽带用户净增1021万户,是农村宽带用户净增数的7.5倍,城乡互联网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为此,政府应在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扩展宽带和3G+基础设施,提供类似“家电下乡”方式的激励方案,加快互联网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以释放积累的消费需求以及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二是加强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电商、快递企业等相关物流服务网络和设施的共享衔接,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区物流体系,发展第三方配送和共同配送,重点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物流设施建设,提高流通效率。加强农产品产地集配和冷链等设施建设。克服区域消费瓶颈,带动区域消费增长。
三是依托资源和区域特色,鼓励依托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以此拉动消费实现包容性增长。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的新阶段,农村电商快速崛起。2014年,中国农村电商销售额已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消费结构正处在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的重要时期。新技术的采纳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往往是相生相伴的。中西部地区更需依托信息技术的包容性创新明确合理的产业定位,实现区域快速发展。
四是提高消费信息的有效供给与引导,增强农民对有效信息的利用能力,进一步缩小“二级数字鸿沟”,使农民享受到“信息红利”。与信息的可接入性被称为“一级数字鸿沟”相对应,“二级数字鸿沟”则是信息的利用和鉴别能力,未来要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的普惠效应,利用公共服务的方式提升信息服务和共享的质量,促进“二级数字鸿沟”的消除。
[1]毕达天,邱长波.B2C电子商务企业——客户间互动对客户体验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12):124-135.
[2]Bhavnani A,Won-Wai Chiu R,Janakiram S,et al.The role of mobile phones in sustainabl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R].World Bank,2008.
[3]Shiu A,Lam P.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ts regions [J].Regional Studies,2011,42(5):705-718.
[4]张历红,周勤,王成璋.信息技术、网络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10):112-123.
[5]Jensen R.The digital provide:Information technology,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122(3):879-924.
[6]Conley T,Udry C.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Pineapple in Gha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35-69.
[7]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J].管理世界,2015(4):52-65.
[8]George G,McGahan A M,Prabh J.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growth: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research agenda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2,49(4):661-683.
[9]Aker J.Information from markets near and far:Mobile phon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Niger [J].Applied Economics.2010(2):46-59.
[10]Qiang C,Z W Rossotto,C M.Economic impacts of broadband [C].//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2009:Extending reach and increasing impact.World Bank,2009:35-50.
[11]谭晓林,赵定涛,谢伟.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8):184-192
[12]Shin J.How does free riding on customer service affect competition? [J].Marketing Science,2007,26(4):488-503.
[13]Duan W,Gu B,Whinston A B.Do online reviews matter?-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a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8,45(4):1007-1016.
[14]Trusov M,Bucklin R E,Pauwels K.Effects of word-of-mouth versus traditional marketing:findings from an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site [J].Journal of Marketing,2009,73(5):90-102.
[15]刘秉镰,刘玉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库存成本降低[J].中国工业经济,2011(5):69-78.
[16]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J].经济研究,2015(1):111-123.
[17]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R].麦肯锡咨询公司,2014.
(本文责编:辛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Inclusive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 Growth
HUANG Wei-dong,YUE Zhong-gang
(Collegeof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210046,China)
Does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bstitute online retail for brick-and-motor retail,or promote newly increase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consump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innovation.Using the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2013,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marginal effect and inclusive effect of consumption growth promo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This paper finds the adoption r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s positively gross consumption and brings more benefits to the consumers in West-middle regions.The conclusions have mor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strategy of Internet plus to promote consumption growth and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inclusive innovation;consumption growth
2015-10-21
2016-04-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71302168)。
黄卫东(1968-),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博士,研究方向: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F49
A
1002-9753(2016)05-01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