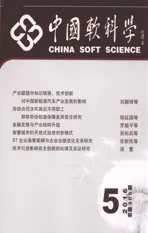智慧城市的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欧盟和韩国的实践及启示
2016-09-05吴标兵林承亮
吴标兵,林承亮
(1.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智慧城市的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欧盟和韩国的实践及启示
吴标兵1,林承亮2
(1.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宁波315100)
开放式治理创新是智慧城市应有之义。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谁来建设、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欧盟和韩国智慧城市实践表明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关键在于用户驱动创新生态系统。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驱动的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尊重利益相关者公平话语权,激活社会资本,促进互惠;加强全局规划,设立权威专门领导机构;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健性和可预期性;求同存异,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因地制宜,着力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的可复制性。
智慧城市;开放式创新;治理;社会资本;共享经济
一、引言
智慧城市(Smart City)概念源自20世纪末的智慧社区(Smart Communities)和智慧增长(Smart Growth)运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渗透,世界各地许多城市开始兴建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开始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虚拟城市、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宽带大都市、知识库、无线城市、数字城市、无处不在的城市(Ubiquitous City)、信息城市、电子城市、智慧城市等都是用来描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城市实践形式。基于技术意义,上述概念往往相互通用。随着物联网和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何谓“智慧城市”,国内外学者定义不一。综合而言,主要从经济、生态、技术、政治、社会文化等五个方面来界定:(一)经济增长角度,智慧城市是指那些已经认识到实现宽带经济巨大挑战的重要性,并自觉采取能够创造经济蓬勃发展措施的区域或城市[1];(二)资源环境角度,智慧城市是指更为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的和宜居的城市[2];(三)基础设施角度,智慧城市是指利用智慧的计算技术使得城市基础设施更为智能、互联和有效的城市[3];(四)城市治理角度,智慧城市是指在经济、人力、监管、交通、环境、生活等方面,以一种管理创新的[4]、前瞻性的方式,公民独立、自觉、自我决策,各种利益相关者智慧(Smart)、高效行动的城市[5],它给市民提供先进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和用户共同创造的服务;(五)社会文化角度,智慧城市是一种能够激发灵感,分享文化、知识和生活的城市,一种促进居民创造和繁荣其生活的城市,一种令人向往的城市、充满智识的自主空间[6]。
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存在认知上的不同,加上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艰难的摸索阶段,出现一些误区和挑战[7-10],在谁来建设、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多争议。
针对上述问题,李克强总理不断强调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注重质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发展智慧城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思想。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改善人居环境”。《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6〕20号)进一步指明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推进城市管理体制创新,打造智慧城市”。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来,社会管理格局转变到社会治理格局,我国如何创新城市治理,进一步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难题?根据魏江教授开放式区域创新理论[11],开放式区域创新作为一项联合决策和行动的结果、过程的治理,在区域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从治理和开放式区域创新视角,通过对欧洲和韩国智慧城市治理模式进行案例分析,归纳欧洲和韩国智慧城市治理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梳理出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一般特点和规律;最后给出政策启示,中国智慧城市治理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为我国智慧城市、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引。
二、资料和方法
1.资料来源
本研究分析资料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官方文件:欧盟“i2010”战略、欧洲2020战略、智慧城市和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欧洲数字化议程、欧盟北海项目、智慧IP项目(SMARTiP)、PERIPHRIA、智能(Intelligent)城市欧洲平台、民生工程(PEOPLE project)以及欧盟成员国制定和实施的智慧城市方案,比如法国“数字巴黎”计划、爱尔兰和柏林SmartBay项目(水资源管理系统)、德国“e-欧洲宽带战略i2010”、英国的“数字英国”、西班牙的“城市2020”项目等,韩国IT839战略、U-City计划等;二是智慧城市课题持续性研究过程中掌握的实地调研资料、会议记录、访谈和专家报告演示稿;三是相关文献[12-17]和网络资料,比如“韩国仁川经济自由区(IFEZ)及u-uITY介绍”等。这些资料都比较详细地呈现欧盟、韩国在智慧城市治理过程是对欧韩智慧城市实践的真实描述,具有客观性,为本文案例研究提供较好的素材。
2.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中案例分析方法,对欧韩智慧城市治理创新进行个案和跨个案分析。通过个案分析展示欧韩智慧城市治理中若干创新方法和举措。通过跨个案分析一方面提高欧韩智慧城市创新治理的概括化程度,寻求智慧城市创新治理的规律性要素;另一方面加深理解和解释力度,利用多重比较组群来探究在什么条件下,欧韩智慧城市治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指出我国智慧城市治理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的政策建议。所以跨案例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确认智慧城市治理中哪些问题是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还可以建立普遍性的智慧城市治理法则,二者彼此关联。
三、个案分析
为了从区域创新角度研究欧韩智慧城市治理模式,本文从治理创新主体(who)、方法(how)和内容(what)的逻辑模式来讨论。
(一)欧盟: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驱动的治理创新模式
1.治理创新主体
在欧盟模式下(见图1),政府起到智慧城市治理创新的引导作用,由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和组织,政府与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积极参与智慧城市治理创新。公众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肯定。服务和应用需要通过用户驱动的开放式创新来维持,以实现公众层面上的可扩展性和复制性。用户生成的内容和共同创造的应用需要联接到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治理模式,以保证有效实施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该模式致力于打造协同创新的、“智慧”的、以市民和企业为中心(Citizens- and Business-Centered)的服务。
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包括市政府、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公众等。其特点有三方面:一是有限政府,政府在智慧城市治理创新中起到引导而非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指引、规划制定和组织协调方面,有限地参与项目运作。二是企业、政府、科研机构跨区域合作,这是欧盟智慧城市治理的非常重要特征。任何项目通常由几个欧盟成员国多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例如,英国智慧IP项目(SMARTiP)由5个欧盟成员国、13个合作伙伴委派杰出的专家共同参与。欧洲智能城市平台(EPIC)由比利时的IMINDS VZW协调,有15名来自6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市政府、大学和创新实验室的合作伙伴(包括布鲁塞尔的IBBT、曼彻斯特城市议会、IBM、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学院FKIE、ENoLL、德勤咨询、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等)。三是公众驱动。公众是“合作生产者”。“合作生产”创造一个更为积极的环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能让系统更好地对社区的需求做出反应。公众参与对于改进本地服务的效率(efficiency)和效力(effectiveness)至关重要。创新实验室(Living Labs)等平台和服务秉持这一理念。
2.治理创新内容
欧盟在智慧城市治理创新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盟的整体推动和跨区域合作战略,也取决各成员国政府的顶层设计。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了一整套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并先后出台欧盟智慧城市治理的战略和重点建设领域,并付诸实施。具体如下:

图1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驱动的治理创新模式
一是致力于发展最新通信技术,建设新网络。物联网是欧盟智慧城市治理的重点。在阿什顿(Ashton)提出“物联网”的同时,欧盟信息社会技术项目建议组(ISTAG)就使用“环境感知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一词。此后欧洲引进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并在这一语境下发展“物联网”[18]。欧盟发展物联网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继续加大物联网投入,关注点是重点技术,如微电子、非硅组件、定位系统、无线智能系统网络、安全设计、软件仿真等;二是在绿色汽车、能源高效建筑、未来工厂和物联网这四大领域加强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以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到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之中。
二是提供物联网应用服务,创造新的媒体内容。例如:促进公众利用电子政府,促成跨界电子政府服务;推动欧盟电子商务发展;节能环保、用于帮助老年人等。欧盟非常重视物联网应用,认为物联网应用将为建设智慧城市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做出重大贡献,如健康监测系统将帮助人类应对老龄化问题,“树联网”能够制止森林过度采伐,“车联网”可以减少交通拥堵,“电子呼救系统”在汽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时可以自动呼叫紧急救援服务。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宽带普及和高速宽带,提高数字包容性、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欧盟特别强调解决“数字鸿沟”,发现数字不平等不仅破坏城市邻里关系还妨碍信息社会的参与。市民增权是欧盟重要的举措。
四是促进绿色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实现智慧型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欧盟在新能源、智能交通和信息通讯(如物联网)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开展系列示范项目,包括高效供热(冷)系统、智能仪表、实时能源管理、零排放建筑、智能交通等。
欧盟各成员国在智慧城市治理的定位上存在一定差异。柏林侧重交通,英国发展智慧社区(比如零碳社区、智能屋)、法国致力于“数字法国”(比如巴黎的SAAS“云”模式、布雷斯特市的ImagineLab平台和拉罗谢尔市智慧垃圾箱装等),都柏林强调水资源管理,斯德哥尔摩注重市民与政府的互动,维也纳关注民生、阿姆斯特丹聚焦可持续发展主题(生活、公众、交通和空间四个方面)、巴塞罗那营造数字节能城市。
平台建设和创新生态系统是欧盟智慧城市治理的一大特色:欧盟一方面发起大量的新项目,比如FIREBALL、FIRESTATION、SMARTiP、民生工程(People Project)等,利用智慧移动和城市信息管理方案研发与公共安全信息、生活、休闲、旅游有关的电子服务;另一方面支持和培育创新流程的创新政策,创建用户驱动创新生态系统,比如创新实验室和EPIC,为欧洲中小企业建立可扩展的、新的、用户驱动解决方案,给公众带来创新的公共管理服务。
3.治理创新方法
一是全局规划,分步推进。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覆盖国家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主权国家联合体,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源浪费,保证系统的兼容性和一致性,进行智慧城市治理顶层设计,比如“i2010”战略、欧洲智慧城市计划(2009)、欧洲2020战略、智慧城市和社区计划(2011)、智慧城市和社区的欧洲创新伙伴关系(2012)等,循序推进并资助成员国智慧城市创新治理。
二是构建组织,设立国家层面的领导机构对智慧城市治理进行统一部署,促成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例如,芬兰成立国家信息管理委员会,加强政府各部门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协调工作。英国由电子事务大臣(e-Minister) 全面领导和协调国家信息化工作,并由内阁办公厅主任、电子商务和竞争力部长协助其分管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
三是架构平台,创建用户驱动创新生态系统。欧盟委员会积极支持创新实验室的发展,到2010年全欧洲有250个区域间的层面(比如北欧-波罗的海创新实验室网络),或国家层面(意大利、芬兰和英国创新实验室网络)创新实验室。欧洲智能城市平台(EPIC)为欧洲中小企业建立可扩展的、新的、用户驱动解决方案,给公众带来创新的公共管理服务。具体分工是:ⅰ)创新实验室负责公众参与创新进程,通过开放式创新,创造市民、商业机构、城市参观者可以为之付费的服务;ⅱ)市政府负责将用户驱动的、基于网络的服务嵌入到开放式EPIC平台;ⅲ)顾问和专家等合作者利用研究成果创造面向商业、公私部门的路线图。
四是制定标准,规范电子政务应用软件的技术标准、开发过程和数据结构。如德国政府发布“面向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标准和体系架构( SAGA)”,英国政府基于政府资源的信息管理发布了电子政府交互框架(e- GIF),挪威政府在1993—1995 年间完成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等。
五是政策引导,项目资助。2009 年10 月,欧盟投资110 亿欧元“在25-30个城市中发展低碳住宅和交通。2012年7月10日,欧盟对欧盟第七个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下的45个2013年度项目公开征集,项目资助经费总额达81亿欧元。2012年已投入8100万欧元支持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智能城市和社区”试点项目,2013年,欧盟将为这些示范项目投入3.65亿欧元。2014年,欧盟将成立由相关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负责人、市长以及来自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相关管理人员和金融机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智能城市和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的实施工作,制定优先领域和工作计划,面向企业发布项目招标信息。
(二)韩国:政府主导-专家推动-公私部门参与的治理创新模式
1.治理创新主体
韩国的创新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部门和企事业组织协调治理的、介入外生性和内生性混合的、有限开放的创新模式(见图2)。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智慧城市治理中起主导作用。
政府带头,在政策的制订、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方面对智慧城市治理作用明显:政府部门对智慧城市进行系统性规划和建设,避免了局部推进带来的其他配套滞后反过来影响建设绩效的问题。韩国智慧城市治理主体主要分为四类:(1)发起者:信息和通信部(MIC)、建设和运输部(MCT);(2)企业,比如LG、KT、三星等;(3)主办市政当局:首尔、仁川、釜山;(4)部分学术界专家。其特点:一是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智慧城市治理成败取决于政府,政府具有最后发言权;二是部分企业和机构参与智慧城市治理,影响政府决策和规划,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缺乏公众协同和互动。
自2003年以来,MIC在推动全国范围内U-城市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MIC发起该项目,起草条款,制定战略规划,描绘技术蓝图,招募有关人员推动项目开发。为了吸引MCT参与,MIC在基础设施方面给MCT委以全权。2006年1月,MIC和MCT签署建设U-城市谅解备忘录。通过签署备忘录,两个部委同意在改造U-城市建设法律体系、发展和认证U-城市模型、实施U-城市建设试点项目、选择和实施U-城市任务、交换信息和人力资源、有关U-城市项目的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全面合作。2006年2月,MIC和MCT成立项目合作专责小组。该组由MIC和MCT两个部门主管牵头,由来自地方政府和相关行业和学术界专家组成。专责小组的目标是与市政府联系,并征求它们参加U-城市项目。小组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其目标:整合和地方化。即整合各城市之间的U-城市服务(如电子政府服务),运用现有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将U-城市项目地方化。小组在2006年制定法律支持U-城市建设目标,比如“2006年政策指令,”“支持U-城市建设法,”和“U-城市方针。” MIC对参与的企业提供巨大的税收优惠和有利价格的土地。此外,该项目初始资金被用来资助民营科技企业和开发商的加入。

图2 政府主导-专家推动-公私部门参与的治理创新模式
当MIC发起U-城市项目,向几个市政府提议时,首尔市政府立即表示他们愿意实施U-城市项目,第一个对该规划做出承诺,并以高昂的精神和全身心的热情,集中于构建新的振兴区域经济的ICT集群。仁川市政府认为加速驱动全国城市发展项目的关键,在于加强ICT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作用。U-城市项目参与者分为:系统开发商、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这些企业负责开发应用和实施技术,比如IT宽带和无线网络。
2.治理创新内容
加速国家经济增长,促使政府、城市和产业转型是韩国智慧城市治理的主要目标。从国家层面出发,它们把U-城市解释为城市振兴的工具,因此他们往往把U-城市看成城市发展项目。与此同时,从地方政府角度,他们把U-城市看作由技术驱动的“基础设施”,旨在向社区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透明治理。其治理措施主要有:
一是建立官、产、学共同参与的半开放式治理组织:U-City论坛。论坛的目标是绘制规划细节:预测未来社会;包括满足社会和市民需求的U-城市服务;为无处不在的计算建设物理移动/建设基础设施和环境;规划U-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管理U-城市及其规划过程。该论坛有三个技术小组:标准、认证和应用服务。论坛的作用是绘制整体战略规划,提供行业标准、设计配套的行政和程序框架。论坛每月定期召开。虽然学界参与智慧城市治理,但是作用十分有限。
二是开发核心技术,包括U-生态城研发项目,推进技术开发与拓展国外市场。从国家战略层面,韩国希望加强国际技术强国的地位:在哥伦比亚波哥大成立当地办事处,攻略中南美的信息通信市场,U-City项目还出口到阿拉伯等国家。配合技术输出,韩国技术和标准局建立无线射频识别和无处不在的传感网络标准。
三是构建U-City制度规范,包括U-City综合规划,U-City规划、建设指南,建设工程与IT的融合技术指南,U-City管理运营指南,U-服务标准,分类标准指南。MIC为地方政府制定指南。每个参与的市政府将向MIC提交最终的规划,MIC最后批准最终的市政规划。当地市政府独立发展U-城市以满足当地需要,然后MIC制定标准模型整合全国不同的U-城市。
四是升级基础设施,实现城市转型。韩国在智慧城市治理中特别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在能源、交通、医疗、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建立技术先进、不断升级改造的网络基础设施。2002年5月首尔推出“数字城市”项目,韩国在部署宽带基础设施方面大幅度领先。继“数字城市”之后,韩国推出“U-城市”举措。U-城市使韩国政府成功转型,电子政务更有效率,更为透明,所有政府合同的投标都在网上公示,大大减少腐败。
五是扶持U-City产业发展,包括U-City试点建设,U-City相关产业的培育,建设工程与IT的融合。韩国采用产业高端化模式,并将一些传统的低端产业或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环节适时适度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以硅谷为范例,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模型。韩国产业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互联阶段偏重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无线网络、传感器安装;在发展阶段偏重服务,即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如U-服务;在成熟的智能阶段,偏重管控一体化(如U-中心),利用无所不在技术(U-IT),特别是无线传感器网络,达到对城市设施、安全、交通、环境等智能化管理和控制。
3.治理创新方法
一是稳步升级,有序衔接。韩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此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并持续了二十几年[14]。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韩国开始警觉加速工业化带来的大量负面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IT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支柱,它在政府做出各种决策指示信息时发挥了重大作用[15]。为了确保IT产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近年来韩国政府一直在寻求新的增长引擎以保持竞争力。继“数字城市”之后,韩国推出“U-城市”。在U-城市环境里,几乎所有事物通过技术(比如无线网络和无线射频识别标签)连接到信息系统。这个理念已经受到韩国高度关注,它计划建立15个无处不在的城市。从2004年起,MIC在努力构建最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未来城市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根据MIC发布的蓝图:从安全、福利、技术以及其他角度,U-城市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2008年韩国制定立法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发展无处不在的网络城市。此外,为了区域经济发展,U-城市项目计划展现出更为全面的路线图。智慧城市治理在此背景下产生。
二是整体规划,顶层设计。2004年信息及通信部(MIC)制定IT839战略,包括8项新的IT服务(无线宽带服务、数字多媒体广播服务、家庭网络服务、远程信息处理服务、无线射频识别服务、W-CDMA服务、地面数字电视服务、网络电话,3项关键网络基础设施(IPv6、Broadband Convergence Network以及软件基础设施),9项有前景的技术引擎(下一代移动通信设备、数字电视/广播设备、家庭网络设备、单芯片系统、下一代个人电脑、嵌入式软件、数字内容与软件、远程数据处理设备、智能机器人)。在9项技术创新产品中,把移动通信和远程信息服务(Telematics)结合起来,并增加了RFID/USN(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为打造“智能社会”奠定基础。
三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作为中央部门,信息及通信部(MIC)、建设和运输部(MCT)在智慧城市治理中起到决定性的核心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无论制度建构、政策制定,还是规划布局实施,MIC和MCT都事无巨细、勤勉尽责,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和重要企业参与智慧城市治理。在韩国中央与部分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韩国主要的系统集成企业与电信运营商也参与到智慧城市治理,把U-City建设作为未来新业务而进行前瞻性的投资。
四是分步推进,循序渐进。2009年,韩国通过了U-City综合计划,将U-City建设纳入国家预算,在未来5年投入4900亿韩元(约合4.15亿美元)支撑U-City建设,大力支持核心技术国产化,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五是重点建设,示范引领。韩国政府将“智慧城市治理”作为商品来运作,通过建立智慧城市的范例,拉动物联网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人们直观感受到物联网技术带来的诸多好处,再向其他地区和国家推广,最后进行模式、方案和技术打包输出。首尔和松岛经济自由区是韩国智慧城市治理的典范。
四、跨个案研究
以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堪称为智慧城市治理的全球领导者[19]。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欧盟国家的合作,比如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平台、中法智慧城市标准联合工作组、中英智慧城市标准工作组,会同欧盟企业总司开展了国际城市间标准化合作的研究。相反,韩国在智慧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一些新城市开发项目停工、应用在现有城区时遇到瓶颈、人们对建设U-City的效果认识不足等原因,在建设和推广上遇到了不少难题[20]。实践和理论证明,欧盟智慧城市治理是成功的,韩国则在失败中继续探索[15,19-21]。本部分主要讨论欧盟智慧城市治理成功经验而韩国失败的原因,智慧开放式创新治理模式的一般规律。
(一)欧盟智慧城市治理成功而韩国失败主要原因
欧盟智慧城市治理主体分为市政府、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公众等方面,积极发挥公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突出公众在智慧城市治理中的治理作用(见图3)。其特点有五个方面:一是主体方面,有限政府,注重社会资本在智慧城市治理的功能性地位,将人的能力因素、关系资本、高等教育的作用、技能、创造性和人才视为城市演变的主要驱动力,跨国超本地知识网络;二是全局规划,顶层设计,重视物联网技术、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建设;三是构建组织,统一部署;四是差异化的治理内容;五是科技政策的连续性。

图3 欧盟智慧城市治理创新主体
欧盟采取的是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驱动模式,是一个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混合的开放式创新范式。无论组织架构还是治理内容,都体现出开放式创新和协同民主理念。它吸引不同区域、部门、行业、职业的兴趣,将不同政府、企业、机构和市民汇集到一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创新精神也蓬勃发展。开放式创新作为智慧城市治理的新范式必然出现。利用开放式创新,政府和开发商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技能、市民知识来开发与人们需求、城市环境相关的先进服务和产品。通过开放式创新,政府、公司和公众成为合作伙伴,有助于研究、开发的进行,有助于提供服务和产品。因此,智慧城市的开放式创新成为跨越不同部门、区域和城市的网络。其核心是促成新的合作生产进程,它需要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开放式创新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强调系统日常互动,带来强大的价值力和能力共享力。所以,开放式创新必然有助于提升智慧城市治理的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力。而且,随着地方和国际层面的越来越网络化和协同,极有可能加速未来的开放式创新。智慧城市创新治理的成功是商业、教育、政府和市民联动的结果。
韩国智慧城市治理主体中虽然有部分专家学者和企业参与,但是缺乏社会共同努力[13],并没有充分体现开放式创新。其特点有四方面:
一是韩国政府在智慧城市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权力分配不均。MIC与建设和运输部(MCT)之间存在张力,MIC权力过大,垄断U-城市项目,MCT不想以配角参与该项目。MIC在U-城市项目举措上的唯一权威,从一开始就对项目其他各参与方产生负面影响。在大科学时代,技术具有政治性。随着2008年李明博执政和国家政策的调整。MIC和MCT在战略层面上势头减弱,这随之影响市政府操作层面。政府消减支持力度影响行业参与和追求。作为政府职能调整的一部分,MIC在2008年3月被撤销,其行政职能被转移到其他部门。随着MIC消失,整个U-城市项目在消退,处于一种疲软状态[20],最终影响政策连续性(见图4)。
二是急功近利,过于注重产业发展和形象工程,缺少公众参与和互动。韩国政府各项治理措施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城市和产业转型,其项目往往是为企业、产业的发展量身定做的,未能依据公众的需要,就公众想要什么做了太多不合理的假设。韩国政府忽略公众的巨大创造潜力、社会凝聚力、生活质量和民主的根本目标。其治理方法和治理内容看起来很美,但是市民缺席于U-城市治理的讨论,制度不完善。U-城市没有惠及市民,市民在利益上没有享受优先权。作为信息社会的缩影,智慧城市治理应该基于公众的需求,反映公众的社会呼声和价值。U-城市仅仅为政府上层群体所形塑,从而失去了使U-城市成为信息商品的机会。技术是一种社会过程,应该把无处不在的计算基础设施连接到城市的物理部分,比如建筑、道路、电子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居住场所。更重要的是,应该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中。
三是话语权不平等,学术界缺乏话语权,学界代表提出社会问题和监管规定,但是这些意见往往不被政府采纳。LG、三星等龙头企业享有绝对话语权,中小企业难以有效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图4 因果关系网:韩国智慧城市治理主体结构的影响
四是狭窄的国内网络,并没有获取外部异质性创新资源,实现创新能力的跨域发展。欧盟智慧城市治理充分吸纳跨国智力成果,利用平台将欧盟资源整合起来实现协同创新形成全欧盟创新体系。
(二)智慧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的建构
对于一个成功的智慧城市实践来讲,有共性规律,应建立用户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一种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见图5)。
1.人的要素
人是智慧城市治理的灵魂。在《欧洲中等城市智慧城市排名》研究报告的衡量智慧城市的指标中,大多数指标与人相关。人的能力因素、关系资本、高等教育的作用、技能、创造性和人才是城市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社会资本推动城市发展,人、教育、学习和知识对于智慧城市来说是重中之重。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智慧城市不可缺少的财产。根据马太效应,智慧地区会变得更加智慧,而其他地区的智慧会相对变少,智慧城市扮演着创意阶层的磁铁角色。智慧城市也是一个学习型城市,它提高城市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在创新人才蜂聚的学习型城市,通过学习,城市治理会变得更加智慧。欧盟跨国知识网络、开放式创新可以让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并平等地参与城市治理。欧洲智慧城市的试点也呈现明显的特点。欧洲许多智慧城市选址在大城市周边的老工业区(比如西班牙萨拉戈萨、英国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市、芬兰的Arabianranta),其目的是在城市扩大的情况下,将老工业区转型成为新的知识经济中心。但是韩国却将智慧城市治理试点于首尔等传统的大都市,从根本上讲韩国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不具有可复制性。近年来,韩国不断反思智慧城市失败的原因,制定出具有实效的市民体验型实践战略和协作式的治理社会的合作[20-21]。

图5 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
2.技术的要素
技术是智慧城市治理的关键。互联网范式转向物联网范式,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欧韩均致力于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慧城市创新治理强调技术基础设施和支撑技术问题,凸显系统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基于此,欧盟和韩国都非常注重最新通信技术和新网络,强调宽带目标,实现高速和超高速互联网连接,提高数字素养、数字技能和数字包容。与韩国相比,欧盟智慧技术更关注民生和为城市居民提供移动生活上的福利。欧盟智慧平台是智慧城市治理创新中技术与公众参与联接的桥梁。智慧技术只有以民为本,着力于民生工程,才能激发公众参与智慧城市治理的热情,才能发挥公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产生智慧大数据。从技术上讲,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必须满足公众的当前需求和根本利益才能获得长效发展。
3.制度的要素
政府支持和治理政策是智慧城市设计和实施的基础。有必要建立一种行政环境以支撑智慧城市治理:不只是扶持政策,还有政府的功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及其治理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欧盟成员国在智慧城市治理的政府机构设置方面更有效率,而韩国在智慧城市治理过程中遭遇到领导机构变更的、突然死亡式的致命打击。在智慧城市治理语境下,开放式创新意味着合作生产和共同交付的不仅是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政策。开放式创新意味着尊重、责任和公平,是城市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保障。如果不能制定一致性的政策路径,那么开放式创新就会止步不前。制度要素也是智慧城市创新治理重要的前提:制度准备(比如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删除)、领导和组织转换、内源性的政治因素(市权力机关、市政府、市长)和外源性因素(上级行政部门的压力、国家大政方针等)之间的协调等。市政府应该与公众共享其想法、愿景、目标、工作重点,甚至与公共利益相关者有关的战略规划。关键领导的领导能力以及他对智慧城市的强力支持,对于智慧城市成功来说至关重要。领导的示范作用对于城市治理以及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而言,也很重要。
五、政策启示
在对欧盟和韩国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实践对比分析和归纳基础上,给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治理创新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切实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开放式治理创新是智慧城市应有之义。从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执政党社会管理思想和理念发生重要转变。(1)要重视开放式治理创新在解决城市社区稳定、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生活美好等方面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2)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驱动的开放式治理创新模式,形成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的价值理念和共识。智慧是技术智能和公众才智有机生态结合。智慧城市治理的开放式创新就是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给公众提供更为持续发展的、包容性的生活和发展方式。(3)创造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的信任环境,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智力资本,通过共享、共建和学习,达到善治和法治的统一。合作生产和合作交付的手拉手式的信任以及相互合作的成为智慧城市开放式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
第二,重视不同的职业和工作,厘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激活社会资本,促进互惠。(1)搭建智慧城市治理创新平台,利用大数据,构建开放式创新的社会化网络。开放式治理创新必须构建高度开放的、自组织的人群系统,打造基于共享经济的生态战略平台。(2)在智慧城市治理及敏感问题上,政府官员要身先士卒,起到率先垂范作用。(3)企业、专家、公众具有知情权和表达权,其需求能够得以尊重和无障碍的反映,社会发展的稳定性能够得到重视,而不仅仅将决策权赋予某个政府领导或机构。公众接受度是衡量智慧城市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4)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积极培育用户创新驱动共享经济,逐步实现由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公众协同互动的治理创新模式。(5)培植政府官员、企业、专家和公众之间产生利益一致的、创造性的关系。开放式治理创新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战略驱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缺乏粘合剂的碎片化结构无法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治理创新方式。
第三,求同存异,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因地制宜,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智慧城市群。中国区域和城市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不平衡,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不能千篇一律。(1)要勇于突破和创新,因势利导,发挥城市地域优势和资源特色,使中国智慧城市创新治理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和开放性。(2)评价标准多样化,不同的城市,其治理的重点、难点会存在差异,因而不同的发展模式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3)要因地制宜,构建特色鲜明、重点突出、有文化气质、有生活品位的中小型智慧城市:加快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在物联网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互联网+服务输出能力,促进东中西部生态农业、旅游休闲业、手工艺产业智慧化;(4)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打造中国沿江、沿海和内陆典型的生态智慧城市群落。
第四,加强全局规划和顶层设计,循序渐进,稳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1)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制定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整体方案,凸显其在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中的导向性作用。(2)要设立权威专门领导机构对智慧城市治理(城镇化)进行统一部署,任何一个部门难以主导和代表其他部门的利益。(3)立足长远规划,切忌形象工程和短平快政绩工程。要注意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智慧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具有动态性和特殊性。(4)要定期举办官方和非官方会议,促进地方、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5)要通过城市、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借力智慧城市治理大数据平台,分享闲置资产和智力资源,精准助力侧供给。部门(区域)间信息、人力、物力、财力合理流通,避免项目恶意竞争性的重复建设和部门(地方)保护主义。(6)要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逐步推进,系统综合治理,完善公共交通网络,改善人居环境。
第五,保持智慧城市治理相关政策连续性、稳健性和可预期性,平抑政府组织和机构调整所带来的科技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要做到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把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把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而不是简单地放弃或搁置既定的科技政策。(1)捋顺信息化、无线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新型城镇化(包括智慧城市)之间的科技政策关系,不仅需要有全面、清晰的路线图,还要保持政策之间内在一致性。(2)增强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和公众对科技政策的安全感,确保科技政策稳定供给和科技研发项目的可持续性。(3)要完善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反腐制度和问责制度。既要强化科技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又要宽容失败。既不能人走政息,也不能新官上任新政策,要科学地消解个人因素对智慧城市治理政策连续性的负面影响。
[1]ICF.About Intelligent Community[EB/OL].https://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index.php?submenu=Research&src=gendocs&ref=AboutIntelligentCommunities&category=AboutUs, 2015-11-11.
[2]Nam T, Pardo T A. Conceptualizing smart city with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people, and institutions[EB/OL].http://www.ctg.albany.edu/publications/journals/dgo_2011_smartcity/dgo_2011_smartcity.pdf, 2012-02-08.
[3]Washburn et al.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 defining thesmart city, its driv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IO[EB/OL]. http://public.dhe.ibm.com/partnerworld/pub/smb/smarterplanet/forr_help_cios_und_smart_city_initiatives.pdf, 2013-03-06.
[4]Nam T, Pardo T A.Smart city as urba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ntext [C]//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New York: ACM, 2011: 186-194.
[5]Giffinger R, Kramar H, Haindl G.The role of rankings in growing city competition[EB/OL].http://publik.tuwien.ac.at/
files/PubDat_167218.pdf, 2011-10-15.
[6]Rios P.Creating “the smart city”[EB/OL].https://archive.udmercy.edu/bitstream/handle/10429/393/2008_rios_smart.pdf?sequence=1, 2013-05-21.
[7]辜胜阻, 杨建武, 刘江日.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软科学, 2013(1): 6-12.
[8]李新社. 智慧城市建设的误区和难点[N]. 科技日报, 2014-02-21(8).
[9]胡宝钢. 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应谨防误区[N].中国信息化周报, 2014-04-14(12).
[10]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建立完整运行机制规避智慧城市建设误区[N]. 中国建设报, 2015-04-29(7).
[11]魏江. 多层次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建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 2010(10): 31-37.
[12]Paskaleva K A.The smart city: A nexus for open innovation?[J]. Intelligent Buildings International, 2011,(3):153-171.
[13]Paskaleva K. Enabling the smart city: the progress of E-city governance in Euro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9, 1(4): 405-422.
[14]Jeong K, & King J.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in Korea[J].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 Policy, 1996, 5(2):119-134.
[15]Shin D H, Kim W Y, and Lee D A. Web of stakeholders and strateg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MB: Why and how has DMB been developed in Kore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 2006, 8(2):70-83.
[16]Shin D H, Kim Y.Ubiquitous City: An Analysis From an Information Society Perspective[C]//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arriott, 2009: 1-20.
[17]GiffingerR, et al. Smart Cities: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EB/OL]. http://www.smart- citie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 2010-12-28.
[18]吴标兵, 许为民. 物联网技术的异化和制度规约[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4(6): 65-70.
[19]Saint A.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smart city[J].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2014, 9:72-76.
[20]金行钟.韩国版智慧城市U-City的现状与课题[EB/OL].http://www.fangchan.com/cchs/109/2015-12-02/6077735771148980498.html, 2015-12-02.
[21]宋熙俊.智慧城市成功关键是打通开放式的生态系统[EB/OL].http://www.fangchan.com/cchs/109/2015-12-02/6077735771148980498.html, 2015-12-17.
(本文责编:王延芳)
Innovative Open Governance of Smart Cities:Practi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U and Korea
Wu Biao-bing1,Lin Cheng-liang2
(1.SchoolofMarxsimofNUPT,Nanjing210023,China; 2.ZhejiangUniversityNingboInstituteofTechnology,Ningbo315100,China)
Op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Smart City.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in our country, such as by who, for what, how to construct. From Op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of Smart City Based on European and Korea practices, we conclude that the key issue is the availability of user-driven innovation ecosystem. Policy implications may be concluded: Build Government guide-enterprises participate-public driving open innovation model; Respect equitable discourse right of stakeholders, activate social capital, andaugmentreciprocity;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set up special leading authority; Seek common ground and reserve differences, combi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ct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and focus on the replicability of Open Governance Innovation Model; Keep the continuity,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policy.
smart city;open innovation;governance;social capital;sharing economy
2016-01-10
2016-04-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社会公众维权与社会维稳均衡治理研究”(15BZZ089);南京邮电大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智慧城市建设中物联网技术选择模式及发展路径研究”(JDS215002);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NYY215002)。
吴标兵(1976-),湖北黄梅人,博士(后),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物联网产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方向:智慧城市治理、ICT与产业创新、ICT与隐私安全。
C93;F29
A
1002-9753(2016)05-005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