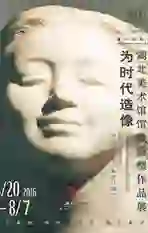缪斯殿堂的台阶是有层级的
2016-08-11张霁
张霁
众所周知,今年是伟大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声势浩大,让即使没有读过他们作品的国人也都在铺天盖地的资讯中知晓,这两位文学家当年处于同一时代。当然,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文豪亦是在这一年撒手人寰,可惜却回声寥寥,纪念活动也远不能与前面两位相比,这与他蜚声世界的作品《堂?吉诃德》颇不相称,我们只能惋惜地说,激情澎湃的战士塞万提斯的生前身后都未免寂寥。但这丝毫无损伟大的《堂?吉诃德》之荣光,不论纪念与否,那个执长矛、骑瘦马,不合时宜的老骑士,连同他狂热而天真的理想主义(作者本身亦然),早在每个热爱文学的人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文学的力量是强大的,作为艺术是优美的,而在这之外,或许更重要的是:虽然疯疯癫癫,有时难免滑稽可笑,瘦骨嶙峋的堂?吉诃德身上却体现了人类执著探寻世界的精神,这精神如此热烈而纯粹,我们无法不将其看作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追求真理的过程本身,正因有堂?吉诃德一般的“傻气”与笨拙,勇敢与真诚,人类文明才跨越荆棘走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堂?吉诃德》不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永恒的经典,不仅伫立在缪斯的文学殿堂核心的位置,也是人类精神史上弥足珍贵的宝藏。是的,不管在技术层面如何考量文学作品,语言、结构、情节、写法……这些都过关后,最终总要上升到精神的殿堂上一较高下,这富有力量和激情的精神之美恰是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世上并不缺会编故事的人,甚至而今那些网络小说在这一点上往往做得更吸引人,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然而经典文学所构筑的那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世界,透过情节背后探寻的人性幽深之处,折射出人类精神的伟大光辉,最终鼓舞、激励了一代代前赴后继者,在这个古老星球上探寻自身的价值。这也正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以及他们的作品跨越国界、种族、文体,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崇敬的根本原因。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名著《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所具备的品质,是以全世界任何一部文学史上,都分明写着《红楼梦》是世界级的一流作品,哪怕因为语言翻译、文化等因素,传播范围也许不如莎翁作品那么广,但这并不影响《红楼梦》以其高超的美学艺术水准和深刻的形而上意义比肩世界上任何一部伟大作品。这些本质上都与作家的民族、国籍、文学体裁,甚至文化没有绝对关系,因为地球上的全部人类都同出一源,来自同一个祖先,思维、情感都具有高度的共通性,都会为同样的人类精神所感染,为同样的情节而动容,也能欣赏同样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今天不少国人提出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对比”,列出诸多相似之处,并得出两个人都是国际性的戏剧大师,具有相同的地位,就无法让人折服了。
有“比”有“较”才叫“比较”
在正值纪念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的当口,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2014年的一篇有关“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对比”的访谈被重新拾起,并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与其他绝大多数谈及此问题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国华教授没有将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拿来条分缕析寻找共性,然后得出“各有各的好”,而是直言不讳“汤显祖不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是中国的汤显祖。我国古典戏剧水平远没有达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度”,并且表示反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国家的古典戏剧很民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但不一定很世界。”可以说,陈国华的这番言论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当下的学界几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学术惯例:大量论文、文章、访谈、讲话,一旦涉及对比,不管是中西方之间,还是本国内部,在洋洋洒洒分析过比较对象后,大多要得出“各有千秋”的结论,仿佛生怕比出了高下,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正确”,或唯恐招来论敌辩论,被攻击“偏激”。这种论调看上去貌似忠厚公允,实际上大多是没有观点的庸俗陈述,如同“摊大饼”一般将比较对象的诸种特质陈列,哪些同,哪些不同,却没有任何深入的判断,只“比”无“较”,这样的论述本身有何意义?事实上,即便是艺术领域上真处于同一级别的作品,也会有读者个人的偏爱,难道让读者对所有作品全部一视同仁地“五五开”吗?没有差异和高下的判断,就等于混淆了艺术的个性,也不利于艺术家的创作。更不要说很多时候,拿来做比较的东西本身的级别并不相称。在我看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本身就是并不相称的比较对象。
如果非要说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可比之处,其实无非是三点:第一,同处一个时代,从中可见中英两国同一时期的诸种社会人情;第二,同为戏剧家,从中可见两种戏剧样式在内容、形式等美学方面的诸种不同;第三,作品都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成就,同时具备反传统伦理桎梏的思想特点。前两者比较简单直观,无需更多讨论,第三点成为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牡丹亭》与中国戏剧形式大于精神的局限
“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梦》)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四梦”中公认成就最高的《牡丹亭》今天依然在舞台上活跃着,经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编排成“青春版牡丹亭”推广后更加名声大噪。然而,绝大多数去看《牡丹亭》的人,与其说是去看剧情,莫不如说是去看昆曲这门传统艺术本身的形式:唱词唱腔、对白身段、表演情态、服装化妆……对于剧情的关注往往是要排在末位的,而这也恰是中国古典戏剧区别于西方戏剧的一个重要之处。中国古典戏剧从一开始就和音乐形式紧密关联,“戏曲”一词就是明证,这有别于西方戏剧一开始便是朗诵为主的特点。对于形式的极度重视使得中国古代诸种戏曲的唱腔优美动人,直至今日,有些剧目的情节和内涵已无法让人接受,像京剧《红鬃烈马》,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却迎来“花心”丈夫薛平贵的调戏诘问,最终一夫二妻大团圆。若单凭故事本身,与现代观念实在相距甚远,今天的观众大多会嗤之以鼻,但因其中诸多唱腔优美动听,该剧却依然可以常演不衰。形式上的美感是今天一些戏曲依然能赢得观众的最重要原因。君不见“青春版牡丹亭”的观众大多对昆曲毫无了解,甚至看完了也对剧情本身印象模糊,却对昆曲的服装道具唱腔,以及整体浓厚的中国传统意境印象深刻吗?汤显祖的作品唱词优美动人,《牡丹亭》中许多句子日后都成为传颂极广的名句,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使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等。但这部作品,除了表演形式和语言上的美感外,提供的精神资源又是怎样的呢?
毫无疑问,《牡丹亭》代表了汤显祖的最高成就,汤显祖自云:“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在八股取士桎梏思想、宋明理学桎梏人心的大背景下,“一生儿爱好是天然”1的杜丽娘勇敢追求爱情,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礼教的背叛,汤显祖笔下这位美丽青春少女的心事,差可比拟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一样的花季少女,一样的旧礼法桎梏,一样的一见钟情,一样的情根深陷,一样的热情似火。男主角柳梦梅也算是中国传统爱情故事中大胆的男性角色了,在当时礼教大防的情况下,他敢于冒着死罪掘墓以求杜丽娘还魂,在爱情受到杜家家长阻碍的情况下坚定不改初心,对比汤显祖其他作品如《紫钗记》《邯郸记》中的软弱男主角,柳梦梅算得上勇敢执著了。然而,接下来的剧情仍然没能避免“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一幕,杜丽娘在作鬼魂时与柳梦梅大胆“幽媾”,醒来后却要求“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且还魂后心心念念的就是陪柳梦梅上京赶考,以便秉明父母,成就姻缘。柳梦梅本身也将科考视为人生最重要之头等大事。也就是说,此前大胆追求爱情的浪漫主义,都是在梦中或死后,现实中的人依然不能逃离礼法约束,反抗性就大打了折扣。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2这段话可谓入木三分,道出了汤显祖《牡丹亭》的局限之所在,汤显祖虽然自称“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但究其实际并未完全突破“理”的范畴,结尾处的大团圆,也全非《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怆结局。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反抗只在梦中和死后的一定限度内,现实里依然选择在旧制度框架下完成礼教的功名要求,求得世俗的婚姻认同,最终达成妥协。反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角爱火熊熊燃烧,从始至终藐视一切,视爱情胜过生命,两个人无比决绝而激烈的行为导致了自身的陨灭,却将两家的世仇泯然抹去,青春的爱情与古老封建家族的世仇同归于尽,这种结局对比《牡丹亭》最终对礼教的妥协,显然更能体现爱情对旧礼法胜利的彻底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抗之所以比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更彻底,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二人所处的文化背景相关,二人背后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并不对等:晚明思想的解放风潮虽然动摇了传统婚姻伦理和理学桎梏,汤显祖也将“情”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究其根本,并没有出现像莎士比亚所处时代欧洲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可能拥有人文主义思想家深厚的理论支持。汤显祖在他所能触碰到的思想范围内以梦的形式为寄托,伸张着人对“情”与欲的渴望,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但他显然缺乏莎士比亚那种澎湃而雷霆万钧的决绝气势和敢于同归于尽的勇气。虽然有外在文化环境的因素,但其结果就是《牡丹亭》这样的作品在今天看来,除了一些文字和形式上的美感,在思想上已难以震撼读者,其大团圆式的结尾也没能带来深刻的命运感,不能不说这是多数中国古代戏剧所具有的缺憾。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激情洋溢的活力,冲破一切阻碍的勇气,对爱情视同信仰,将爱人视为灵魂,本质上是为了个体心灵的自由宁愿舍弃一切——最终也的确付出了生命,与恶同归于尽。这种青春的力量好似峭壁之上垂直挂下的瀑布,巨大的冲击力穿越了时代与国界,直到今天还在激荡着每一个易感而丰富的心灵。
莎士比亚的天才就如同他笔下朱丽叶的那句话:“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就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3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的觉醒”带来的巨大自信和无穷魅力。或许,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爱情存在一天,阻碍爱情的因素存在一天,《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会永远拥有自己的读者;但在《牡丹亭》的礼教背景不复存在的今天,显然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故事已经很难再激起当代读者的兴趣,也难以产生共鸣。如果用尼采的理论来解释,那就是中国戏剧的酒神精神普遍被礼教和伦理抑制、削弱了,出于现实的妥协在本质上便缺乏和命运更深层次的对抗性,一旦时过境迁,就不再具有从前的生命力;而高扬的酒神精神却恰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莎剧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中国戏剧的“平面化”与直面矛盾的莎剧
无论是汤显祖笔下“最佳男主角”柳梦梅、为情生生死死的少女杜丽娘,还是梦里历经人世变幻,醒来大彻大悟修道成佛的卢生、淳于棼,抑或软弱的李益,痴心一片的霍小玉……汤显祖笔下的人物从始至终都缺少性格的变化,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非常简单。如同中国古代大多数叙事文学作品一样,汤显祖的剧作主要是靠优美的语言和跌宕的情节取胜,外部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梦幻和仙法的因素显然最大程度能提供传奇多彩的情节效果,于是,汤显祖大量运用了这些魔幻手法。离奇的际遇牵动了情节,使得主人公的行为被迫发生各种改变,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每一部都是如此。在皇权一统天下,礼教力量极为强大的当时,汤显祖的作品的结尾要么如《牡丹亭》《紫钗记》一样妥协、大团圆,要么如《邯郸记》《南柯梦》一样,主人公最后顿悟出家,几乎完全用佛道的观念完成结局,或许这也是汤显祖在时代背景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吧。
人物性格既没有太多变化,整个故事的矛盾往往也就只能停留在外部而非内部。或有奸人从中阻挠,或是礼教妨碍团聚,或是仙人制造迷局……若将外部矛盾解决,故事就完美落幕,至于人性是怎么演变的,人物内心深处有怎样的矛盾冲突,一概不知道也从来不被关心——这也是中国古代戏剧乃至多数叙事作品都忽略的重要环节。中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太聪明了,过早看透了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觉得或缥缈的思想或幽深的内心都同样难以捉摸,那么只要“意”到了也就罢了,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国人似乎总不喜将一件复杂事情的具体细节细细勾勒,而更多关注此中的感情、感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特点,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就如同在绘画上,吾国的水墨画也好,工笔画也罢,一直未能像西方油画那样,涉及更复杂也更逼真的立体、光影、解剖范畴上。同样,苦修的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也出现了依靠“顿悟”,“自得曹溪法,诸经更不看”4的禅宗。于是,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不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大量游走于外部空间的表现方法,也就顺理成章的容易解释了。人物性格也只好相应大体不变,对人性虽有描摹,也无非停留在一开始设定的几个要点上,一经确认便即固定,呈现出一种“平面化”的状态。
这一点在对比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后就会看得更清楚——虽然这样的对比对莎士比亚来说真的有些不公平。二人的可比之处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即汤显祖的思想性已说到这里为止,而在他止步的地方,恰是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之所在。是的,莎士比亚构筑了一个和现实世界并行,却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心灵的王国,与现实世界一样丰富多彩,且更加深不可测。这个世界是如此隐秘却又重要,在莎士比亚之前,即便是在西方,也鲜少有人能用这样行云流水的方式将它呈现。
几乎所有莎士比亚身后的评论家都惊叹于他在探究人类心灵方面登峰造极的能力。十九世纪的英国评论家赫士列特援引莎士比亚作品《辛白林》里的句子说:“‘世上各个角落,国王,王后,国家,少女,妇人,甚至坟墓中的秘密都躲不过他那探索的目光。他像是人类的天才,随意和我们易地相处,玩弄我们的心意,似乎那是他自己的。”5的确,对莎士比亚来说,除了人与世界深刻的矛盾外,人性的幽深之处也是他最感兴趣之所在。他的悲剧中,情节都围绕着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矛盾进行,哈姆莱特身上完全体现了这一点:外来事件的突变(父亲被杀)使哈姆莱特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学生变成了浮躁轻率的青年,继而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中,情节根据这些变化而一幕幕展开,著名的延宕王子此刻性格变得更加成熟,贯穿作品始终的是哈姆莱特的怀疑(也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人这“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怎么会犯下那么卑劣龌龊的罪行?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关注的已不仅是某个人的命运,某个复仇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品性到底是怎样的?人类该怎样对待自身的诸种力量与这力量可能导致的结果?
这样深入的思考绝不是汤显祖以及其他中国戏剧家所具备。莎士比亚的背后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文艺复兴,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种下了日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种子。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其实并非他自己首创,早在他之前,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就认为,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应该是研究的主题。他说:“有人对野兽、飞禽和鱼类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从何来,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兰迪诺也主张,人应该集中精力思考人类的根本问题,从普遍的现实中抓住人生的目的。6不过,这种探究人性的纲领虽早已提出,但真正实施起来却需要绝顶的天才,莎士比亚过人的天赋和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其中最优秀的那个。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莎士比亚,这场文艺复兴会是什么样子。莎士比亚从不回避那些人生中的尖锐矛盾,不仅如此,他从来都勇敢地向矛盾的最深处进军,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在那暖流与寒流交汇处,有着最为丰富的养料,能最大限度揭示人类和这个世界的本质。如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样,莎士比亚从不吝惜让自己的主角陷入极度麻烦棘手的情节中,并且决不会出于个人感情来改变剧情应有的内在逻辑,所有的情感和矛盾全部集中在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人生的多样性和人性的难以捉摸。这样复杂丰富的情感,广阔的空间,充分的矛盾冲突,是中国戏剧完全无法相媲美的,就像赫尔德感叹的那样:“每逢读莎士比亚的时候,我就觉得,剧院、演员、布景都消失了!完全是世界天意之书在时代的风暴中纷飞的散页!是个别的对于民族、等级、灵魂的刻画!”7
莎士比亚的心灵全息图像与真正的比较方向
与其说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在讲述一个个故事,莫不如说他是在研究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伊阿古、埃特蒙们的心灵全息图像,所有的情节都在向观众讲述:人是多么多变的生物,人性是何等的复杂立体,人是怎样在欲望和思想中苦苦挣扎。莎士比亚不仅表现了多彩的现实世界,还将揭示表象下的心灵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样并行的内外两条线,即使是在后世,也只有少数文学大师才能做到。而从莎士比亚开始,这也成了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确切地说,作为文艺复兴的巨匠,莎士比亚关注和表现的是在当时被无限高扬的“人”本身。站在文艺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莎士比亚肯定了反抗的力量,人性的美好,同时对人性的弱点及其可能导致的未来剧变感到忧虑,四大悲剧便是这样的产物。这种仅为天才所具有的洞见力在全世界的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汤显祖和其他中国戏剧家都远远不能与其相比。任何为了证明二人“各有千秋”而进行的“摊大饼”式论述,论述者本身就如同汤显祖一样,只停留在了一个表象的层面,“再现表现”,“反映反抗”,再之后?没有了。而这恰是莎士比亚刚刚开始的地方。“活着,还是死去”在汤显祖那里并不成其为问题,却是人文主义者对这个世界发出的终极追问。
所以说,如果从更高的形而上层面和精神境界来看,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在文学殿堂中根本不属于相同的级别,不具有可比性。汤显祖在他所处的时代非常优秀,反映了时代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和人类文学中的顶级巨匠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艺术和思想不会因其所处的国籍民族不同就随意变换标准,汤显祖的平面化叙述、为伦理道德所囿而妥协了的矛盾,以及没能进入形而上层面的缺憾,在后世终于由他的同胞,伟大的曹雪芹全部弥补,如果说非要比较,这才是本民族真正与莎翁一个级别的作家。缪斯的殿堂花团锦簇,巍峨的宫殿亦是拾级而上的,只有极少数顶尖的作家才伫立在那台阶的最顶端,这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二者对社会生活鞭辟入里的全方位再现,对人类个体心灵和人类前途的探究,形而上层面的忧虑与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最终竟然也异曲同工指向了一样的彼岸世界。如同屠格涅夫当年拿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对比一样,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比较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史诗性对比。跨越时空、跳出文体,将中英两个民族最出色的作家拿来,比较其代表的两种文化最优秀的部分,找出人类的共性和文化的差异,恐怕才是未来比较的方向。而只是因为所处时代相同,文学体裁相同(其实中英戏剧在这方面也并不相同),外在形式相似就动辄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是非常幼稚的。如果说非要给汤显祖找一个比较对象,我倒是认为,更接近汤显祖著作精神的可能是文艺复兴的另一个先行者——薄伽丘。当然,这是另一个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