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中国艺术史:海德堡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胡素馨访谈录
2016-08-03艾姝邵亮
艾 姝 邵 亮
⊙ 科学·艺术·时尚
问道中国艺术史:海德堡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胡素馨访谈录
艾 姝 邵 亮
本文在对中国艺术史学者胡素馨教授的采访中,通过对研究者个案的展示,探讨了美术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艺术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时代跨度、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与跨界合作等。
艺术史;研究方法;问题意识
编者按:中国艺术史学者胡素馨教授于2014年底接受了本刊专访。胡教授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家庭里。她于1982年在密西根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87年至1996年,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高居翰先生,主攻中国古代绘画及佛教美术,并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5年,她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艺术史学系任助理教授,于2006年在此获终身副教授资格,并兼任艺术史系主任。2012年,胡素馨教授接任雷德侯教授的中国艺术史教席,任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所长。胡教授的研究集中而有深度,同时也兼具丰富的面向: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人画及佛教美术领域。2004年出版的《视觉盛宴:七到十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是她多年系统分析并研究现存敦煌粉本,考察敦煌壁画的制作方式的心血之作,为同时期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范本。因此,她是世界上专门研究敦煌手稿及粉本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近年来,基于对敦煌石窟壁画的深入研究,胡素馨教授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成为研究中国现代艺术大家张大千的专家。她着重讨论张大千对敦煌遗址的发现和再探索,并以此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家对边疆及“异域”的发现,即中国现代美术考古的兴起。同时,胡素馨教授还有意识地将民族学与艺术史研究结合起来。2013年到2015年,由美国盖蒂基金会资助,胡素馨教授牵头发起,海德堡大学与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共同合作的培训项目“民族志之眼: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开展。该项目受到国内艺术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从与民族学紧密相关的殖民视角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摄影史,也是胡教授近年的研究范围。
记者:作为一个美国人,您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艺术史之路,和中国结缘的?
胡素馨:我的母亲是一位油画家,父亲从事印刷行业,所以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对视觉艺术有浓厚兴趣。刚进大学,我学习的是西方艺术史。当时我所在的密歇根大学可选的语言课程有希腊语﹑斯瓦希里语和中文。我选择了中文,因为我看到了中国书法,并被它迷住了。1979年,我就到台湾学习中文,先是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后来还去了台中东海大学。在东海大学,我还选修了书法和中国美术史课程。后来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学术背景和语言能力成为优势。我有西方艺术史的基础和中国美术史的知识,本科时连续学习了5年中文,还有中文文言文的学习经历,提前学习了研究生的中文课程,并学习过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于是,我有幸成为高居翰先生的弟子。可以看到,我从西方艺术史出发,通过书法和中文,逐渐与中国艺术史结缘。
记者:您于1992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为何不是艺术史专业,而是考古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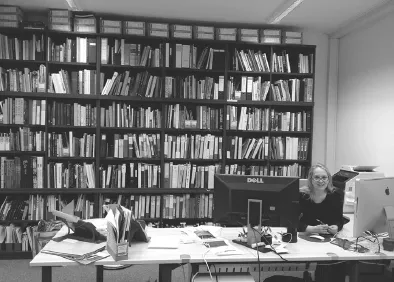
图1:胡素馨教授在海德堡大学的办公室

图2:“民族志之眼”项目中,胡素馨教授与项目成员交流
胡素馨:在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艺术史这个专业。如果你要学艺术史,得去像中央美术学院下面的艺术实践类的专业和民间美术专业。但当时有佛教考古专业。这个应该是从宿白先生那开始的。佛教考古,在英语和德语中对应佛教艺术史,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被归在考古下面。我当时就跟着宿白先生和马世长先生做佛教考古。
记者:您正在主持旨在帮助中国艺术史在读研究生提升学术能力的 “民族志之眼:抗日战争时期艺术”研究项目。对中国抗战时期的艺术进行研究,您为何选择从“民族志”入手?
胡素馨: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对“民族”这个概念尤为感兴趣。战争期间,日军于1937年8月开始增强的侵华行为,使得大量艺术家随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及考古所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被迫从沿海一带迁往那些具有“多元文化”的内陆地区。对内迁艺术家来说,那些比如被庄学本①称之为“白地”的地方,是完全未知的地域。40年代初,多次辗转迁移的图书馆﹑大学等多前往四川平原一带。围绕这个区域,艺术家和研究人员有机会前往这些多元文化的地区,比如甘肃﹑四川﹑青海﹑宁夏—这些地区有些实行自治,有的受政府控制。而政府层面,尤其在教育部,对西部地区进行全面和系统认识的意识随战火的蔓延愈发强烈。从1931年伪满洲国建立开始,一个思潮开始兴起,即“东部”已经失守,所以整个西部地区得到全国广泛的关注。人们希望对西部建立系统及全面的认识。而当那些研究者开始全面地观察西部地区的时候,他们更多开始关注那里的少数民族族群。因此,当艺术家真正进到这些地区后,他们也开始大量描绘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比如在敦煌,他们被所谓的“民族”素材所深深吸引,比如维吾尔人﹑藏人等非汉人的素材。在内蒙古乃至甘肃地区,到此采风的艺术家的临摹和素描作品所表现的都是些民族题材。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着重考察那些战时的民族材料。
记者:围绕“民族志之眼”项目,您如何理解民国时期语境中的“民族”(Ethnic Group)和 “国家”(Nation)?
胡素馨: “国家”在整个民国时期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从1912年1月1日开始,中华民族第一次采用了“国家”(nation)概念。此前,大清国只是一个封建帝国。“国家”诞生后,采用了两个时间制度,一个是格里历法(即公历),即“西历”或“太阳历”,另一个是民间传统的“月历”,即“农历”。所以从民国建立之初开始,中国人就意识到,国家与时间一样,不是天然存在的。国家是现代进程的产物,需要被研究和反思。出生于中国昆明的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1936~)曾写过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书名叫《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现在看起来,它所表达的观念可能有点“过时”,但它的确探讨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大到“国家”,小到“民族”和“族群”该如何定义?这些概念又是如何被建构和想象的?你看,以你我为例,汉人和盎格鲁-撒克逊族人(Anglo-Saxon),双方各自把对方想象成一个族群。但在民国时期,不同“族群”(Community)要被整合成一个国家﹑一个更大的单位,当时的人们需要把国家想象﹑描绘并叙述为一个实体。
从安德森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与“国家”话题同样重要,两个概念紧密相关。这就涉及一个紧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民族学角度来具体定义一个“国家”。于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去湖南﹑四川和云南等地考察调研。考察发现,的确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族群存在。但问题是,如果将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所有人收纳到一个“国家”的大概念中,有没有可能凝聚成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单一“民族”。这在当时是个热门话题。1949年后,中国的所有“民族”被分成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加一个汉族。但在民国时期,少数民族被划分得更细,其数量远远超过五十五个,大概有一百多个。所以,考察当时做的一些民族研究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有些人,比如傅斯年,就不喜欢讨论民族这个话题。他不支持在史语所下面设立民族所,他只要一个“中华民族”,即我们前面谈到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单一民族,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国家变得更统一﹑更强。所以,傅斯年给当时在四川松潘进行田野调查的芮逸夫②写信说,不要跟当地人谈什么民族,谈谈知不知道国父孙中山是谁。傅斯年主张不问民族区分的问题,因为他觉得这种问题使国家这个整体概念被弄得四分五裂。在民国时期,“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就涉及到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等观念层面的问题。
记者:您正着手写作的专著《中国艺术何以为 “中国”:战争、考古及中国现代性的形成(1928~1945)》(How Chinese Art Became Chinese: War, Archaeology,and the Making of Sino-Modernity, 1928-1945)聚焦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艺术,与“民族志之眼”项目所关注的对象一致。而您之前的专著《视觉盛宴:七到十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③则是有关唐代佛教绘画的。为何您的这两项研究跨越了如此长的历史时段?是您的研究兴趣点发生了转移,还是二者之间仍有所关联?
胡素馨:我写的后一本书与之前写粉本和敦煌壁画的专著有关系。1992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得到班宗华(Richard Bernhardt)先生的建议,考察青海塔尔寺一带的佛教印刷作坊。但他似乎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艺术家在青海作画。应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青海塔尔寺的佛教印刷作坊仍有很多人在制作佛教绘画。当时有个复兴的风潮,即壁画和唐卡得到复制,青海所有的寺庙也都得以修复。而他们所有用的都是些老技法,比如“刺孔”﹑临摹,和敦煌壁画的绘制方法一样。之后,我一共分别去了十三次去看那儿的人作画。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本专著《视觉盛宴:七到十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
在考察过程中,我发现,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间有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同仁(藏语称“热贡”),在同仁周边有个叫五屯的小镇。字面上,“五屯”是军队驻扎地的意思。这里最早可以追溯到藏军在唐朝的驻军。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这个地区所用的语言是唐代汉语和藏语的混合体,甚至附近村子的人都听不懂这里的话。这个村子恰巧是夏吾才让出生的地方。他曾作为张大千(1899~1983)的助手于20世纪40年代前往敦煌进行壁画复制工作。所以我去五屯找到了他。那个时候是1992年,当时我正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发现这条线索之后,我还计划就这个主题再做点什么。这就是我正在着手写作的《中国艺术何以为“中国”》的由头。
记者:您的专著《视觉盛宴:七到十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其关注点主要在佛教绘画的作坊式生产方式和社会赞助两个方面。您为什么选择从这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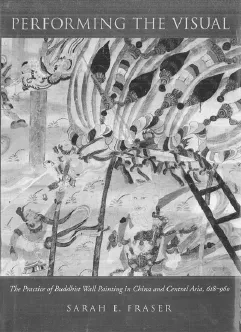
图3:胡素馨教授的专著《视觉盛宴:七到十世纪中国和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英文版封面
胡素馨:如果想要研究佛教壁画及相关的艺术实践,必须考察以作坊为中心的制作过程以及供养人。要制作壁画,必须有团队协作。并且,壁画的制作有某种“重复性”。在归义军时期(848~1006),曹议金(?~935)家族统治着敦煌地区。他们尝试在石窟中不断地重复一些特定的场景和编排,比如,讲述六道外师和佛教徒的“劳度叉斗圣变”占据了196窟的整个西墙。但我书中的观点是,除“阿弥陀佛经变”外,在南北墙上同样还有七个不同经变不断地重复着,并都由相同的画师们绘制。这意味着供养人要求画师不断重复某些故事情节。这是因为供养人也在团队中工作,不是供养人想要一个窟,付钱就完事。参与团队工作的供养人家庭成员必须和家庭及其管理者商议。以曹议金和曹元忠(?~967)父子的个案来说,他们赞助了洞窟的开凿。而他们下属的管理者中有人是“窟主”,像电影的导演一样,负责指导协调。在第98窟中,有超过两百位供养人,他们都被画在壁画上。这表现的不仅是金钱意义上的供养人及其社会地位。有些供养人还是政府官员。他们的官职都写在画像的附近,表明他们在地方政府中的职位。比如我在书中谈到过,第98窟中曾表现有负责农业灌溉的人﹑负责军队及骑兵等的人等等,展现一种社会协作的景象。当你看艺术制作和故事场景的“重复性”的时候,再看供养人,就能见到人与人协作之中有着某种“机构化的网络”。这里不仅仅讲述谁是主要供养人,谁有可能是主要的画家,还有上百个和完成洞窟有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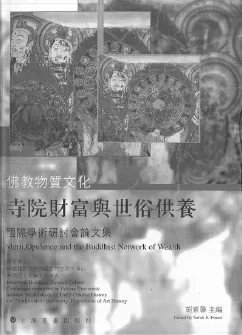
图4:胡素馨教授主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封面

图5:2007年7月,胡素馨(右)拜访张大千敦煌写生的助手夏吾才让(中)及其子更登达吉(左)
记者:您是张大千研究的专家。您是从什么角度来研究他的?
胡素馨:首先,我不认为有人可以自称是张大千专家,除了很少数的一些人比如李永翘﹑巴东﹑魏雪峰还有傅申。他们真正了解张大千职业生涯的每个细节,是真正的专家。而我只是研究了张大千一生的很小一部分。我和张大千的机缘与我的导师高居翰是分不开的。高居翰刚认识张大千的时候,张先生正居住在加州蒙特雷(Monterey),而他的侄女正好在高那里学习。所以高先生与张大千的侄女就结伴去张先生的家里去拜访他,和他聊天看画。在以高先生为中心的圈子里,对张大千的关注一直伴随着对中国美术和绘画的讨论。
我对张大千在敦煌活动感兴趣,因为他在敦煌的临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壁画制作方式。一群人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一件壁画。同样的,在敦煌复制壁画,没有其他画家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以这种方式来说,他和他的艺术家们在敦煌所做的临摹,更像一个画行所做的事情,像一个做摹本的唐代画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记者:如何评价张大千敦煌时期的美术考古?有人说他破坏了敦煌壁画。
胡素馨:我和宿白先生之前有个对话,我想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即张大千是中国第一个美术考古专家,是将实践艺术﹑艺术史及考古相结合的第一人。他去看了那些古迹,并以壁画来考察绘画史以及风格史,比如北魏﹑隋﹑初唐﹑盛唐和晚唐以及宋等等—这在当时是很新的做法。当然,后来不只是张大千这么做,王子云以及其他艺术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去了像唐昭陵﹑乾陵这样的古墓,做了碑拓并和前朝进行对比,以探究风格史。更早些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里格尔(Alois Riegl)就主张要通过参访古代遗迹来总结艺术风格的变化。德国艺术史家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考察,去了土耳其﹑希腊等地。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还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张大千之所以令人敬重的原因在于,他试图还原的中国绘画史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材料之上。
记者:那么张大千和王子云的 “美术考古”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是中国最早进行美术考古的研究者吗?
胡素馨:张大千和王子云都分别开始建立墓葬和寺庙的目录。他们对用记录风格发展的编年方式来了解中国佛教及墓葬艺术中的图像史颇有兴趣。对王子云来说,他的活动中还包含了对新石器时期陶器纹样﹑佛教圣像及石刻﹑墓葬雕刻乃至佛教壁画的复制。王子云的复制品中,包含了一幅巨型壁画的供养人—曹元中,10世纪敦煌的地方执政者—它被放置到王子云工作室的后墙上。而在这件供养人复制品的上方,王子云放置了汉墓的拓片。对王来说,把这些复制品放在一起,和展示原作一样重要。就“美术考古”的方法论来说,把不同物件放在一起来对比并建立艺术史的连续性,这种方式尤为重要。而张大千对佛教壁画的掌握却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收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绘画的兴趣。他把成百张的佛教壁画复制到帆布上去。他依靠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群体,比如家族成员﹑学生乃至朋友。有时庞大的团队会有二十多人。而实际上,张和王的做法都根植于当时历史学科的大潮流中:在民国时期,研究重心转向了人文学科的各种田野调查及实证证据上。张大千的调查属于个人行为,而王子云的调查具有官方性质。他带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国立博物馆﹑地理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进行了1942年到1944年间的三次大考察,获得了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的墓葬﹑敦煌的石窟及附近的佛教遗址的科学数据。
实际上,与美术考古密切相关的是,向达﹑劳干以及石璋如在40年代构建了中国佛教考古的起源。作为测量专家,石璋如之前在安阳的挖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又带队和劳干一同穿越了西北地区。除了敦煌和榆林地区的石窟外,他们还于1942至1944年勘测了汉代的塔楼﹑宁夏和甘肃边境的唐粟特人遗址。北京大学的向达还在学生夏鼐和阎文儒的协助下,带队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主持了从兰州到敦煌的考古发掘,探索长城﹑拓跋墓葬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北朝遗迹。而他们所记录的“多元文化物件和传统”为他们的田野调查行为增添了几分“民族”色彩。由于丝绸之路遗存皆为西藏﹑唐古特﹑突厥﹑粟特及和田文化的产物,而这些物件又和佛教寺院联系甚深,因而多以民国时期的佛教研究以及内陆边疆的少数民族研究为主。

图6:2014年胡素馨教授在海德堡大学大礼堂作终身教授的任职演讲
记者:那么,美术考古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比如与美术史的方法相比。
胡素馨:我有一篇刊登在《Asia Major》上的文章叫《佛教考古的物质文化:置物于原境》(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Dunhuang Buddhism:Putting the Object in Its Place)④。文中,我认为,考古学,尤其是佛教美术考古,需要考察其原境(context),而不是一件独立的物品。这需要把物品放到它们相应的位置中,就像罐头要在厨房中。考古学要看到的是所有的锅碗瓢盆,以及它们各自的位置。对于考古学而言,当挖出一件东西,我们需要看它的原境。而美术史考察的是“柜子”或博物馆中的“罐头”,并且讨论它自身的美﹑材质或结构等。
在佛教美术考古中,我们和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做了敦煌的3D图像项目,因为我们要看洞窟中的东南西北的每一面墙壁。我们看每个图像所在的位置,它相对于其他图像所在的位置,赞助人画像在甬道或墙面的某个位置。我记得,我和宿白先生的另一个学生一起,在洞窟里临摹。我们把洞窟画成方形,有甬道,有转角。通常情况下,这样就可以了。但他说,你需要画条界限来分化洞窟以外。因为敦煌壁画中的图像总是很巨大,延伸得到处都是。你总得想办法指出哪里是入口。它引入到并不规则的石头,而不总是方形的空间,而且不同洞窟之间有一些过道相连。这是关于如何重建原境的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图像而言,它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当你看敦煌的图像,如果只是用单独的照片,就只能看到图像的一部分。而我们做的这个3D图像可以提供一种观看的轨迹,看到连续的图像。但很多时候,人们拿到了一件物品,而试图复原它原本的原境是什么。当然,总体上,考古是要思考在其原境下的物品与其环境的关系。
但佛教考古可能也是比较老套的研究方法。它不太关注理论的问题。宿白更多强调要搞明白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在敦煌藏经洞的那些经卷和文书被视为“可移动”(transitive)的考古材料。它们于1002到1006年间被放进去,但到1900 年6月21号才被再次发现。所以它们就像被存放在某些地方,然后一些人拿走了它们。所以很多人移动它们,也触摸到它们。这就是“可移动的考古材料”。虽然它们被转移了很多次,但它们仍是考古材料。
记者:在中国,一个学者的硕士、博士论文基本会奠定其毕生研究的主要方向。您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近古的石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古的8世纪到10世纪的唐代艺术家,有一个走向中国古代美术历史深处的变化。但后来您又一步步地深入到佛教美术的研究中去了。为何您选择以佛教美术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呢?
胡素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的导师在我准备博士考试的时候说,你的领域要包含中国所有时期的绘画。所以我要搞的是整个中国绘画史。我的荣誉本科论文写的是唐代的重要建筑大明宫。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行旅图”类型的作品,以及相关的叙事绘画及叙事理论。可能是因为我对唐代的强烈兴趣,在博士论文中,我将叙事绘画的研究挪移到唐代壁画研究中。而我转向佛教美术的原因是,在敦煌17窟中,即“藏经洞”,有很多8到10世纪的粉本。在中国的绘画传统中,画稿和粉本大多没有被留下来,所以这些材料显得弥足珍贵。除了饶宗颐,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粉本。他做了很多图像学辨认工作。除了他和日本的秋山光和,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所以这是研究艺术实践层面的不可多得的机会,而我做这方面的研究本身和我的研究专长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我自本科以来的研究,还是有前后关联。
记者: 您的研究中,除了佛教美术之外,还有一个研究重点在摄影方面。您的摄影研究中,“殖民文化”和 “民族学”仍是研究的核心。这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但并不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摄影进行研究而选择的唯一切入点。为何会选择这个很多西方学者都会想到的“西方”角度?
胡素馨:在2007到2008年的时候,我正在洛杉矶盖蒂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撰写《中国艺术何以为“中国”》一书。他们当时正好购入一个大型的殖民时期摄影收藏,包含了日本﹑欧洲和美国摄影师的作品。刚开始,我完全没有兴趣—我对非中国人所作的艺术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基金委鼓励我去看看这些藏品。出于礼貌,我当时说我会去看这些藏品。老实说,当我看到义和拳运动期间所拍摄的一些关于砍头行刑的场景后,我真的感到异常伤感。我当时想,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我应该为消除那些照片中所纪录的偏见做些工作。所以我开始了研究摄影的历程。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早期“拳乱”这段时间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种西方世界对整个中国的同情。那个时候,在美国有某种“泛太平洋”情感,即对中国人(包括对日本人)生存境遇的责任感—这是半殖民化的一个产物。所以我认为,摄影是观察战时中国,甚至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亚洲及中国的全球化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记者:您前年开始就任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将工作的常驻地从美国西北大学转到德国—艺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就您的感受,德国与美国的艺术史研究的最大差异体现在哪里?
胡素馨: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德国有个很好的机构框架,有点像日本。每个人都在一个组织下工作,都支持机构的领导,以团队的形式来实现大的研究目标。在美国对大型研究项目的资助要少很多,大家一起在一个大项目下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小。
记者:您近年不断与中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合作。这样的合作使您有怎样的收获?
胡素馨: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很多伟大的想法。我很荣幸,我们目前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很好的学术联系。今年7月,故宫的研究处处长余辉先生在海德堡做格策中国艺术史访问教授(Heinz-Götze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的时候,就提议:在2015年,即郎世宁抵华三百周年纪念日,我们一起组团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看意大利绘画,重新思考18世纪中国绘画及其所受欧洲(尤其意大利)之影响,反思郎世宁艺术的根源。追寻其根源并不只是单独地讨论清代宫廷绘画,而更多从全球视角来探讨他的艺术。余辉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全球视野”的中国学者,这在中国的艺术史领域内也是个大趋势。
(特别感谢海德堡大学王廉明博士的大力帮助。)
注释:
① 庄学本(1909~1984),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他于1934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近十年的考察和拍摄工作。
②芮逸夫(1898~1991),中国最早一批人类学家之一。曾任职中央研究院,并于1930年随凌纯声到东北开展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即对赫哲族的调查。
③该著作是基于胡教授于1991年开始,1996年完成的学术论文而写成。其部分内容基于欧洲所藏的敦煌材料。该书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获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学术图书奖以及美国大学美术史协会(CAA)艺术史最佳著作奖。其中文版正由中国美术学院王道杰女士进行翻译,并将于2015年底与中文读者见面。
④“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Dunhuang Buddhism: Putting the Object in Its Place.”Special Issue on Buddhist Material Culture, Asia Major, 2005: 1-14.
(本文转载自《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艾 姝天津美术学院学报编辑 美术史博士
邵 亮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
Probing into Chinese Art History:An Interview with Sarah E. Fraser,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 at Heidelberg University
Ai Shu and Shao Liang
This interview of Professor Sarah E. Fraser tries to discuss such themes on art history study as what i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n art history scholar should be, how wide a scholar's focused reasearch eras is, whether and how the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could be mixed together,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and the multi-discipline cooperation, etc. And the latest reserach trends are also revealed.
Art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consciousness of problems
J110.9
A
1674-7518(2016)01-00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