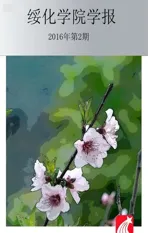从《觉醒》看凯特·肖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书写
2016-04-13郝燕蚌埠学院外语系安徽蚌埠233030
郝燕(蚌埠学院外语系 安徽蚌埠 233030)
从《觉醒》看凯特·肖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书写
郝燕
(蚌埠学院外语系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凯特·肖班的代表作《觉醒》讲述了主人公埃德娜反抗男权社会的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勇敢走出家庭,寻求爱情和事业的故事。小说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诸多核心思想,包括消解性别的二元对立,重建女性话语,强调女性经验的多元性等,借此批判了19世纪美国南方父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关键词:凯特·肖班;《觉醒》;后现代女性主义
《觉醒》是19世纪末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特·肖班(1851~1904)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觉醒”的艰辛历程。该作品出版后,曾因涉及“婚外恋”等禁忌话题被列为禁书。随着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又被世人发掘出来,并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评价,被推崇为美国有史以来关于女性生活最重要的作品。该小说具有从多重视角解读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视角主要有女性主义、心理学和象征主义等。本文建筑在前人经典解读的基础之上,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理论框架,尝试对小说文本进行重新阐释,揭示作家肖班创作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意识。
一、消解性别的二元对立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探索性别不平等根源时,将矛头尖锐地指向西方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并指出正是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决定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1](P155)正是凭借着“男性中心/女性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男权社会才得以维持稳定。为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倡消除性别对立,把男女关系拉回到零度平等的地位,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和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因此,只有女性具有些男性的气质,男性拥有些女性的特征,达到一种“双性同体”的境界,两性才能完美融合。
肖班在塑造人物时,极力弱化两性间的差异,摆脱性别偏见的束缚。《觉醒》的女主人公埃德娜正是消解了性别二元对立的产物,这体现在其男性特征的凸显和女性特征的缺失上。首先在相貌上,肖班如此描绘埃德娜:眉毛浓密,双手厚实、有力,手臂结实而滚圆,表情率直,“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2](P4)埃德娜解构了父权制中心文化设定的女性特征,如温柔、怯懦、忘我与屈从等,在性格上被塑造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男性角色:积极能干,性情豪爽,像男人一样大杯喝酒,热衷于赛马,喜欢谈论文学、宗教和政治问题。另外,她精力旺盛,有着男人般的胆识,敢于在大海中“游到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游到的地方去”。[2](P32)在家庭中,埃德娜拥有自己的经验和主体的存在,彻底瓦解了男人为女人制造的“原型”——贤妻良母。她与丈夫关系冷淡,认为彼此之间没有相通之处。身为母亲,她却很少关心孩子的生活,自称“命运没有赋予她履行这种职责的能力”。[2](P21)潜意识里,埃德娜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当听到“孤独”这首歌曲时,“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他赤裸着身体,站在海边的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上,凝视着远方展翅翱翔的鸟儿,脸上流露出绝望的神情”。[2](P30)这个想象中的男人何尝不是她自己?正如脑海中的这一场景,孤独、寂寞的她最终也是赤身裸体地葬身大海。在与情人罗伯特的感情中,埃德娜始终处于主动的一方。当罗伯特为了躲避她而远走墨西哥后,她毫无顾忌地向莱思小姐、罗伯特的母亲,甚至她的丈夫打听罗伯特的消息。罗伯特从墨西哥回来后,她主动亲吻其额头、眼睛、面颊和双唇,大胆表白,“让我们爱到天荒地老,我的罗伯特。我们将永远为对方而生存,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与我们无关”。[2](P128-129)埃德娜破除了恋爱关系中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定位,由爱情的客体转变为爱情的主体,在她看来,“世上最大的幸福是占有自己的情人”。[2](P133)可见,埃德娜完全颠覆了男性为女性塑造的歪曲形象,寻找、认识并实现了真正的自我。
与此同时,肖班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的男性形象标准,如主动、强大和充满智慧的主导者,其笔下的男性往往被塑造为被动、弱小和缺乏才智的从属者,罗伯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性格温顺,喜爱巴结身边的女性,甘心情愿做她们的侍从,且乐于参与女人的谈话,甚至毫不避讳地谈论连女人都羞于启齿的妊娠话题。他多愁善感,在遇到挫折时会显露出女性柔弱的一面,曾经“无助地拜倒在莱迪奈太太的脚下,乞求她赐予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和安慰”。[2](P12)在埃德娜面前,罗伯特完全丧失了父权制社会的男性应有的大男子气概,成为需要人保护的孱弱形象。在埃德娜作画时,他会下意识地把头靠在她的胳膊上,这是典型的男女主体意识的倒置。在“温柔”和“坚强”这一对反义词中,男性在传统上被认为占据了“坚强”的角色,但罗伯特的举动实际上表明他已被置于女性角色之中,而埃德娜担当了男性角色,照顾和保护罗伯特。罗伯特胆小怯懦,屈服于社会习俗和传统道德的压力,不敢接受埃德娜的爱情,最终悄然离开。显然,肖班在罗伯特身上注入了诸多女性的特征。
二、重建女性话语
后现代女性主义吸收和利用了福柯(Michael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致力于重建女性的话语。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它们也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3](P75)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的论述,使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解到存在于话语内部、外部的复杂性和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性,并为重塑妇女主体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发明女性的话语——一种颠覆了父权制中心话语的“新”语言。[1](P158)
肖班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风尚在整个社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男权中心的话语秩序中,男性是文化发言的主体,女性只是纯粹的客体,处于话语的边缘地带。然而,肖班在小说中勇于挑战男性的主体地位,她意识到,要改变女性作为“他者”和“第二性”的命运,就必须根治女性失语症,创造女性的话语系统,因为语言是控制文化和主体思维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福柯指出,在话语政治中,边缘群体试图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差异,使其自由发挥作用。[3](P74-75)《觉醒》中的埃德娜正是通过抵制男性的霸权话语来反抗父权制社会,同时,她以女性话语的形式制造出新的真理,并为自己赢得新的权力。她在少女时代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毅然嫁给一位天主教徒,以此瓦解父亲任意处置自己婚姻的霸权话语。婚后的埃德娜颠覆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地位,极大地冲击了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传统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面对丈夫的号令,她报以不满的轻视和反抗,“别再用那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否则我就不理你”。[2](P37)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杀死屋里的安琪儿”,指在父权社会中体现男性意识、温柔贤淑的传统女性形象;二是女性必须书写自己。[4](P208)埃德娜勇敢地走出家庭,对绘画事业的追求成了她书写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她摸索出女性自己的话语模式,拥有了区别于男权文化的独特语言,从而可以自由表述女性真实的经验、感觉与思维。面对丈夫的训斥,“埃德娜以桀骜不驯的姿态予以回敬,她已决定不再退缩。……‘你别管我的事,不要干涉我!’”。[2](P67)除了管理豪宅,她还广泛参与社交活动和应酬,并主办一些家庭聚会,结交社会名流。她的才干打破了男性世界的话语特权,使她在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埃德娜敢于冲破传统社会道德,积极寻求婚外性关系,并在多个男人间周旋,获得了性的话语权。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探索使后现代女性主义意识到:要彻底颠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就必须解构男性对女性在肉体方面的统治,即“性”的统治。同样地,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拉康(JacquesLacan)也强调性的欲望同人的精神意识活动及语言表达的密切关联。[5](P373)在传统意义上,性是男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规训女性的话语,而埃德娜通过满足女性身体性欲的方式破除了这一话语特权,实现了“性的自治”。当罗伯特因惧怕社会传统势力而故意躲避她时,她运用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力,驳斥道:“你简直是自私自利的化身,……你可能认为,这是女人不该有的行为,但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表达自我的习惯”。[2](P125)埃德娜运用话语的方式折射出她对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角色的定位。她在周围人的心中树立了女性的话语权威:她的丈夫惧怕她脑子里关于女人“永久权力”[2](P77)的想法;罗伯特在信件中时常写道:“‘就像蓬蒂利埃太太(埃德娜)常说的那样’。”[2](P74)埃德娜掌握了话语权力,建构了女性的话语,让社会听见了女性的声音。在小说结尾,她排除一切外界的干预和支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脱掉了象征着男性话语樊笼的衣服,将自己赤裸裸地呈现在现实生活中,这标志着她最终获得了女性身体的支配权。根据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有关女性身体的理论“阳具逻辑中心主义”,女性身体永远都是男性身体,特别是男性生殖器的客体和性欲发泄对象。[5](P380)可见,通过身体的叛逆,埃德娜向整个男权社会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她的经历向人们传达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的有关话语权力的论断:原来没有话语权力的生物,随着说话中主体化过程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能够演变成为主体化的人。
三、强调女性经验的多元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拒绝男权的普适性理论,否定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概念,试图寻求一种多样性,强调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琳达·尼克森(LindaJ.Nicholson)指出:“应该用多元的、具有复杂内涵的社会属性概念来替代简单笼统的女人或女性性征的概念,要把性征看作是多种属性中的一种,与阶级、民族、族类、年龄、性取向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考虑。”[6](P34-35)
肖班在作品中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觉醒》即是一部关于女性的成长小说。正如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伊瑞格瑞(LuceIrigaray)所言,女性的特征是“残片,她具有不稳定性,非确定性,矛盾性,流动性,多样性”。[7](P373)埃德娜出生在清教意识浓厚的长老会家庭,但她生性叛逆,为了逃避做祈祷,逃避公老会的礼拜,她跑到一片大草原上自由地飞奔,这是她反抗父权制的体现。对于爱情,她有着浪漫的幻想,她曾恋上一个目光严厉而忧郁的骑兵军官和一位订了婚的年轻绅士,甚至想象中的一位悲剧演员的面容和身影也能激起她无限的遐思。然而,在谈婚论嫁时,她还是“接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2](P21)嫁给了一位来自新奥尔良上流社会的富商。婚后的埃德娜按照父权制社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自己,尽力做一个贤惠的妻子和称职的母亲。然而,周围的环境使她渐渐发生了改变,她对狭隘孤寂的家庭生活感到厌倦,开始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连她的丈夫也意识到了其变化,“她正在恢复她的本来面目,正在抛弃那个虚假的自我,那个自我像衣服一样伪装了自己的真面目,而以另一张脸谱出现”。[2](P67)为了撇开丈夫的恩惠,摆脱她不愿意履行的责任,她搬出丈夫的豪宅,靠绘画为生。“我不想让人牵着鼻子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许除了孩子——即便那样,在我看来——那也是以前的事了”。[2](P132)最后,爱人罗伯特的离去切断了她对人世间的唯一一丝牵挂,已经“觉醒”的她已不愿再回归家庭,她选择了死亡。
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由于社会地位、种族、阶级和文化等的不同,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体现出多元性的特点,没有单一的女性理论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肖班强调千差万别的女性经验,在《觉醒》中向我们呈现了多种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包括莱迪奈太太和莱思小姐。
莱迪奈太太具有“一切女性的美德和魅力”,[2](P9)有着“圣母玛利亚的性感”。[2](P13)然而,她的美貌成了男性“凝视”的产物,“那双碧蓝眼睛恰似一对蓝宝石,翘起的双唇是如此红润,使人一看就想起樱桃或其他什么香甜的深红色的果子。……她那白皙丰满的颈脖,她那美丽修长的胳膊,都合得天衣无缝”,[2](P9)“蓝宝石”“樱桃”“果子”“天衣无缝”,这些描绘的话语无疑将女性的身体“客体化”了。莱迪奈太太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美国南方上流社会和克里奥耳人所崇尚的女性传统美德:“宠爱孩子、崇拜丈夫,愿意牺牲自己的个性,长出侍奉天使的翅膀,并把这作为自己最神圣的天职。”[2](P9)这是男权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伊瑞格瑞曾言:“我们整个西方文化都建立在谋杀母亲的基础上”。[8](P81)另外,莱迪奈太太还是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卫道士。在得知埃德娜与罗伯特的婚外恋情后,她先是恳求罗伯特不要再纠缠埃德娜,以免“铸成不幸的大错”。[2](P23)在相劝无果的情形下,她又转而在埃德娜面前故意挑拨两人的关系,说罗伯特根本没把埃德娜放在眼里,继而诋毁罗伯特,称其“装腔作势,哗众取宠”。[2](P51)她时刻劝告埃德娜要恪守妇道,甚至搬出《圣经》,教导她要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莱迪奈太太不同,莱思小姐代表的是反抗传统习俗和偏见,崇尚自我的女性,她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她感情生活的描写,可见她对传统的婚姻生活没有丝毫的向往。她也不会像其他女性一样,为寻找一个好的归宿,竭力按照男人的需要和利益塑造自己,相反,她敢于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她挑战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观,“对衣着从不在意,发卡上戴着用旧黑丝带系着的一串人工紫罗兰花”。[2](P29)身为钢琴家,她献身于音乐事业。对艺术的热爱使她与埃德娜视彼此为知音,她引导着埃德娜走上“觉醒”之路,让其意识到“艺术家必须具有勇于反抗的灵魂”。[2](P137)面对埃德娜与罗伯特的恋情,莱思小姐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她很想尽自己的努力成就这一对两情相悦的爱人。每当埃德娜前来拜访时,她总是与其分享罗伯特的来信,为的是让埃德娜明白罗伯特的真心,澄清他们之间的误会。莱思小姐深深地体会到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哀与不幸,她把她们比作“翅膀软弱的鸟”,“摔得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在地面上扑腾,甚是可怜”,[2](P98)她以自己的言行向世人展示女性“觉醒”的决心。
四、结语
虽然肖班生活在19世纪末期,比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早近一个世纪,但其作品《觉醒》所表现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足以显示其敏锐的眼光和不凡的智慧,以及作为有责任感的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的思考。通过消解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重建女性话语,强调女性经验的多元性等举措,肖班有力地批判了美国南方父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该作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女性主义运动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Chopin,Kate. 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 Stories of Kate Chopin[M].NewYork:Penguin,1976.
[3][美]贝斯特,凯尔纳,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田颖,韦琴红.女性主义书写:从双性同体到身体书写[J].求索,2012(3):208-210.
[5]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Nicholson,Linda J.Feminism/Postmodernism[M]. London: Routledge,1990.
[7]孙绍先.女权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8]Irigaray,L.Le Corpsà Corps Avec La Mere[M].Montreal:La PleineLune,1981.
[责任编辑王占峰]
Seeing Kate Chopin's Post-modern Female Writing from The Awakening
Hao Y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30)
Abstract:The Awakening, the masterpiece of Kate Chopin, tells a story of Edna,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who fights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values, and pursues love and career. The novel embodies some key theories of post-modern feminism, including deconstructing the gender antinomy, reconstructing female discourse, and emphasizing the pluralism of female experience. It criticize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Southern American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Kate Chopin; The Awakening; post-modern feminism
基金项目:2015年安徽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多重理论观照下的肖班小说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13052015SK15)。
作者简介:郝燕(1984-),女,安徽潜山人,蚌埠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应用语言学。
收稿日期:2015-05-24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2-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