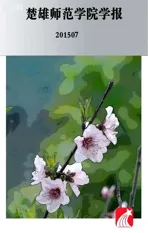从“硬控制”到“软治理”: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之路 *
2015-03-19邹荣
从“硬控制”到“软治理”: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之路*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嵌入式治理’研究—基于权力与利益博弈关系的分析”,项目编号:2012Y134;楚雄师范学院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项目:当代彝族村落文化变迁与治理转型研究,项目编号:YZZX1402。
邹荣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675000)
摘要:在现代治理体系中,乡村作为一种重要的共同体,其依赖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基础成为其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伴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浓厚的“乡土文化”逐渐远去,乡村社会的发展正在经历转型带来的治理困境。面对处在变革之中的乡村社会,以文化重建和价值引领,伦理粘连和价值塑造,人文关怀与认同建构,国家理性与包容发展为路径的“软治理”模式的推行,无疑对于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的价值。将“软治理”与“硬控制”有机统一起来,保障社会从刚性约束到韧性治理的转变,最终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技术的变革与转型,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软治理;治理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5-04-06
作者简介:邹荣(1981—),男,楚雄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8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5)07-0087-05
Abstract:In the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the village as an important community, its dependence on the culture, spirit and value basis become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long with the strong local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the predicament of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In front of the reforms of rural society, lea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and value, shaping the adhesion and ethical valu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national rational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oft governance mode undoubtedly for the reality of the plight of the crack in current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has important value, the soft management and hard control organically, social security shift from rigid constraints to toughness governance, and ultimately to promot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 technolog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乡村社会治理转型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面对处在变革之中的乡村社会,推行“软治理”模式,无疑对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今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
在当今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正在让乡村社会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性洗礼,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带来的治理困顿。现代化浪潮正在一波又一波地席卷中国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内部人文地理关系正在逐渐被重塑。乡村社会的没落,带来的不仅仅是青壮年人远离村落、土地的荒芜,更是乡村社会人文逐渐流逝,与之伴随而来的是无数的留守儿童与老人,乡村社会逐步远离了正常的“生态”。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家庭伦理、公共道德、代际关系被逐步消解,家庭温情、敬老爱幼传统,家庭归属、土地依赖、聚族而居逐步为流动社会所冲击。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牵引下,乡村社会为器物和工具理性层面所充斥,而现代社会发展应该具有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国家权力撤退、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冲击,村庄共同体逐渐趋于解体,“村将不村”现象在一定范围显现,乡村社会治理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空前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治理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治理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凸现,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在这样背景下,社会一旦缺乏一种有力的纽带或者力量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的失衡和断裂倾向就将不可避免。随着与外界的接触深入和融合增多,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世外桃源”,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被打破,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等鲜活而充满变革性的时代价值被注入乡村社会之中,成为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和未知因子。以农耕维护为文化基础的整个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最为深刻而剧烈的文化变迁,也带来了新的治理困境,即乡村社会正面临“法制悬浮、功利下沉、信任流失的三重主要困境”。[1]
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诸如土地大面积抛荒、农民高龄化、农业孱弱化等为代表的乡村经济发展困境不断显现的同时,深层的人文困境与社会治理困境则显得更加令人忧心。面对日趋复杂的治理环境和治理体系,客观上需要对现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做出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整个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进而推进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复杂社会还需要在基本原则或道义职责上界定能够连结各社会集团的纽带,这种纽带所联系的共同体有别于其他的共同体。”[2](P8)而扮演这种纽带最常见的形式,则多是精神、价值与文化。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而言,乡村社会“秩序并非一种以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3](P183),更需要通过文化力量的重建和重塑来助力整个社会的治理转型发展。
二、从硬控制到软治理:乡村转型治理的必由之路
(一)治理转型:从单一性向多元化
回顾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通过国家和执政党的组织架构、政治动员、政策引导等多种措施和途径,推动了其快速转型的进程,为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然而,国家刚性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同时,也使得乡村社会柔性治理的显得滞后无力。伴随国家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场域中从“前台主演”到“后台导演”,从直接管控到间接嵌入,从刚性十足到刚柔并济等一系列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方式的转变与调整,乡村社会治理开始步入“软治理”时代。本质上,现代国家的治理也应该不仅仅只是硬生生和冷冰冰的国家权力维度,而且也是充满着德性和文明的柔性治理过程。[4]
如果说在税费改革以前,乡村社会的治理是围绕着国家与乡村社会权力与利益纠葛为重心的话,那么,在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心显然是围绕乡村社会秩序为核心,寻求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为重点。社会的快速转型带来了乡村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快速变革,一些新的公共问题开始凸显出来,需要通过创新治理方式给予回应。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仅只建立在暴力为基础之上,也需要通过文化指引、精神感召、制度规训、心理认同等多种方式来推动。实际上,推动治理对象与治理主体之间互动,通过引导和激励等柔性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成为利益平衡、秩序共建、资源优化、互利共赢、催生民主的治理方式,也在很大程度迎合了整个时代治理的潮流和理念。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软治理是国家主导、社会互助,共同推动开放、协作、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所必由路径。
(二)融合互补:从硬控制到软治理
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沿循总体性支配方式,或者通过群众性的规训、动员和运动来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严格的控制。[5]乡村社会作为国家依附体而存在,国家几乎统摄了整个村落社会的全部领域,掌控了整个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也塑造了整个基层社会内外形态。对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相对不足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国家和政党的进入有效地弥补了乡绅缺失带来的治理“真空”,较好地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目标,也较好的迎合了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与调整,乡村社会个体变得更加理性、多元化,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农业税费的免除,国家权力和政党的权力逐步开始在村落社会收缩,国家权力的收缩带来的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逐步疏远、疏离,原本以税赋负担为核心的矛盾冲突转变为以公共物品供给、有效服务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权力的理性回归和村落社会有序互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村落社会诸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文化性问题凸显出来。从治理逻辑、结构、体制、制度等层面上深刻改变了村落社会治理内外环境,也改变了乡村治理模式。面对理性化的村落社会利益诉求,当一部分硬治理被束之高阁,而软治理又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时,国家及其代理人对村落社会实行“力治”难以适应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需要。因此,国家权力的理性回归和社会自治的有效成长,对于整个村落社会秩序治理转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国家强有力“力治”还是寻求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寻求更加开放有序的治理体系,对于推动村落社会与国家有序互动无疑是现代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从硬性的管控到柔性化的软治理,较好地实现了对传统的全面管制突破和超越,将平等互利、合作共治、柔性推动与富含人文关怀的新方式引入社会治理领域。软治理也较好的实现了与硬治理之间融合互动,将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治理策略很好融合到治理进程中,理顺国家与社会二者关系,也与现代协商民主政治的新思维走上了契合之路。
三、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乡村软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文化重构与价值引领
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总是与特定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较为稳定性、深层的符号化结构,文化是政治治理体系中最为厚重基础性资源,也是推动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变革与发展的坚实基础。文化往往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自发地左右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模式。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而言,失去了文化活力的乡村,不只是文化的问题。文化活力的丧失,导致乡村不再是可以慰藉心灵的家园,从而失去了保护和发展的内源动力。[6]因此,文化作为社会资本最为关键和核心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资源的重要依赖,对于推动社会治理进程的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文化重构在村落社会转型治理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社会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政治和经济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7]国家通过文化治理技术把一整套国家意识形态嵌入到基层社会之中,通过社会主流的政治文化、政治符号的融入,将国家的治理理念与乡村社会现实需求有机的融合起来,对于推动乡村社会软治理的实效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而言,治理的转型与发展也就意味着乡村群体和个体心理的重塑与社会文化的更新再造过程。新的文化因子在社会的母体中不断孕育、萌芽和成长,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不断冲突、协调与融合中实现文化重构。
乡村文化的存在本质和发展关键在于认同,这是乡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根基、精神支柱,是广大乡村居民的广泛认同、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是乡村个体对所身处的乡村社会心理依恋感、文化归属感,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也表现为乡村的公共理性。同时,乡村文化的重建不是对原有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基础上的全新建设,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人要“文化自觉”,同样中国乡村文化重建也需要这种“文化自觉”,而不应该是仅仅依靠政党和政府组织单一主导下的重建,否则,文化认同的危机也将由此不断产生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像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8]单纯依靠国家主导下的文化“嵌入”,往往都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当然,政府积极引导和参与无疑推动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推动力,如在文化设施、文化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是乡村内部无法企及的。
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其内部更加开放和现代化,传统乡村价值观念的消解亟需新的价值观念的引领,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乡村社会价值观无疑是当前乡村社会软治理根本所在。一是要强化对传统精髓价值观念的继承和融合。现代乡村社会的治理不是对乡村社会传统的摒弃重建,任何形式的价值塑造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价值观念有机融合,实现二者的融合互动,增强乡村社会的认同;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引领现代乡村社会多元价值观念,并将其逐渐凝聚成乡村社会普遍价值共识。二是要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效性。只有通过更加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关注民生的文化建设活动,向乡村输入更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从而不断地提升赋予村落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主题。三是要强化文化价值阵地建设。要充分发挥现代通讯技术和媒体的功效,加强各类宣传、文化机构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伦理粘连与精神塑造
当下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治理困境的化解更加需要伦理精神这一“普照之光”。[9](P1)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而言,伦理粘连与精神塑造同样具有其内在的重要价值。对于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伦理性危机问题的凸显同时,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即通过伦理粘连实现乡村社会的新整合。伦理精神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改造和形塑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当今世界公共领域一个重要的治理技术。甘地曾经说过,“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作为乡村社会精神秩序的基础,伦理道德的整合作用显然是乡村软治理不可以回避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家族和村落中所建构起来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当代的乡村社会治理中仍然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控制是无法抗拒的。20世纪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政权通过对乡村社会权力体系的再造和重构,确立了国家权力乡村社会核心地位,乡村作为民族国家建构中重要的政治单位或者“细胞组织”而存在。但是由于“伦理精神及其道德规范只有在不与权力意志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冲突产生了,权力意志就会表现出对伦理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蔑视,从而使伦理精神及其道德规范的矫正和约束功能丧失殆尽。”[9](P6)因此,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乡村社会治理进程基本上都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和组织机构的主导下进行,这一段时期内伦理粘连就显得十分脆弱。
伴随现代治理理念的崛起和快速推广,多元社会治理因素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在乡村的主导地位,国家权力组织需要通过服务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扮演。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意志以及法的精神都无法实现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统摄性功能,从而不得不呼唤伦理精神去取代它们在以往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位置。[9](P8—9)对于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而言,以公共精神、伦理精神为代表的公共性是维持乡村社会场域内的自治的重要力量,也是现代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本质源头。乡村社会精神家园凸显着对乡村个体的“终极关怀”,也暗含着文化秩序在规约民众行动中的重要旨意。[10]正如熊培云先生所指出的“一个人,如果深爱着一个村庄,你摧毁了他的村庄,也是在摧毁他的精神世界。”[11](序言)可见,村庄社会的存在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精神世界的塑造也成为左右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当代乡村社会的软治理的实现客观上不能忽视乡村社会精神层面的塑造,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通过重建村民的生存价值,保障乡村社会个体的精神福利。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乡村社会的治理要在不断提升乡村居民物质条件和水平的时候,通过不断提升精神服务水平,提升幸福感。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在“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冲突中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对于现代乡村“新乡土”伦理精神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要通过吸收、借鉴、扬弃实现新乡土伦理能既显其“新”之内涵,又不失其“乡土”之本色,真正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乡村社会只有守住自己道德的交往空间,也才有可能真正把守住乡村社会认同精神家园,才能够保证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人文关怀与认同建构
急剧而快速的社会转型、深刻而激烈的社会变革,让乡村社会正在面临因为转型变革发展带来的潜在机遇的同时,也在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现实阵痛。这些阵痛不仅仅来自外在形态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更多是源自乡村社会个体内心世界漂浮不定。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情感的逐渐遗失,让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一种精神缺失的无序状态。因此,重视和强调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人文主义关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理论,在注重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并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提升其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在经历拨乱反正,回归到人文主义关怀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保障。
坚持尊重个体价值信念为基础,注重将人文关怀纳入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将乡村个体的价值与整个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将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地融入到乡村社会服务体系之中,尊重乡村社会个体的地位、价值、行为方式,将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自治有机统一起来,注重乡村社会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心态的塑造。“社会软治理”理念,注重强调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心灵的滋养、精神的提升和心智的开发来调节和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12]乡村社会的软治理要注重通过人文主义关怀的推行,使得乡村社会个体在满足其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不断提升其精神的需求。乡村社会内部要更加注重道德约束、文明规范、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心理疏导等方式,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乡村社会生根、发芽,努力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硬规范与软约束的并重。
软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用共同的价值信念去引导和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因此,建构一种有序的价值认同是社会软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任何一种制度(或者理念)总是要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制度设计得再合理,若不能成功地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中,或者说,倘若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遭遇到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则最终不能带来效益,也不可能为这个社会带来长久的稳定。”[13]因此,乡村社会的认同建构无疑是整个乡村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整个乡村社会有序的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当前乡村社会个体与整个社会价值规范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冲突,要实现乡村社会的软治理必须通过将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乡村社会个体的内在诉求。通常而言,作为个体的人往往难以简单、被动接受外在社会价值的灌输。因此,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建构是建立在个体价值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要通过不断引导乡村社会民众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心态,引导他们通过理性的看待转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帮助他们找到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软治理理念和实践,帮助他们找到精神上慰藉。“作为社会现代化之根本因素的人的现代化绝非只是少数社会精英分子心态的现代化,而是广大民众的心态的现代化。”[14]要实现广大民众的心态的现代化,通过“文化公共性”的塑造与建构,增进乡村社会内部的内在认同度。
(四)国家理性与包容发展
村落社会的解体在客观上需要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国家来积极构建,单纯的依靠乡村社会自身显然无法保证拯救乡村社会的没落。国家需要从整个社会全面、和谐、有序发展的高度,基于国家长远发展、稳定发展的战略高度,准确、客观认清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厘清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如果继续坚持把“城市偏向理论”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依据,必然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必将对乡村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局面。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与非排斥性发展战略才是保障乡村社会得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治理的责任所在。
伴随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家在给予城市、城镇高度关注的背景之下,如何保障乡村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政治关注,是一个国家理性治理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保障乡村社会发展关键所在。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乡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整个有序发展社会支撑基础。当前,整个社会为城市、城镇话语所充斥,乡村社会利益与发展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价值不言而喻,深刻变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已经将乡村社会置身于整个社会发展巨浪之中。现代国家治道的变革与发展是包含国家治理心智与心性的成熟,国家治理要通过不断完善健康有力的国家精神人格,确保治理进程中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实现。唯有如此,乡村社会的未来发展有希望在健康的环境之中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推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下,“城市中心”价值理念,乡村社会发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缺乏了国家层面的有效支持。包容性发展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其本质问题就是平等与共享、公平与合理的问题。乡村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回归到发展机会、地位的保障,国家要以主动、理性的包容观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有序发展。在乡村场域中,任何主体的利益垄断和话语权垄断都不利于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结语: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展望
乡村社会作为“治理体系的微观层级,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和末梢。它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绩效高低的重要变量。”[15]乡村的社会的善治关键在于有内在文化的支撑和支持,否则,乡村社会的发展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从刚性控制到韧性治理转变与调整,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国家治理方式、治理结构、治理内容和治理模式的诉求。乡村社会变革与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开放、互动、有序的合作治理模式。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而言,通过对乡村社会文化、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心理变化等非强制性的要素施加相应的影响,并实现其对乡村社会发展和秩序调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软治理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还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还需要通过不断完善来推动治理成效。软治理在实践中突出和强调非公共权力因素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当下一种时尚推崇也好,亦或者是创新实践也好,软治理是对已有理论和实践总结反思的新思考和新思维。它形成和产生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替代已有的治理理念和行为模式,而是作为一种新的调整和完善。
我们强调和重视乡村社会的软治理,并不意味着对硬治理的否定。在保证国家权威制度运行的刚性约束的条件下,必要的运行和治理机制的弹性空间的存在也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内在需要。单一的硬治理模式会引发治理失灵,只依赖软治理也无法满足乡村社会现实需要。只有二者的有效融合互动、并行不悖、各展其长、各得其所,才能够有效地推动乡村社会的“善治”进程。
软治理是柔性的,它的实现和运用更多地是依赖舆论导向、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的保障与实施,依赖的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自律与遵从和外在环境的社会引导。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软治理模式的推行需要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在治理问题的理性契合:一方面是国家要通过理性思路建构,探寻转型中的乡村治理路径;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也要理性对待转型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社会的治理进程中。软治理不是对硬治理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对硬治理的完善和补充,是现代公共治理模式的调整。软治理的实质意义在于在保障国家强制力之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同时,强调协商、契约等非强制性方式,在治理领域中软治理与硬治理是可以实现共生的,是乡村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软治理模式应是题中之意,也是国家治理必然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不仅仅在于技术工具层面,更在于价值理念层面,在政治生态缺少活力,行政文化逐步枯萎,文化精神日渐缺失的背景下,要通过软治理模式的推行,将实现公平、正义等先进理念贯穿于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之中。[16]唯有如此,“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才可能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
参考文献:
[1]张丽琴.法制悬浮、功利下沉、信任流失:乡村治理的三重困境分析[J].农村经济,2013,(9).
[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英)哈耶克.自由秩序的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4]任勇,肖宇.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2).
[5]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6]李华东.乡村的价值与乡村的未来[J].建筑学报,2013,(12).
[7]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4,(2).
[8]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J].社会科学,2007,(1).
[9]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0]陈浩天.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悖论与价值赓续[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1]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12]社会心态考验执政者中国社会“软治理”谋破题[EB/OL],2011年05月3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5-31/3077895.shtml.
[13]李汉林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4]唐魁玉,张妍.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以30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为中心[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
[15]秦德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与层级[N],学习时报,2014-07-14.
[16]徐勇,吕楠.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
(责任编辑刘祖鑫)
From “Hard Control” to “Soft Governance”: the Road to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ZOU Rong
(ChuxiongNormalUniversity,Chuxiong, 675000,YunnanProvince)
Key words:rural governance; soft governanc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