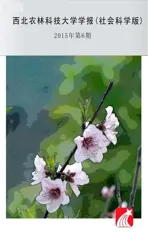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2015-02-23高万芹蔡山彤
高万芹,蔡山彤
(1.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武汉 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3.西南财经大学 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成都 610000)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式家庭农场
高万芹1,2,蔡山彤3
(1.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汉430074;
3.西南财经大学 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研究所,成都610000)
摘要:在政策与市场的推动下,以改造传统农业为目标的企业式家庭农场应运而生。企业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具有如下特征:高资本技术要素、大规模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及企业化的市场销售和风险规避方式,这完全符合政府对现代农业的期许,因而常常被树为典型。但是,因为在发展中要求较高的环境、面临较大的风险,企业式家庭农场只能是少数精英农户的选择,大多数小农无法走通此路。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完全寄托于企业式家庭农场身上,大量存在的小农、中农等多元经营方式作为现代农业基础,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企业式家庭农场;高值农作物;资本劳动密集;规模经营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引出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新型家庭农场开始,各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把家庭农场视为新型农业主体的重要实践方式之一[1]。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实质是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中落后的经营方式。之所以提倡家庭农场,一是对大规模企业经营实践效率效益的反思[2,3],另一方面是因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符合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的国情,土地的社会保障仍是重要的战略问题[4];加之家庭经营的方式十分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而具有效率效益[5],因此,家庭农场被视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发展方向。然而,学界对家庭农场的具体经营形式及其规模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大家庭农场和小规模家庭农场两种模式的争论上。
主流观点认为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不同于传统小农的经营方式和逻辑,家庭农场应该走资本密集型的大农场之路,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融合科技、信息、农机、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以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为组织特征[6-9]。这种家庭农场类似于企业,其本质是农业资本经济[10]。企业式家庭农场能够面向市场需求,以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生态高效农业,解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并实现农民增收[11]。作为高资本、高技术投入的现代农业经营形式,弱质的小农是难以发展成现代化的家庭农场的,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主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大金融、技术等政策扶持,为家庭农场的成长打造好外部环境[12-14]。
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应立足于小农经济,以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力投入为主,发展“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15]或者是“小农+中农”的小规模家庭经营,而非依赖机械和雇佣劳动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家庭农场[16],政府应该加强生产环节的配套服务,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大市场之间的困境[17]。
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农业现代化走一条资本密集型的规模经营之路,收益让资本或者少部分农民占有,还是农业收益保留在农业领域并由大部分农民占有?也就是说家庭农场的规模和经营方式要不要立足“小农经济”。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现代农业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比例的加大,很可能会造成农业被资本异化,但是,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确实存在难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18]。面对这种两难困境,黄宗智认为发展资本和劳动双密型的小规模园艺业是一种有效的路径,中国高附加值农作物的发展空间(主要是蔬菜、瓜果、木本坚果、花卉等园艺业),给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而精”家庭农场带来了机遇[15]。蔬菜等非谷物类农作物,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栽种、收割、采摘、浇水、除草、施肥、施药等),很多环节无法采用机械,同时这些作物的产值又比较高,农户可以凭借小规模土地收入所得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与谷物类家庭农场可以高度依赖机械不同,非谷物类家庭农场需要高度依赖劳动力,这对以家庭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小而精”家庭农场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人多地少的国情,也比雇工经营的方式便宜和高效。
黄宗智看到了高值农作物的发展空间带给小而精“非谷物类家庭农场”的重要契机。然而,高值农作物的发展空间也引来了资本,特别是政府对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雇工式家庭农场大量产生,因其较高的现代技术要素和企业化的运营管理,而容易被政府塑造为典型,其经营规模也超出以自身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家庭农场。这种雇工式家庭农场已经超出黄宗智意义上的“小而精”家庭农场,因其在农业生产中无法用机械来替代劳动力,其雇工成本占据生产投入的很大一部分,现代农业技术的资金投入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生产要素配置已经不同于资本节约型的小农经济,走上了依赖雇佣劳动和技术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类似于企业经营。
原本小农是无资本优势、保守型的,但在市场经济兴起下,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以及一些畜牧水产养殖的发展空间让农民自我积累有了质的突破,再加上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一些家庭农场已经出现了资本和雇工投入双密集的现象,农业经营的企业化逻辑不断凸显。本文着重探讨非谷物类的家庭农场生产方式及其经营的特殊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
二、企业式家庭农场的生成及其特征
2009年起全国开始试点家庭农场,各地依据自身条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规模和经营模式,城镇化进程中村庄内部的资本积累、留守劳动力和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成为家庭农场产生的重要力量[19]。然而,在鼓励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一些家庭农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家庭经营的范畴,走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式家庭农场,陈义媛更是把这种农业转型过程中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比重的上升,看做是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在中国的产生[20]。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资本技术要素投入比重的上升,这不仅从生产力上,也从生产关系上改造着农业经营的方式和形态[21]。在这场现代化的改造中,家庭农场的形态和类型也出现了多样化,由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变为家庭成员为主要的经营管理者,然而又不完全类似于农业企业式的大规模经营,因此很值得我们研究。笔者以中部地区H市郊区家庭农场的发展经营状况为例,探讨在资本、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相对匮乏的小农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雇工式家庭农场,并进一步反思其生成条件、经济属性及其典型性。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 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展开的为期15天的课题调研。
H市从2009年起,开始试点发展家庭农场,并逐步形成了一批现代都市郊区型家庭农场,这些家庭农场一般直接面向市场。H市农业主要在新城区,本文以其中N区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为例来进行说明。N区是一个人少地多的地区,农户大都在种地,当地政府比较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截止到2013年底,N区有家庭农场百余家,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20多家,带动土地流转达1万余亩。家庭农场共有劳动力200余人,雇佣人数近1 000人,土地承包面积从20~300亩不等,土地流转根据土地所处位置的好坏,每亩按600~1 000元/年租给农场主,家庭农场农业收入平均达20万元以上,其中较为成功的是土生土长的“菜乐家庭农场”。
(一)企业式家庭农场——菜乐家庭农场的发展
G村现有村民小组6个,农户315户1 139人,全村劳动力889个,其中常年外出务工189人。全村农用地总面积4 847亩,其中耕地3 308亩、林地70亩、养殖水面100亩,其他1 369亩(村庄外垸由河流冲积形成的滩涂)。因为较多的土地面积,很多农户留在村庄中务农,村里3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有14户。
李某,今年50岁,村里规模最大的家庭农场主,他原本是一个菜贩子,90年代末因生病加上生意失败背负债务,被迫回家种地还债。刚开始种了近10亩的常规蔬菜作物,夫妻俩自产自卖,但总体效益不高,很有生意头脑的李某发现反季节蔬菜的收益更高,便在2001年搭起竹架大棚,改种反季节蔬菜。李某为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效益,还主动学习和接受一些农技培训,以改进品种和种植技术。2004年,在市里的农业技术培训过程中,受到启发,开始引进“猪—沼—菜”生态农业模式,当年搭建了15亩的竹架大棚,建起了养猪场,养了3头母猪、出栏了54头小猪。收益见效后,李某逐渐扩大种植规模和养殖规模。截止到2013年底,一共拥有148亩的钢架大棚,创利润80万元左右;养殖场母猪数57头,出栏数超过1 000头,纯利润10万元左右。2014年种植规模扩大到186亩(租金也由原来的600元上涨到900元,租期延长至16年)。现在他的“菜乐家庭农场”已经是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和科技示范基地,成为集生产和销售一体,种养结合,外加餐饮休闲的综合型家庭农场,并拥有了自己的商标和品牌。
(二)企业式家庭农场的主要特征
1.生产面向市场。李某并非单纯的商品化小农,而是具有较高市场分析与定位能力,用现代技术和经营理念改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管理者。李某长期坚持自销,每天都会到菜市场摆摊,除了销售,还能时刻了解市场行情,根据市场行情及时掉头转向,争取在价高时卖出,在行情不好时更换品种。李某的蔬菜基地里面种植的都是有特色、产量大、卖价高的品种,这些品种都是他在详细观察了市场之后引进的。此外,李某也非常注重农产品的市场信誉和品牌效应,经过几年的积累,他的农产品已经在当地农贸市场中有较高的口碑。
2.高技术投入。李某十分重视引进新技术来抵御风险,增加市场收益。从刚开始种植蔬菜,他就积极学习一些高收益品种的种植技术,定期参加市里、区里的技术培训,与政府的农技服务人员长期保持联系,并在专家的指导下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模式用于实践。“猪—沼—菜”循环生态模式就是他在接受技术培训时受到启发而采用。一是种养结合,循环使用,降低了成本;二是提升了错季销售能力,降低了市场风险;三是形成了高附加值的品牌效应。这种循环农业中,一些质量较差及其销路不好的蔬菜等可以用来养猪,猪粪、蔬菜废渣等用来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做温室育苗养殖,沼渣作为有机肥料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沼气沼渣还有防虫效果,降低了对农药化肥的需求,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因而具有了较高的附加值。每年他节省肥、水、电支出2万多元,节省农药支出0.5万元,而且蔬菜上市期提前,产量和质量提高了15%左右。循环农业的模式,连年为他节支10万元以上。一般来说,他的菜一到批发市场就会被商家一抢而空,价格还比别人贵。即使遇到行情不好的时候,李某也有较强的抵御能力,蔬菜可以不用出售,直接作为猪饲料;猪肉价格较低时,用无法销售的蔬菜作为饲料,可以推迟销售时间,等到价格较好时再出售,增强了产品的错峰能力,高价售、低价藏。有些农产品上市供不应求,他就请教专家,提高产品的复种能力,以增加产量,延长产品的销售时间。
3.高资本投入。面向市场的定位和高技术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李某仅搭建148亩的设施大棚,总投入就超过300万元,其中政府补贴60万元。到现在,蔬菜基地和养殖场投入已有420万元。实际上,李某从2002年采用设施农业开始,就踏上了民间借贷之路,为了搭建竹架大棚从民间借款3 000元,利息5分,付利息2 200元。2004年建设猪场和沼气池时,民间贷款10万元,利息3分,付利息7万元。2006年扩大养猪规模时,还从民间贷款20万元,利息是3分。2010年李某将贷款还清,有了60万元的剩余资金,他又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23亩(每亩租金600元)。当年为了搭建33亩的钢架大棚又贷款18万元(总共花费45万元),民间借贷仅利息累积达到50万元。
除了民间借贷,还有大量的银行贷款,特别是从政府鼓励发展科技示范户和家庭农场以来,从2006年开始,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陆续贷到一点银行贷款。2011、2012、2013、2014分别通过承包经营权向银行贷款30万、40万、35万、35万元,获得全部贴息。截止目前,他从银行贷款160多万元,到2014年底为止,李某还有100万元左右的贷款尚未偿还。
4.大量雇工。伴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蔬菜等高附加值农作物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远远超出家庭投入能力的范围,两夫妻只能雇工进行生产,夫妻两人主要负责生产安排、监督管理、市场销售和技术指导等,很少直接参与生产过程。
雇佣的农业工人基本都是本村人,2014年,在总成本投入中,长工20人,每年每人工资是2.4万元;短工最多时有40多人,雇工工资每天60元。每年的雇工成本不断上升,占据了很大一块份额。再以2010年为例,李某用去年盈利的60万全部进行扩大生产,流转土地123亩(每亩租金600元),租金再加上种子、农药、化肥等其他流动成本57万元;长工18个,投入近42万元,短工投入21万元左右,当年投入雇工成本63万元;不计夫妻俩人的劳动收入及其固定资本的折旧费,雇工成本占据流动资本投入比重的52%左右;当年纯收入蔬菜33万元,猪15万元,流动资本利润率为41%。
李某的家庭农场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在利润的驱使下,其流转的土地倾向于突破人情边界,以支付流转费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他们并不担心扩大规模后劳动力不足所造成的生产不便,而是采取雇工的方式[20]。且雇工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这就具备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经营性质[21]。此外,从生产要素的投入看,李某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节约资本或是降低风险的保守态度去经营农业,而是不断通过对农业技术的学习和市场机会的敏锐把握,不断地加大对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比重,借贷在资本周转中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是有着较高现代生产要素投入、资金循环和雇工体系的微型企业式家庭农场。
三、企业式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总量上计算,李某的家庭收入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的,但实际上其边际效益是不稳定的、经营风险是成倍增加的。大部分企业式家庭农场由于在市场风险控制能力、经营管理能力、资金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很难像李某一样成功。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经营模式,让不少农民在盲目投资扩大以后,出现亏损。企业式家庭农场的运转面临一系列制约条件,只有少部分农场能够成功突围。
(一)企业式家庭农场发展的人力资本困境
小农一般倾向于保守,其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大都以维持家计和保持家庭内部的生产、消费平衡为准[22],很少有农户会有企业家般的扩张精神,纯粹为了生产和利润,而非消费目的,把全部收益,甚至是依赖借贷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一般小农缺乏这种类似于企业家的扩张精神,因此,村庄中能成为企业式家庭农场主的人比较少,一般都是由经济能人和村庄精英转化而来,他们不断地扩大规模,甚至是采取雇佣劳动,直到超出家庭劳动力直接管理的范围和资本投入的承受限度。
此外,企业式家庭农场在面向市场、集约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比一般农户要高。不仅要求农场主要有企业家般的精神和魄力,更需要经营能力,而不是盲目地扩大规模。其集约化的经营管理方式要求农场主能够根据市场来进行决策和转型,更集中合理地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策略,提高效率效益。李某在经营家庭农场的过程中,不管是“猪—沼—菜”模式还是钢架大棚的改进、新品种的引进,都是在探索市场和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生产模式的结果。其直接的经营管理和直销式的营销策略,也控制了层级管理的风险并降低了中间环节的成本。此外,做品牌农业、注册产品商标、提升产品附加值的营销策略,都让他保持了较高的收益状态,但这种经营能力和魄力是普通农民所不具备的。即使是村庄精英或经济能人,像李某这样成功的也很少,很多人在走向规模经营的道路上,以背负债务告终。例如同是省科技示范户的夏某(村主任),就在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后,背负债务,走向破产。20亩左右的规模,他可以控制和盈利,但达到一百多亩以后,采取雇工的企业式管理,就难以获利。像夏某这样的村庄能人盲目扩大规模后,走向失败的很多。
(二)企业式家庭农场的市场困境
受市场供需结构及其市场饱和的限制,决定了家庭农场盈利空间有限,只有少部分农场主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不像大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收益受市场供需结构影响显著。我国经济作物的市场结构总体上供大于求。以蔬菜市场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菜篮子工程”的推动下,我国蔬菜的总产量迅速提高。2002-2011年,蔬菜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19 000千公顷左右,而蔬菜总产量在60 000万吨上下浮动。目前,我国的蔬菜市场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23]。随着资本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大力推行,局部农产品呈现过剩状态。现在,人口只占世界19%的中国,集中了世界上80%的大棚,生产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中国生产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费了。除了蔬菜,50%以上的生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是中国生产的[24]。很多地方出现了菜贱果贱伤农的情况。与市场供过于求相对应的是市场供给信息的不对称,这导致市场波动性很强。不少地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一村一品,农民一哄而上更是加大了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此外,农业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鼓励资本下乡大规模经营,让农业收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农民能够分得的利益越来越少。
正因为市场结构性供给过剩,而依赖市场稀缺和高经济附加值的企业式家庭农场的生长空间才更加有限,在市场利润空间的压缩下,只有少部分生产管理、营销能力强的农场主才能在市场的淘汰赛中存活,大部分企业式家庭农场像夏某一样处于赔损状态。
(三)企业式家庭农场的制度困境
企业式家庭农场的发育需要土地流转市场、劳动力市场、农机市场和农技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不断成熟。从土地流转市场来看,因为企业式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一般超出了自己熟人社会的范围,有的甚至是流动性的家庭农场[25],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出面解决土地流转的问题,租金高、租期不稳定是家庭农场面临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额外的交易成本,都增加了家庭农场的负担。从劳动力市场上说,农业较低的平均利润使家庭农场难以承担较高的雇工成本,农场主只愿意付较低的工资价格,而较低的工资价格无法解决农场优质劳动力稀缺的问题。从农技的供给状况上看,大部分家庭农场都无力解决现代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引进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创新型的家庭农场比较少,大都是跟风式学习他人较为成熟的技术和模式,这也将其带入市场慢慢饱和的困境。再就是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在治理农业的过程中,更多地出于对政绩的考虑,而非单纯的市场绩效[26];那些符合政策要求的、代表政府发展现代农业理念的家庭农场更容易获得扶持。国家及省市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政策规定在“千亩”以上,还有一些财政贴息贷款和农业政策保险都必须是省市示范型家庭农场才能获得,只有家庭农场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申请。许多家庭农场为了获得一些设施农业的项目补贴,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能力流转土地,从而最终导致经营失败。政策扶持环境的不利,难以真正有效地给予家庭农场正确的支持。
(四)企业式家庭农场的资金困境
对于企业式的家庭农场来说,资本投入在家庭农场的运转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资本投入和周转资金跟不上是很致命的。因此,良好的金融借贷环境对家庭农场的发展来说十分必要。家庭农场面临的金融环境的制约主要是指金融借贷能力的限制。一方面普通的农户不具备成长为企业式家庭农场的资金,缺乏预付资本和初始基金。农村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农民获得信贷资金特别困难, 中国2.4 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85% 左右的农民要获得贷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信贷来解决;另一方面,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愿意进入农村,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质群体,贷款回收的风险较高,成本也比较高,只种几亩地的2.4 亿个农户,要进入金融系统,确实让很多大银行感到成本很高[27]。
家庭农场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资本量(预付资本包括租金、农资、机械投入和部分雇工工资)和良好的“人力资本”(面向市场、经营能力,风险抵抗力等)[18]。此外,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环境。正是因为上述结构困境和外在条件的限制,在当下的环境中,家庭农场只能是作为个体突围性的存在。家庭农场的成功意味着农业的收益由少部分农户来获得,国家出钱出力来帮助这少部分农村精英成为现代化的农业主体。为此政府要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创造好制度环境,包括融资环境、税收优惠、土地流转市场、农业公共品供给的倾斜以及大量政策补贴。帮助精英成为更强的精英,让其成为现代农业和新型农民的示范。
四、企业式家庭农场发展的误区
企业式家庭农场的成功运营似乎化解了“三农”问题的困境,满足了当下政府和学界对家庭农场的全部想象。职业化的农民、专业化的生产和规模化的经营,既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这种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不易普及。家庭农场的繁荣具有虚假性,留守在农村的2.4亿农民,只有少数能够像李某这样在稀缺性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和较高的经营收益。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探索,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大都市的郊区,外在环境和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适当提倡,少部分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努力发展为效益较好的家庭农场。但政府不能因此就过度提倡。一方面,家庭农场存在结构性问题,发展空间有限,大量补贴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28];另一方面“三农”问题并非单纯的现代化问题,从政治、社会影响上看,在大部分农民无法离开农业、转移为市民的条件下,农业作为保障而非发展用途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大力扶持家庭农场实际上是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帮助大户打败小农[29]。扶持“精英农户”,边缘化小农;同时也挤压了那些以自身劳动力投入为主的“中农”的生存空间和非雇佣劳动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的发展。而不管是作为农村社会稳定器的留守老人农业[30],还是作为农村中坚力量的中农[31],还是具有发展意义的小规模家庭农场[9],依然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效益和政治社会意义的保障功能。
因此,政府在提倡发展家庭农场时,也要把规模控制在家庭劳动力投入为主的范围内,防止雇工式的家庭农场,尽量实现农业产值的平均化,尤其是高值农作物的家庭农场,其资本和雇工式的经营方式,已经超出普通农户的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范围,过度鼓励其发展,只会让农民去冒险创业,导致农业经营失败的几率更大。
五、结语
中国现代农业的局面不应是家庭农场一支独秀,而应是小农、中农和企业式家庭农场多元共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企业式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实现方式的一种尝试可以获得适当扶持,但不能因少数典型个案的成功而忽略了广大小农的利益。通过技能培训和社会化服务推进小农经济的改造,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也许更加符合国家和农业的长远发展。
致谢:本文写作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与魏程琳、王海娟、杜鹏、杜娇的集体调查,张建雷、韩庆龄博士对本文提出了修改建议,特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EB/OL].[2013-01-31].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1/31/c_124307774.htm.
[2]于洋.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反思[J].农业经济,2003(12):15-17.
[3]罗伊·普罗斯特曼,李平,蒂姆·汉斯达德.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政策适当吗?[J].中国农村观察,1996(6):17-29.
[4]张晓山.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8):28-33.
[5]许经勇.论农业企业规模经营[J].农业技术经济,1986(10):13-16.
[6]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7]蒋辉.苏南地区进一步发展家庭农场的探讨[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
[8]关付新.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制度含义与组织形式[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3):47-51.
[9]张敬瑞.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最适合的组织形式[J].乡镇经济,2003(9):18-19.
[10]曾福生.中国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创新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11(10):4-10.
[11]刘启明.家庭农场内涵的演变与政策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7-94.
[12]胡筱亭.家庭农场发展与金融支持策略研究——以上海松江家庭农场为例[J].农村金融研究,2013(12):22-29.
[13]任亚军,施勇.家庭农场发展与金融支持——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J].金融纵横,2013(6):75-79.
[14]施国庆,伊庆山.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2):135-139.
[15]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 2014(2)::176-194.
[16]贺雪峰.重新认识小农经济[EB/OL].[2014-07-17].http://www.guancha.cn/he-xue-feng/2014_07_17_242295.shtml?XGYD.
[17]黄宗智.中国新时代的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J].中国乡村研究,2010(8):11-30.
[18]桂华.中国农业生产现状及其发展选择[J].中国市场,2011(8):18-22.
[19]张建雷.社会生成与国家介入:家庭农场产生机制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4(10):16-27.
[20]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3(4):137-156.
[21]王立新.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5):189-208.
[22]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2.
[23]我国蔬菜供给数量趋于饱和,产品质量有待提高[EB/OL].[2013-09-05].http://market.chinabaogao.com/nonglinmuyu/0951642962013.html.
[24]温铁军.资本过剩与农业污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6):64-67.
[25]余练,刘洋.流动性家庭农场:中国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9-13.
[26]龚为纲.农业治理转型——基于一个全国产粮大县财政奖补政策实践的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9-30.
[27]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4(1):4-9.
[28]孙新华.农业经营主体:类型比较与路径选择——以全员生产效率为中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59-66.
[29]贺雪峰.政府不应支持大户去打败小户[EB/OL].[2013-05-17].http://news.wugu.com.cn/article/20130517/52525.html.
[30]贺雪峰.土地问题的事实与认识[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19.
[31]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开放时代,2012(3):71-87.
[32]黄宗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J].开放时代,2012(3):10-30.
The 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AO Wan-qin1 ,2CAI Shan-tong3
(1.Department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4;
2.ResearchCenterofChinaRuralGovernance,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
3.InstituteofElderlyServicesandManagement,TianfuCollegeof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0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ing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s the goal, 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s have emerged under the policy and market driven. It was held up as a typical model, because the mode of operating family farms contains high technical elements of capital, professional scale, intensive produc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ial risk-averse way. It almost satisfies the government’s expectations for modern agriculture. However, because of higher risk and require great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is can only be a select of few elite farmers, while most small farmers can not go this road.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n not merely relies on enterpreneurial family farms, it needs to achiev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multi-mode of operation, and small and middle farmers are still important.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 high value crops; capital and labor-intensive; scale operation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6-0074-07
中图分类号:F306.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高万芹(1987-),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4T70706)
收稿日期:(20)2015-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