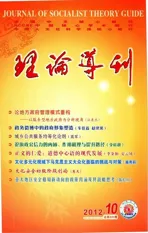“诗缘情”及其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关系二题
2012-12-22翟源
翟源
(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西安710061)
“诗缘情”及其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关系二题
翟源
(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西安710061)
《文赋》提出的“诗缘情”是中国文论审美性观念之滥觞,当代文艺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遥遥呼应的正是中国文论的“诗缘情”一脉。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序列中进行审视,发现“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及其论争是主流文论思想与“反质”文论思想的又一次博弈而已。
文学审美;“诗缘情”;“日常生活审美化”;关系
随着教育的普及、大众媒介的勃兴、大众文化的繁荣,“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不断被学界关注。但对此问题的讨论多着眼于西方理论和当代人生活情境的影响,而忽略了产生该问题的中国土壤。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中国理论资源可以上溯至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观念。
(一)
正如L.A·理查兹所说:诗歌是“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1]174不论在多么专制的社会,不论对文学的限制有多么严格,不论主导性意识形态如何为诗歌定位,诗歌仍然是表达个人内心情感的最直接的文学文体。因为诗歌打动人心的力量并不在于思想的深刻和理论的精辟,而在于它的情感感染力和审美感染力。政治功能上的规约即便扼制了诗歌审美特性的发挥和情感表达的自在需求,但并不能完全泯灭诗歌与生俱来的这种抒情功能。对中国文学而言,“诗缘情”是与“诗言志”相伴相生的审美性文学观念,其拓展出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审美空间。如果说,“诗言志”是以社会性、群体性的善为核心的事功性文学观念,那么,以“诗缘情”为滥觞的审美性文学观念是以个体心性、自我表白及自我呈示为文学写作的创作理念和根本目的,及至疏离社会事务,高蹈于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或形而下的个体欲望的满足,包括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对文学性技巧的探索、文学非意识形态的表现、肯定文学的娱乐功能等。可以说,“诗缘情”观念促使文学的审美手段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以“诗缘情”而闻名的《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论文,它是特定的文学发展和历史的产物,是不同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崭新文学观念的代表作。陆机在《文赋》中高度概括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而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说。
“诗缘情而绮靡”的源头当属屈原,屈原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抒情文论。在屈原的倡导下,楚辞的产生可算是“诗缘情”的一个充分的例证。楚辞大量使用口语方音以及“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使文章的整体呈现出一种“绮靡”之风。但是“发愤以抒情”的文论观并未持久。到了汉代,经学兴盛,许多人又开始逐渐转向文学的使用论,屈原的“抒情”理论被汉代的文论批评家们逐渐扼杀。直到建安时代,由曹氏父子提倡和实践,文学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文学创作冲破了必须为“法度所正,经义所载”和“依五经以立义”的桎梏,进入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的诗歌创作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赋由汉代铺排张扬的大赋转而发展成为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散文则自由通脱,或抒情,或议论,都朝着抒情化、个性化、形式优美的方向发展。曹丕《典论·论文》指出,这一时期“文以气为主”,“辞赋欲丽”。建安文学之后,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已经明确地为人们所认识。具有浓厚美学意义的文学创作论——陆机的《文赋》,便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
《文赋》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彻底冲破了儒家传统文学观念对文学创作的藩篱,树立起“抒情化、个性化”的艺术旗帜,不仅集前人对诗歌本质的“吟咏情性”理论探索之大成,还对后世经钟嵘、孔颖达、白居易、叶燮、王夫之诸家而最后形成的“文质并举、感物吟志、情景交融”、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缘情而绮靡”说又是在对文学运动规律和趋势高度把握和总结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诗歌审美思想。文学创作是为了抒发这种因具体事物感动而产生的感情,那么,整个的创作过程当然必须以“缘情”为宗旨,以文辞绮靡华艳等艺术形式美为方法,《文赋》强调诗歌创作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即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要尚巧贵妍,绮靡清丽,注重音声之美。这正是魏晋以来诗歌创作上的新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审美观念由此成为可能。
与“诗缘情”观念相通的,还有一些说法,如《宋书》卷六九《范晔传》载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的说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总结建安文学特征时提出“以情纬文”的观点。以“情”论文也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最基本特色之一,全书涉及“情”处即使除去《序志》篇外,尚有三十九篇,占全书篇目近八成。特别是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非广义的、杂文学的)篇章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到了。《文心雕龙·情采》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还把文学创作看做是“情变所孕”(《文心雕龙·神思》)的产物。《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云:“体物缘情,则寂寞于世。”将缘情体物当作批评北朝诗歌创作零落的标准。这些观点和理论,都与陆机的缘情说一脉相通。
但是,将“诗缘情”过度发挥而导致弊端常被诟病。最典型的莫过于梁简文帝萧纲鼓吹文学高于一切,提倡放荡的郑邦文学与宫体诗,反对道德、事功,一时“且变朝野”,致南朝文风走入堕落的色情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历史上不乏将“诗缘情”视为六朝形式主义文风之罪魁的文论家。如沈德潜《古诗源》指责其“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批评说:“……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实际上,在文学本体已经足够自觉的今天看来,恰恰是陆机的缘情说补充了言志说的不足,为文学自觉自律提供了理论指导,丰富了、深化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趣味。
“诗缘情”观念中,对后世具有积极影响的主要是“情”的解放,而此“情”既不是“圣人之情”,也不是“诗言志”之“志”,而是个体之情。魏晋清谈关于“有情无情”的争论中谈及“圣人之情”:“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以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不累于物也。今以其无累,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魏志·钟会传注》)尽管有圣人之情与常人之情的区别,但情在根本上已经被肯定了。即使是持圣人无情论的人,也并不是让自己努力除去情感而趋向圣人,而是与圣人划清界限而更充分地肯定个体之情。
“诗缘情”的“情”也不是天之意志的涵义、社会性强烈的“志”。《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更侧重于诗歌创作的普遍心理过程,而“诗缘情”则侧重于个体的情感,侧重于诗歌应该表达什么、诗歌来源于什么、诗歌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特点等诗歌本质论。正是在对个体之情的突出上,尽管有《毛诗序》的“情志合一”论,我们毋宁说“诗言志”与“诗缘情”确是两类不同的诗学观。
“诗缘情”对个体之情的肯定,老子、庄子、列子的理论等均是其渊薮。中国思想史上,儒道都将人的生命作为本体,然而在人生何者为本的问题上,却存在巨大分歧。儒家人之为人在于他的仁义道德,所谓“人者,仁也”,即存在于人和他人的关系中。老庄则认为人之为人在于其自由无待的逍遥境界,是放弃当下、超离现实的至美人生。尤其是庄子,他第一次突出了个体存在,个体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是庄子思想的实质。[2]171老庄哲学发展到魏晋玄学是“贵无”:“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3]317后来的禅宗将个体修养的注意力完全转向心灵自身,严格说来,连自性都是空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哲学将此前贵“无”的玄学中与人心灵的远离作了重新解释,将般若视为自我与心灵的觉悟,而般若的求得就在自己,即人人都能成佛,将佛学引向顿悟与自证的方向。六祖慧能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他将传统佛学中的最高范畴之一般若真性还给普通人生,将其心灵化,并且将心灵与自尊自强结合起来,破除了外在精神权威对于心灵的主宰,认为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吃饭、走路,还是担水、砍柴,通过刹那间的内心觉悟(“顿悟”),都可以体验到那永恒的宇宙本体。这意味着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可以直接呈现宇宙的本体,在形而下的东西中可以直接呈现形而上的东西。这一切都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肥沃的中国土壤。
源自这一条思想脉络的各家哲学思想,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人那里发展为两种极端的模式:一是虚无缥缈的玄言思辨;一是“道成肉身”,见物见性。这两种极端的模式都远离现实的社会化生活,向内转,向个体心灵深处开掘。对个体心灵的关注一方面发展了抽象的富有逻辑的玄理寻绎,一方面以顿悟见佛的思维方式提升了与个体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哲学价值,并赋予其绝对价值,所谓“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古尊宿语录》卷二)。这样,主“情”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可以是玄淡超脱的哲学,一方面却又可以发展出浓郁的烟火气息,对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津津乐道。对表现世俗的文学的品鉴也因此因人见性:“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坛经·行由品》)是也。
(二)
日常生活至少关乎两大内容,一是自然之界,二是身体之域。从对自然的模仿到对自然本身的赞美,再发展到对自然身体即诉诸感官的形式美的肯定,屈原第一个做出了尝试。与孔子将形式美附庸于内容善不同,屈原对自然之美自觉承认,高度肯定其价值,并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予以实践,强烈地加以表现。屈原对音乐舞蹈、服饰、建筑居室、自然形体等许多自然的、形式的美都尽情展现,他认为形式美具有独立价值,外在的、形式的美不但不依赖内在的、内容的善而存在,而且它更是善的必然的、唯一的表现形式。“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楚辞·九歌·东皇太一》)这是音乐舞蹈的美。“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来。”这是服饰的美。“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楚辞·九歌·湘夫人》)这是建筑居室的美。“溺溺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这是山川的美。“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楚辞·九歌·山鬼》)这是人的自然形体的美。所有这些动人心旌,能给人以高度审美愉悦的形式上的美都不是从任何伦理道德的判断出发,不依赖任何伦理的“善”,自然风光、形式美与人体修饰等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假如说,诗词对日常生活的表现更依赖于对其形式美的表现,小说则更充分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的世俗、欲望之美。成于明代的奇书《金瓶梅》是表现世俗生活、财色欲望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与以往长篇小说大多关注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扩大了叙事窗口,将笔触下移到了市井生活和私人领域”。[4]276沟口雄三认为,晚明时期,对“欲”的肯定和“私”的主张,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根本的变化。[5]27这一本乎“人欲自然”的坐标转换,尽管就理论的层面而言,只是开辟了一条“欲”进入“理”中的道路,而“欲”本身“并没有获得自立的基盘,毋宁说是由于为理所包含,人欲才获得存在的保证”,但“由于欲被纳入理中,于是逐渐渗透到理的内部,终于使理的内容发生实质的变革。”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消除了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张力关系。既然灵魂与身体并不冲突,还原性敞开地描写“身体”就是自然的了。《金瓶梅》中的身体被还原到“穿衣吃饭”的切“身”需求和“欲望”的自然本性上。
从当时王阳明心学对“无”的开显(“无善无恶心之体”),其高弟王龙溪对“无”的进一步立义(“无者,圣学之宗也”),再到李贽对“童心”的凸显、对“真空”的开启,其中贯穿的就是沿老庄到玄学到禅宗的哲学思想。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理”被奠基于人的“身体”的自然需求之上。随着身体的解域,历来遭到拒斥的“色欲之情”遂被视为一种“造化工巧生生不已”的“真机”,即邓豁渠所谓的:“色欲,性也,见境不能不动,既动不能不为。羞而不敢言,畏而不敢为者,皆不见性。”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叙事基质恰恰也是日常生活。从新写实小说对“烦恼人生”的日常状态的“零度还原”开始,到新生代作家大力铺叙日常生活中人的物欲、性欲,再夹杂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以稗史、民间视角的戏说等,日常生活成为90年代小说的内在主题话语。如《一地鸡毛》《渴望激情》《私人生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像卫慧那样疯狂》等,都是日常生活叙事的代表作。在这种文本创作语境下,文论界、美学界掀起“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热潮自然而然。
常见的理论追溯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是由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一次题为“大众文化协会大会”的讲演中明确提出,他把这视为当代西方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并将那些风格杂糅的后现代式建筑、追逐时尚、玩弄风格的生活方式都统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6]1-9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意味着人们从表层的形象之流的紧张体验中获得审美满足。中国当代学者于是也很快发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景观:“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审美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更遑论什么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了。”[7]在这种审美革命中,一切日常生活都可以被审美化。街心公园、度假胜地、居民小区等被审美化,对身体的修饰以及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则成为中国当代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另一大景观:美容护肤、减肥健身、服装、模特、卫生用品、保健用品等与人的外在形体有关的一切事物中,美丽的身体形象充斥其中,“身体工业”日渐走俏。
如何看待这种从文本到生活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当代文论界争论很激烈。2003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与《文艺研究》编辑部曾联合发起召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第1期《文艺研究》在此次会议的基础上,以“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为题整理发表了陶东风、陈晓明、曹卫东、高小康四人的文章,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到了学科范式的高度。其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性的重建》一文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文艺学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从而挑战了文学自律性的观点,导致1980年代所建立的文艺学范式面临深刻的危机,当前的任务是重建文艺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倡导新的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式。在2003年12月暨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童庆炳则主张以文学艺术中审美的诗性精神对抗提倡生活中“低级趣味的欲望美学”。[8]在后来一系列的讨论中,“价值立场”成为焦点,童庆炳批评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研究是“二环路以内的美学”、“食利者的美学”,回应者则指出,应该持学术上重视,审美上宽容,政治上反思的立场。
可以看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质疑的学者其理论资源主要源于1980年代以来文艺学所确立的主流话语立场,即主张在学科自主性的基础上创立和使用自身关于审美和文学性的话语体系,这种文学审美观要在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张力中建构起审美的自律性。这种文艺学在审美自律中似乎远离了社会生活,但实际上它以一种本质论的、普遍性的学科自主性诉求使一种具有范式性的普遍的审美观成为绝对观念,从而介入生活,塑造并提升整体人格。[9]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诞生于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语境中,追求绝对、形而上学,有自我封闭之弊。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文艺学领域的一股思潮,表面上看起来是直接横向移植西方后现代理论资源,实则深层原因在于,处于主流地位的本质主义文论的弊病在中国也已经暴露了出来,文学创作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早于理论界十年就是证明之一。“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学创作以极度的敏感早早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创作了大量有意味的作品;文论界被社会文化领域对消费文化的讨论卷入,由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扩展为文化研究(也称“文艺学的文化转向”)。
然而传统文化史范式的主要特征首先是“历史化”原则,文本、艺术作品、文化现象应该被纳入到某个特定的历史序列中来考辨其功过,这是一种整合人类生活历史的模式。因此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除了从上述特殊语境和哲学层面上思考外,尤其需要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序列中进行审视,才能够真正明了其在中国的运行轨迹。这样,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内容和讨论本身都遥遥接应了中国文论中的“诗缘情”一脉。与古代对“诗缘情”的诘难一样,由于个体情感、财色等“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的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为‘欲望制码……乃是社会的要务'。”[10]111-112崇尚秩序对于群体生活重要性的理论家,当然会要求以社会性的“志”、“礼”来节制个体性的“情”、“欲”。所以,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其更为隐蔽的面孔也许只是古代主流文论思想与“反质”①文论思想的又一次博弈而已。
注释:
①敏泽《中国文学思想史》第三章将非儒家的道、墨、法等诸家均视为“中国文学思想之反质”。
[1][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陶东风.新文化媒介人批判[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6).
[8]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J].暨南大学学报,2004,(2).
[9]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J].文艺研究,2005,(4).
[10][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黎峰]
I 206
A
1002-7408(2012)010-0104-03
翟源(1980-),女,陕西扶风人,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及美学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