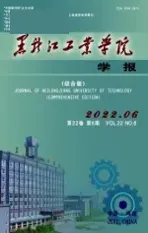浅析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叙事人称和时空机制
2012-08-15李昕
李昕
浅析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叙事人称和时空机制
李昕
鲁迅的《伤逝》是很具独特性的小说,文中运用内心独白式的叙述,看似是第一人称叙述,实则并非如此,同时不仅有独特的时间感还有灵活的空间机制,恰到好处地引起读者反思共鸣的同时展现了鲁迅小说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独特魅力。
叙事人称;时间机制;空间机制
《伤逝》作为鲁迅先生唯一的爱情小说,自从1925年诞生以来,随着叙事学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渐成显学,运用叙事学方法来研究《伤逝》的研究者和论文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叙事策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之一,那么本文就试图在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三个策略方面进行分析,挖掘此篇手记体小说的特色。本文作者将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放置到“五四”退潮后依然浓重的封建黑暗背景中,透过他们的悲剧命运寓示人们要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引领青年去寻求“新的生路”。
一 《伤逝》中的叙事人称
对于《伤逝》的叙述者历来颇有争议,没有叙述者的小说是不存在,因为小说不可能自我讲述。“无叙述者的叙事,无陈述行为的陈述纯属幻想”,[1]“叙述者是任何小说、任何叙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2]毋庸置疑,《伤逝》也有自己的叙述者,一种认为《伤逝》的叙述者即主人公涓生,另一种认为小说采用的是缺席叙述者,涓生只是聚焦者。从故事世界来看,作品很明显的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故事的“我”就是涓生,涓生同时也是作品所叙故事的男主人公。虽然这种观点占绝对优势,但是仍有些痕迹或多或少地透露出隐含作者的叙事秘密。
题目作为小说文本的完整组成部分,与小说内容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常暗示透露作者对所叙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此篇小说有正副标题,钱谷融曾注意到《伤逝》题名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人对妻子的悼念习惯上称为‘悼亡’,对朋辈才用伤逝。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但没有取得妻子的名分,那个社会并不承认他是涓生的妻子。”[3]传统社会固然不会承认子君是涓生名正言顺的妻子,然而涓生自己却不能不承认子君是他名副其实的妻,一个“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4]崇尚五四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敢于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典型代表,他断然是不会站在传统社会价值立场以朋友身份伤子君之逝,与其异口同声吧!倘若如此,涓生又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子君,又有何脸面开门见山地声称“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4]所以选定“伤逝”作为题名,这似乎也在暗示涓生并不是一个可靠叙述者。
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个副标题——“涓生的手记”,如果我们站在故事世界认定涓生是小说叙述者,那么标题的异故事叙述者角度就与涓生的同故事叙述者角度相互矛盾。涓生会给自己的手记命名为“涓生的手记”吗?当然不会,这明显是一个站在旁观者角度看故事的叙述者所命的标题。因为手记跟日记一样的私人化,那么自设的隐含读者就是作者自己,用不着这样多余的标题来点明是一个叫“涓生”的人写下的手记。所以更多的可能性是发现涓生手记并给它加上这样标题的叙述者所为,只是在故事世界中缺席,成为幕后操纵者。从标题看,此小说的预设读者群应是除了涓生外的所有人,这样大大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域,让读者思考进而明确作者的创作目的。
二 《伤逝》中的时间机制
“小说家对叙事的文本机制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有效利用上。”[5]鲁迅在写《伤逝》时对时间机制的有效利用体现在对叙述节奏的把握上。叙事节奏往往由叙事时长和叙事频率两个因素决定。掌握好叙事速度对小说叙事节奏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关系。
1.叙事时长。
“没有任何一个述本能完全尊重底本的事件所固有的时间范畴。”“因为叙述文本不像口头叙述那样是一个时间中的存在,它只有以转换成空间形式(书写或印刷的篇幅)的抽象时间。”“因此,我们所说的叙述时间,是表现在述本篇幅上的事件的相对比例和相对位置,这些相对的比例和位置与底本事件的实际所占时间与严格先后顺序有很大差别,这差别就是时间变形。”[6]这样把叙事的节奏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速度:即省略、概要、场景、停顿、减缓。①米克·巴尔说:“节奏分析可以从对素材的时间过程作一个鸟瞰作为开始。”[7]在小说《伤逝》叙述者回忆故事当中,叙述者虽然在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叙事,但在叙述过程中交替使用了概要、停顿两种方法,及一处明显省略来控制叙事的节奏。
概要,依据热奈特的提法,即叙事伪时间TR小于故事时间TH,②就是说不写言行的细节,用几段或几页叙述好几天、好几个月或好几年的生活。在《伤逝》中,概要的比重远远大过于场景,其中涓生向子君表白,与子君同居,子君与官太太的暗斗,涓生被局里辞退等都以陈述式的叙事模式交代清楚,即便是有回忆起子君的话,也只是一两句,无法形成对话场景,这也是回忆录式小说的特色,也让读者在这样情境之中一同追忆。
停顿,是叙事的伪时间TR趋于无限,而故事时间TH等于零,这就使叙事时间无限长于故事时间。《伤逝》中作者主要是通过环境描写、叙述者干预以达到停顿所具有的这种效果的。文中有些场面描写在时间流程上构成停顿效果: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4]
这段描写是涓生在图书馆取暖的遐想,叙述者表明自己所处的方位却没有点明小说中的任何人物,也没有叙述要发生的事件,故事时间静止了,而叙述者叙述却并未停止,造成极度慢速效果。
除此外,叙述者干预也能造成叙事节奏的停止,文中多次运用叙述者干预在客观上引起叙事的停顿,如文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段经典:
“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4]
这一段的插入不仅停顿了叙述,同时也表明了叙述者的价值观,渗透了鲁迅先生对五四时期因妇女解放而女性大量从父家出走,寻求婚姻自主的深刻思考及其态度立场。
省略,与停顿恰恰相反,叙事伪时间TR为零,而故事时间趋于无限。《伤逝》中的省略属暗含省略,“即文本中没有声明其存在、读者只能通过某个空白或叙述中断推论出来的省略。”[1]文中从涓生讲出了实情到子君终于被父亲领走,整整经历了冬天最难熬的时光,既是自然界最寒冷的季节,也是子君生命中最严酷的冬天,但是子君究竟在寒冷的小屋中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冬季”,没有人知道,因为涓生中断了对子君的关注和记忆,这种缄默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从严冬到初春的漫长日子里,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也成了涓生记忆中的一个缺失,这或许是一个有意的缺失。子君就这样独自负着空虚的重担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成为一个觉醒时代的献祭。
2.叙事频率。
“叙事频率是指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简言之重复关系”[1]分为话语重复和事件重复。在小说《伤逝》中,主要是话语重复,像“寂静”“空虚”这两个词在文中出现的频率都比较高,“寂静”出现了九次,“空虚”出现了十八次。作者借助这两个词的话语重复,来抒写哀怨的沉重笔调,直烙人心。另外,在对会馆环境和陈设描写时也用了话语重复:
“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4]
用“依然”一词意味重复,一年后,屋子还是那间屋子,环境还是那个环境,陈设还是那些陈设,可是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子君已经不在了。由物及人,烘托一种空虚的心境。
其次,是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当一个事件仅仅发生一次而被多次描述时,我们称之为重复。”[7]《伤逝》中涓生向子君表白的一幕,而后常常被子君温习,叙述者也不断提及子君这样的一种状态,由开始的“每日相对温习”到“稀疏”再到“往事温习和新的考验”,子君不厌其烦地重温,是对这份爱情不灭的期待,而涓生早已在同居后一两个月便不记得情节了,反复被提及,只能越来越明显地看出俩人对这份感情态度的悬殊,预示着没有结果的未来。
三 《伤逝》中的空间机制
除了时间关联,叙述中的时间也有一定的空间关系,“事件在空间中的延续关系组成了情节中事件的空间链。”[6]
1.故事投影。
《伤逝》叙事中的空间性首先表现在故事层面的投影上,故事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可被分为大小空间,那么大空间主要是当时的时代及社会背景,《伤逝》创作的年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爱情至上成为了许多人的自觉态度,许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也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反映的对象。易卜生的剧本《娜拉》(《玩偶之家》)受到当时青年学生的追捧,女学生都以娜拉为偶像,支持“离家出走”。针对这种思潮,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为《娜拉走后怎样》,其中阐述了经济平等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指出没有经济后盾的娜拉在出走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回来。那么折射回小空间便是子君与涓生同居的吉兆胡同,那样追求婚爱自主的大潮流同样也感染到了子君与涓生,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如此的呼应“我首先是一个人,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的娜拉,但没有物质基石最终仍是熬不过生活的艰辛,子君跟父亲回去了,这是两条出路中较好的一个。吉兆胡同并未带来吉兆,先是丢了工作,后是丢了感情。伤逝更是一种对爱的忏悔吧,是对盲目追随爱情的男男女女别具匠心的警钟。
2.语言层面的空间构成。
“在小说中,语言所指被能指化了,所言非所指。这样在一个句子的表面涵义和实际涵义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空间。”[8]这在《伤逝》中也不难被发现,鲁迅对暗示和象征等修辞格的运用形成了语言文体空间。例如:在子君走后,涓生回到屋子只见:
“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4]
这些剩下的全幅生活材料维持较久的生活,显然是无以为继的。看似描写房间一角实则暗示之前以及之后的生活的艰难。
在入冬后,涓生常常在图书馆取暖,有“不死不活的煤的火”“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几乎是没有的。”[4]这图书馆象征着封建传统,虽然还有些喘息,但已无任何更新,迟早是会燃尽的,涓生就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退后一步虽有余温但是作为受过五四文化熏染的年轻知识分子,已无法接纳这些“陈腐”,向前一步却找不到出路,寒冰刺骨。为整个小说营造出一种缺乏活力,苍白的叙事氛围,和主人公欲渐冷漠的心态。帮助读者在阅读时形成一种情绪空间,以便更好地进入故事空间。有相同效应的还有阿随归来场面,阿随更像是对待生活的信念,曾在生活困难之际被丢弃过,却死里逃生的回到涓生面前,鼓舞着他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鲁迅先生对于故事层面的精心编排,使女性解放离家出走的哀伤浓缩在涓生和子君身上,在语言层面的独到安排,使读者可以多角度阅读,多向度介入。
四 结语
《伤逝》对叙事手段的合理运用,使得关于个性解放的小说命题,便因此次出色的艺术操作而成了一个近百年的文学命题,也传达出作者对于“第一,便是生活”价值观的中肯,鲁迅在对生活切实了解的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他的怀疑、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的怀疑、对那个时代的怀疑。通过对这部小说叙事手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鲁迅小说的复杂性与高超的艺术性。可以说,《伤逝》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恰到好处,把叙事手法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读者挖掘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之外,又加深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注 释
①其中省略、概略、场景、停顿是热奈特提出的,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59-72页,而减缓则是由美国学者查特曼在热奈特的四个术语的基础上提出的。见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M].Ithaca: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78.第72-73页.米克·巴尔在其《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用“减缓”这一术语,意思与查特曼相仿。见该书中译本,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25页。
②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用公式来概括停顿这一运动的时间价值:即停顿:TR=n,TH=0。故:TR∞ >TH,其中TH指故事时间,TR指叙事的伪时间或约定时间。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59-60页。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51,69,73.
[2]赵毅衡.苦难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
[3]钱谷融.谈《伤逝》[J].鲁迅研究月刊,1991(6).
[4]张弘.鲁迅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99,198,207,198,210,206.
[5]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47。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90-91,194.
[7]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8,132.
[8]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6-267.
[9]吴中杰.鲁迅的艺术世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0]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唐毅.重温《伤逝》——兼论鲁迅小说文本的艺术张力[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9).
[12]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Analysis of Narrative Person and Time and Space Arrangement in Novel Regret for the Past Writen by LuXun
LiXin
Regret for the Past,a novel written by LuXun who is a famous writer in China,is regarded as a novel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The narration approach adopted by LuXun in this novel is interior narration and to which the person used is the first person,b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rst person get people feel something flexible in time and space arrangement.It is the flexible time and space arrangement illustrated the complexity and the unique charm of LuXun’s novel which can arouse the sympathetic response and reflection of readers.
narrative person;time arrangement;space arrangement
I210.6
A
1672-6758(2012)05-0111-3
李昕,在读硕士,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新疆·乌鲁木齐。邮政编码:830046
Class No.:I210.6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