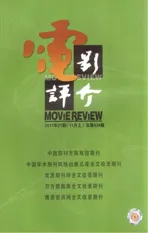歌颂生命 超越死亡——浅析劳伦斯诗歌《灵船》
2011-11-16周维贵
一、 引言
纵观劳伦斯一生的创作,生与死的母题是其文学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劳伦斯在小说、诗歌、文论等领域对生死主题都有较深入的探索。然而,生与死的关系在其作品中并非恒定不变,因为“死亡”一词在劳伦斯作品中具有多元的意义。死亡可以表征为生的对立面,体现为异化力量对血性生命的践踏;也可以体现为一种彰显生命激情的高峰体验。(潘灵剑,140-141)劳伦斯对死亡的书写实际上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高扬对自然生命的赞颂。然而,真正体现出劳伦斯直面死亡、解构生死二元对立的作品应属其晚期创作的死亡诗歌。受结核困扰的劳伦斯在病床上写下了《灵船》及其他多首死亡诗歌。这些诗歌收于1932年劳伦斯去世后出版的诗集《最后的诗》中,该诗集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宗教、神话与死亡。基于诗集的主题,有评论家推测,其中一部分诗篇可能隶属于诗歌《灵船》,只不过劳伦斯未能完成这一任务。(Salgado,148)同时,由于劳伦斯的反复修改,读者熟悉的《灵船》即有两种版本。因此,要考查劳伦斯晚期对死亡的书写,需综合分析其晚期的多首死亡诗。
二、“灵船”意象溯源
意象既是传达诗意的手段之一,也是诗歌内在形式的重要体现。意象是作家通过审美思维创造出来,融会了主体意趣的形象,它能够在读者的审美体验过程中生成某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这种感受是把握诗意的重要渠道。对诗歌意象的强调在英美意象派的诗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象派诗人认为,“要传达瞬时性的印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一个主导性的意象。”(常耀信,220)劳伦斯的许多优秀诗歌也是成功运用意象的典范,如劳伦斯创作中期的诗集《鸟•兽•花》。正因为劳伦斯在运用诗歌意象上的独到之处,他早期的一些诗歌曾被洛威尔(Amy Lowell)收入意象主义诗集中。庞德(Ezra Pound)虽然认为劳伦斯是一个“可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劳伦斯在他之前发现了“对现代题材的恰当处理方法。”(Bell,179)劳伦斯《灵船》一诗的中心意象是灵船(Ship of Death)。这一意象承载了劳伦斯对死亡的哲学思考,是解读全诗的关键所在。
灵船的意象首先取自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圣经中上帝对人类的罪行深恶痛绝,准备用大洪水涤清罪恶。但是,正直的诺亚得到了上帝的指示,预先建造了一艘方舟,并带领家人及选中的各种生物躲入方舟,最终逃过了大洪水。因而,诺亚方舟是保存生命、获得新生的工具。和诺亚方舟一样,劳伦斯的灵船也承载着延续生命的重要作用。同时,劳伦斯在诗歌中直接引用了“方舟”的典故,“哦,造起你的灵船,造起你的避难方舟,装上食物,装上蛋糕和甜酒,为了通往湮灭的黑暗的航行。”这和圣经中上帝对诺亚的指示如出一辙。劳伦斯对死亡洪水的描述也出自圣经中大洪水这一典故。因此,劳伦斯对灵船的书写离不开圣经文本的影响。
灵船的意象还源自劳伦斯在伊特拉斯坎墓地见到的一艘青铜小船。1927年劳伦斯与朋友到古代伊特拉斯坎人居住的地区旅游,该地的古坟墓等古迹极大地激起了劳伦斯的兴趣。在实地探索墓地遗迹时,劳伦斯喜欢上了伊特拉斯坎人,认为“他们既是‘蒙昧’的,又是开化的。他们没有虚假的文学文化,有着生殖的意识,懂得‘事物永久的奇迹’。”(穆尔,578)这种“生殖意识”是劳伦斯所宣扬的自然生命的重要因素,伊特拉斯坎人古老的思维方式激起了劳伦斯的哲学思考。在探索一处墓室时,劳伦斯发现了一艘青铜小船。小船与死者及死者的神圣财物一起躺在石床上,劳伦斯认为这艘青铜小船是将死者载向另一个世界的工具。《灵船》一诗所刻画的船的意象正体现了劳伦斯对伊特拉斯坎人的青铜小船的理解。
对于浸淫着西方文化的劳伦斯来说,他对灵船的书写直接来源于古代北欧人的葬礼仪式。船在北欧人的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北欧人的葬仪中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相信人死后船能将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死者要借助船才能够顺利进入死后的世界。因此,在古代北欧葬礼中,死者被合适地安放在一艘船里,然后才能进行土葬或者火葬。死者需得到合适的安葬,并得到与其社会地位和职业相符的祭品,才能够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安宁,并过上与此生一样的生活。否则,死者的灵魂只能无家可归,永远漂泊,甚至出没于亲人的家。即使贫困家庭无船可用,安葬时也须用石头摆成一艘船的形状。这种葬礼风俗给劳伦斯笔下的灵船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在劳伦斯的另一首诗《当心不幸的死者》中,死后不能乘船踏上旅途的灵魂出没于人世,人们应该摆放最好的食物奉献给这些亡魂。显而易见,劳伦斯对死亡的这些观点来自于北欧人的信仰。
劳伦斯诗中的“灵船”意象并非凭空想象而成,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结合劳伦斯晚年辗转漂泊于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现实,劳伦斯在晚年诗歌中对大海和船这类意象的迷恋也在情理之中。
三、书写死亡:过程与仪式
《灵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书写了劳伦斯对死亡的思考,或者对来世的期望。但劳伦斯并不相信有来世,在他看来,自然的死亡只不过是灵魂通向新生的一个过程。这是灵船一诗所包含的基本主题。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一题旨,劳伦斯将死亡的过程上溯到秋天,也即衰老的开始。自衰老开始,灵魂逐渐脱离旧的自我,经历漫无边际的死亡之洋,最终达到黎明的彼岸,形成一个环形结构。对死亡的这种观照充满了神秘而玄幻的色彩,劳伦斯借用一系列的意象将这一过程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出来。
诗歌开篇即以秋的肃杀来暗示衰老的荒凉图景。诗人用掉落的水果隐喻衰老的开始,苹果“撞破自己”则喻示老年的寒碜和伤痕累累。正如丝丝生气从苹果的伤口流逝,灵魂从百孔千疮的躯体向外渗漏,死亡的气息开始在躯体里积聚。叙述者以无可奈何的口吻敦促“造起你的灵船”,因为灵魂要依靠灵船才能泅渡死亡的海洋,这是“通向湮灭的最漫长的征途”。紧接着,劳伦斯以诗意的笔触构建了死亡的漫长过程。死亡最终不可阻挡地降临,灵魂在死亡的洪水面前战栗哆嗦。由于前文秋景的铺垫,这一痛苦的过程在他的笔下虽显急促却又超然。随后,灵魂驾着死亡之船,漂泊在死亡之洋上,这是漫长的湮灭(oblivion)。“湮灭”类似一种混沌状态,安宁平静而黑暗,漫无目的,毫无意识。黑暗的洪水、毁灭之海之类意象增强了死亡的可感性。劳伦斯经常用黑暗来描述无意识这块非理性的大陆,这是劳伦斯所谓的血液意识的深埋之地,而此诗中黑暗代表着意识的沉睡、自我的消解。灵魂与黑暗的海洋融为一体,没有方向,这是一种消解了主客二分的鸿蒙状态,直到漫长的湮灭结束。灵魂最终浮现于黎明的苍白细线。与死亡之海的黑暗不同,复活之后的灵魂由苍白转为玫瑰的粉红色,暗示着灵魂从迟钝的状态渐渐苏醒,继而融入平静而动感的生活中去。经历涅槃的灵魂不再带有走向死亡时的痛苦,而是受到湮灭之宁静的洗礼,“用宁静填满心房。”这是劳伦斯对新生的期望,也是劳伦斯对解脱的构想。诗人动荡漂泊一生,他的创作生涯颇多坎坷,为了自己的信念诗人也从没停止过战斗。而在面对死亡时,诗人却找到了一种欢乐的宁静。因此,死亡对于劳伦斯来说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新生的设想展示了诗人乐观面对死亡的信心。
劳伦斯《灵船》所书写的死亡纵然充满神秘的色彩,却奠基于作者对仪式的挪用。首先,灵船意象本就取材于葬仪。叙述者敦促死者造好灵船,同时要准备好食物、木浆及各种用品。然而,灵魂并不能掌舵,也没有港口,只能飘荡于茫茫黑海上。灵魂辞别了躯体,浪迹于漫长的湮灭之旅。劳伦斯选择“湮灭”一词,是为了突出灵魂的自在性,即灵魂已褪去了意识的牵绊,只处于一种原始而混沌的宁静。食物及各种用品不过是生者或将死之人对死亡之旅的寄托。因而,为死亡所做的这些准备只带有仪式性的意义。同时,整首诗以人之衰老开始,继之以死亡之洗礼,最后获得新生,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灵魂会沿着这个轨迹不断重复自己的旅程,这样一种环形表述在很多民族的祭祀仪式里都有体现,它是对自然节律和植物更替变化的模仿。《灵船》一诗的开篇即借用自然的衰落来影射人的衰老。掉落的水果、严霜等意象与千疮百孔的躯体相互映衬,而苹果的种子则像灵魂一样将确保生命的延续。
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描绘的未知世界,而劳伦斯以其神秘主义笔触书写着他对死亡的严肃思考。在劳伦斯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连续性的终结,而是通向新生的过程。劳伦斯从人类的一些仪式中汲取素材,将死亡描写得栩栩如生。然而,劳伦斯所认同的只是自然的死亡,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死亡。
四、 劳伦斯的死亡之思
死亡虽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却又玄妙而不可逆,这赐予了诗人极大的想象空间。诗人对死亡的思考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世界、对人生的基本观点。面对死亡,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情感体验,有对生的依恋、对死的恐惧,也有表现出平静而坦然的。劳伦斯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都有对死亡的探索,而晚期诗歌更是直接书写死亡。这些诗歌集中反映了劳伦斯晚年对死亡的哲学思考。
在劳伦斯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通向新生的过程。他在《灵船》及其它一些诗歌中都将死亡刻画成一段漫长的湮灭之旅。灵魂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宁静中,丝毫不受意识的干扰。这与劳伦斯的一贯哲学主张相吻合,他认为“无意识是原初的创造性力量,是生命的本质体现”(刘洪涛,47),而劳伦斯所崇尚的无意识并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里的无意识,而是“属于人的躯体活动,是每个有机体中自发的生命动机,它产生于大脑之外,是非脑力的。”(刘洪涛,47)诗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并没有随着肉体一起死亡,而是以其自发的生命本能漫游于彻底的黑暗之海,直到灵魂获得新生。灵魂在死后所处的这种完全的宁静令劳伦斯着迷,他甚至认为人完全处于沉睡状态也能获得这种宁静。对这样一种无意识存在的向往使得劳伦斯对死亡高唱赞歌,正如他在《死亡之歌》一诗中所说,“没有了死亡之歌生命之歌也变得愚蠢无益。”
然而,劳伦斯并非认同一切死亡。在《灵船》一诗的第三节,劳伦斯这样写道,“一个人能否用出鞘的剑来解除生活的苦难?用匕首,用长剑,用子弹,人们能为自己的生命捅开一个出口;但是,请告诉我,这是否就是解除苦难?”劳伦斯随后予以直接的回答,谋杀与自杀皆不能解除生活的苦难。此处“解除苦难”对应于原诗中的“make quietus”,“quietus”一词源于拉丁语,含“静止、安宁”之意。显然,这一词汇的内涵与诗中的“peace”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只有自然死亡才可能让灵魂踏上安宁的旅程。因此,劳伦斯歌颂死亡并非弃绝生命。事实上,劳伦斯热爱生命,强调肉体和血性对于生命的本质意义,他对那些充满生命能量的动物甚为钦羡。非自然的死亡是对生命的亵渎,因而遭到劳伦斯的否定。在短诗《艰难的死亡》中,劳伦斯对自然的死亡作了清晰的分析,“死亡来则自来非我们意愿可左右。”诗歌《当心不幸的死者》表明未能做好准备的死亡将导致迷失的灵魂,这些灵魂徘徊在陆地暗影的边缘,不能开始死亡之海的旅行,因为他们被突然掐掉了生命,毫无准备。
劳伦斯赋予船以象征意义,灵魂脱离躯壳之后,需要乘上通往湮灭之旅的灵船。因而当死亡来临之前,人应该造好自己的灵船,准备好旅途的供给。灵船是一个虚指概念,它存在于人的心中。可以说,灵船代表着一种从容并淡然面对死亡的宁静。然而,从《灵船》一诗可以看出,诗人在面对死亡时仍然带有一丝忧虑和苦痛。从“惊恐的灵魂”、“胆怯的灵魂”、“赤身裸体地哆嗦”的灵魂这样一些表述可以看出诗人此时对于死亡并非抱有完全的自信。然而,在几经修改之后的《灵船》中诗人变得更加超脱而淡然,语气也更为平缓。可以说,此时诗人真正坦然地接受了死亡,已经造好了自己的灵船。
五、 结语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劳伦斯写下了多首关于死亡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诗人表达了自己从容面对死亡的信心,死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通向新生的一个过程。死亡可以使灵魂脱离开牵绊,真正达到一种彰显生命意志的自主存在,因为“生后的轻风把我们亲吻成人性的花朵。”(《死亡的欢乐》)经历过死亡的涅槃之后,灵魂会找到一个全新的家,并获得崭新的欢乐的宁静。死亡的过程也是不死鸟燃烧自己最终恢复青春的过程。这样一种消解了生死二元对立的死亡观正体现了劳伦斯对自然生命的歌颂和对死亡这一乌有之乡的超越。
本论文属于西华师范大学2008年科研启动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B037。
[1]Bell, Michael. Lawrence and Modernism.In Anne Fernihoug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C).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3: 179-196.
[2]Lawrence, D. H. The Complete Poems of D. H.Lawrence[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4.
[3]Salgado, Gamini. A Preface to D. H.Lawrenc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4]D•H•劳伦斯.劳伦斯诗选[M].吴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5]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刘洪涛.劳伦斯与非理性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41-48.
[7]穆尔.血肉之躯:劳伦斯传[M].张健,舍之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8]潘灵剑.劳伦斯诗歌创作散论[J].当代外国文学,1999,(3):137-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