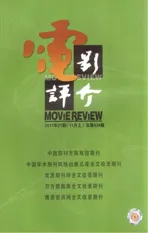父权家庭体系的建构与解构——以《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为例
2011-11-16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马修伦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马修伦
以“家庭”为架构体系和叙事核心的电视连续剧一直是中国荧屏的重要力量,其中许多作品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切实展现了中国传统以及当代文化在家庭结构中的存在方式。2010年12月播出的《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就是一部展示了典型的“父权”家庭的结构方式。《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塑造的以“父亲”符号为核心的“父权”家庭体系是很“接地气”的,该剧以中国文革后期至当下的社会变迁为背景,以上海老弄堂里“老马家”近三十年的时代变迁为故事线索,表现了“老马家”这一普通百姓家庭在时代浪潮中的历程。在社会语境的次第转换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通过“父亲”符号的建构,折射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模式中的“父权”延承,以及在历时性轨道中,父权延承对传统文化组成方式的消解与重构。
一、家庭结构的纽带:血缘与姓氏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借用“父亲”符号,阐释了中国式家庭体系下的“父权”组成。在中国社会,“父亲”往往担当着社会组成元素的“单元符号”,这一“单元符号”代表着社会结构单位——“家”,其存在和延续与男性直系血缘关系密切相联;父亲的姓氏是一个血缘团体的认同标识,是一个社会单元符号标识,也是个体家庭在社会上的认知标识。
剧中,“老马家”是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由父母(父亲马一毛、母亲胡根娣)和未成年子女(女儿马拉、长子马鸣,次子马风)组成的社会单元。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父亲”的“直系血统”是家庭横向组成的最重要纽带,“父亲”的代系传承是家庭组织的最重要历时链条。在《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中,“老马家”自然是以“父亲”马一毛为单元身份建立的,三个孩子是马一毛和妻子胡根娣的亲生孩子。胡根娣是家庭中唯一非马姓的成员,但是作为马家的嫁入者,她是马一毛传承马氏家族链的重要条件,在为马家建构家族体系的过程中,她已经自觉把马家利益内化为其生存目标了,处处以“我们老马家”成员自居。
为了强调父系的代际传承关系,马一毛不时用“我们马家”这个带有权力意味的词语强调“马家”的历史身份,并且虚构了一个“山东倔县耿庄”的祖籍,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反复强化,借以巩固家族和父系权威。
在传统文化意识中,祖籍既能彰显地域性格,更能显示家族代际传统。“山东倔县耿庄”这一祖籍地,在显示马一毛对家族性格塑造的同时,也指认了家族随着地域变迁带来的血缘传承。从家族性格上来讲,马一毛给其赋予的特征是耿直、倔强,这既是马氏家族中以血缘相联系者共有的秉性,也是作为血缘传承的外在标志出现的:马氏家族所有成员共同拥有一个祖籍,强调的是“马家”的直系血统为此家庭的根蒂。每当家庭出现危机,需要借用家族纽带消除危机时,马一毛就会申明“老马家”的人祖籍来山东倔县耿庄,并且以此为准绳来辅助强调“是”或“不”是“我的种”,以家族性格来佐证血缘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结构并维系其父系家庭组织。
在中国古代,姓氏的命定就是以血缘关系为标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姓,是指按照一定社会关系沿续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标志,它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血缘,一是世系。”[1]“氏,是姓的分支”[2]标记,是缘于同一父姓始祖的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因此姓氏就成为家族和人血缘关系的典型外在标识。所以马一毛在对自身父权使用过程中,就不停地借用“你是(不是)马家的”来塑造和限制自己的下一代。为了更好地建构其家族理想,马一毛不惜牺牲女儿马拉和次子马风。因此遭到了马风的反抗,声称与马家断绝关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田丰”,划清与家族姓氏的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叛逆者最后却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马顺”,自觉地延续着原有家庭体系的新建构。
在剧中这一男权传承标识也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称呼中,马一毛对孩子的称呼都是全称,不曾省去姓氏“马”字,反复强调其姓氏意义;胡根娣在称呼孩子时,对长子较少使用昵称。这一话语行为于无意识中把马鸣在老马家的长子地位树立起来:马鸣是传统中国家庭结构中的“嫡长子”,这个“嫡长子”恰恰是“马家”社会认知身份延承的符号,因此马一毛对马家的长子也格外看重。因此他对两个儿子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马鸣在生活中阐述的小知识被上升到智商与做大事品质的高度,而次子马风做好事救人却遭批评;马鸣惹事被袒护鼓舞,马风被兄长牵连反抗却受批评。不仅如此,马一毛也把人生经验悉数传授给长子,不仅反复强调高蹈的文化传承中的“倔强和耿直”的品格,也通过“打蚊子事件”把个体人生经验传承给马鸣,教给他经验性的生存策略,为马家代系继承人提供最全面的培养方式。
马一毛成功了,他去世后,真正掌握马家发展方向、并成为马家精神建构主宰的就是长子马一鸣。
因此剧中呈现的由马一毛→马鸣(→马顺)的父系代际关系,以及由血缘关系和姓氏作为纽带的家庭体系,仍在当代社会中延承。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的剧作结构设置上也与此相吻合:剧作前半部以“马一毛”为中心结构剧情,后半部则以“马鸣”为结构中心,在这两个段落结构中,导演分别采取了马一毛和马鸣的视点讲述故事,由此在结构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家庭的以“父亲”符号历时性传承为架构的父系家族史。
架构父系家庭体系的过程也是历史语境不断变迁的过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外来思想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原有的爱情、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由是,这种直系血统的家庭观念也受到了时代的挑战,由直系血统和姓氏作为纽带的家族结构也不断受到冲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定的被解构面貌。
首先,剧情对血缘纽带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消解与冲击。具有叛逆性格的马风,与一个从小被卖到唱戏班子的“戏子”米玲珑结婚,并生下一子马顺,给老马家带来了希望和生机。但吊诡的是,该子并非马风亲生,而是米玲珑与前男友之子。老马家出现了非直系血统的“父亲”符号,直系血亲的“父系”传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从一定程度上对由血缘纽带结构的父系家族进行了解构。另外,马一毛去世后,嫡长子马鸣承担起了“父亲”权力,但他却没有生育男孩来继承直系血统的“父亲”符号,而由一贯叛逆的马风担当了传承责任,剧作借此进一步对直系血统的“父系”结构进行了消解。但剧作结尾,米玲珑的怀孕仍给影像后叙事留下了无限思考空间。
其次是剧情对姓氏纽带关系的冲击。“老克勒”莫文辉作为早年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完成了自身身份的改变,以及精神高度的提升。在剧中他一直参与马家事件,并在马家子孙尚未成长为合格“父系”权力代表时,一直支撑马家发展,正如剧中人物自己所言:“这些年,马家哪一件事我没有经历过?”作为马家历史的重要参与人,莫文辉是一个异姓人,更是一个血缘系统外的人,其在马家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对姓氏结构纽带进行了消解。
但在影像空间中,这些消解都具有条件性、边缘性,并不足以对父系家族的结构核心、以及代系延承的传统起到彻底的冲击作用。
二、家庭权力的分配
在中国传统家庭话语权(以及其他权力)的分配中,成规文化特征就是通过性别与辈分进行分配吗,家长在世时,父辈中男性(父亲)拥有主宰性的话语权力。剧中马一毛在辈分与性别角度便占据了中国传统家庭话语权分配的先验优势。
马一毛在剧中不仅掌控了家庭的话语权,还掌控着“老马家”的命运与未来发展走向。马一毛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其全家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代表,当他被打为坏分子时,全家人在家庭以外的场合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马一毛摘掉“坏分子”帽子的时候成为全家人现实境遇和精神命运的转折点。
同时剧中家族权威的代表马一毛主要的奋斗目标,就是合理安排“老马家”的后继发展:安排长子作为家族核心接班人,女儿马拉和次子马鸣主要为马鸣发展服务。事实上,这一策划也得到了如期效果,剧情后半部分,马鸣成为实质上主宰马家发展方向的接班人。“父亲”马一毛这一权力也体现在对后代的教育上。马一毛决定了三个孩子的命运与发展:马鸣凭借其嫡长子的身份与学习成绩好的优势,成了马一毛的宠儿,也是命运的宠儿;女儿马拉、次子马风成为这一权力意志的牺牲品。尽管自己的职业为马一毛带来了不少生活便利,但他一直认为“考上大学”并且拥有此后所具有的一切后续福利,才是真正进入了社会主流。因此,马鸣考第一和做班长给马家未来社会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希望,马鸣被评为三好学生所取得的社会认可,又塑造了一个未来成功者的雏形,这些为马一毛实现未来家族愿景带来了希望。作为马鸣的牺牲者——次子马风的出场镜头充满了隐喻意味:马风被两个人挤推在墙上,脖子被一只手卡住,左手被同一个人的另一只手按在墙上;另外一只手抓住马风的右手,另一个学生一只手压住马风的肩膀,一只手抓住马风的左手;这个形象成为马风被家族和时代钳制的象征。屡屡受到命运和家族钳制的马风意欲反抗,却被马一毛将一只耳朵打穿孔,并被告知:“我没你这个儿子,……你不要说你姓马,永远不要回到我们马家……一刀两断。”马一毛并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告诉马风说:“你当最后一次听爸爸的话,去自首,你为了你哥哥的前途,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老马家”后继的“父亲”符号马鸣不受影响,马一毛的许多做法已然超出人性范畴。不仅是与马鸣同性的马风是父亲意志的牺牲品,女儿马拉更是如此。
正是这个父亲符号决定了晚辈们的生存与发展走向,在他的努力下,马家也实现了发展目标,此后马鸣在马家发展方向上的主导性作用,正是马一毛终生奋斗的目标,也是马一毛父亲权威的延续。
母亲胡根娣在“老马家”这一家庭系统中具有第二话语权,马一毛去世后,胡根娣成为了话语权的中心,但其话语权是在“父亲”符号支配下行使的,她是“老马家”权力代言人。她自觉的维护着“老马家”的利益,当这一利益受到威胁时,胡根娣总是仪式似的在马一毛的遗像前完成对子女的教育,凸显了中国这一传统的父权话语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承传。马顺身份由胡根娣确认,既是代父职权的体现,也是“耿县倔庄“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扩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剧中对以“父亲”的话语权进行解构,这一解构突显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家族权力的法定继承人马鸣对马一毛权威的质疑。在关于家族前景规划中,马鸣认为自己可以不读大学,对削除马拉和马风幸福的行为,马鸣认为:“我是你儿子,他也是你儿子,他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上什么狗屁大学,把马拉和马风都牺牲了,我不想在姐姐和弟弟的痛苦上完成我的学业。……都是一条命,谁的命也不比谁命贱”。质疑了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家族理想。马风对老马家所带来的罪孽的质疑与反抗,甚至对姓氏的背叛,都没有得到马一毛的让步,而马鸣的反抗却成为马鸣替代父亲权威的契机。马一毛说:“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老子,你是我老子”,正道出了这一“父亲”这一权威符号受到时代思想的质疑而将发生权力的转移。马一毛男性器官的病变成为其权力衰退的身体象征。治保主任道出了真实的原因“这是自然规律啊,你不好阻挡历史的潮流往前走呀”。
其次是代表经济物质权力的外姓人物莫文辉在马家渗透。莫文辉面对物质利益与情感的博弈,最终选择了物质,抛弃了马拉,由此给老马家带来了形象的贬低和荣誉的损失,因此莫文辉成为老马家的仇敌。但此后莫文辉对“老马家”在物质和社会地位上的帮助,却成功地提升了其在马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完成了老马家对其祖籍“山东倔县耿庄”文化意义上的渗透和背叛,更借此实现了对“父亲”话语权的消解。正是这一曾经给老马家带来耻辱的人,凭借物质和社会身份给老马家带来的利益,实现了对马家的社会身份的一定渗透和解构意义。
再次是来自新时期母系关系的李小娜在马家发展中的作用产生的消解意义。马鸣作为重要的“父亲”符号的象征,其社会地位是马家社会地位的具象化。而在这一具象化的背后,不仅有老一辈父亲的规划和操作,同时也有来自母系关系的作用。如果说在第一代父权体系中,作为母亲的胡根娣除了实现其传宗接代的作用外,基本没有自己的个体和性别价值,就连生活费也需要由马一毛分配。而李小娜在与马鸣第一次见面时,不仅与马鸣产生了正面冲突,还嘲笑其祖籍“山东倔县耿庄”的文化和地域身份。而其异与上一代父系范围内的母亲形象,更是对父亲形象产生了重要冲击:抽烟喝酒,远离家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凌驾于男性家庭地位之上自我意识。不仅如此,象征马家的社会身份的马鸣的副区长头衔与李小娜背后的社会关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以独立意志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父权家族发展对以“父亲”主导的成规文化产生了挑战。
三、家庭社会网络关系建立
在父权家庭模式下,父系的家庭关系往往即是家庭的核心网络关系,这同样凸显了“父亲”系别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剧中马一毛的家庭网络关系是“老马家”社会身份的中心,妻子胡根娣的母系关系在剧中没有体现出来。剧作前半部分,马一毛作为父权符号结构的剧情中,马一毛与治保主任、兄长马一山等社会各阶层、各职业人群的关系是家庭网络关系的中心,他们构成了老马家生活的主要社会关系网。马一毛去世后,马鸣作为马一毛缔造的“老马家”新的社会身份标识,其社会关系网络成为“老马家”社会网络关系的中心。与马鸣情感或者利益关系密切的李小娜、徐丽娜、黄爱国、胡斯文、莫文辉等人,组成了马一毛后的“老马家”生活关系网络中心。正是在与这些人的关系网络中,马鸣找到了属于老马家的社会身份和价值,其“老马家”传统得以延续,并最终取得了家庭内外的认同。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关系网络的解构。事实上,时代语境的位移首先对老马家传统的家庭网络关系产生了解构。传统的父系家庭网络关系通常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在共同的生活和长期的传统人际交往中完成,并产生稳固性。随着中国大环境的改变,“老马家”传统的家庭网络关系由上海弄堂逐步扩展,对以父权为中心的较稳固状态进行了动摇与拆解。当次子马风带着叛逆的性格携裹进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时,“老马家”家的辅助网络关系一度扩展到海南、广东、北京等地,对传统的稳固的地域性家庭网络产生了冲击。尽管这些网络关系,以马风回归上海为标志,最终被整合进了传统的地域性范畴,但其却呈现出新的历史时期家庭网络关系的变化的新趋势。
同时,在马一毛父系家庭中,被隐匿的母系关系网络也逐渐参与进老马家社会关系网络中来。马鸣的妻子李小娜在突破了上一辈母亲符号价值系统后,也将新的家庭关系带进了老马家。不仅马鸣借李小娜“爷爷”的老革命家身份,实现了仕途的升迁,而由李小娜的社会关系网络给马家家庭关系网络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在马鸣家庭生活和仕途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黄爱国,不仅是马鸣中学同学,更重要的是李娜一起长大的哥哥。李娜参与马家关系网络的建构既是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更是女性在社会大环境下生存意义和价值意义的新突破。
这些因素既是传统父系家族被消解的体现,也是父系家族网络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展的新趋势,而荧屏外空间也逐渐表明了这一趋势发展的势头和价值。
四、结语
《老马家的幸福往事》结合三十年中国社会语境的变化,巧妙地将“父系”家族变迁架构在“文革”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中,既是对传统家庭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父亲”权力符号的透视,也是对“父亲”符号在时代变革中受到的冲击与挑战进行的展示与思考。剧作塑造的新一代“父亲”符号马鸣,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马家真正的当家人和事业核心,不仅获得了剧中人物的认同,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因此剧作在完成父系家族变迁的历史性叙述时,也匠心独运地讲述了一个家国同质的寓言。
[1]张淑一:《姓氏起源论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页。
[2]张淑一:《姓氏起源论略》,《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