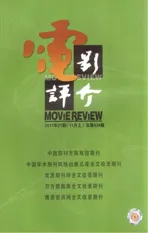强权规训与意识去弊:纪录片《海豚湾》的叙事学分析
2011-11-16毕蕾,景秀明
2009年上映的纪录片The Cove(中文译名为《海豚湾》),讲述了在一个名叫太地的日本小镇上,当地政府、渔民与来自西方国家的动物保护者围绕“海豚”而发生的故事。该片由电影人路易•皮斯霍斯导演,荣获第八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等荣誉。作为一部典型意义上的“真理电影”模式纪录片,《海豚湾》的叙述立场鲜明,充分利用了多种叙事学手法,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导演意图,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切实有效地推动了“保护海豚”这一社会行动的开展。那么,这部纪录片是如何将现实转变成为电影结构的呢?在转变过程中,它又是如何将意识形态根植其中而为主题本身服务的呢?
一、叙述视角与叙述者: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
视角在叙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决定着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即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简言之,它是叙述传达的依据。在“真理电影”模式的纪录片中,大量使用访问、采访者参与叙事、承认人为的环境是其三个主要的叙事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编导的意图,是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海豚湾》的叙述视角是里克•奥巴瑞为代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视角。开场的第一个镜头,采访者就在积极主动地干预叙事,他通过对话告诉我们,这个叫“太地”的小镇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与小镇的美景大相径庭。紧接着,影片通过里克•奥巴瑞被跟踪并被日本警察盘问等情节营造出一种“这个秘密被镇上的渔民和当地政府异常团结地守护着”的印象,而他们一直在试图掩盖,那这就一定是个“见不得光的秘密”,既然这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那么就让我们去揭开它——一场典型的好莱坞式的“英雄叙事”呼之欲出。在这里,导演巧妙地选择了内聚焦型叙述视角。在内聚焦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
既然如此,那么片中不包括日本渔民的观点在观众看来一定是理所当然的[2]——这就像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先入为主地认定其有罪,然后收集一切有利证据以证明其有罪,那么所有不利证据都可以被合理地忽略。里克•奥巴瑞驱车带着路易•皮斯霍斯进入小镇,路易•皮斯霍斯讲述了他们如何相识并一起来到“太地”的原因,也引出了这个小镇的秘密——屠杀海豚。当他们来到禁区边上,里克•奥巴瑞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们要进去拍摄发生的事情,需要知道真相。此时,影片最大的悬念——“他们将如何获知真相”被成功引出。接着,片中出现里克•奥巴瑞被日本警察盘问的情节,这种间谍片式的叙述手法开始展现出其强大的叙事魅力——一方面调动观众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本片的主要戏剧冲突(揭露者与遮挡者的矛盾)。影片适时地叙述了里克•奥巴瑞帮助海豚的种种遭遇和他坚定不移地解救海豚的决心,以及他与海豚的渊源等内容,并引出了“海豚是依赖听觉的动物”这一事实加以论证。当里克•奥巴瑞说出:这也是它们在“太地”被捕捉的原因时,画面切入“太地”渔民利用海豚的声纳系统驱赶、捕获海豚的画面,路易•皮斯霍斯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看到这一幕的内心感受的画面。显而易见,当导演与苏联导演维尔托夫一样,认为“艺术不是反映历史斗争的镜子,而是斗争的武器”时,这部纪录片就不再按照时间顺序或叙事的前因后果来结构,而是根植于导演的论点[3]。
一旦意识到从客观真实事物角度上看,纪录片产生的所指无法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完全保持一致,而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即想象与虚构的成分[4],纪录片就无法脱离叙述视角与叙述者身上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九十分钟的影片,“坏人”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空间来申辩或者反驳,即使他们被偷窥了。从这里能够充分看到内叙述视角的种种优势:在创作上它可以扬长避短,多叙述人物所熟悉的境况,而对不熟悉的事物保持沉默[5],因而可以较为容易地亲近观众,赢得观众的信任。这一点在“真理电影”模式纪录片中被大量使用——他们首先在选材上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后按照主题组织故事素材,让记录则成为了一种佐证,提供了事件不能推翻的证据;再采用完美的屡试不爽的典型的好莱坞叙事手法来煽动观众的感情;从而最终完全获得观众的信任与认同。
二、叙述接受者: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象
叙述接受者是与叙述者相对应的概念,是叙述者的交流对象,文本里的听众。叙述接受者的信号是由叙述者发出的,叙述接受者的形象也主要是从叙述者的叙述中建构的。在影片文本内部,导演路易•皮斯霍斯担任了叙述接受者的角色,不同的人与其进行对话,告诉他屠杀海豚的种种恶果,这是叙述接受者出现在文本中的显而易见的信号。作为内叙述接受者,他表现出了一个主动配合叙述接受者是怎样带领观众一同认同叙述者立场的强大力量。这条围绕“揭秘与对抗揭秘”而展开的逻辑线是:海豚表演并不人道,请让海豚回归海洋——如果要捕获海豚,那么不能表演的请放生——如果不肯放生,汞含量超标的海豚肉也不宜食用——欺骗购买者,并且让青少年食用海豚肉——既然政府根本不在乎人民的健康,那么退一万步来讲,虐杀海豚的行为残忍至极。观众透过路易•皮斯霍斯的眼睛走进了一个逻辑缜密牢不可破的道德网络,使得观众不得不认同叙述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
在《海豚湾》里,无处不在的“我们……”在告诉观众他们的行动进行如何的同时也无时不在地透露出“那么,作为这次行动见证者的你们……”这样的信息。如果说影片的主体部分对于叙述接受者的建构还较为隐蔽的话,那么,影片结尾叙述者向叙述接受者发出倡议:“‘太地’海豚屠宰场,每年九月开始运行,除非我们阻止,除非你阻止,发送‘海豚’至44144,或登陆网站Takepart.com/thecove。”则去掉了遮挡的树叶,直接向叙述接受者发出信号。在此情形下,人物表现为“好像是他让人观看影片”,直接召唤影片的对象[6]。直接对话的口吻发出的信号往往显示了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又是自上而下的。
因为,从根本上说,景象就是独裁和暴力,它不允许对话[7]。
在《海豚湾》中,因为叙述者们向观众展示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将小镇的秘密曝光于天下,同时使观众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规训。“充分的光线使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8]如果说片中的日本渔民与小镇政府是在黑暗中被审视,那么每一个观看这部影片的人都是在日光下被审视。审视的力量充分地体现在观者的自我规训上——如果我对于这样的杀戮视而不见,那么我就是冷血的、无情的、不被大众所接受的。
三、纪录片:意识形态的叙事互动
在众多类型的媒介中,纪录片或者是最为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的一种,或者意识形态是纪录片的必备要素之一,这一点在“真理电影”纪录片中尤为明显。一部“真理电影”纪录片的产出,必然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强权与规训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我们应当如何做。而纪录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只要你在拍摄中能保证一个完整的叙事系统,选择特定环境、特定时间、特定情境,给观众提供能做出正确理解和判断的信息;只要你拍的自然流畅并叙事完整,给人以真实感,观众就会觉得你是真的[9]。《海豚湾》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巨大的信息量扑面而来,在不断的蒙太奇切换之间,关于海豚湾的种种争斗都被剖析得一清二楚,从而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影像世界[10]。对于每一个观众而言,只要他是正常的、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他都会对屠杀海豚持反对态度。这样的普遍心态与叙事的契合使得观众极为相信所看到的“真实”,并对制作者的意识形态产生高度认同。正如有关学者所说:“如果纪录片文本所反映的内容,符合人们习惯了的或理解力之内的意义模型,那纪录片所反映的内容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11]
这种遮蔽的意识形态注定了纪录片是纪实的而非真实的,即使它千方百计地想要一个“真相”。即使有些纪录片看起来是没有立场的,也不过是因为它使用的叙述方法遮蔽了它的意识形态。反观《海豚湾》这样一部解蔽意识形态的影片,在整个观影的过程中更加让人酣畅淋漓,因为它更能够毫无避忌地将意识形态融进叙事当中,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的好故事。
无论纪录片的叙事是遮蔽还是解蔽意识形态的,它们存在于纪录片中,为意识形态所服务,负责讲一个令人信服的好故事。如果观众在看完《海豚湾》之后,能够增加一点保护海豚的知识和意识,这部影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片中所说的:“日本人屠杀海豚是因为‘残留的帝国主义的传统观念,他们不愿再让西方国家对他们指手画脚。’”这样的观点,不过又是美国文化与日本的文化的又一意识形态的冲突罢了。
注释
[1]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27页
[2]胤祥,《海豚湾:意识形态VS意识形态》,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985674/[EB/OL],2011年4月5日
[3][美]路易斯•贾内悌[著],焦雄屏[译],《认识电影》[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第1版,第309页
[4]景秀明,《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论纪录片叙事的真实问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5]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27页
[6][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刘云舟[译],《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7页
[7]马藜,《视觉文化下的女性身体叙事》[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第93页
[8][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3页
[9]《“却嫌粉脂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北京三月电影纪录片学术研讨会简述》[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报》,1992年第三期,43-44页。
[10]萤火虫,《千疮百孔的真相》,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917039/[EB/OL],2011年4月5日
[11]景秀明,《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论纪录片叙事的真实问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