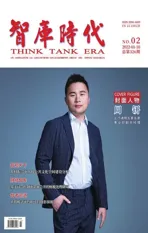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2023-01-08刘灏
刘 灏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空间转向”实际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现实层面的“空间转向”,一个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层面的“空间转向”。所谓现实层面上的空间转向,是指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所谓理论上的“空间转向”则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研究转向。现实层面的空间转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现空间转向,而理论层面的空间转向则为其提供了借鉴和理论依据。因此,本文将以这两个维度为研究起点,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现“空间转向”的可能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现“空间转向”的现实需求与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是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主客体双向互动的一种实践活动,其目标是使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价值观被大众所理解、接纳,并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获得检验和践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转变和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把握。
“只有真正把握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以及漫长延绵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性维度,捕捉某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1]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现实的个人,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够在根本上把握住时代的思想根源,能够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所认可的思想根基或者说现实的思想困惑出发,不论从话语和形式上就都能更好地对客体产生影响,进而完成思想教育的目标。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切入社会现实就是关注多样化社会群体的精神交往和思想互动,把握社会成员相互之间政治性思想观念的接受状态及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与规律性。”[1]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切实发挥其效用,就必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接受政治思想观念的本质规律。而其本质规律只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具体的现实的交往中才能把握。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交往、生产、生活模式的出现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挑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着眼于现实社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上的引领作用。
当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角拉回到现实社会的时候,不免会关注到空间对人们思想和生活转变的塑造与影响作用,因而对空间的考察也就成为思想政治研究不应回避的对象。空间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日益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应积极关注空间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利用空间对人们思想行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探寻利用空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空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日益凸显,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和视角。20世纪以来,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产生、发展并且得到了很广泛的普及,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因素。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将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群体都联结起来,搭建起了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覆盖范围极广的虚拟空间。同时,虚拟空间具有趣味性、实时性、传播性,虚拟空间中的主体会更加容易受到不同思想空间的影响,多元价值观的冲击无疑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更利于主流的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价值观的虚拟空间,怎样利用虚拟空间的利好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虚拟空间的产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虚拟空间的诞生改变了过去从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话语传递,更多来自“草根”的事迹和话语也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不同阶层的意见和想法。从微观视角来看,一个引发大众谈论的网络事件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不同的阶层和生活背景的群体的意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能够去探讨影响其思想发生转变的本质规律。虚拟空间提供了这样一个聚集多元意见的场域,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掌握思想教育客体的思想的根源和纬度,进而找到更为有效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纬度。除此之外,虚拟空间为日常的一些被忽视的碎片化空间提供了场域,使得大众能接触到这些碎片化的空间,这对于受众的思想会产生过去所没有的冲击。如今,大众在社交网络上对日常生活的分享已经成为常态,不同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会对不同阶层处在同一生活空间的人带来心理和思想上的变化,对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可能会产生怀疑。同时,“虚拟网络不再虚拟,而成为实实在在的交往与生活空间,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考察人们的思想流变,了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动态提供了现实基础。”[2]因此,虚拟空间的出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元价值观冲击的挑战,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第二,空间带来的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变化和群体化差异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具备优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资源、生活环境,所以较之乡村来说更具吸引力。因而,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空间便成为了一个容纳大量人口的空间。
城市空间的变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大众认知和理解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也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需要关注空间的变化。
一方面,聚集在共同的空间下的人在生活过程中,生产着同质化的空间。但其又都是现实的具有个性的人,所要构建的又是个人的具有异质的空间。那么,同质化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分歧与矛盾成为了当代人的困惑,也会对其思想产生影响。而空间本身又为这样的困惑提供了解决办法,这是因为空间可以提供情感体验,人们在生成性的空间中会加强对主体性的认知,也会在正确的引导下对空间产生一种情感寄托。在空间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社会认同基础,会形成对空间的集体的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因而要想解决空间变化给现代人的思想困惑,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必须要关注社会空间的生产、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认同基础。
另一方面,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空间,使得两种异质的社会生活空间在碰撞中产生冲突,不同的思想形态的交流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现实场域。现代的城市空间是一个不同的思想交互影响的现场,“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3]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仅需要对不同空间的群体、环境、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同时也需要关注具有差异的空间所交融构成的空间,探究思想交流传递的内在本质。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城市居民之间的陌生感与距离感日益增长,每个门户之内都是独立的空间,彼此交往意愿下降,正常的纯真的邻里交往受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缺失共同的场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发挥其有效作用,就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须去思考的问题了。
第三,空间的研究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启发。超时空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一种时空上的错乱感。信息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播到中国竟然比在同一栋办公楼的三楼到四楼还要快,时间对人们的影响逐渐在减小,而当下复杂的生活、社会空间成为了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换句话说,时间的重要地位正在慢慢改变,反而空间变成了动态与主体活动密切相关的现实场所。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应从空间的角度为切入点,利用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进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二、空间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列斐伏尔、哈维等的空间理论的引领下,空间的特质以及其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逐渐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空间开展进入到研究者的研究视域之中。“学者们开始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关注城市空间是如何隔绝人们的自由实践,又是如何促使人们找到自我空间的分布,关注在空间中的定位、移动和渠道化以及符号化的共生关系。”[4]一系列空间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涉及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定向。这一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把“空间”作为僵化的、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使空间以一种“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之下。空间理论家指出人对于社会空间具有主体建构性,具体来说,人们借助所生活的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行考量,并根据主体性来改造空间以适应新的需求,构建出一个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而所构建出来的社会空间,对于主体的活动又会产生“秩序性”的制约和影响。这一变革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
福柯作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转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首先,福柯对空间的重视,实际上是思想方式上的一种转变,他指出,“19世纪以前的西方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而更可能是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成的网络。”[4]在福柯看来,过去的历史学或者说社会学家更多的是采用线性的连续性的分析法,更加关注的是事件的历史根源。而20世纪则需要将视野从线性的时间上,拉回到立体、复杂的现存的空间上。这种视角的转化其实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的关注与反思。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环境中进行的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实践活动,其也必须有这样的视角转变,才能考虑到、处理好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各种因素,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其次,福柯还提出了知识的空间化理论,他指出了空间代表一种潜在的秩序,知识在一定的空间秩序下得到传播,而知识空间化的现象是比较容易重现的,是通向知识的一条途径。“知识空间化”的提出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对日常空间进行研究并探讨空间与思想的稳定性、空间对思想的建构的具体联系,以及如何通过空间的建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用,加强科学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生产的概念,他指出同质性的空间生产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增加了空间的可复制性,同时,社会空间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样,他就把空间的价值凸显了出来。空间的可复制性和空间的生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生产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最后我们可以从阿尔都塞提出的“文化场域”,来理解“空间转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阿尔都塞提出“文化场域”是任何文化实践都难以绕开的“大写的总问题”。主体在进行文化实践时会受到传统的、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场域的影响,而不同主体的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会促成新的文化场域的形成。而社会空间又是不同文化场域的表现形式,因而从空间的角度去探讨不同文化场域想互作用影响的机制,对于构建有利于政治思想被大众接受的社会空间有现实意义。考虑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的空间性,注意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与受教育者的文化场域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理论实践的发展。
总之,空间理论家们的思想突破传统的以时间为主导而忽视空间的,线性的、静态的、因果的、必然的历史的决定论观念。从时间到空间的关注反映出关注点从长远的趋势或历史的传统,转移到现实到当下。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极大的启发,思政教育的定义就要求它不得不着眼于现代的场域,关注复杂的社会、思想环境,在复杂社会空间内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机制。
三、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现实可能性
空间转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具体展开有两个方向上的现实启示,一方面就是微观探讨,即把空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要素,关注空间变化对于社会群体的思想接受的影响,探究不同社会空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途径。有学者就曾在其文章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不仅要在理论上澄明其内在意蕴,更需在实践上充分关注社会的空间结构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者的选择及策略等。”[5]他们以城市社区空间为着眼点,分析了城市社区教育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社区空间的问题,最终提出了城市社区生产的行动策略。像这样从微观的空间的视角切入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缺失的场域,更加容易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在具体空间内的问题,并能在综合考虑复杂的空间因素之后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有针对性的社会空间的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尝试,更是实现“空间转向”的有益途径。另一个方面就是宏观建构,要在深入探讨空间生产与思想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系统。张哲根据空间生产理论,认为发挥好空间的“秩序”优势作用,构建出合理、复杂、动态多维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体系,并对教学运行空间、个体精神空间、沟通交往空间、虚拟环境空间、制度安排空间、社会生态空间和学科发展空间的建构与发展提出具体的实践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构建,可以发挥空间的“秩序性”作用,在社会生活中隐形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但系统的构建不是僵化和静态的,要在系统学习空间理论,掌握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出科学的、动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系统。
这两个方面的尝试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空间转向”的现实路径,不论是微观探讨,还是宏观构建,都可以看出空间视角的转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带来了创建性的影响。同时,这两个层面上的研究都还有长足的研究空间,因此,将空间的时间和空间研究的方法带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