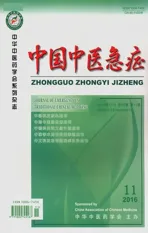痛风各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2016-01-29何昱君马佳维
何昱君 马佳维 孙 静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3)
痛风各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何昱君 马佳维 孙 静△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3)
痛风是一种有明确临床分期的风湿免疫性疾病,临床常伴血尿酸增高,急性关节炎,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与关节畸形,甚至肾脏损害。西药在治疗上存在局限性,而中医药在改善临床表现和控制病情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中医辨证论治角度分析痛风5个阶段的临床表现,分析其病因病机,并予相应的治疗方法,体现中医药强大的优势。
痛风 临床分期 辨证论治 中医药
痛风是一组遗传性或获得性尿酸代谢失调的疾病,由于嘌吟代谢紊乱造成的血尿酸水平过高,或尿酸排泄减少而导致的尿酸盐沉积,分原发和继发两种类型。原发性痛风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约20%的患者有阳性家族史,除1%左右的原发性痛风由先天性酶缺陷引起外,绝大多数发病原因不明;继发性痛风是继一些疾病过后出现的高尿酸血症,因尿酸盐结晶沉积(痛风石)所致的特征性急、慢性关节炎不典型的疾病,除慢性肾功能衰竭所致继发性痛风起病缓慢外,多数起病较急、痛情严重、肾脏受累多见。
痛风病的临床特点包括:血尿酸增高,急性关节炎,慢性痛风性关节炎与关节畸形,甚至肾脏损害。其中约95%的痛风发生于男性,起病一般在40岁以后,且患者发病率随着年龄而增加,但近期有年轻化趋势,女性患者大多出现在绝经以后。临床上,西药如非甾类抗炎药、秋水仙碱等用于治疗痛风的疗效确实可靠,但具有一定毒副作用,存在局限性和依赖性,停药后易复发,使病情加重。中药在治疗痛风上有明显优势,其疗效确切且安全,不良反应不明显,能稳定控制病情发展,预防并发症等[1-9]。
中医遵循“辨证论治”规律,笔者认为辨识和掌握痛风分期是临床诊断的首要内容,为临床用药提供导向作用,只有清楚诊断每个阶段表现才能对症准确用药。本文拟从中医药角度分析痛风各个阶段的用药规律,从而体现中医药在改善临床表现的优势。根据痛风症状和程度的轻重缓急应分为以下5期。
1 第1期: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
这是病发的早期阶段,患者往往未觉明显不适,通过体检或其他检查得知尿酸偏高,此时西药只能降尿酸治标治疗,中医则可以通过一些清热利湿利尿药物降低尿酸含量,调节全身机体,从调理体质去杜绝疾病发展,这属于未病先防的早期阶段,体现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往往初期阶段的发病与体质相关:痰湿质和湿热质在无症状高尿酸血症中起到主要作用;阳虚质和气虚质在此起到重要作用,伴这些体质的人群是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故早期医者可以通过调理体质偏颇和对多种代谢危险因素进行早期干预,这样能有效降低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10]。此外,本病的发生与先天禀赋、体质及饮食习惯有关;胖人、饮酒食肉者可诱发加重。近期研究统计表明:治疗无症状高尿酸血症以祛邪为主,常用利水渗湿药,其次是清热药、补虚药,其中最常用中药为土茯苓、萆薢、金钱草等,且研究表明其可显著改善血尿酸水平[11]。
2 第2期:急性痛风关节炎期
这是疾病发展的第2阶段,也是关键阶段,此期临床表现明显,常于深夜关节疼痛惊醒并进行性加剧,12 h左右达到高峰,呈撕裂样、刀割样或噬咬样,疼痛难忍。受累关节红肿灼热,皮肤紧绷,常侵犯单关节。其病因病机主要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阴阳失调,以致湿热痰瘀等病理产物聚于体内,留滞经络;复因饮食劳倦、房事不节、感受外邪、内外合邪、气血凝滞不行,故发生痛风。此时有效缓解疼痛是首要任务,体现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中药主要以祛邪为主,重在清热解毒、利湿化浊,少佐健脾和胃之药。此期相当于中医的“痹证”范畴,与古代的“历节风”“白虎历节”等有一定联系。根据其临床特征: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往往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红肿胀痛等,认为本病归属“热痹”,治宜清热利湿、祛风通络,临床上常用四妙散和五味消毒饮加减[12],具体药物包括苍术、薏苡仁、牛膝、黄柏、车前草、玉米须、萆薢、山慈菇、络石藤、茯苓、金钱草等。
3 第3期:间歇发作期
此期为慢性期,出现关节疼痛反复发作,起初1~2年复发,灼热感明显减轻,出现关节僵硬、畸形等变化,存在活动受限。西药常通过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尿酸排泄的方法长期有效控制尿血酸水平。中医药在这个阶段处于优势。分析主要病机为肝肾不足,脾胃损伤,痰瘀互阻,中药治疗一方面可以通过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来缓解症状;另一方面配合调理气血、补益肝肾增强体内正气,延迟复发年限。两者标本兼治,从而改善患者整体情况。故发作时常因湿、热、毒、瘀痹阻关节,治宜清热利湿、解毒祛瘀;间歇期为痰瘀胶着,虚实夹杂,治宜补肝益肾、化浊排毒[13]。发作期常用四妙丸加减,配伍海藻、昆布、赤芍、姜黄、浙贝、牡蛎等化痰通络散瘀药物;间歇期常以逐瘀汤配伍地黄汤化裁标本兼治。
4 第4期:慢性痛风石病变期
此期发展成慢性痛风石性关节炎,临床表现为持续性关节肿痛、压痛、畸形、功能障碍等,慢性症状相对缓和,但在诱因下易急性发作。中医认为其属久病气衰,脾肾亏虚,瘀血痰浊闭阻经络,凝固不化故成石,治宜补脾益肾、活血化瘀、涤痰通络、利湿泄浊。方用参苓白散合肾气丸加活血散寒之品,常用药物:土茯苓、生薏苡仁、党参、白术、牡丹皮、泽泻等[14]。
总结第2、3、4期病机多为湿热痰浊痹阻经络,气血不畅,不通则痛。若流注关节,筋骨失养,则可见关节僵肿畸形。临床表现都是关节的变化,根据程度缓急呈现红肿热痛、畸形等。此3个阶段应遵循中医“已病早治,既病防变”的原则,一方面要做好巩固性治疗减少急性痛风发作再复发;另一方面要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保护其他脏器免受损害。临床常用药物也多相似,以清热解毒,利水渗湿为主,兼以活血通络,化痰逐瘀,辅以调理气血。
5 第5期:肾脏病变期
此期主要包括慢性尿酸盐肾病、尿酸性尿路结石和急性尿酸性肾病等,临床表现多复杂,根据痛风发病的症状及演变规律,一般归属于中医的“痹证”“石淋”“尿血”“腰痛”“肾劳”等。此病发展到后期,虚实夹杂是其病理特点,常以虚为主。有医家认为肾虚是本病发生的始动因素[15],故后期最容易涉及的是肾脏病变。中医从整体分析认为本病病机为:脾虚不能运化水湿,肾虚不能主水,使湿浊留滞关节发为痛风,湿浊蕴结肾络则发为水肿、虚劳等病。故陈以平教授[16]认为本期辨证当以肾虚为本,以湿浊瘀热痹阻腰府为患,要求固正求本。笔者认为,病发至后期,脾肾两脏俱虚,脾阳依靠肾阳的温养才能发挥运化作用,肾阳不足可致脾阳虚弱,运化失职,出现水肿、腰酸、少尿、无尿等一系列肾虚症状,故治疗应循“虚者补之”“损者益之”之旨,以补虚泻实为原则,以健脾益肾,并兼祛邪。此期常用地黄丸加减:生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泽泻、茯苓、牡丹皮等,如肝脾肾虚甚者,真武汤、肾气丸、左右归丸化裁,加二至丸、淫羊藿、川续断、桑寄生、桂枝、黄精均可。
痛风的临床表现按时期进行性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也发生改变化,从起初的无症状型到后期的肾脏病变甚至伴随全身疾病的发生。我们应该重视每个阶段的变化,尽量控制早期的病变情况。其病因病机在不同阶段各不相同,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各医家多将本病分为急性发作期和慢性缓解期:发作期以邪实为主,多用清热利湿、化浊通络治法;缓解期以正虚为主,多采用补益肝肾或健脾益肾、调养气血之法,并兼顾祛邪。总的治疗原则以利湿泻浊、祛风通络为主;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为辅;同时要兼顾补肾健脾。
6 病案举隅
患某,男性,29岁,2014年7月突发右脚趾关节红肿热痛,某医院诊为痛风。期间服用西药症状缓解,然时有复发,2015年11月23日来门诊就诊,自诉:周身关节酸痛,脚趾和跖趾关节尤甚,腰酸,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胃纳睡眠尚可,喜食动物内脏。查体:脚趾和跖趾关节红肿明显,下肢稍有水肿,舌苔薄白根腻,脉弦滑。此可辨间歇发作期,证属脾肾不足,痰湿阻络。治疗拟补益脾肾,化痰通络。方用茯苓20 g,白术20 g,熟地黄20 g,山药20g,桑寄生15 g,炒薏苡仁30 g,炒车前子20 g,土茯苓30 g,川萆薢20 g,豨莶草15 g,昆布、海藻各15 g,山慈菇15 g,生白芍20 g,生甘草10 g。中药7剂,告知患者不食动物内脏,不饮酒。
患者11月30日前来复诊,情况较前好转,疼痛明显减轻,下肢浮肿消失,大便成形,小便可,腰酸仍存,舌淡苔薄白,脉沉弦。予地黄汤加减服用,方用熟地黄20 g,山药20 g,山茱萸20 g,茯苓15 g,泽泻15 g,白术15 g,车前子20 g,桑寄生15 g,怀牛膝20 g,陈皮6 g,土茯苓30 g,川萆薢20 g,豨莶草15 g,山慈菇15 g,炙甘草6 g,继服半月,症状相对稳定,后未来复诊。
按语:方中茯苓白术健脾利湿;山药补脾益肾;熟地黄、桑寄生、怀牛膝补益肝肾;炒薏苡仁、炒车前子祛湿通痹兼能止泻或利小便;土茯苓、川萆薢、豨莶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昆布、海藻消痰利水;因患者存在关节红肿,发作期加山慈菇15 g,芍药甘草汤酸甘缓急止痛。
总之,临床上正确掌握分期,准确辨证是关键,对症治疗是中医药的特色。中医药在祛除病理产物,改善病理变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标本兼治的优势和中药灵活配伍的特点,使中医药治疗各阶段痛风具有显著优势,不仅在临床治疗上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并能够减轻西药治疗所引起的药物不良反应,极大程度缓解了症状及并发症的发生。
[1] 郑学军,王晓霞,阮海玲,等.高尿酸血症的干预研究进展[J].河北医药,2016,38(16):2525-2527.
[2] 盛峰.痛风的临床与基础研究[D].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2014.
[3] 徐娜,陈海生.治疗痛风药物研究进展[J].药学实践杂志,2013,31(1):14-18.
[4] 何咏龙,青玉凤,周京国.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性关节炎动物模型及其中药复方治疗概况[J].川北医学院学报,2015,30(4):574-578.
[5] 董鹏,宋慧.痛风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基础医学与临床,2015,35(12):1695-1699.
[6] 刘永贵,赵丽嘉,崔艳丽,等.抗高尿酸血症药物研究进展[J].现代药物与临床,2015,30(3):345-350.
[7] 杨瑞青,肖镇.痛风的诊治现状及进展[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6,10(4):550-553.
[8] 张卓莉.痛风最新诊治指南解析[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14,6(10):1-3.
[9] 苏金梅,曾小峰.痛风的药物治疗进展[J].临床药物治疗杂志,2014,12(4):13-17.
[10]乐文君.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中医体质分布及危险因素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3.
[11]霍晶晶,王丽,于世家.中药治疗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用药规律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15,42(4):685-687.
[12]朱丽臻,邱联群.痛风的中医药临床研究进展[J].新中医,2007,39(10):101-102.
[13]眭蕴慧,殷海波,石白.从中医“治未病”探讨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的防治[J].北京中医药,2013,32(1):44-46.
[14]杜静.中医药治疗痛风临床研究概况[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8(2):174-177.
[15]刘颖.中医药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研究进展[J].中医研究,2013,26(4):74-77.
[16]李迎巧,高建东.尿酸性肾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4,15(3):270-272.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TCM in Gout Stages
HE Yujun,MA Jiawei,SUN Jing.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Zhejiang,Hangzhou 310053,China.
Gout is a kind of rheumatic autoimmune disease with a clear clinical stage.Their clinical manifestation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blood uric acid,acute arthritis,chronic gouty arthritis and joint deformities and kidney damage.Western medicine has limitations on the treatment of it,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and controlling the condition development.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five stages from the angle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Chinese medicine.It analyzes its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and gives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methods,reflects the powerful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out;Clinical stage;Syndrome differentiation;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Q16H270016)
△(电子邮箱:tomorrow123go@163.com)
R589.7
A
1004-745X(2016)11-2072-03
10.3969/j.issn.1004-745X.2016.11.017
(201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