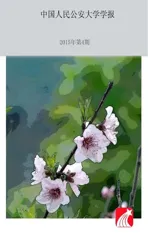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型”的转喻认知理据分析
2015-01-21罗赞,杜芳
罗 赞, 杜 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 北京 100038)
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型”的转喻认知理据分析
罗赞,杜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部, 北京100038)
摘要转喻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交际之中,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有其认知动因。其中理想化的认知模型及其格式塔结构是指称转喻运作的基本框架和前提条件,在特定的语境中,理想化认知模型中各个概念之间的显著度及可及性的差异使得人们倾向于以显著度较高的转体来激活显著度较低的转喻目标,语境对于指称转喻的使用具有很大的限制性。
关键词转喻; 理想化认知模型; 理据
0引言
转喻(metonymy)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关于符号任意性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区分了四种“隐喻”,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转喻”的一种隐喻。转喻在古希腊语中的本意是“换名”,即用一个名称来代替另一个名称。一直以来,转喻被看作是语言的修辞性用法,是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效果而以一种非正常的表达方式来故意对语言规则的“偏离性”使用。韦氏大辞典对转喻的解释是 “以一个名称来代替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名称的修辞格”,因为此种定义涉及到事物名称的替代,因此又被修辞学家称为指称性转喻,本文所探讨的转喻即为指称性转喻。例如:
a.The ham sandwich left without paying.
动词 “leave” “pay”要求在主语必须为人时句子才有意义,但例1的主语却是一种食物,这就是偏离了语言的正常使用。“ham sandwich”这个语言符号通常是指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食物,而在在此句中却用来转指点这道餐的人,这种名称的替换使用即转喻。但事实上,有些转喻并没有偏离语言的使用规则,例如:
b.In the play, Julius Caesar was too young.
例2的表达完全符合语言的使用规则,但在这个句子中,“Julius Caesar”却是转喻的使用,用历史人物指代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由此可见,修辞学
对转喻的解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尝试从认知的角度对各种语言想象进行解释。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Johnson)[1]的研究表明,隐喻和转喻是人们认知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并分析了其普遍性特征。瑞登和考夫科思(Radden&Kovecses)[2]区分规约性转喻和非规约行转喻: 规约性转喻指有的概念转喻模式已经固定,而非规约性转喻则是指转喻模式是临时性的,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大。潘桑和桑恩伯格(Panther&Thornburg)[3]进一步发展了转喻理论,提出了转喻的层次性。以上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转喻在语义和语法层面的认知研究,其实转喻是语言的使用特征。斯特劳森(P.F. Strawson)是日常语言学派牛津学派的元老之一,早在上世纪初,他就意识到了指称的使用特征,认为指称发生在人们对词语的使用过程,而语言使用时的具体语境,决定了指称的实现,例如:
c.I want a bottle.
如果说话人想要一个瓶子来装水,那这里的“bottle”就不是转喻的用法;如果说话人在商店想要买一瓶装饮料而不是罐装的,那“bottle ”就是转喻,即容器来指代里面的内容。由此可看,对转喻的研究不能脱离语境。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在言语交际中转喻能够得以实现及语境对它的制约作用。
1基于“相近性”联想的转喻
所有对转喻的研究都注意到了转喻中转体和转喻目标的关系, 布瑞登(Bredin) 认为,“隐喻创造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转喻预设了这种关系”[4],即转体和转喻目标的关系是先于转喻的使用而存在的。这种关系被描述为“有联系的”,“密切相关的”或“邻近性”,本文使用“邻近性”这一说法因为它能更具体地揭示转体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乌尔曼(Ullman)[5]认为这是一种语义上的邻近性,而认知语言学家泰勒(Talyor)[6]和德尔文(Dirven)[7]认为这是一种概念层面的邻近性,因为转喻同隐喻一样,其表层的语言形式是人类深层次认知方式的体现,是人们认知外部世界,对认知对象概念化过程中的一种思维模式,因此这种邻近性是思维过程中两个概念的邻近。转喻中两个邻近性概念的转指是以特定的概念结构为背景的,即转喻是在特定的认知模式中产生的。莱可夫(Lakoff)[8]认为,我们是用一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CM)来组织大脑中的知识储存。这种认知模型具有格式塔结构,是整体性被感知的,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某一领域认知的所有中抽象出来的,一致的概念总和。它不仅包括人们对某一领域理解的百科知识,还包括该领域的文化因素。例如,“母亲”这一概念的ICM 应该包括:生殖模型—要生孩子;遗传模型—提供一般基因;养育模型—担当养育任务;婚姻模型—是父亲的妻子;谱系模型—是孩子最直接的女性长辈等,每个模型中包括的各种相关认知,就构成了“母亲”这个概念的合集,即由一系列认知模型组合形成的复杂模型就是“母亲”的ICM。转喻就是以这种认知模式为基本框架而实现的,即转体和转喻目标是共存于这种认知模式之中的。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中,诸多的概念是以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包括节点和链接[9]。人类记忆与电脑记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电脑中的信息都是以特定方式储存的,既有分类又有关联。人类大脑储存的信息、概念也一样以特定方式形成网状系统。在这个概念网络中,所有的概念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而概念之间的相关性就是连接节点的箭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测试发现人类大脑中概念网络的系统性、条理性。首先让一个人在10秒内写出所有以T 开头的单词,然后再给他10秒钟写出所有跟家具有关的单词,我们会发现他第二次写出的单词更多。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大脑中存在着跟家具有关的概念网络,而没有以某个共同字母开头的单词的概念网络。我们的记忆中储存了成千上万种不同领域的概念网络。当这个概念网络上的一个概念节点被语言信号激发,其能量会传播至它邻近的节点和链接,相邻的概念也会被激活。人们在进行认知活动时对有关概念的提取就是建立在这种扩散激活模型基础上的。这种扩散激活模型被描述为“一个概念激活另一个相关概念的过程”,这是人们认识新事物,进行概念整合的心理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转喻之所以能够实现,其认知基础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中存在各个不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型,每一个认知模型都是一个概念网络,在特定的环境中,某一个概念的激活就会带动同一认知模式中具有邻近性的概念的激活,能够实现以此代彼。
2显著度与可及性
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转喻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实质是概念性的。杰肯道夫[10](Jackedoff)认为,指称的实现有赖于语言使用者,即指称是相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的,这正如对空间距离与时间的体验依赖于观察者内在的参照框架。那么,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为什么指称转喻会发生呢?这就涉及到人类一个基本的认知心理,即显著度(salience)。显著度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11]。它对于转喻的意义在于,人们常用显著度高的事物来转喻显著度低的事物。例如:
d.The kettle is boiling.
e.He broke the window.
在例4中,水壶被用来转指里面装的水,因为从人们的视觉感知角度,水壶比里面的水更容易看到,具有较高的显著度。而在例5中,打破的其实是窗户玻璃,之所以人们常常用“窗户”转指窗玻璃是因为人类心理的格式塔效应,即人类倾向于以整体性来感知对象,因此,整体的显著度要高于部分。兰盖克(Langacker)[12]比较了几组有关联的认知对象的显著度问题,例如在人与非人中,人的显著度高于非人,在整体与部分中,整体的显著度高于部分,可见事物要大于不可见事物的显著度。沈家煊也认为,相对于部分,整体的显著度更高,相对于容器内的物品,容器的显著度更高[13]。高显著度的认知对象,其对应的语言形式就有较高的可及性,在语符的编码解码过程中,对其进行处理更具经济性。可及性( accessibility)又称便取度,是指说话人从大脑信息存储系统中激活有关记忆或语言单位的方便程度。由于经济原则的制约,可及性高的信息会被优先处理。在人们记忆的概念网络中,显著度高的概念相应地具有较高的可及性,更易被优先提取和处理。
显著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用概念A来转指概念B是因为相对于B,A的显著度更高,但是这种高低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语境中,A与B显著度的相对高低也会有变化。例如,因为格式塔结构,人们往往用整体转指部分,但有时候却正好相反,例如:
f.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
在这个例子中,部分被用来转指整体,因为在大学里,聪明的头脑是人们更重视的因素,因此 “heads” 被用来转指 “person”。而对于人与非人显著度的问题,语境也起很大作用。如果是在餐馆,服务员会用桌号来转指这个餐桌上的客人,如果是在医院,医生会用床位号来转指这个床位上的患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各个概念的显著度及可及性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如果离开了语境去讨论转喻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3认知语用学的语境观
语境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境因素直接影响着交际是否可以成功,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制约因素。任何言语交际行为都不能脱离语境而独立存在。语境分为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言内语境指交际语言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即上下文;而言外语境则是指言语交际时的一切外在社会因素,如社会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还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及交际者本人的个体因素,等等。这些语境因素是先于交际行为而存在的,交际双方根据这些语境因素对话语进行推理,以实现交际的成功进行。但是此种语境理论不能解决主客观的对立问题,并且对话语含义的生成和理解的解释力不够,这一点引发了诸多语言学家对它的批判。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传统的语境概念是静态的,而在真实的交际过程中,语境则是动态生成的,它其实是一种认知过程,即认知语境。斯铂珀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14]认为,人们认知外部世界,获得有关信息,进而形成有关心理表征,形成知识储存系统。知识系统之间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性,可以被推理、感知,形成一系列可显映的概念或命题。当所需的外部交际环境得到满足,这些心理表征便会被认知系统所凸显,形成某种语境下的意识或想法。不同的交际个体,其认知能力和所处环境也不尽相同,形成各自特有的认知语境。交流双方认知语境中重合的部分,对双方是互为显映的。只有在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中,交际才能正常进行。
认知语境观强调语境的动态性。在交际过程中,随着话题的推进,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是在不断地变化、重组,也就是说,理解每一句话语的认知语境都是不同的,双方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交际者的交际目的会不断激活相关的语境因素、还有一些客观事物共同构成了动态的交际认知语境[15]。例如,在图书馆, 学生想要借阅一本书,会与图书管理员有以下对话:
g.S: Can I borrow Oliver Twist?
A: Charles Dickens is on the top shelf.
在此轮对话中,学生想要借本《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而管理员则说狄更斯在书架的最上面一层。在图书馆这个环境中,借书是常态,学生与管理员的交流也大多跟书有关。学生想借《雾都孤儿》这本书,图书管理员大脑中有关《雾都孤儿》的概念网络被激活,而与一部作品相关的最显著信息是它的作者,并且,对于文学作品图书管理员往往以作者为区分在不同的位置进行摆放。因此对于管理员来说,关于书的位置他首先能够想到的是哪个作者在那一层,再加上他本身认知模式中作者与作品的密切相关性,使他用 “Charles Dickens”来转指其作品。而对于学生而言,管理员使用“Charles Dickens”也激活了他大脑中有关“Charles Dickens”的认知模型,还有他本人的意图,这些都重新构成了新的交际语境,使他能够理解管理员的话语,从而保证交际的成功性。
4语境对转喻的制约
认知语境观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言语交际中,转喻形式千差万别,这是因为对于不同的交际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的认知模式中哪两个概念之间构成邻近性是不相同的,概念之间的相互显著度也是在变化的。转喻是基于人类概念网络中两个概念的邻近性而生成的,而这种邻近性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进行成功交际,双方既要受到语境因素制约,同时又要不断地控制、构建语境因素已达到最佳的关联性。双方互为显映的语境是转喻得以实现的条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语境对转喻的影响和制约:一是同样的转体在具体的语境中转指不同的转喻目标。二是不同的转体在具体的语境中转指相同的目标。我们看下面一组例子:
h.①Chicago is all excited about the Bulls.
②Chicago has just won another Champonship.
③Chicago was late in sending in its applications.
④Chicago was right here in the stack between Dallas and Memphis.
在例8中Chicago分别转指“芝加哥市民”、“芝加哥队”、“芝加哥市政府”和“芝加哥的申请材料”。因为在“Chicago”这个概念的理想化认知模式中,包括与“Chicago”相关的一些列知识结构,如这是一个城市,城市就有市政府,有市民,还有这个城市的运动队等等,而在不同的语境中, “Chicago” 就会激活不同的相关概念,从而形成“一词多指”。再看下一组例子:
i.①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
②We need a couple of strong bodies for our team.
c.They are just new hands.
在这组例子中 “faces” “bodies” “hands”都是转指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人”的认知模型中人脸、身体、手等不同的部分分别得以凸显、具有较高的显著度及概念提取的可及性,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被用来转指相同的目标。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转体与转喻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动态生成的,因此,转喻实际上是语言的使用特征,如果脱离了语境便很难对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转喻现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语境概念包括了更宽泛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的上下文,还有交际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交际者本人的个体经验、个体倾向性,具体的交际场合,甚至交际者当时的心理状态等,所有这些因素动态地构成了转喻能够实现的语境条件。
5结语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语言现象受认知规律支配。因此,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转喻之所以能够实现“以此代彼”的功能是建立在人们的认知特点及规律之上的。人们认知外部世界的理想化认知模型中,各个概念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每个概念都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一个概念的激活可以带动邻近概念的激活。由于经济原则,那些具有较高显著度的概念常被用来激活具有较低显著度的概念,而显著度的高低则有很大的语境依赖性。因此,转喻实际是一种语用现象,语境对转喻的实现具有很大的制约性。
参考文献
[1]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PANTHER K U,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9:17-60.
[3]PANTHER K U, THORNBURG L L. Thornburg.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C].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3:1-22.
[4]BREDIN H. Metonymy. Poetic Today[J].1984:45-58.
[5]ULLMANN S. Seman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M]. Oxford: Blackwell, 1962: 218.
[6]TAYLORL J. Linguistic Categorizait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123.
[7]DIRVEN D, VERSPOOR M H.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14.
[8]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9.
[9]BEST J B. Cognitive Psychology [M]. New York: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228.
[10]JACKENOFF R.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304.
[11]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1999(1):12
[12]LANGACKER R W. Langacker.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13]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1999(1):13.
[14]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18.
[15]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147.
(责任编辑陈小明)
作者简介罗赞(1975—), 女,河南开封人, 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化,警务英语。
中图分类号D0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