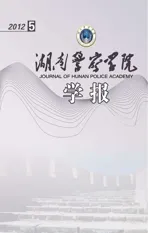“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2012-04-12冀洋
冀 洋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冀 洋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定性不定量;刑法谦抑性;法益关联性;防备一体化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从罪状表述上看,新分立出来的盗窃行为(下划线部分)消去了数额、次数等定量因素的限制;并且每一个字本身表达的也都是行为“质”,没有释放行为的“量”。这种“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模式带来了“动辄入罪、刑法膨胀”的尴尬与危险。那么以下问题就不得不去厘清:这一模式下的“非数额型盗窃”的立法意图是什么?其法益关联性何在,是否意味着盗窃罪的手段变得不再“平和”?行为在定性之后“是否一律入罪”?只有经过这些指向立法目的与司法现状的反思,才能为“非数额型盗窃”的入罪找到妥当性的根据,才不至于使司法者既“大手大脚”又“蹩手蹩脚。
一、“定性不定量”的立法冲动稀释着刑法谦抑性
世界范围内,刑法典在具体罪状的设定上有“定性不定量”与“定性且定量”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指立法者在对罪状描述上,只对行为性质进行考察,不作任何量的分析,在形式的犯罪构成中只含有“质”而没有“量”;后者是指立法者在对罪状描述上,既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考察,又对行为中所包含的“数量”进行评价[1]。
大陆法系的大多数国家(地区)采用的都是“定性不定量”的入罪模式,如日本刑法第235条,窃取他人的财物的,为盗窃罪,处……;德国刑法第242条,行为人以使自己或者第三者违法地占有的意图而拿走他人可移动的物品的,处……;台湾地区刑法第320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窃取他人之动产者,为窃盗罪,处……。这与我国新修正的“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既然“定性不定量”模式如此普遍,为何还要质疑盗窃罪的这种修正呢?这就需要反观其所依存的中国语境了。
我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一般认为,这可归结为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而“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属性”,对其他违法行为来说,“社会危害性虽然也有一些,但没有达到像犯罪这样严重的程度,它们并不触犯刑律,也不应受刑罚处罚”。[2]这表明我国刑法典明确规定了“定性又定量”式的犯罪概念,即犯罪构成要件的本质是“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达到一定质和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3]。不仅如此,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五条,“只有违法行为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可能引起国家刑罚权的发动”;[4]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的,处……。所以,我国确立的是“违法→犯罪”二元的制裁体系(小刑法),明显区别于欧陆刑法“重罪→轻罪→违警罪”的犯罪分层体系(大刑法);并且当前的“刑事立法(至少是财产犯罪的立法)并未做好观念性和体系性变革(变二元机制为刑事制裁一元机制)的准备”。[5]那么,同样的“定性不定量”模式在中国必然具有与众不同的评价体系和“大国法治”的独特境遇。
根据立法者的解读,“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原因在于,“虽然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并对群众人身安全形成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往往由于犯罪分子一次作案案值达不到定罪标准无法对其定罪处罚,只能作治安处罚,打击力度不够,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导致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屡打不绝。因此建议……不论数额、次数多少,均可以作为盗窃罪处理”。[6]从“但”字转折关系看,与其说是出于社会危害性考虑,倒不如说是刑法前置法的“失灵”推动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单独入刑。换言之,“非数额型盗窃罪”的立法意图首先就是为政府行政管理能力虚弱的窘境解围:将达不到“数额较大”的“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单纯以行政处罚,只会“抓了放、放了抓”;“不论数额、次数”一律入罪,则“一逮一个准”、“伸手必被捉”,如此既可以有效威慑犯罪,也不再“案件难办”了。可是,(1)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化,再将数量繁多的“扒窃”予以入罪,那么,“留下来的盗窃违法行为还剩多少?”[7](2)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盗窃行为强行纳入刑法轨道,那么“但书”包涉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何以存在?(3)将治安警察处理的行政违法行为交由刑事警察、检察官、法官处理,无疑压缩了行政执法空间,扩大了刑事处罚范围,这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与资源消耗。由此,刑法面对那些未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轻微盗窃,先于行政法提前登场,就成为了替代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法”、未穷尽其他措施即予启动的“最先保障法”。[8]
其次,“非数额型盗窃”的入罪还重于对人身伤害的提前预防。如立法者认为,将“扒窃”入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扒窃往往为多人共同犯罪,迫使被害人不敢、不能反抗,一旦反抗,他们往往进一步伤害被害人人身”,[9]有必要提前威慑、防微杜渐。先抛开法益不论,立法者的理由恰恰说明刑罚更重的第269条“事后抢劫罪”的威慑效果并不理想,既然如此,如何确信刑罚更轻的“非数额型扒窃罪”的威慑效果呢?这种“带有背水一战的冒险性质的犯罪对策之后,如果其抑制犯罪效果仍不明显的话,下一步还能有什么样的犯罪对策呢?”[10]舍去“定量因素”,不计数额、次数的倾向传递了一种以“行为无价值”控制犯罪的规则功利和“万能主义、积极活用”的刑法迷信。立法者每当力有不逮之时,总偏执于犯罪化、设新罪,把刑法臆想为“万能的上帝”,动辄挥舞刑法大棒俨然成为了一种工具式需求的立法惯性。
可见,无论从刑法出场的时点看,还是从刑法干预的场合看,“定性不定量”模式下,不计数额、次数的“非数额型盗窃罪”显然是一次立法的浪漫与冲动,它使刑法“二次法”、“补充法”的基本特征黯然失色,不断稀释着本已“伤不起”的刑法谦抑性。
二、“罪与非罪”的司法迷失消褪着法益关联性
众所周知,面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定性不定量”模式,“一律入罪”还是“区别对待”?官方表达了的大为不同的声音,一时间争议不断。[11]同样,在“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适用中,尤其是对数额极小的行为,公安、司法机关的处理也大相径庭。以扒窃为例,有的不论数额一律定罪处刑;有的因进退两难而“折中”为劳动教养;有的先“劳教”,后又犯的,再起诉[12]。如此选择性执法,主要源于司法者受立法者“刑法依赖综合症”的传染,对“非数额型盗窃”之罪与非罪标准的误解与迷失。
“刑法干预权的界限来自刑法的任务与目的,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是保护法益,所以刑法所干预的只能是侵犯法益的行为”,[13]因而必须首先明确“非数额型盗窃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对此,立法者的逻辑是:“进入他人家庭居所盗窃,影响群众最基本的安全感”;“携带凶器盗窃,往往有恃无恐,一旦被发现或者被抓捕时,则使用凶器进行反抗……对他人的人身形成严重威胁”;“扒窃行为直接接触公民人身,往往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建议对这三种盗窃行为,不论数额、次数多少,均可以作为盗窃罪处理”[6]。据此,“非数额型盗窃”单独作为“定性不定量”式的基本犯(而非加重、从重情节)且不论数额一律入罪已经意味着,盗窃罪不再情困于财产法益,而更关心“群众的人身安全”、“群众的安全感”了。以上“一块五案件”的处理也遵从了这一“教义”。可问题是:
其一,盗窃罪何言“群众”?“群众”是一个政治话语,即“人民大众”、“公民的绝大多数”。在分则的分类中,盗窃罪是侵害个人法益而非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即便是多次盗窃、盗窃多人也绝不可能同时侵犯“不特定的人或多数人”(竞合的情形除外),否则就是“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扰乱公共秩序”了。以“群众”作为一种犯罪受害群体纳入犯罪化的考量,无疑是立法者从国家整体主义的角度表达的对社会集体的温情关怀,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极容易使立法者“基于保护共同体安全的考虑而放弃对行为产生实害的要求,从而通过确立危险犯来进行刑法干预”,[14]尤其在那些个案上很难确定是否造成了法益实际侵害的场合。如此,保护就会提前,法益关联性就会稀薄。如下所述,“非数额型盗窃”的入罪逻辑正以此为起点。
其二,盗窃罪如何“危及”群众的“人身安全”?在盗窃罪中“行为→财产”本来是最为平和的过程——“偷”,它的人身危害性何来?冲动的立法者及迷失的司法者会说,那是来自于被发现后的反抗行为。假设这一说法合理,那么在不计数额而又撇弃第269条“事后抢劫”对人身安全之“实在危害”的情形下,对“非数额型盗窃罪”的入罪考察就只剩下对人身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使盗窃成为了威胁“人身安全”的危险犯。不仅如此,在第二百六十四条的文本中找不到“足以……”等任何要求危险具体化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在其基本犯入罪的场合,纳入的危险评价——如同“危险驾驶罪”、“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一样——只是行为的“抽象危险”。可见,与传统盗窃罪相比,“非数额盗窃罪”更注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并且由实害犯(数额)转为抽象危险犯。令人惴栗的是,如果处罚诸如盗窃罪这种古老的自然犯罪都只需考察“抽象危险”,那就意味着刑法的所有犯罪只要“抽象危险”即已充足实质违法性了。这无疑“透显立法者的霸气,是刑法把防卫线向前与向外的扩张”,[15]这样的盗窃罪也无所谓“手段平和”了,它与财产法益也没多少关联性了。可是,刑法并未将行为更“不平和”的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规定为抽象危险犯,那么为何对盗窃罪如此“礼遇”呢?
其三,什么是群众的“安全感”?“安全感”的对立面即为一种“慌乱不安”,二者是风险刑法理论中的关键词。风险刑法下的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损害,而是一种慌乱不安”,即“在主观上具有罪恶的意图或者客观上对所有生活领域的安全条件造成损害的行为”。[16]如果“非数额型盗窃罪”以防范对人身的抽象风险为目标,在具体危险、实害发生之前就发动刑事制裁,那么它就是风险刑法思维的产物。可是将仅具有抽象危险而离具体危险、实害还很遥远的盗窃行为犯罪化,意味着“作为刑事立法特征的犯罪行为‘法益关联性’的丧失被充分表现出来”。[17]
而财产法益关联性的消褪必然影响着犯罪行为要件及其着手、既遂的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会更加扑朔迷离,因为“与法益侵害结果的引起相关的一切违法要素同时都是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只能像这样,确认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行为”。[18]如,有检察官认为,“入户盗窃侵犯的是双重法益,不但侵害了公民财产权,还侵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全权”;[19]有检察官进一步认为,“入户窃得财物的,无论财物价值大小,只要使财物脱离了户主的实际控制,就应当认定为盗窃既遂……入户未窃得任何财物,由于未对户主的财产所有权造成实质性的侵犯,应当认定为盗窃未遂”;[20]有法官走得更远,认为着手实施入户行为时就已经对住宅安宁权造成了侵犯,即使未盗得任何财物,也构成盗窃罪既遂[21]。
可见,由于立法者的冲动,司法者对“罪与非罪”的标准陷入了认识模糊,实践中的各种司法迷失不断刺激着法益保护的抽象性、推动着法益保护的早期性,最终消褪、消解着其与财产的法益关联性。
三、“犯罪圈膨胀”的刑法风险催促着防备一体性
行文至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情绪冲动的立法者与意识迷乱的司法者对“非数额型盗窃罪”不计数额、次数并纳入抽象危险的考量,那么将继续动摇刑法谦抑性、逸出法益侵害性,由此带来的动辄入罪、刑法膨胀的负效应,必会使刑法屡次“以法的形式损害法本身”。[22]
现代法学理论一致认为,“法律的应用和实施在现代法律科学中被认为是核心的问题”。[23]于是,为了犯罪圈的明确与妥当,司法者必须优先扛起“释疑”、“矫枉”的重任——从司法上为“非数额盗窃”设定一定高度的犯罪门槛。
从实体法的角度,犯罪门槛的高低(1)首先取决于法益的确定,这是“定性”的前提。面对前文所述的法益关联性的不断消褪及其产生的种种疑问,答案只能是:一切盗窃行为都应当与“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相关联,“非数额型盗窃”仍然是以结果(数额)论的实害犯,而绝非以行为论的危险犯;着手、既遂等一系列“罪与非罪”标准的认定只能以财产法益为核心,除此之外的都是不合逻辑的“胡思乱想”。(2)其次取决于定性之后是否定量。“但书”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也指出,“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对于财产(犯罪)来说,这样的尺度就是它的价值(价值之必然表现方式是交换价值→价格→数额,笔者注)”。[24]
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为“非数额型盗窃”的入罪确定一种数额的定量标准,其反面就是,如何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盗窃行为出罪,也即如何适用“但书”。对此,有两种策略:(1)先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形式解释),然后再直接以“但书”否定(可罚的)违法性,继而出罪;(2)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能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实质解释),对符合“但书”的行为应以不符合构成要件为由宣告无罪。笔者以为,只能选择第二种策略。由于“但书”是总则指导分则的一个宏观概念,其本身是模糊的,就数额而言,如果说1元属于、500元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之间的50、100、200元呢?其临界点是多少?这是不能够自由裁量的,况且“裁判官的法律观与价值观各不相同,轻微性的判定就可能见仁见智,以至于难以划一适用法律,从而导致法律公平性的丧失”。[25]以脱离具体判断资料(构成要件)的“但书”去释放隐性的数额要素并对个案作具体违法性判断,结论可能一样,但却更容易陷入主观性、恣意性、选择性。所以,“但书”对罪与非罪的筛选功能“不是表现在直接依据第13条之但书而认为某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是表现在其指导法官实质地理解与适用犯罪构成之解释机能上”。[26]这就把问题消解之道引向了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即要保证“非数额型盗窃罪”所反映的财产法益侵害性确实达到了“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这也就须要在构成要件中确定一个“值得引起司法者注意”的一定量的数额,唯此,才能“更早地得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结论”。[27]例如,为了应对“刑八”颁行后的执法尴尬,苏州市公检法联合下发新规,率先对“非数额型盗窃”规定了500元的数额起点(普通盗窃为1000元)[28]。这种实质解释虽然保守,但显示了司法的冷静与慎重,值得肯定。
“刑法是刑事司法体系得以存在、运行的实体法律依据;反过来,刑事司法体系则是刑法得以解释、适用的基本依托”,[29]因而犯罪也是“一个动态的程序意义上的范畴”。[30]
从诉讼法的角度,盗窃案件(公诉)的司法程序一般是,“公安局立案→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而只要“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换言之,即使在静态实体上构成犯罪,只要最终没有进入审判程序或者没有被宣判有罪,行为人就可以避免被贴上“犯罪标签”,他就是无罪的。这就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在程序中预留了空间。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法第110、173条;旧法第86、142条),对明显不符合构成要件即“没有犯罪事实”的行为,当然不准立案、起诉;对“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也应当不予立案或者可以不起诉。可见,在刑法教义之内明确“轻微刑事犯罪”的范围及其责任追究的启动机制,为“非数额型盗窃”的犯罪圈膨胀在程序上设防是可遇可求的。而且,这种“放小”的策略[31],还能为那些对实体上何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认识混沌的司法者在程序上提供一种“宁可错放、不可枉杀”的保障人权的权宜之计(大宪章)。
而这种具体的程序操作有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最高司法机关以刑事政策解释的方式……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变为具体的实施细则”。[32]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贯彻刑事政策的若干文件,笔者以为,对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可以不立案、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人民法院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没收违法所得的,移送有关管理机关处理(但绝对禁止适用劳动教养):(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残疾人、老年人、严重疾病患者等无再犯能力的;(3)全部退赃、退赔的;(4)偶犯、初犯并自首或立功的;(5)被胁迫参与且未分赃或分赃较少的;(6)与被害人就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达成和解协议并切实履行完毕的;(7)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综上,对“不应罚”的“非数额型盗窃”,可以通过实质解释无条件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不需罚”的“非数额型盗窃”,可以通过“放小”刑事司法政策的细化有条件阻断有罪判决的追究程序。这就是防备其犯罪圈膨胀的一体化路径。
[1]储槐植、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J].法学研究,2000,(2):34-37.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3]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5.
[4]于志刚.二元制立法模式引发的司法尴尬[J].公民与法.2010,(4):2.
[5]付立庆.让立法远离浪漫主义的迷雾[N].法制日报,2011-3-30(10).
[6]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三)[J].人民检察.2011,(8):57.
[7]李翔.新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路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1,(5):114.
[8]刘艳红.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J].环球法律评论. 2012,(2):79.
[9]朗胜.刑法修正案(八)解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J].2011,(2):160.
[10]黎宏.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6):103-107.
[11]陈伟.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2):119-120.
[12]《扒窃1.5元获刑8个月被处罚金1千》[EB/OL].(2012-05-28)[2012-08-01].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205/t20120528_872190.html;《扒窃一元拟劳教》[EB/OL].(2011-07-08)[2012-08-01].http://www.cq.
xinhuanet.com/news/2011-07/08/content_23194664.htm;《扒窃1元被劳教又扒窃1.5元被判刑》[EB/OL].(2011-05-23)[2012-08-01].http://news.163.com/12/0523/05/825S7A2J00014AED.html.
[1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
[14]王振.风险与超越: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理论之流变[J].法学论坛.2010,(4):72.
[15]林东茂.刑法综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1.
[16][德]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J].刘国良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38.
[17][日]关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A].王充译.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45.
[18][日]宗冈嗣郎.犯罪论与法哲学[M].陈劲阳,吴丽君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81-82.
[19]孙荣杰.入户盗窃的刑法解析[EB/OL].(2012-02-03)[2012-08-01].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theories/essay/201202/t20120203_797838.html.
[20]刘兵.认定“入户盗窃”要把握三种情形[N].检察日报. 2011-05-25(3).
[21]张星.对非数额型盗窃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与适用问题的探讨[EB/OL].(2012-07-04)[2012-08-01]http://www.hafxw.cn/Article/xhlt/sfdy/201207/258618.html.
[22][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94.
[23][美]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唐前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3.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
[25]于改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A].赵秉志.刑法论丛(第1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9.
[26]苏彩霞、刘志伟.混合的犯罪概念之提倡[J].法学.2006,(3):90.
[27]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4):62.
[28]苏州严打入户盗窃及扒窃“入罪”案值降到500元[N].现代快报.2011-11-23(F 4).
[29]刘远.司法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J].现代法学.2010,(7):25. [30]陈卫东.刑事诉讼程序意义上的“犯罪”定义[J].法学研究. 2008,(3):154-155.
[31]蔡道通.论“放小”的刑事政策[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8-29.
[32]姜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J].理论导刊.2011,(1):78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Crim inalation of Larceny w ithout Amount
JI Ya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46)
The Eighth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has criminalized burglary,stealing with weapon,pickpocketing in a form of only requring qualitative analysis.This legislative intent deserves much reflection.From the angle of the whole law systems,an ordinary illegal ac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a criminal act,and therefore larceny without amount strikes against the modestly restraining spirit of criminal law;from the angle of rechtsgut,all larceny acts still infringe others’property rights,and consequently the larceny without amount makes the relevance of property rechtsgut fade away.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the extensification of criminal law’s intervention,judicators must read the rule in an objective and material way and should set up defenses in both substantial stage and procedural stage.
qualitative not quantitive analysis;limiting criminal law;relevance of rechtsgut;unitive defense
D924.35
A
2095-1140(2012)05-0042-05
2012-08-28
冀洋(1988-),男,山东临朐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解释学研究。
叶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