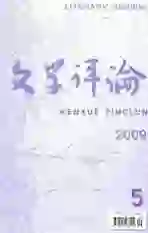论周作人的儒释观
2009-01-08哈迎飞
哈迎飞
内容提要周作人认为自己的思想“半是儒家半释家”,但长期以来,人们很少正视儒家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对他的思想、创作、人生道路的复杂影响,亦很少研究他这种独特的儒释观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以及它独特的思想内涵。本文认为,强调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儒家而非儒教,自觉地解构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光环,并以佛教中反本体论的中观思想改造儒家的中庸思想,使原始儒家中富于理性和人道的思想精华真正发挥出来,形成既有中华文化之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文明,是周作人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最主要贡献。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风云人物之一,作为一流的文学家和学人,周作人在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散文创作及思想革命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就已有人明确地将他视为深刻的思想家。周作人的文学造诣与他深厚的思想功底分不开,在某种意义上,正如舒芜先生所说:“他的各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的思想家身份再次得到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绩,但由于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及其他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从总体上看,周作人研究的成果与周作人自身的成就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周作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评价太高,而是估计不足,不是研究‘过热,而是有许多研究的空白或薄弱点,还存在着许多误读与曲解,在追求周作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对周作人独特的“儒释观”重视和研究不足,是目前制约周作人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就曾宣称自己“半是儒家半释家”,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思想的来龙去脉时,他再次谈到自己的儒家立场,并将自己一生杂学的归结点概括为“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如“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颇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丽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日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等。
对儒家思想的思考,可以说是贯穿周作人一生的思想红线,从留学日本时批判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删诗定冗,“天阏国民思想之舂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到“五四”时期,致力于礼教和三纲伦理的解构,以及40年代重提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儒家而非儒教,理性、人道、科学始终是周作人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
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像古希腊文化一样富于理性,但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自然之伦理化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具体来说,这种伦理化的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然儒教化,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来解释或附会动植物生活,如把猫头鹰说成是不孝鸟,把姑恶鸟说成是不孝妇所变,把“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蚯蚓说成是独善其身的廉士等。一是将自然生物现象道教化,如桑虫化为蜾赢,腐草化为萤火等,极尽神秘玄妙之能事。周作人指出,自然之伦理化绝非小事,因为这些传说和迷信“实在都从封建思想生根,可以通到三纲主义上去”,绝不可等闲视之。另一方面。考虑到传统中国政治、宗教、伦理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始终未曾解体,伦理道德在中国不仅拥有崇高的地位,而且拥有神圣的权威,以至于自古以来“即使有人敢诽谤皇帝,也总不敢菲薄圣人”,这也使周作人坚信用科学之光清除附着在传统伦理上的种种谬说误论,把人道从天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使道德从政教合一的传统中独立出来,是现代中国思想启蒙和道德重建中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工作。正是为了厘清道德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上世纪40年代,周作人正式提出了“伦理之自然化”的口号。“伦理之自然化”是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也是他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上世纪4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亦谈到“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为了解构附着在儒家道德身上的超自然神力,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在谈到儒家“半宗教半哲学”的特点时,亦曾强调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必须厘清。虽然李泽厚所提出的将作为个体的内心信仰、修养和情感(宗教性私德)的伦理道德与作为社会的外在行为、准则和制度(社会性公德)区分开来的解构之法,与周作人所提出的通过发展科学,打破“天”的神秘性来使儒家道德从“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传统中脱颖而出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使道德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追求,却是一样的,而且由于周作人对这个问题发现的早,思考的深,强调的多,他在后世的影响也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共鸣。
“五四”时期周作人还曾有意识地比较儒家思想与希伯来宗教思想的异同。他认为基督教虽然在压迫思想自由上很有害处,但它所宣扬的“博爱”、“牺牲”、“怜悯”等价值取向对于我们肃清法家文化的“余毒”,摆脱对“暴力”和“强权”的迷信,解构儒家文化中君权至上,专为强者辩护而非为民争权之不足,以及改变国人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蔑视人权的病根等,却是极有意义的。过去,我们常常批评“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托尔斯泰的“无我爱”、新村式的“非暴力革命”和“爱之福音”文学的关心和提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并全盘否定之。事实上,在这种看似脱离现实的乌托邦里,有着周作人对本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传统中国式的暴力革命及民众造反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睿智思考。
将儒家思想放在与古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对比中,拷量儒家文化的优长得失,使周作人的研究视野显得十分开阔,不仅如此,他还自觉地从儒、释、道、法等中华文化内部比较反思儒家文化的优劣得失。周作人指出,中国的儒家实际上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和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但由于“法家”一直占据上风,所以这种化合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成。对于后世儒生“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的作法和“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的倾向,周作人极为不满。他多次撰文批判对法家化的酷儒、禅和子化的玄儒和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士化倾向,并称赞佛教的理性品格和广大厚重的人生态度,“根本与儒家相通而更为彻底”。对于强权的反抗与对于弱小的同情,使周作人由衷地喜爱大乘菩萨救世济人
的弘愿,“觉得其伟大处与儒家所说的尧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读了令人感激,其力量似乎比经书还要大些”。他曾多次引用《六度集经》中的“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来表达自己的济世弘愿。印度佛经文学的伟大气象和超迈情怀,使周作人深感“要了解中国的思想和文艺,佛教这一方面的许多东西不可不知道一点”,“佛教文学是何等伟大,但是中国学者能有几人是研究得有成绩,很叫人失望”。
同时,对老庄道家,周作人指出也要具体对待,不能盲目否弃,尤其是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自然论和齐物论等思想,在他看来,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庄子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提到庄子,人们几乎马上就会把它与“阿Q精神”、“滑头主义”、“混世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消极隐逸”等联系在一起,如鲁迅诅咒自己思想上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胡适批判庄子的任天、安命、处顺之说“流毒中国最深”,陈独秀指责中国学术文化之所以不发达,坏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等,但是最早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周作人却很少加入对庄子的讨伐,并一再强调在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必须增加一些“道家思想的分子”,使之调和渐近自然,这是很耐人寻昧的。在“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对老庄道家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严肃而别致的,虽然他的道家立场常被他的儒家身份所遮掩,但把他对道家的好感简单地等同于消极隐逸,甚至视为他附逆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二
周作人多次说自己是儒家,但不是儒教徒,他不仅明确地表示自己“厌恶儒教徒”,而且认为“儒本非宗教,其此思想者正当应称儒家,今呼为儒教徒者,乃谓未必有儒家思想而挂此招牌之吃教者流也””。把先秦儒家和后世儒教徒区分开来,肯定前者而批评后者,是周作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坚决反对和抵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儒教”复古运动。
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开端,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中,日本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使自己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非白人的“宪政国家一,但日本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府主导下的复兴儒教。抵制西化的文化选择,不仅使日本的近代化保存了大量的封建糟粕,而且也为日本日后的发展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隐患。“五四”时期,周作人多次对近代日本的“忠君”教育提出批评,“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1926年日本子爵清浦奎吾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大谈“儒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周作人当即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这是多么谬误的话。……我想告诉他们,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现在也早已消灭了。他的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性化的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民族之优点的,但这也已消灭,现在被大家所斥骂的‘新文化运动,倒是这个精神复兴的表示。想理解中国,多读孔孟之书是无用的,最好是先读一部本国的明治维新史。……读了维新的历史,对于当时破坏尝试等等底下的情热与希望,能够理解,再来看现时中国的情状,才能不至于十分误会”。
和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一样,早期的周作人也认为日本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惊讶地发现,日本民族的根本信仰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儒家而是它自己的“神道”,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村上重良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国家神道》一书中所说:“截止二十几年以前,国家神道是统治我们日本国民的国家宗教,是宗教性的政治制度。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为止约八十年间,国家神道,对于日本的宗教自不待言,就是对于国民生活意识的每个角落都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近代,只要与思想、宗教有关系的,就都是根据国家神道,规定了它的基本方向的,这么说并不为过。”二战期间,国家神道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给世人留下了极其野蛮和恐怖的记忆,也使周作人对日本的国民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首先,他发现日本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对君、对国的感情也与中国截然不同。如果说中国的皇权是“靠武力取得,靠武力维持,也被武力所推翻”,人民并不认为当皇帝是一件特别神秘的事情,那么,在日本,由于万世一系的神国传统,人民普遍看天皇如神一样神秘莫测,正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说:“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像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他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与尽义务,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位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庭血缘关系,认为天皇就是他们大家的父亲,明治天皇临终前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恢复健康,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守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他死时,举国就像一家人那样悲恸。”日本的皇道教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孩子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一个演说家提到‘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把姿势坐正。如果某个记者突然问起天皇的私生活,那么人们就会冷冰冰地告诉他,对于神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这一点是不熟悉日本文化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
其次,日本社会真正的精神结构是“神体儒用”,儒学在日本社会中实际上只是一种适用的工具,因此,要想了解日本,必须从神道人手,否则抓不住要害。据村上重良先生研究,日本神道教起源于原始宗教,既没有教义,也没有经典,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原始的、素朴的宗教。作为日本的民族宗教,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神道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历史阶段,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招人厌恶、憎恨的是国家神道。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国人对天皇的狂热崇敬之心,拼命鼓吹为天皇献身是最高尚的使命,为天皇战死是最大的光荣,把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天皇而进行的“圣战”。无数的日本青年被这种宗教式的狂热宣传弄得神魂颠倒,将为天皇献身和死后进靖国神社当作此生最大的光荣和人生最美好的归宿。为了天皇,他们可以充当“肉弹”去进行自杀式袭击,可以做“特攻。队员,驾驶着载着炸弹的飞机去撞美国军舰,可以命令不能行动的已方伤员和居民集体自杀,即使是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他们也宁愿“一亿玉碎”,为天皇去殉死。周作人认为,由国家神道所引发的这种“超宗教”的宗教感情的大爆发,既是二战中日本军人的残暴、奴性、兽性和野
蛮性被推到了“离奇狂暴近于发疯”的绝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日本必然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有一句格言道,‘上帝叫一个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这句话是不错的,希特拉或德国的国社党是如此,日本的军国也是如此灭亡的”。
第三,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研究日本必须研究宗教,否则,不容易看清日本的真面目。这一点周作人感慨极深。在《缘日》一文中,他曾这样反思自己的日本研究,“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的文化大略,结局是徒劳而无功,后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无及,如要卷土重来,非从民俗学人手不可。自古文学美术之菁华,总是一时的少数的表现,持与现实对照,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或者反有抵牾亦未可知,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周作人认为仅从儒家文化人手,很难理解日本文化中极其卑劣、野蛮和丑陋的一面,必须另觅他径,“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正是带着这一困惑,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着重考察了中日两国民众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上的差异,并发现中日两国人民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宗教信仰,“日本民族与中国人,绝不相同的最特殊的文化是它的宗教信仰”。周作人指出,日本民族的宗教感情从“巫”演变而来,虽然在表面上仿佛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但它的根底却是“萨满教”。近代以来,日本的上层社会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表现出了某些新气象,但是由于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原来的神道,所以,与中国民众相比,日本国民更富于宗教情感,这一特点在民间祭祀迎神等活动中表现得最明显,即“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
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周作人就不断地强调要研究日本的宗教,“了解日本须自其宗教人手。这句话虽然很简短,但是极诚实,极重要”,“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中日两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味,想要了解他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以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人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等。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周作人认为自己的日本研究是一场大失败。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失败”对周作人来说却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首先,日本的教训促使他重新审视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性优长。其次,近代日本在政府主导下以全面复归传统为目标的“儒教”复古运动,非但未能推动日本的近代化,反而使日本在“神体儒用”的跑道上陷入军国主义深渊,以至于80年的维新成果功亏一篑的沉重教训,进一步坚定了他思想启蒙的信念。第三,日本研究的失败直接促成了他40年代在更高的意义上重回儒家,并最终成为了有中国特色的启蒙思想家。
三
纵观周作人一生,可以看到,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启蒙思想家,周作人思想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他的“非宗教”立场。周作人的这种“非宗教”思想既表现在感性层面,如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肯定人的感性欲望、以世俗性对抗中世纪封建礼教的禁欲主义,提倡健康合理符合人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等,又表现在理性层面上,如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重视教育,反对一切形式的造神运动和现代迷信等。“非宗教”倾向的影响几乎贯穿了周作人思想的方方面面,他之所以一再强调理性、常识、人情物理,一再提醒民众的宗教意识是值得注意的,始终坚持现代中国最要紧的不是培养花样繁多的信徒,而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提倡个人解放,并且终生对民众的非理性宗教情绪保持高度的警惕,以及他对思想启蒙的咬住不放,对希腊神话的终身爱好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都与他的“非宗教”思想背景有关。
周作人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无宗教国,宗教的狂热也未必更少,尽管与日本等民族相比,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更发达,民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有着明显的功利特征,而且不够虔诚,但由于民智未开,迷信心理严重,种种低级的巫术、法术及迷信等仍在底层社会具有广大的号召力,因此民众的宗教意识、民间宗教中非理性隋绪和知识界“专制的狂信”一样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对国民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予以高度重视的作家之一。即使在今天,周作人对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特点、成因及存在状况的考察和对巫术传统的重视,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同时,对儒教的宗教实质以及儒家思想宗教化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和精神桎梏的深刻认识,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非宗教”立场。儒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宗教,由于它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隐蔽性极强,加上近代中国始终没有经历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彻底、深广的反封建运动,封建的神权意识形态始终未得到彻底的清理,因此,尽管在“五四”时期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对儒教的宗教实质,现代知识分子大多认识不足。同时转型时代由于传统价值的崩溃所造成的“精神真空”,也容易使现代作家在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文化等层面反省传统文化的弊端时对自己潜在的宗教诉求和宗教心态习焉不察,如陈独秀等人一方面反对宗教,一方面又希望以基督教来改造国民性,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主义代宗教”等主张之所以不胫而走,广为流行,客观上也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如何摆脱形形色色的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进而真正走出中世纪,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尤其是当“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一面在理性的层面上自觉地追求科学与民主,一面又在价值的层面上不自觉地以一种准宗教的心态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寻求宗教的替代品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以这种心态来对待科学或主义,虽然信仰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信仰的方式心态却与过去如出一辙。
孔德曾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谈到,无论是个人、各门学科还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周作人亦认为现代化本身即是一个去魅的“无神化”过程,科学思想的养成实为现今思想改革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正如胡适所说:“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从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的角度来说,打破那种妄求“最后之因”的思想传统,立定清醒的、实证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立场,把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看作参考的材料、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
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真正走出中世纪的希望所在。但是,20世纪的中国却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一方面驱除外来侵略势力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以及救民于水火等追在眉睫的政治任务,迫使中国思想界强烈地渴望一种包罗万象而又简明扼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传统价值——信仰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思想失调,也使重构价值——信仰体系成为知识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正是这种时代遭遇使得置身其中的学者、知识分子常常不自觉地在一种潜在的、形而上的宗教诉求的作用下陷入苦闷、焦灼而浮躁的境地,不能自拔。周作人既很为知识者“总喜欢知道一切,不肯存疑,于是对于不知的事物只好用空想去造出虚构的解说,结果自然走到玄学里去了”而惋惜,又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宗教的、准宗教的主义、学说的大行其道而忧心。他之所以一再告戒世人“不要有宗教气而成为教徒”,与这种深沉的忧虑是分不开的。
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在“五四”以后之所以更多地提到佛教而不大讲独尊上帝的基督教,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西方学术界中有人称佛教是唯一的“无神论”宗教。佛教缘起论认为,一切事物皆因缘和合而生,所以都没有自性,也即是空,这里的“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指宇宙间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存在。因此。佛教在世界观上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或“造物主”,在思维方式上否认有任何终极本体存在于事物之前或之后并主宰其发展。即使是佛也要受因果律的支配,虽然他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但并不能主宰人间的吉凶祸福。尽管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解脱的需要,出现了把佛神化和以“真如”“实相”为本体的佛性论思想,但是从作为整个佛教理论基础的缘起论来看,佛教(尤其是原始佛教)是反对本体论或一元实体论的,这既是它区别一般宗教或哲学的地方所在,也是周作人认为佛教思想透彻而与之亲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释似经过大患难来的人,所见者深,儒则犹未也”。“五四”时期,有感于国内思想界的混乱,特别是对非理性宗教情绪的警惕,周作人试图通过对传统儒学中的理性、中庸传统的创造性阐释来重新建构中国精神文化。在佛教中,所谓“中道”意谓脱离二边,不堕极端。《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二云:“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形色,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现;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现。”《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亦云:“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佛家中道思想兼顾了性空与假有两个方面而又指向性空,因此,它在本质上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子和相信存在终极本体的亚里士多德是有区别的,正如阿部正雄在《禅与西方思想》中所指出,佛教的中道“超越一切可能的二元性,包括有与否定”,而指向即超越又包括空与有、相与无相的“空”。而这正是周作人“中庸”论的精神向度所在。周作人不承认有第一因或终极本体,他的中庸论所要解构的正是传统的定于一尊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和偶像崇拜心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流入“狂信”、“盲从”和“独断”的怪圈,显得偏狭霸道,有一种带有“准宗教”色彩的教士人格和教徒心理,便在于他们“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好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被赋裁判的权威”。他多次指出,“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绝对”是不可能的,“彻底”是决没有的事,“中庸,实在也可以说就是不彻底,而不彻底却不失为一种人生观,而且这也并不是很容易办的事”。将佛教中的反本体论的中观思想融入到儒家的中庸主义,打破传统儒家对“天”、“帝”、“神”的敬畏和迷信,形成自己独特的汇合儒释的现代中庸思想是周作人思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是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依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哪一部书”,。我说‘中庸也是我理想中的‘中庸”。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由于周作人的中庸思想的内核是反独尊、反正统、反圣化、反统一,与非权威与反偶像崇拜的“五四”启蒙思想一脉相承,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温文尔雅、中庸随和的周作人竟会时时爆发出甚至比鲁迅更为强烈的“流氓气”或“反叛”的激情。
总之,从广义的宗教文化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优长得失进行价值评估,力求解构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光环,使原始儒家思想中的富于理性和人道的思想精华发挥出来,并在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会通、权衡较量的过程中,形成既有中华文化之特色,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文明,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周作人儒家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最大贡献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周作人多次说自己抱有“宗教之恐怖”,不信任何宗教,但他对《圣经》和佛经的喜爱,对民众宗教心理的同情和理解,对工作的认真、专注、勤奋和严肃,以及不汲汲于名利、超然物外的淡泊,宁静与豁达,甚至他的冥顽不化和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执著,也让人感到虽然站在社会的层面他坚决反对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但作为个体,他对宗教的态度是相当严肃和宽容的。宗教对他人格的浸润亦是相当深的,尤其那种宁静致远,紧紧咬住思想启蒙不放松,沉默顽强地走自己所选定的路,以及博大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宗教徒似的恒心和定力。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代号20080440113)、广东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代号08GL-03),广州市社科联项目(08SKLll)和广州市教育局项目(08812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