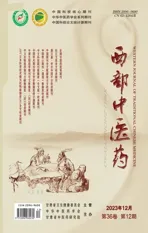基于“燥、毒、瘀”理论探讨中医治疗干燥综合征合并间质性肺疾病*
2024-01-26梁亦欣黄小娟刘小平侯秀娟朱跃兰
梁亦欣,黄小娟,刘小平,侯秀娟,朱跃兰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 100078;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 100078
干燥综合征(sjogren's syndrome,SS)是一种以累及外分泌腺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SS的典型临床表现以口干、眼干为主,可伴有其他外分泌腺功能下降及腺体外其他器官受损表现。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是SS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有数据显示,约9%~75%的SS 患者合并肺部受累[1]。ILD 是以弥漫性肺实质、肺泡炎症和肺间质纤维化为基本病理改变,以进行性气短、干咳和乏力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群[2]。SS-ILD 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SS 与ILD 的内在病机演变过程,方可取得较好疗效。
古代文献中没有与SS 及SS-ILD 相关病名的记载,但根据其症状表现,目前医家一般将SS 归属于“燥证”“燥痹”等范畴,将SS-ILD 归属于“咳嗽”“肺痹”“肺痿”“肺胀”等范畴[3]。临床观察发现,SS-ILD 的病位在肺,可累及肾,与“燥”“毒”“瘀”关系密切。中医治疗当以清燥润肺为主,活血解毒应贯穿始终,同时要注重病证结合和、顾护脾胃。
1 SS-ILD的病因病机
1.1 燥邪为病是本病发生的始动因素燥邪为病开启了本病的病理进程。《类证治裁》言:“燥有外因,有内因。因于外者,天气肃而燥胜,或风热致伤气分……;因乎内者,精血夺而燥生。”指出燥邪有内外之分,外燥源于外感六淫之燥或风热,内燥源于阴津亏虚,反之内燥甚津伤益甚。燥邪无论内外,致病本质均为阴津亏虚。机体阴津亏虚,脏腑肌肤失于濡养,外在表现为眼干、口干、毛发干枯、皮肤干燥皲裂等症状,此合于SS 的表现。即“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4]。
燥之为病,内涉乎肺,患者多出现咳嗽。究其因,《薛氏医案》中云:“肺主皮毛而在上,是为娇脏”;《血证论》中载:“肺为华盖,肺中常有津液。”[5]肺质清虚而居高位,肺叶娇嫩,喜润恶燥,不耐寒热,肺津充盈是保证肺正常发挥生理功能的基础。“肺者,气之本”,肺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气司呼吸,肺失濡养,肺宣肃功能失司,则肺气上逆,发为咳嗽。阴津亏虚,故患者大多干咳无痰或少痰。肺的另外一个生理功能是通调水道。肺失濡养,通调水道失职,则津液输布不均,加重其他脏器阴津的亏耗。此外,咳嗽日久也可伤津耗气,患者眼干、口干、干咳、气短、乏力等表现呈进行性加重。阴津亏虚日久不愈,可伤及肾中之真阴,病位由肺及肾,肾不纳气,患者多于SS-ILD 后期出现呼吸困难、动则尤甚的症状。《黄帝内经》有云:“阳化气,阴成形”[6]27,提示阴伤太过可导致实质形体的损伤。SS-ILD 后期,阴津亏虚较甚,肺失濡润日久,损及肺叶实质,患者大多出现肺叶焦枯,即肺间质纤维化改变。
1.2 毒邪为病是SS-ILD 发生的重要病因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包括疫疠之气、六淫邪毒及有毒致病物质。各种病原微生物感染属于外毒的范畴。《金匮要略心典》载:“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7]提示邪气日久不解即可由普通邪气质变为内生毒邪,也提示内毒是久蕴体内,不能及时排出的,导致邪盛正衰、形体溃烂的病理产物。
毒邪在SS 以及SS-ILD 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燥邪深伏潜藏于机体内,日久不解,可蕴结成毒。《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言:“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6]387。提示毒邪暴烈,毒犯机体具有发病及传变迅速、病位深、病情重的特征。燥毒既具有燥邪伤津耗液之性,又有毒邪猛烈顽固之性。一旦燥毒形成,津液就会被更加剧烈地消耗,机体会迅速出现阴津亏虚,甚至可在短期内伤及肾中之真阴,使患者处于阴津耗伤甚至阴虚火旺的状态。且毒邪致病,传变迅速,短期内即可出现其他脏腑受累的表现,影响全身气血津液的运行,从而加重机体的阴津消耗。阴津亏虚,机体失润,则眼干、口干、皮肤干燥、毛发干枯。阴津亏虚,肺失濡润,肺叶受损,肺主气司呼吸功能失常,肺气上逆,则出现干咳,宗气生成受阻,则出现乏力、气短等气虚表现。毒邪传变迅速,短期即可及肾,肾虚纳气失司,则出现呼吸困难,动则喘甚的表现。
此外,毒为实邪,毒邪侵袭人体时,正邪斗争会比其他邪气侵犯人体时更加剧烈,可出现大量病理产物的蓄积,从而引起免疫功能亢进。实验研究证实SS-ILD 患者可出现C-反应蛋白(Creaction protein,CRP)、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s,Ig)、白细胞介素、血沉异常[3-4,7-9]。
1.3 瘀血为病是本病发生的关键因素瘀血既是SS-ILD 发展过程中的病理产物,也是其发生的关键因素。SS-ILD 患者除口干、眼干、干咳、乏力等症状外,还可伴见舌质紫,舌上可见瘀点或瘀斑,苔有裂纹,脉细等瘀血表现,也可出现腮腺、淋巴结肿大等瘀血相关症状[5,10]。
燥、毒均可导致瘀血的产生。《灵枢·决气》篇记载:“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11]126提示津血同源,相互影响。燥邪致病,阴津不足,血脉不充,血行滞涩,停而为瘀。《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中指出:“津亦水谷所化,其浊者为血,清者为津。”[12]血为水谷精微中较为厚重黏稠的部分,津液不足,则血液更易出现凝滞,停而成瘀。毒邪入里化热或入营血灼营阴,伤津耗液,津液不足,血行不畅,亦可停而为瘀。瘀血作为有形的实邪,可阻碍气血津液的运行,从而导致SS-ILD 的发生。瘀血阻碍气的运行,则气机不畅,津液输布失常不能上达,则口干、眼干;气机不畅,肺气上逆,则出现干咳。瘀血阻碍血的运行,则血行受阻加重,瘀血更甚,故出现腮腺、淋巴结肿大等表现。久病耗气,瘀血日久不愈则气虚,故出现气短、乏力等症状。此外,瘀血郁久可化生郁热,热灼津液,津亏加重,且瘀血不除,其血行受阻情况会不断加重,故患者的症状呈进行性加重。
瘀血在SS-ILD 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有研究发现SS患者普遍存在体内D-二聚体、血浆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血沉等血瘀相关指标明显升高的现象[6,13];活血解毒类方药可降低血清中的干扰素γ及趋化因子CC 配体5 的表达水平,从而缓解干燥综合征模型小鼠下颌腺的炎症反应,提示瘀血可影响SS 及SS-ILD 的发生发展[7,14]。有学者认为,干燥综合征患者存在免疫功能亢进的现象,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值,大量免疫球蛋白易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于微小血管,造成微小血管损伤,从而引起微循环障碍,导致血液流速减慢,最终形成“微型癥瘕”。提示瘀血是SS 及SSILD 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病理产物,瘀血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8,15]。
1.4 燥、毒、瘀相搏导致本病迁延难愈燥、毒、瘀三邪关系密切,互为因果。燥邪致病以阴津亏虚为本,瘀血为血液停滞而成,燥与瘀的关系源于津与血的关系。《灵枢·痈疽》篇云:“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11]153津血同根同源,可相互转化、相互影响,津亏血不丰,血少津不盛,由此可见燥、瘀两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燥邪为病,阴津亏虚,脉道不充,血行不畅则成瘀;阴津亏虚,肺失濡养,肺的生理功能失常,则肺失宣降,气机不畅,影响血液运行而成瘀;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失常,则宗气生成不足,气虚无力推动血行,血液凝滞成瘀;肺通调水道的功能失常,则津液输布失常,加重局部阴津亏虚,间接加重血瘀;肺朝百脉的功能失常,则血脉正常运行受阻,血停成瘀。瘀血日久化火,热灼津液,则津亏生燥;瘀为实邪,可阻碍气血津液输布,津液输布不均,则局部阴津亏虚,化生燥邪。由此可见,燥可生瘀,瘀可化燥。同时,毒邪也可生燥、生瘀。毒邪易入里化热或入营血、灼营阴,伤津耗液,津液不足,则血行不畅,停而为瘀;毒邪生热,耗伤阴津,则津亏生燥。
燥、瘀皆为有形实邪,毒邪有结聚依附之性,易与其他实邪互结,燥可化瘀,瘀可生燥,毒可生燥、瘀,毒可附于燥、瘀,最终燥、毒、瘀三者胶着,导致病情复杂难治。
2 SS-ILD的治疗
2.1 清燥润肺是基本治则SS-ILD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SS 症状(如眼干、口干)合并干咳、气短、乏力等。患者疾病初期呼吸道症状较轻,剧烈活动后可出现呼吸困难,后期会出现明显气促、气短,动则尤甚。清燥润肺是SS-ILD 的基本治则。清燥润肺法常用的滋阴药物有地黄、麦冬、黄精、沙参、百合、西洋参、天花粉等。临床治疗时,具体用药需辨证选择,若热象显著则宜选用生地黄、麦冬、天花粉等清润之品;若无明显热象或有寒象者可适当加用熟地黄、黄精等厚重之品。同时,治疗时尽量选用可入肺经的药物,也可适当使用引经药,以增强疗效。
酸甘化阴是指酸味药配伍甘味药具有滋阴之效,是滋阴剂常用的配伍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6]28后世医家将这一理论归纳为“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并将其应用在方剂配伍中。常用的酸味药有乌梅、芍药、山茱萸、五味子等,常用的甘味药有甘草、地黄、枸杞子等。芍药甘草汤是酸甘化阴的代表方,此方以芍药配伍甘草,酸甘化阴,滋阴养血,缓急止痛,可治疗阴虚筋脉失养所致的拘急证。临床中酸甘化阴之法常用于热病后期阴虚较重的患者。SS-ILD患者长期处于阴液不足的病理状态,若单用补阴药物,有形之阴液难以速增,适量使用酸味药和甘味药可加速其阴液生成,以助其阴液的恢复。
2.2 活血解毒贯穿始终SS-ILD 的发生发展是燥、瘀、毒相互搏结的结果,非独一燥邪,因此在治疗时需兼顾毒、瘀之邪。燥可致瘀,瘀阻经络,津血输布失常,可加重阴虚,因此活血必不可少。毒邪性猛烈、顽固、难治,毒成往往提示患者预后不佳。故在SS-ILD 的治疗过程中应始终兼顾解毒,以此来延缓或控制毒的发生发展,改善患者的预后。研究显示,治疗SS或SS-ILD时使用活血解毒法可通过抑制趋化因子CXC配体13、B细胞活化因子及干扰素调节因子4 等细胞因子的表达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9,16];与白芍总苷相比,活血解毒方可更大程度地降低血清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21 水平,减轻局部淋巴细胞浸润,改善SS模型小鼠唾液腺慢性炎症[10,17]。
常用的活血解毒药物有当归、赤芍、红花、丹参、牡丹皮、莪术等。毒邪易郁久化热,因此临床用药时可适当加用金银花、连翘、白花蛇舌草、积雪草、金莲花等清热解毒之品。研究表明,莪术可降低血清IL-6 水平、抑制颌下腺组织趋化因子CXC配体12表达,从而延缓SS进展[11,18];金莲花的主要化学成分有黄酮类、有机酸、生物碱等,具有抗炎、抑制免疫、抗血小板聚集等作用[12-13,19-20];连翘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连翘脂苷、连翘苷,抗炎效果显著[21];姜黄中的姜黄素可通过抑制RA-FLS的增殖,间接降低血清中IL-6 及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从而起到抗炎作用[15,22]。相关药理研究发现,加用活血解毒药可减少免疫抑制剂及抗生素的使用量,有利于患者的预后。因此,活血解毒法应贯穿SS-ILD治疗的全过程。
2.3 辨病与辨证结合“证”是对疾病发展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可不断变化;“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不同疾病即使其临床表现相似,病理转归也会大不相同,用药也会不同,即《医学源流论》所云:“欲治病者,必先治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23]。此外,辨病是从总体上把控疾病,辨证则是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病变,可不断变动。故治疗SS-ILD时需注意辨病与辨证结合。
S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淋巴细胞在肺部增生浸润可破坏肺泡结构,引起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影像学可见双肺弥漫性网状或网状结节样改变,患者出现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基于SS-ILD的病理,在治疗时可适当选用雷公藤、青风藤、穿山龙等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中药。研究证实,雷公藤可多靶点干预结缔组织病相关的ILD的进程,其关键化学成分为山柰酚、雷公藤内酯醇、川陈皮素等,通过调节Toll 样受体信号通路、IL-17信号通路、TNF信号通路等,抑制抗体反应从而调节免疫功能[16,24];青风藤的主要活性成分是青藤碱、β-谷甾醇、千金藤啶碱等,通过调节细胞凋亡通路、P53 信号通路发挥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功能及调控细胞凋亡等作用[17,25];穿山龙的主要药理成分穿山龙总皂苷,可通过干预核因子κB 炎症信号传导通路,降低IL-1、IL-6、TNF-α、基质金属蛋白酶9 等炎症因子表达,调节免疫,延缓ILD 的发生发展[18,26]。总之,相关药理研究表明治疗SS-ILD时应病证结合,在辨证用药的基础上适当加用有免疫调节作用的中药,可更好地延缓及控制SS-ILD疾病的进展。
2.4 注重时时顾护脾胃滋阴药物大多滋腻碍胃,长期服用会损脾胃运化受纳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纳运功能失常,则气血津液生化乏源,药物吸收受阻,进而加重阴虚。脾升清功能失常,不能疏散精微于上焦,上焦失濡,亦可影响肺的生理功能,进而影响患者恢复。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患者的脾胃功能,使津生有源,从而更好地促进药物发挥疗效。
注重顾护脾胃需在辨证治疗基础上酌情加用黄芪、白术、陈皮等健脾和胃的药物。研究表明,黄芪可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减轻炎症反应,改善炎症相关血清学指标[19,27-28];白术主要有效成分为白术多糖,可保护胃黏膜并调节内环境,此外还可改善血清学炎性指标[20,29]。
3 典型病例
案杜某,女,74 岁。2020 年10 月中旬初诊:以间断咳嗽、咳痰伴活动后喘憋5 年,加重1 周为主诉。患者5 年前出现反复咳嗽伴口干、眼干,在中日友好医院被诊断为“干燥综合征继发肺间质纤维化”,并给予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后患者自行停用免疫抑制剂,活动耐量减低明显。随后于门诊就诊,目前规律服用复方环磷酰胺及中药,病情控制尚可。1周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喘憋,不能平卧,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无喉间痰鸣。刻下症见咳嗽咳痰,痰白量少,易咯出,无血丝,活动后喘憋,不能平卧,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无喉间痰鸣,口干眼干,反酸烧心,夜间尤甚,纳差,眠可,大小便正常。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双中下肺可闻及爆裂音。舌淡暗,苔白少津,脉沉弦。胸部CT 示:两肺纤维化伴感染。中医诊断:咳嗽肺阴亏虚,毒瘀互结证;西医诊断:干燥综合征继发肺间质纤维化。予甲泼尼龙口服,每次16 mg,每日1次;同时予中药汤剂治疗,药物组成:青风藤30 g,忍冬藤20 g,穿山龙15 g,生地黄15 g,麦冬15 g,玉竹15 g,知母10 g,白芍30 g,五味子10 g,天花粉15 g,金银花15 g,丹参30 g,赤芍15 g,红花10 g,当归15 g,苦杏仁10 g,薏苡仁15 g,生黄芪20 g,桔梗10 g,瓦楞子10 g,谷芽15 g,砂仁6 g,炙甘草6 g,共14剂,水煎分服。
2020 年11 月二诊:患者自诉服药后,咳嗽咳痰、反酸烧心感减轻,进食情况稍好转,舌质暗,苔白少津,脉沉细,辅助检查示CRP、WBC 增高。在上方基础上加用金荞麦15 g,共30剂,水煎分服。
2020年12 月三诊:患者自诉咳嗽、咳痰、反酸及烧心症状较前进一步减轻,舌暗,苔薄白,脉沉细。激素逐渐减量,继服复方环磷酰胺治疗,同时调方,药物组成:青风藤30 g,忍冬藤20 g,穿山龙15 g,生地黄15 g,麦冬15 g,玉竹15 g,五味子10 g,白芍30 g,天花粉15 g,金银花15 g,金荞麦15 g,丹参30 g,赤芍15 g,红花10 g,当归15 g,苦杏仁10 g,桔梗10 g,砂仁6 g,薏苡仁15 g,生黄芪20 g,炙甘草6 g。共30剂,水煎分服。
2021年1 月四诊:患者自诉咳嗽咳痰减轻,活动后喘憋减轻,反酸烧心缓解,舌暗,苔薄白,脉沉细。甲泼尼龙减至每次16 mg,每日1 次,上方不变,继续服用30天巩固治疗。定期随诊。
按患者以“间断咳嗽咳痰伴活动后喘憋5年,加重1 周”为主诉就诊,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痰白量少,活动后喘憋,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无喉间痰鸣,口干眼干,反酸烧心,纳差,符合中医“咳嗽”范畴,故被诊断为“咳嗽”。患者是老年女性,阴血本虚,则燥邪内生。燥邪犯肺,伤津耗液,则肺阴不足。肺阴不足,宣肃失司,肺气上逆,则出现咳嗽咳痰、痰白量少。肺阴亏虚,津液输布失常,脾胃津液不足,纳运失常,则出现反酸烧心,纳差。津液不足,机体失濡,则口干眼干。燥邪日久不愈,化生毒邪,燥毒急剧伤津,可损及肾中之阴,导致肾不纳气,则出现活动后喘憋,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无喉间痰鸣。津液不足,血行不畅,瘀血内生,则舌淡暗。毒、瘀互结,病情复杂难解,则患者反复出现咳嗽咳痰,病情呈进行性加重。苔白少津,脉沉弦为肺阴亏虚,毒瘀互结之征象,故辨证为肺阴亏虚,毒瘀互结证。治疗时以清燥润肺、活血解毒为主,兼以健脾和胃。青风藤、忍冬藤及穿山龙有免疫调节作用,可辅助甲泼尼龙抑制免疫,同时其还具有活血通络之效;生地黄、玉竹、麦冬可清燥润肺,五味子、白芍配炙甘草酸甘化阴,增强清燥润肺之功;患者肺阴亏虚日久可出现虚火上炎及肾阴受损,故用知母上清肺火、下滋肾阴,但其性苦寒,易伤及脾胃,因而在后期患者阴液渐复且无明显热象后将其去除;天花粉、金银花、丹参、赤芍、红花、当归可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二诊时患者C 反应蛋白、白细胞水平增高,加用金荞麦增强解毒之效;苦杏仁、桔梗可止咳平喘,桔梗还可作为引经药,引诸药入肺经;砂仁、薏苡仁、瓦楞子、谷芽、生黄芪可健脾和胃制酸,瓦楞子为金石类药物,长期服用有碍脾胃运化,故后期患者反酸烧心缓解后需去掉瓦楞子。四诊时患者症状均有所好转,则守方不变。
4 小结
SS-ILD 发病机理复杂,目前多以激素、免疫抑制剂干预为主。在疾病晚期对于肺功能的治疗上目前可选用的药物有限,且价格昂贵,故而选用中医药结合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方案对患者更加有利。中医立足于辨证论治,认识到燥、毒、瘀在疾病发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燥邪为病是本病发生的始动因素,毒邪为病是本病发生的重要因素,瘀血为病是本病发生的关键因素,燥、毒、瘀相搏导致了本病的发生。治疗SS-ILD 当以清燥润肺为主,活血解毒贯穿始终,同时顾护脾胃,可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