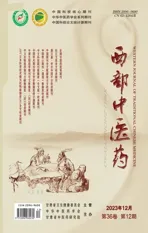毒邪学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证治探讨*
2024-01-26蓝绍航庞宇舟李娜娜陈秋霞尚昱志
蓝绍航,庞宇舟,李娜娜,陈秋霞,方 刚,黄 安,尚昱志,3△
1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2;3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广西 南宁 530011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滑膜的炎性反应和异常增生为病理表现,影响关节和关节外结构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1],临床以多关节对称性疼痛肿胀甚至畸形和功能损害为主要特征。我国RA 的患病率约为0.42%,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RA的病因至今未明,西医认为主要与遗传、感染、内分泌失调和药物诱导等因素有关。目前,西医学治疗RA 多选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抗风湿药及小分子植入药等,但这些药物存在剂量大、给药频繁、毒副作用严重等缺点[3]。由于RA发病率高,易致残,治疗棘手,迄今仍无特效疗法,为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因此迫切需要其他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改变这一现状。中医治疗RA 虽具有一定疗效,但单纯常规辨证用药,往往收效甚微。从毒论治RA 可有效抓住病源,切中病机,扼其病势,提高疗效,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 毒的理论源流
1.1 毒之本义“毒”字古来有之。何谓“毒”?《说文解字》曰:“毒者,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毒的最初本义是指毒草,有害人、厚重之性。《广雅·释诂》载:“毒,犹恶也。”清代《康熙字典》中“毒”的含义为“恶也,一曰害也;痛也,苦也,恨也,药名。”可见,所谓毒者,险恶深重,超态之常。
1.2 毒在中医学中的含义在中医学中,毒的内涵非常广泛。《金匮要略心典》云:“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古书医言》曰:“邪气者,毒也。”王冰注《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有言:“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认为邪盛谓之毒,即邪气亢盛、败坏形体可转化为毒,毒必兼邪。《诸病源候论·温病发斑候》曰:“冬时天时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毒气不得发泄,至夏遇温热,温毒始发于肌肤。”表明疫气也是毒。《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篇》云:“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指出毒是一种具有强力致病作用,有别于六淫的特殊病因。华佗《华氏中藏经》记载:“蓄其毒邪,浸渍脏腑,久不摅散,始变为疔。”毒之为病其害甚大,直言“毒邪”致病。清代徐延祚《医医琐言》更有“万病唯一毒”之论,把毒列为万病之首,认为毒是指一切致病因素的总称。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阴毒、阳毒的概念,并制定出相应的证治方药,对后世颇有启发。《周礼·天官冢宰》记载:“聚毒药,以共医事。”秦汉时期的人们将药物称为“毒药”[4],并学会运用毒药以偏纠偏来治病,使机体逐渐恢复“中正平和”的健康状态,如张景岳《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又如《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神农本草经》曰:“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强调用毒药治病要注意中病即止,以防过之伤正。《神农本草经》亦有“解毒”“逐毒气”之论。盐山张锡纯十分注重毒邪的致病作用,擅长运用解毒药,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出以毒攻毒之妙用[5]。在近代温病学中,温热疫毒致病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6]。此外,有学者认为,临床上一些疑难杂症多与毒邪相关,在审证求机的基础上,从毒论治常取得理想疗效[7]。总之,各家之说,其言毒者,或言病因,或言病机,或言病证,或言药性,或言治法,包罗广泛,不一而足。
2 毒邪致病的特点与RA证候相关性
毒邪种类繁多,有内生之毒和外侵之毒,并可再细分为有形之毒和无形之毒,加之毒力大小、病损部位、兼挟它邪及患者正气强弱有别,致病特点复杂多样,临床表现各异。笔者团队根据相关文献[8-11]及多年临床经验,发现RA 在整个病程中反映出了毒邪的大多数特性,并依此总结毒邪致痹的共性特点及其与RA 证候的相关性,主要有如下几点:1)凶险性。RA 可突然起病,病势重,病程长,毒邪流注经络,腐蚀肌肉,侵蚀关节,病急势猛,酷烈暴戾,常表现为关节疼痛剧烈不可接触,肿胀不可屈伸,活动受限,甚至导致关节畸形或功能丧失,足不能履地,手不能持物,终成废人。2)顽固性和难治性。RA 病期漫长,病位深疴,深重难愈,深伏骨骱,顽劣难驯,痹阻经络,销筋蚀骨,迁延难除,病趋不治,常规辨治难以奏效。3)多发性和复杂性。RA 除侵犯四肢关节肌肉,还会导致血管炎、肺纤维化、类风湿结节,腺体破坏,而表现为发热、瘀斑、咳喘、痰核、口干、眼干等经络、脏腑、四肢、九窍受损的全身症状,可急可缓,可寒可热,有虚有实,兼夹证多。4)损正性。RA之毒邪深达血脉经髓,深伏痼结,正气难抵,导致阴阳失和,气血逆乱,脏腑败伤,且邪势猖獗,甚难搜剔驱逐,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组织器官等造成严重损伤。毒侵骨髓,骨节蹉跌,常表现为病变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破坏等。毒蚀脏腑,血脉受累,可累及心、肺、肾及眼等结缔组织病变,常伴心律失常、肺纤维化及肾脏损害等。5)变化性和依附性。RA 常变化多端,病变无常,变证丛生,且毒邪少有单独致病,其发病常依附于痰瘀浊湿、六淫七情,毒邪胶结,凝聚经髓,毒依邪势,邪仗毒威,兼挟为患,合而为病。如毒依风邪则痛无定所,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毒依寒邪则疼痛剧烈,手足拘紧,遇寒痛甚,遇温痛减;毒依湿邪则重着酸痛,痛处固定,肢体肿胀。由此可见,RA 之所以证候繁杂,缠绵不愈,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根源,总因一“毒”字作祟。
3 毒邪侵袭是RA关键的病因病机
RA 在中医文献中无相应病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当属于“痹证”“历节病”“白虎病”等辨证范畴。“痹”最早出现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12],《足臂十一脉灸经》中称“畀”。古代医学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毒邪致痹的论述。《素问·痹论篇》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黄帝内经》首提“痹”之病名,并详细记载了其病因病机、证候分类及演变规律。邪气盛者谓之毒,风寒湿三气亦如是。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对痹证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热毒气从脏腑出,攻于手足,手足锨热赤肿疼痛也。”巢元方首先提出“热毒”的概念,并指出脏腑积热、蕴毒致痹的病因病机及其证候。此外,他还在书中阐明了痹证的病源及其证候,并对各候症状进行详细的论述和鉴别,赋予痹证以新义。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热毒流入肢节,深入营血,血脉瘀滞不通。”他首次提出“热毒致痹”的病理机制,指出热毒流注于四肢关节,留滞而成痹,确立了清热解毒的治疗思路,并运用犀角汤治疗。《杂病源流犀烛·诸痹源流》记载:“或由风毒攻注皮肤骨髓之间,痛无定处,午静夜剧,经脉拘挛,屈伸不得……或由痰注百节,痛无一定,久乃变成风毒,沦骨入髓,反致不移其处。”毒入血脉,则凝结而成痰核、结节、痈疽等[13]。明清时期,随着温病学派的兴起,暑热致痹成为重要学说,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了“暑湿痹”的新名称[14]。有学者认为,RA 病理变化的关键因素如细胞因子、炎性介质及免疫复合物、血管炎、滑膜炎、血管翳等都属于毒邪的范畴[15]。总之,RA虽病机复杂,病因多端,但追根溯源,总与毒相关。
4 从毒论治是RA的最终转归
基于上述探讨及笔者团队多年临床体会,可知RA 病位深而病情重,常规辨治难以奏效。而治病必求于本,毒邪是RA 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毒邪入侵及其危害贯穿RA 整个病程始终,故治疗时须以祛毒为要,从毒论治,兼调脏腑,使致病之毒有路可出,毒祛正安。
4.1 辨“毒”论治,通络祛毒《景岳全书·风痹》记载:“盖痹者,闭也。”RA 症状繁多,但以痛为其首苦,痹痛责之不通,不通则痛,毒祛络通则病可向愈。通经活络和清除毒邪密不可分,故其治疗当宗“通络祛毒”为旨。致痹之毒既可外侵又可内生。一方面,天之六气,过与不及,化为“六淫”,“六淫”邪盛,达到一定程度,对机体造成严重损害,则化为“毒”。如“六淫”过甚可化为风毒、寒毒、暑毒、湿毒、燥毒、火毒。另一方面,或因饮食不节,嗜食肥甘厚腻,宿食内积,致脾胃升降失常,气血逆乱,脏腑失和,痰浊内生,痰夹瘀血,滞留体内,久酝互结为毒;或因起居无常,昼夜颠倒,劳逸失度,气机升降失常,瘀浊腐秽壅滞体内,损伤脏腑,致气血津液运行障碍,闭阻脉络,渐成痼疾顽症,邪毒难除。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善抓主证,这也是中医治疗的核心优势。RA 病情复杂,致痹之毒虽种类繁多,可相互胶结,合而为病,但往往每病必有致痹之主毒,抓住主毒对症下药方可提高临床疗效。因此,笔者团队提出在RA 通经活络的治疗基础上,根据毒性之别及毒之偏盛(如热毒偏盛、湿毒偏盛、寒毒偏盛、风毒偏盛、痰毒偏盛、瘀毒偏盛),采取不同的治则治法(如清热通络解毒、祛湿通络解毒、散寒通络解毒、祛风通络解毒、祛痰通络解毒、化瘀通络解毒),须抓住毒之主线,全程紧紧围绕辨“毒”论治。
4.1.1 热毒致痹,清热通络解毒 热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关节肌肉肿胀疼痛,痛处掀红灼热,疼痛剧烈,遇热痛甚,得寒则舒,活动受限,或伴发热,口渴,烦闷不安,便秘,尿黄等,舌质红,苔黄或黄燥,脉滑数。治以清热通络解毒为法,方选白虎加桂枝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可酌加黄柏、防己、桑枝、忍冬藤等。
4.1.2 湿毒致痹,祛湿通络解毒 湿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关节肌肉酸痛肿胀,肌肤麻木,或伴肢体沉重,舌质淡胖,苔白腻或厚腻,脉濡缓或濡细。治以祛湿通络解毒为法,方选薏苡仁汤合羌活胜湿汤加减,可酌加土茯苓、地龙、山慈菇、萆薢、黄芪、红花等。
4.1.3 寒毒致痹,散寒通络解毒 寒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手指或足趾小关节肿胀,麻木冷痛,疼痛较剧,遇寒痛甚,得热则舒,痛处多固定,亦可游走,舌淡苔薄白,脉弦紧等。治以散寒通络解毒为法,方选镯痹汤合乌头汤加减,可酌加全蝎、乌梢蛇、蜂房、土鳖虫、补骨脂、当归、丹参等。
4.1.4 风毒致痹,祛风通络解毒 风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肢体关节疼痛,游走不定,痛无定处,或关节肿胀,此起彼伏,经久不愈,或伴恶风寒,皮肤瘙痒,舌苔薄白或薄腻,脉多浮或浮紧。治以祛风通络解毒为法,方选宣痹达经汤合防风汤加减,可酌加桑枝、威灵仙、姜黄、川芎、淫羊藿、巴戟天、续断等。
4.1.5 痰毒致痹,祛痰通络解毒 痰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骨节疼痛,肿胀变形,易凝结而成痰核、结节、痈疽等,或伴胸闷痰多,舌暗红,舌下静脉迂曲,苔白厚腻或黄腻,脉弦滑。治以祛痰通络解毒为法,方选黄连温胆汤合导痰汤加减,可酌加全蝎、蜈蚣、天南星、土鳖虫、白芥子、川续断、补骨脂、骨碎补、党参、淫羊藿、仙鹤草等。
4.1.6 瘀毒致痹,化瘀通络解毒 瘀毒致痹主要临床表现:关节刺痛,痛处固定,肿胀,甚至僵硬变形,屈伸不利,或伴面色黧黑,舌质暗红或淡暗,舌下络脉青紫或曲张,脉弦涩或细涩。治以化瘀通络解毒为法,方选桃红四物汤合活络效灵丹加减,可酌加全蝎、蜈蚣、三棱、莪术、连翘、蒲公英、地龙、山萸肉、白芍、怀牛膝等。
4.2 全程兼调脏腑,扶正补虚祛毒扶正补虚、祛邪解毒是RA 重要的治法治则。如《素问·评热病论篇》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不足是RA 发生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因素。《医学心悟》认为痹病是由“三阴本亏,恶邪袭于经络”所致[12]。明朝龚信《古今医鉴》曰:“盖由元精内虚,而为风寒湿三气所袭……入而为痹。”清朝董西园《医级》强调:“盖邪之感人,非虚不痹。”可见,正气虚弱,腠理疏松,卫外不固,致毒邪乘虚而入,营卫不和,脏腑阴阳失调而致痹。刘清平等[16]强调治疗RA 要在“扶正祛毒”治疗原则指导下,一方面积极控制RA 病情,缓解各种临床症状;另一方面改善RA 相关微环境,消除炎性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力,力求从整体和根源上防治RA。现代免疫学研究表明,在RA 的临床治疗中使用补虚扶正方药,具有广泛调节免疫的作用,可使正复毒祛,五脏安和,阴阳平衡[17]。扶正补虚以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为主,多选狗脊、补骨脂、山萸肉、白芍、怀牛膝等药物;祛毒解毒宜选虫类药以毒攻毒,可选全蝎、僵蚕、蜈蚣、土鳖虫、地龙、蜂房、蕲蛇等药物。使用虫类药须遵循邪去而不伤正,中病即止的原则。此外,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医中药走向国际,中西医结合与融汇已成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中药与化学药配伍是基于“异类相制”[18]理论下“扶正制毒”的基本思想,从整体思想出发,通过调动机体内在的积极因素,加强机体免疫能力,改善和恢复患病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等,可达到正复邪退、毒祛病愈的目的[19-20]。
5 结语
总之,RA 具有鲜明的毒邪致病特征,毒邪是RA 发病及其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毒邪侵袭是RA病因病机的关键,从毒邪论治RA不仅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临床实践依据。RA 之毒包括痰毒、瘀毒、寒毒、风毒、湿毒、热毒等,诸毒可相互胶着,合而为病,治法应相互兼顾,但往往每病必有致痹之主毒,抓住主毒对症下药方可提高临床疗效,临床上可根据毒性之别及毒之偏盛采取不同的治则治法。总体来说,治疗RA 须以祛毒为要,抓住毒之主线,辨“毒”论治,并全程注重兼调脏腑,扶正补虚,使致病之毒有路可出,毒祛正安,最终达到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