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快闪”在海外:一种国际传播的“艺术地理”范式
2023-10-11杨光影
■ 杨光影
近年来,展示汉服、民乐、中国舞的“国潮快闪”成了海外华人青年和留学生热衷的一种公共艺术活动。(1)高娓娓:《美国华人华侨发起街头快闪,祝大家新春快乐,北京冬奥圆满成功》,“新浪网”,2022年2月5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35106672/6175bf7002700wl7m,访问日期:2022年8月18日。此类活动通过挪用在西方青年中流行的“快闪”形式,不仅在海外诸多城市的公共空间内传播开来,更在“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国际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可以说,“国潮快闪”通过艺术地理的创造性实践来展示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形成了独特而醒目的艺术传播现象,由此也会成为我们研究国际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的一种新维度。据笔者所见,国内学界当前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尚不够多,系统性的研究也比较缺乏。笔者认为,在相关研究普遍关注国际传播中国家政策的正面宣传(2)比如姜飞、张楠:《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2021年研究综述》,《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文春英、吴莹莹:《国家形象的维度及其互向异构性》,《现代传播》2021年第1期;胡正荣、田晓:《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分层、分类与分群》,《中国出版》2021年第16期。、领导人访问等重要时政新闻的外媒报道与国际舆论偏向(3)比如刘娜、田辉:《国事访问的国际媒体可见性及其影响因素——以1978—2018年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报道为例》,《新闻记者》2019年第4期;胡钰:《当代国际政治传播的新趋势》,《人民论坛》2022年第13期。的同时,我们也不妨深入观察和思考这些“快闪”活动中的艺术行动形式与策略,关注其效果转化和在国际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传播。
鉴于海外的“国潮快闪”与公共空间及其数字化的密切关联,本文拟借用哈里特·霍金斯(Harriet Hawkins)的“创造型艺术地理”(Creative Art Geography)理论,探讨这些活动在“创造”文化地理空间过程中建构出的国际传播新范式,即一种“艺术地理”实践范式。霍金斯的这一理论将艺术理论家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的“扩展领域”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创造转向”理论结合,论述了在从景观建构到参与实践的公共艺术实践范式变革中,艺术化的创造性行动形成新的公共空间与新的文化地理形态的潜能。(4)Harriet Hawkins,“Geography’s Creative (Re)turn:Toward a Critical Framework,”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3,no.6(2018):1-22.鉴于“国潮快闪”牵涉到艺术化的参与行动以及文化艺术空间的建构,“创造型艺术地理”对国潮快闪的国际传播研究当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一、艺术塑造新文化空间:艺术地理的“创造型”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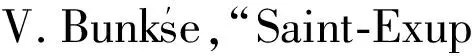
在对“创造型艺术地理”的论述中,霍金斯还提到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参与式艺术”、权美媛(Kwon Miwon)的“特定场域艺术”(Site-specific Art)理论,并从地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社会空间的参与机制。艺术理论家通常以“关系美学”作为理论支撑,阐述参与式艺术如何打破公共空间中既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关系。(11)参见Miwon Kwon,One Place after Another:Site 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2);Claire Bishop,Participa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6).相比这种“关系美学”的思路,霍金斯更注重艺术在重建社会关系之后生成了(或会生成)何种文化地理生态。在此,连接艺术与生活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参与式艺术被霍金斯所重视。参与式艺术的空间实践力及其“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强调参与者对空间进行形态和意义的再创造,以及重构空间地缘、空间政治、地方想象、身份认同的可能性。(12)参见Harriet Hawkins,Geography,Art,Resrarch:Artistic Research in the GeoHumanities(New York:Rouledge,2021),pp.83-85;Dagmar Danko,“Artivism and the Spirit of Avant-Garde Art,”Art and the Challenge of Markets 2(2018):235-261.类似的话题同样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谈及,当然,以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的理论底层逻辑是:政治经济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引发空间经验和艺术美学形态的变迁(如哈维认为后福特主义制度是后现代美学的缘起);(13)David Harvey,“Monument and Myth,”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9(1979):362-381.而与之相比,霍金斯更关注艺术本体所包含的活态的空间创造力,并聚焦于这种创造力的激活方式。她认为,艺术所创造的文化地理生态不一定是固定的、持久的,这是一种生成式的、有兼容性甚至临时性的创造性空间,它有别于资本的规划空间。霍金斯希望此类空间能够生成打破地缘区隔的文化生态。(14)Harriet Hawkins,“Geography’s Creative (Re)turn:Toward a Critical Framework,”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3,no.6(2018):2.
二、在艺术行动中创造“认同空间”:海外国潮快闪的艺术地理生态
通常认为,“快闪”活动由美国时尚杂志《哈珀》(Harper’sMagazine)的主编比尔·瓦西克(Bill Wasik)发起。当时,他通过电子邮件招募了数名参与者,临时集合到纽约的梅西百货店。这群参与者不断询问售货员有没有“爱情地毯”(实际并无此物)出售,而10分钟后又立刻离开。“快闪”(flash mob)这个称呼则是瓦西克事后定的。(15)Bill Wasik,“My Crowd or,phase 5:A Report from the Inventor of the Flash Mob,”Harper’s Magazine(March,2006):56-66.“快闪”强调匿名参与、突发介入和即兴表演,组织者基于电子邮件或网上社交平台发出行动号召和主张,将彼此匿名的参与者集结到公共空间,进而把预先的行动主张表演出来,然后快速散去。显然,这种活动因其参与性和空间创造性,可归入霍金斯“艺术行动主义”的范畴。(16)参见Paulina Bronfman,“‘A Rapist in Your Path’:Flash Mob as a Form of Artivism in the 2019 Chilean Social Outbreak,”Connessioni Remote 2,no.2(2021):210-225.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从“创造型艺术地理”的角度解读“快闪”。与西方的“快闪”活动相似,海外的“国潮快闪”同样在参与中创造着新的文化空间,而且这里更有学术意味的是:这种在异国他乡的城市中创造出的文化地理生态,包含着霍金斯所说的“临时”“包容”与“活态”。但同时,海外的“国潮快闪”又有与西方“快闪”的明显不同之处,其进行的传统艺术展演不会像询问所谓“爱情地毯”那样扰动公共空间。因此,我们可以发问:西方式“快闪”如何创造新的文化空间?海外的“国潮快闪”如何重构西方“快闪”?这种重构创造出了怎样的文化地理生态?
(一)空间的创造性破坏:西方快闪的“艺术行动主义”
维拉格·莫尔纳(Virág Molnár)从艺术史角度出发,同样将西方的快闪活动溯源到达达主义的“艺术行动主义”(17)Virág Molnár,“Reframing Public Space through Digital Mobilization:Flash Mobs and the Futility of Contemporary Urban Youth Culture,”Space and Culture 17,no.1(2014):46-47.。从先锋艺术的脉络来讲,“艺术行动主义”一开始就是文化抵抗的实践路径与艺术形式之一,当今的西方快闪则是网络社会中“艺术行动主义”的延伸。“艺术行动主义”基于艺术介入公众与社会的主张,意在让艺术家走出画廊与美术馆,通过艺术化的行动引发公众关注、制造文化话题,以此表达观念。这与达达主义艺术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况与人道危机,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建构的理性、科学精神产生怀疑,从而通过“反理性行动”传播抵抗立场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在霍金斯看来,先锋艺术是集表演、实物、参与和组织于一身的综合体,可以通过某种意义上的“没有预设”的创造性行动去建构鲜活的文化地理生态。不过,在说到创造的方法与路径时,霍金斯对“创造性”的解释依旧滑动于“参与”“组织”等描述性语汇中间,没能提炼出一个富有理论穿透力的概念。对此,笔者拟借用戴维·哈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加以弥补。哈维将先锋艺术归入后现代艺术美学的范畴,把它与现代艺术作对比。他结合利奥塔、詹姆逊等后现代哲学家的论述,将后现代美学的特质总结为“为破坏而破坏”的“创造性破坏”(18)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44.。对先锋艺术而言,“创造性破坏”不仅呈现于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艺术体制的努力,更表征于介入与扰动公共空间的创造性实践。无论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参与式艺术,还是纽约的涂鸦艺术,起初都带有艺术家和参与者群体的扰动甚至破坏倾向,但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行动主义对空间的“搅动”并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对空间中既有的社会关系的革新。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空间通常被视为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其中也包含社会关系的组织结构。因此,“情境主义国际”等左翼的先锋艺术流派力图通过行动和表演制造暂时的感性连接和情境,以此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那种已经让他们习以为常的操控的反思与抵抗。(19)J.Brien Houston,H.SeoandL.A.T.Knight,“Urban Youth’s Perspectives on Flash Mobs,”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no.3(2013):236-237.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扰动式的艺术行动开始延拓其数字化维度,快闪活动也成了其代表之一,在网络社会语境中延续突发介入、“越轨”表演等形式的“创造性破坏”。具体来说,首先是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参与者突然介入公共空间。在介入梅西百货店的活动引发关注后,快闪活动逐渐流行,德国慕尼黑火车站的“吹泡泡”快闪、英国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快闪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同上。而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前期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联络。其次,快闪继承了达达主义、“情境主义国际”对“越轨”的偏好。并不存在的“爱情地毯”打破了日常化的消费行动;而在泰特美术馆,本应观看艺术作品的观众却成了带着耳机跳舞的“迪斯科舞者”。这些无伤大雅的“越轨表演”打破了公共空间中既有的关系结构,在搅动空间秩序的同时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
在快闪的“创造性破坏”中,行动者共同建构出一个异质集合的、感知互相激发的、情境激烈生长的抵抗空间。快闪的组织往往没有特别精确的计划,组织者仅仅通过一个号召,将对此感兴趣的各色陌生人聚集起来,每个参与者基本都是根据自己对号召的理解展开行动的。如此一来,各人的行动方式会存在一些差异,却又能暗合成一种相关性的联结。在此,行动者实际创造出了一种德勒兹所说的“集合”空间。所谓“集合”,恰是指异质的物互相联结并不断产生新意义的“生成状态”;(21)Martin Müller,“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Politics and Space,”Geography Compass 9,no.1(2015):29;另参见Deleuze and C.Parnet,Dialogu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69.而异质的参与者在相关行动中的联结,就组成了“异质集合”(assemblage)的空间文化生态。在“集合式”的连接中,参与者之间、参与者与好奇的观看者之间的感知是相互激发的。由于行动的突然性与创意性,参与者共同打破了既有的空间关系,而且在各自打破的过程中相互启发,从而拓展新的可能性。如慕尼黑火车站的“吹泡泡”快闪,在参与者吹泡泡的同时,候车的乘客也可能加入其中进行触碰泡泡的游戏。在行动者的相互激发中,原本繁忙且颇有焦虑气息的火车站短暂地变成了欢乐的嬉戏场。此外,异质集合还会有其数字化的生长。打破空间既有关系的行动意味着空间认知边界的拓展,这种拓展会因为临时性和偶发性而呈现动态扩张的趋势,并在相互激发中呈现出激烈生长的扩张状态,这样的生长状态通过数字媒体的传感,可能引发更多人的模仿。
(二)破坏性创造:海外国潮快闪对西方快闪的机制转化
如上所述,西方式快闪对公共空间的“创造性破坏”主要以群体的突发介入为起点。海外的国潮快闪也挪用了这种包含临时性、随机性、偶发感和意外感的介入形式,搅动异国城市的公共空间。譬如2018年华人青年和留学生在英国曼彻斯特街头开展的汉服快闪,在曼彻斯特多个街区的英伦风格景致中展现了独特的差异化美学;又如2018年新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巴西圣保罗、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华人华侨以快闪的形式欢度春节、唱响“中国”,也暂时打破了公共空间惯常的社会关系——像金门大桥这样的地方原本是横跨旧金山的通道,当国潮快闪以古琴的表演介入该场所时,它临时变成了演出的场所,其间出现了展演和观看的关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挪用形式的背后,国潮快闪的参与者以组织化连接将西方快闪的“破坏性”转化了。所谓“连接”,是存在于数字互联时代的人、数字平台与社会空间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而西方的快闪搅动社会空间的那种“破坏性”来自于一种异质性的连接。西方快闪因发起者更加个人化、计划性更弱,其连接方式属于数字平台上的陌生化社交,由此形成的快闪社群基本也是一种高度异质的集合体。在西方快闪中,“破坏性”来自于现场行动的在场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非固定的行动形态才能破坏既有的社会空间关系。而要实现这样的不确定性,也离不开多样化、临时性的参与者群体。可以说,连接的异质性越强,其所涉群体的多样性就越丰富,快闪的“破坏力”也就越大。与之相比,国潮快闪将异质性连接转化成了同质性连接,大大降低了“破坏力”。国潮快闪往往通过官方的社团组织发起,这等于将其数字连接的核心变成了数字媒体上的熟人社交,陌生化社交则成为其外围延展,由此形成的快闪群体是同质聚集的网络共同体,如留学生群体的国潮快闪背后是成员相互熟悉的校内社团、校友会、同乡会等。这一变化让快闪群体更加可控,减弱了快闪对空间的“破坏性”。
我国的纳税人身份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因为不同的纳税人身份所纳税的方式和税额有较大的区别,享受的优惠政策或者待遇方面也不同,所以纳税人事先要对自己的纳税人身份有一个充分的考虑,到底选择哪个身份最有利于自身的税负。新出台的的政策明确表示,在2018年12月31日前,一般纳税人如果满足相关政策条件就可以从一般纳税人转回小规模纳税人,在此之前没能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作转出处理。所以,这就让很多企业都心动了,导致一些企业盲目的想要转回小规模纳税人,以便给自己减税,却忘了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全盘考虑,这将会带来物极必反的后果。
另外,从“在场”的连接来看,西方快闪活动的连接随机性、随意性和偶发性也很强,在临时“游戏”中显现了对空间的较强“破坏性”;华人在海外进行的国潮快闪则将之转化为计划性连接,在精心设置的“程式”中削弱了这种“破坏性”。我们知道,西方快闪的社群连接逻辑依然是“情境主义国际”的行动方式的延续,讲求以临时集体创造出“情境”,进行一种游戏化的“破坏”,以连接艺术、日常与空间,只不过“情境主义国际”带有更讲求政治美学的抵抗性,以此反思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和日常而已。相比之下,海外的国潮快闪的连接大多出于自上而下的计划,参与者在正式开展活动之前,是在社团的组织下精心排演过的。在排演的基础上,程式化在参与者的表演中替代掉了不少随机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创造力的消解。相反,国潮快闪通过唤起文化记忆的表演策略,实现了从“创造性破坏”到“破坏性创造”的转变。在海外的国潮快闪中,汉服、古琴、传统戏曲等成为主要的内容,这些集体表演创造出传统文化的“情境”,在临时解构既有的社会空间关系的同时,制造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空间。如果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些表演可被视为传统文化符号的一种活化。
进一步以文化符号的视角来看,亚文化研究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将西方的青年亚文化视为一种“风格抵抗”(22)[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比如嬉皮士、酷儿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制造抵抗性文化符号去对抗主流文化和父权文化,而西方的快闪同样包含亚文化的维度,其偶发的表演形态同样可视为一种“风格的抵抗”,只不过抵抗的焦点已由物质符号的制造转向了非物质的行动生成。与之不同,国潮快闪的表演在突然介入特定空间后,创造出一种以传统文化符号为纽带的“风格协商”。这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快闪社群内部互为观众的相互确证;其二是快闪社群与国外观众之间的美学沟通——这种沟通并不是符号意指层面的,而是基于对符号能指如汉服的色彩、古琴的音色、戏剧的唱腔的感知,这样的在场感知无疑能唤起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其三是传统文化情境与异国公共空间的协调关系。所以,国潮快闪中的文化展演并未扰乱公共空间,相反,其文化情境通过文化符号的活化渗入了异国的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东方情境”与当地地方性的对话关系。
(三)青年亚文化、传统艺术和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共构:海外国潮快闪创造的认同空间
西方的快闪活动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形态,以“创造性破坏”去生成一种带有反叛色彩的“抵抗性认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分为三类:其一是认同国家、民族和主流文化的“合法性认同”,其二是反叛主流文化的“抵抗性认同”,其三是社区通过组织和参与而自发生成的新的社群认同,即“计划性认同”。(23)[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显然,无论是在梅西百货问询“爱情地毯”还是在慕尼黑火车站吹泡泡,快闪都具有“非主流”的意味,通过对公共空间中既有关系的“创造性破坏”,生成并不一定是激烈反对,而是带着戏谑性质打破陈规的“抵抗性认同”。这种戏谑无疑继承了先锋派否定艺术自律、轻视艺术体制、讲究艺术介入生活的传统。
与之相比,海外的国潮快闪通过程式化参与、展演互见、跨域连接,形成了基于社群计划的“合法性认同”。卡斯特认为,网络社区与社群是个人在网络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组织群体,而社区的组织实践会形成“计划性认同”,它区别于“合法性认同”和“抵抗性认同”,是一种新的认同类型。在海外的国潮快闪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体现着同质化连接和计划性连接的群体性组织实践,这样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参加国潮快闪的社群认同取代了“合法性认同”,相反,他们建构出的是一种青年亚文化、传统文化、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者“共构”的认同空间。
对此我们稍作展开。从活动过程来看,这种共构包含“社群认同—身份认同—民族与国家认同”的渐进。尽管组织方式已经转化,但海外的国潮快闪依然包含青年亚文化的形态。这类快闪的参与主体是青年,且以留学生、“二代移民”等华人青年为主,他们的聚集有利于产生社群认同。同时,他们将传统文化植入活动之中,既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呈现传统文化,也以传统文化的风格呈现青年亚文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共构。这种共构的连接点就在于身份认同,特别是华人身份的确证与展现。最终,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歌曲的演唱,华人的身份认同又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而从组织机制来看,前述的三者共构是在程式化参与、展演互见、跨域连接中得以“落地”的。此类国潮快闪多是经过精心排演的,这种程式化的参与强化了其活动的计划性,消解了参与者的猎奇心态,计划中出现的传统文化符号则可以不断催化“合法性认同”的生成。而“合法性认同”的生成过程也是展演互见的过程,参与者既作为表演者开展活动,也能成为唤起围观者“合法性认同”的“触媒”。例如2019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唐人街和海港大桥出现的汉服快闪,迅速引发了路人围观,特别是当地华人。在围观中,观看者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会被传统文化符号的活化表演所唤起,与表演者形成关于认同的相互确证。另外,“合法性认同”的形成还可以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跨域连接来实现。国潮快闪制造了临时的传统文化情境,这就与异国的文化语境形成了跨地域的连接,而该连接中的语境反差可以激发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由此强化其“合法性认同”。用具体例子来说,澳大利亚的汉服快闪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举行,该建筑作为整个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与由汉服指代的中国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除了异域空间与传统符号的反差之外,国外围观者的认可也是跨域连接中激发“合法性认同”的一个面向。在澳大利亚的汉服快闪中,不少当地本土人士也积极围观,他们的“打卡”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乃至初步认同的反映,而这种来自异域族群的认同也从侧面激发了华人参与者的“合法性认同”。
概言之,国潮快闪将艺术行动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转化为“破坏性创造”,在组织化连接中创造出生成“合法性认同”的文化空间。这种生成是通过程式化参与、展演互见、跨域连接而实现的。
三、基于“图景族”的空间认同:从艺术地理到艺术数字地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海外的国潮快闪的国际传播不仅在异国物理空间中的艺术地理创造之中展开,还延伸到了数字空间中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闪的诞生本身即始于电子邮件往来形式的组织,而当移动互联技术普及之后,社交平台不仅可以集结快闪活动,还可以将快闪的状况“再平台化”。快闪所创造的艺术地理图景会被转化为社交平台的“共情酶”,由此形成包含空间化认同的数字传播——这里的“共情酶”是受到“讨论酶”(discussion catalysts)的启发而衍生的概念。伊泰·西美尔博伊姆(Itai Himelboim)等人以“讨论酶”描述社交平台中催生受众参与讨论的中介,(24)Itai Himelboim,Eric Gleave and Marc Smith,“Discussion Catalyst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Content Importers and Conversation Starter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no.4(2009):771-789.然而能驱动网络受众参与的不仅有话题讨论,还包括共感共情、共趣激活、文化想象。因此,本文拟以“共情酶”一语来指称国潮快闪在社交平台上催生情感认同的要素。
(一)快闪空间数字化:艺术的“数字地理图景族”
在自媒体发布和大数据推介的支撑下,国潮快闪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会将物理空间中的地理生态数字化与图像化,进而使之变为呈“图景族”样态的艺术数字地理生态。“图景族”的说法受到媒介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启发:曼诺维奇提出,社交平台的视觉文化不再是单一作品的观看,而是相关作品的“族类”聚集。他对海外社交平台“图享”(Instagram)上的“自拍”图像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对同一城市标志物的自拍,揭示这数以亿计的图片为受众建构出来的对城市空间的重新认知。(25)N.Hochman and L.Manovich,“Zooming into an Instagram City:Reading the Local through Social Media,”First Monday 18,no.7(2013),accessed August 9,2022,https://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4711/3698.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国潮快闪内容的自媒体,除了有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外,还包括其围观者,这些“共趣”粉丝的转发增加了国潮快闪消息扩散的速度和广度。在民间化、多样化与微观化的传播过程中,同一地点的国潮快闪即构成一个“图景族”。由此,当国潮快闪成为热点议题之后,不同地点的国潮快闪还可以形成有共通议题的相关性联结,由此构成更大范围内的“图景族”。“图景族”会在议题保持足够热度的时间段内动态生长,不断强化相关行动的空间转向与正向传导。
同时,在平台的受众端,对此类快闪感兴趣的西方受众同样会在大数据推介中接收到相关的艺术地理图景,从而在内心建构出国潮快闪的地理“图景族”。这样的接受机制近乎一种视觉化的“网络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经典概念,主要是指媒介精英对公众舆论议题的引导;网络议程设置则是议程设置概念在网络空间中的延续。研究者郭蕾分析道,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焦点在于内容生产,而网络议程设置的焦点在于关系建构。若借鉴心理学的“认知架构”观念,可将网络议程设置视为网络传媒对受众进行的一种相关内容的“认知架构”建设,而这样的架构依赖于网上的社交关系。(26)Guo Lei,“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in Guo Lei and M.E.McCombs(ed.),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Directions for Agenda Setting(London:Routledge,2015),p.16.在基于大数据的类型化推介之下,国潮快闪实际上已成为网络议程设置的一个议题,而由此形成的“艺术地理图景族”则是平台试图给予受众的一种视觉化的“认知架构”,能够引导更多的西方受众去理解中国的风貌与思维。
(二)破除歧见:“共情酶”的空间化认同
海外社交平台的受众主体自然是西方民众,其中不乏大量青年。对西方青年而言,海外华人青年的展演具有一种青年亚文化的亲缘性。参与这些快闪的海外华人青年长期在当地学习、生活,更熟悉当地的青年文化及亚文化,拥有鲜活的文化体验。于此而言,相比国内的快闪参与者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图像去模仿,海外华人青年更能接触快闪的原生形态,其介入公共空间的行动状态也更接近于西方的快闪,也让西方青年更容易形成对国潮快闪的“数字共情”。
除了青年亚文化层面的共情之外,汉服、古筝等元素的出现亦带动了西方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原本具有一种地理向往与地缘想象,这种想象以陶瓷、丝绸等作为“物媒”。在国潮快闪中,以丝绸为材料的汉服会以其东方风格重新唤起西方青年的这种想象,兼以民族音乐实施听觉维度的感知操练,在彰显文化魅力的同时引导文化认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针对华人的族裔歧见,好莱坞电影中以“傅满洲”为代表的反派华人形象亦深入许多民众的心里。所以,海外的国潮快闪在社交平台中所传播的传统文化,其首要作用目前尚不全在于展示文化魅力,而是让“数字共情”通过平台用户的转发和评论得以扩散,从情感维度通过共情想象去减弱和消除偏见。
综合来看,西方青年基于亚文化的青年共趣与传统文化的想象共情,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目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往往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的负面消息,将中国塑造为未来的“敌人”,以期引起西方民众的敌意和恐惧;而对参与社交平台的多数西方青年来说,对中国的认知同样主要依靠社交平台上有关中国的新闻来建立。莱巴茨(Claire Laybats)和特雷丁尼克(Luke Tre-dinnick)认为,传媒场域没有所谓的“事实”,只有“竞争式真相”(competitive truth)(27)Claire Laybats and Luke Tredinnick,“Post Truth,Information,and Emotion:View All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Business Information Review 33,no.4(2016):204-263.。因此,比起国事访问报道等时政新闻的传播,国潮快闪可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民族与国家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利于西方青年形成对中国的正面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西方主流媒体的负面议程设置的效果。
(三)认同的空间转向: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数字地理
我们已经看到海外的国潮快闪可以创造出青年亚文化、传统文化和民族与国家共构的“合法性认同”。这样的认同在国际社交平台上以破除歧见为基础,力图有效引导西方青年转变对中国形象的看法;而这种转变无疑基于国潮快闪在物理空间创造的“认同空间”之艺术地理生态。在数字空间中,艺术地理生态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中的自媒体账号扩散,助推中国国家形象数字传播的“空间转向”,落实其民间性、社群性和微观化。下面稍作展开。
首先是民间性传播。国潮快闪的性质为非官方活动,其参与者也并非官方正式派遣,这让它区别于宣传国家形象的正式仪式。比如,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政府就曾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发布国家形象宣传片,其内容和传播机制分别以宏大叙事和国际辨识度为重点,既展示了中国的标志性成就,也有国际影视明星和国际体育明星加盟。相比之下,无论从机制上说还是从内容上说,国潮快闪在国际网络社交平台上的传播都带有民间性:其发布机制是偏向随意性、个人化的,其内容是“素人化”的和“接地气”的,也正是这样的民间性收获了西方民众特别是其中的青年人的额外认同。
其次是社群性传播。快闪活动的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是聚合“粉丝”的“个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ies)(28)Vincent Chua,Julia Madej and Barry Wellman,“Personal Communities:The World according to Me,”in John Scott and Peter J.Carringto(ed.),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Los-Angeles,London:SAGE,2011),pp.1-29.,所以整个活动可以成为“个人社区”吸纳“共趣粉丝”的“共情酶”。由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面认同会在“个人社区”中展开,实现一种基于“共趣粉丝”的社群性的扩散。“粉丝”的转发和评论会加剧这样的扩散,而国际网络社交平台用户以西方民众为主体,更不乏西方青年,所以他们的关注、转发与评论也会对中国形象的正面传播有不少助益。
最后是传播的微观化。参与者通过自己的账号发布的活动图像与视频,其记录现场的视角、剪辑方式多有不同,属于个人化、多样性的呈现。这种多样性可以给平台受众以足够强的趣味性,不容易使之产生刻板的、类型化的印象。
国潮快闪在正面传导中国形象的同时,还形成了传播中国主张的艺术地理范式。比如在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等国进行的国潮快闪中,“‘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主题之一。当然,这种主题并不会在活动过程中刻意提出,而是在社交平台的后期传播过程中加以标注或提示的。社交平台以喜好、标注等作为连接参与者关系网络和内容传播网络的节点,通过对主题的标注,“‘一带一路’倡议”即可成为国潮快闪的重要主题,构成新的“共情酶”。即便西方青年用户对“一带一路”的具体内涵不甚了解,也能通过国潮快闪的数字传播“感知”该倡议所展示的开放态度、沟通立场和合作诉求。
小 结
综上所述,以霍金斯的“创造型艺术地理”理论为视角,可以确认海外的国潮快闪活动实际上建构出了一种国际传播的“艺术地理”新范式。霍金斯聚焦于艺术如何创造艺术空间与文化地理,将理论视野聚集到先锋艺术等行动主义的艺术流派对空间的意义与文化地理生态的再创造上。快闪活动作为对艺术行动主义的一种继承,以讲求突发介入、偶发连接的“创造性破坏”打破既有的空间关系,解构既有的公共空间形态。而海外的国潮快闪活动又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破坏性创造”,通过对突发形式的挪用以及将偶发连接转化为组织逻辑,建构出了青年亚文化、传统文化、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者共构的“合法性认同”的空间。国潮快闪不仅创造了物理空间中的艺术地理生态,还能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数字地理图景族”。在从物理空间的单一图景到网上社交平台“图景族”的聚合中,平台的西方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易于通过亚文化的“共趣”和传统文化的想象,破除其族裔偏见和政治歧见,转向对中国国家形象及主张的空间化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