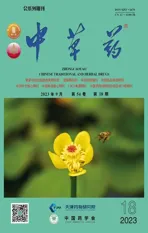天麻本草考证与现代资源利用问题探讨
2023-09-13刘鸿高王元忠
沈 涛,刘鸿高,王元忠
天麻本草考证与现代资源利用问题探讨
沈 涛1,刘鸿高2,王元忠3*
1. 玉溪师范学院 化学生物与环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2. 昭通学院 云南省天麻与真菌共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云南 昭通 657000 3.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0
天麻为我国传统药食同源中药,在医疗卫生、康养保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梳理天麻名称、效用、产地、加工炮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近年药材生产、资源利用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当前天麻开发利用面临的新趋势与新问题进行探讨,建议后续进一步完善天麻药用资源评价体系,挖掘天麻传统用药经验,解析天麻加工炮制科学内涵,建立药材质量控制、产地溯源、保鲜存储新技术与新方法,为助力高品质天麻生产及其产业现代化提供依据。
天麻;本草考证;产地变迁;加工炮制;资源评价
天麻为兰科植物天麻Bl.的干燥块茎[1-3];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尼泊尔、印度、俄罗斯等地,我国云南、四川、贵州、湖北等省是当前栽培天麻药材主产区[2-4]。天麻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并被认为“久服益气力”,将其奉为上品药材[5-6]。目前天麻已被《中国药典》2020年版收载,并属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品种,用于治疗头痛晕眩、肢体麻木、癫痫抽搐等症状[1]。此外,天麻也被日本、韩国、欧洲药典收录,作为法定药材或保健品使用[7-10]。现代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发现天麻富含芳香族类、甾体类、糖类、苷类、氨基酸类等化学成分[10-11];其中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巴利森苷B、巴利森苷C等是报道较多的药材有效成分,具有镇静安神、修复神经损伤、改善学习记忆、降血压、调血脂、抑制炎症、抗癌等功效[11-13]。本文通过文献考证,以历史朝代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天麻国内外名称、民族用法、性味功效、加工炮制的历史沿革。同时结合近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文献报道,分析探讨天麻资源评价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天麻传统药用价值的深入发掘及其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本草考证
1.1 名称考证
1.1.1 天麻古名探源 历代本草古籍“天麻”名称记载至少有18种。通过不同历史时期药材名称梳理,其药名变化多反映古人对天麻植物形态特征、功效特点、药用部位、优良品质的认识与界定。先秦时期“天麻”一词尚未出现,从秦汉、南北朝、隋唐至五代十国较长的历史时间,“赤箭”和“鬼督邮”是本草典籍中使用最多的药材名称[14-17]。通过文献查阅比对,可以确定“赤箭”名称源自古人对天麻属植物地上茎部及花序形态的描述与直观感受[3,16]。现今形态最为接近的物种即为天麻原变型:红天麻Bl. fS. Chow,其植株茎干为橙红色,并具有黄色和橙红色的花及花序,历史上该物种也广泛分布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分布区与古籍记载较吻合[3-4]。古代还用“离母”“合离草”“定风草”“独摇芝”等称呼天麻[18-19]。上述名称均源自古人对天麻不同生活史阶段地下、地上性状特征的认识。如晋代《抱朴子内篇》就有“离母者,下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的描述,因此“离母”“合离草”形象反映了处于白麻阶段的天麻形态特征[20-21]。唐宋本草还描述天麻茎部“有风不动,无风自摇”,可能是“定风草”“独摇芝”等名称的由来[17,22]。上述名称一方面反映了处于箭麻阶段的天麻形态特征,另外也寓意天麻善于疗风去湿。
“鬼督邮”是宋元之前天麻的又一称谓,最早在《神农本草经》中作为“赤箭”的别名收录[6]。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鬼督邮”和“赤箭”是否同属一物医家各有争议[14-16]。魏晋时期《吴普本草》将“鬼督邮”描述为:“茎如箭、赤色无叶、根如芋”的植物,该描述与天麻的植物形态较为相似[15]。但南朝《本草经集注》对“鬼督邮”代名“赤箭”提出质疑[16]。因“督邮”为汉代官名,专司巡视监察之职[22]。天麻、徐长卿等在古代作为专主鬼病(多指精神类疾病)的一类药材,均被冠以“鬼督邮”的称谓[19,23]。现代植物分类学及本草考证认为“鬼督邮”可能是古人对兰科药用植物天麻、萝藦科药用植物徐长卿及金栗兰科植物银线草或类似植物的统称[23]。
“天麻”是目前最常见的药材称谓,该名称最早出现于《雷公炮炙论》,表明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天麻”一词已被中国古代制药领域所使用[24]。宋金元明时期“天麻”和“赤箭”在不同本草专著中被单独或混合使用。宋代官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主要收录“赤箭”一名[25-26]。《本草衍义》按不同条目收录“天麻”与“赤箭”,并认为“赤箭,天麻苗也,然与天麻治疗不同”[27]。宋代本草学代表性著作《证类本草》亦将“天麻”和“赤箭”归为不同药材进行收录[28]。元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与《汤液本草》主要使用“天麻”一词[29-30]。明代李时珍通过历代本草著作的收集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将“天麻”和“赤箭”作为同一药材的不同名称进行收载和说明[19]。明清之后中药方剂中“赤箭”一词使用渐少,明代《景岳全书》及清代《本草崇原》《本草备药》《本草从新》等著作均采用“天麻”为药材主要或唯一名称[31-34]。清代《临证指南医案》涉及医治中风、晕眩、痰等症状的药方中多使用“明天麻”作为药材名称[35]。《本草害利》就“明天麻”的涵义进行了解释和备注,指出天麻“明亮者佳”[36]。因此“明天麻”反映了优质天麻药材经采收、加工、炮制后所呈现出的色泽白亮状态。目前“天麻”和“明天麻”在诸多方剂和医案文献中均已被广泛使用。
除文字描述,历代本草著作中原植物绘图有助于厘清天麻的药物基原[37-40]。从宋代开始,天麻手绘图逐渐在各类本草典籍中出现,尽管多数绘图较粗略,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麻的基本形态特征(图1-A~G)[19,28,37-38]。17世纪初《本草纲目》传入日本,当地本草学家通过对书中天麻原植物进行采集、移栽与实地观察,绘制了植物彩图呈现当时药用天麻形态特征,发现药用天麻茎杆及花序颜色至少可分为橙红色和蓝绿色2种(图1-H)[39]。详实的图谱与《本草纲目》形成有益互补,为明清之后天麻植物来源的确定,红天麻及其变种入药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佐证(图1-I)[40]。
1.1.2 天麻在少数民族中的称谓 除传统中药,民族药中天麻的名称也有较多变化。苗族和彝族可能是开发利用天麻历史较久的少数民族。宋金元时期《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和《汤液本草》中明确指出“定风草”为天麻药材的苗名[29-30]。此外,“洋芋有”和“高立日”也是我国苗族地区天麻的民间称谓,分别为苗语“Yangwit vied”和“Ghok wouf hind”的音译[41]。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地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天麻在彝族中至少有2种以上的发音和彝文表述方式,彝族将“天麻”也做“天马”象征着神圣、美好、祛除百病的意愿[42]。《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的天麻别名“木浦”源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43]。“东彭”“挂补门”“昌开”和“毛泽儿”主要是藏族、傈僳族、怒族族和阿昌族对天麻的称谓[39];其他天麻相关民族药名见表1[41]。

A~D-宋代《本草图经》与《证类本草》中绘制的赤箭和天麻 E-明代《本草纲目》中的天麻 F、G-清代《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天麻配图 H-日本江户时代《本草图谱》中的天麻彩绘图 I-《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中的天麻彩图
1.1.3 天麻国外译名考证 日本、韩国、尼泊尔等也是天麻的传统药用国家,其天麻药材植物来源与中国相同[7-10]。英文报道中“Tian ma”和“Tianma”的表述应用较多,为“天麻”汉语拼音的直译[10]。部分文献或著作中也见“Chijian”“Red arrow”或“Crimson arrow”均为“赤箭”的音译或意译[10]。除上述英文表述,“rhizome”“root”“Tall gastrodia tuber”等在英文文献中均指中药天麻[7,9,44]。喜马拉雅及周边山区是野生天麻的重要分布区,“Sungava”和“Deng phung”是当地天麻发音,分别源自尼泊尔语和藏语[45-46]。韩国和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天麻药用大国,并有野生天麻分布[2-3]。韩语中天麻表述为“천마”或音译为“Cheon ma”[9,47];日语中天麻被称为“オニノヤガラ”(https://www.pharm.or.jp/),被译作“Oni no yagara”或“Orge’s arrow”语义与“赤箭”相似[10]。江户时代晚期(1821—1828年),日本本草学家岩崎常正基于《本草纲目》的分类体系编撰了日本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本草彩色图鉴《本草图谱》。书中收录天麻并绘制其彩图,同时用汉语和日语对药材基原、分布、植物性状等进行对照注解[39]。目前《日本药典》收载约190余种生药,天麻是唯一的兰科植物,其药材日文名为“テンマ”,对应译文为“Gastrodia tuber”,药材拉丁名为“”[8]。从天麻名称在亚洲各国的演变及中文译名传播可看出,中医药文化对东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的深远影响。随着《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天麻逐渐融入汉方和韩医,成为当地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39,47-51]。
表1 民族药中的天麻称谓
Table 1 Names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ethnic medicine
天麻药材名民族 东彭、热木夏千藏族 乌兰-索莫、东布额、闹海音-好日嘎、索斯勒-嘎尔蒙古族 天麻、天马彝族 天麻、赤箭、明天麻白族 天麻德昂族 定风草、洋芋有、高立日、赤箭苗族 赤箭瑶族 毛泽儿阿昌族 水洋芽侗族 威外、威外黔、窠勒仡佬族 优邬泥赤景颇族 挂补门傈僳族 聋补弄毛南族 昌开怒族 格巴热思、别苦思贵、木都德日斯羌族 席鲁嘎太、自动草、定风草土家族
1.2 功效与用法考证
1.2.1 性味 性味是药材的重要属性,也是评判药材是否适用病证的主要依据[52]。《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记载天麻性平、味甘,与《神农本草经》中最初记录的性温、味辛相比发生了细微变化[1,6]。国内研究者就历代本草天麻四性变迁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发现秦汉至唐代医家多认为天麻性温,之后至清朝晚期性温、性平在不同医书中交替出现,总体天麻性平居多,当前《中国药典》2020年版对天麻药性的记载与多数医家观点相符[1,53]。药材五味是药物味道和作用的综合体现,辛味药材多具有挥发性成分,富含生物碱、苷类等,而甘味药材可能含有更多的糖类、苷类、氨基酸等化学成分[52]。在药效方面辛味药材具有发散、扩张、解热等功效,而甘味药材则具调和、补虚、缓急止痛等功效[52]。古籍中多描述天麻味辛,《汤液本草》认为天麻味苦[30],天麻味甘明清之前仅见于《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少数典籍有记载[18,54]。《本草纲目》认为天麻味辛,但书中引述前人专论反映出当时天麻味“辛”“甘”“苦”并存的情况[19]。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云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药典》2020年版等著作或药物志中天麻气味表述已较为统一,均为味甘[43,55-57];目前用辛、苦描述天麻气味已极少见。
古代与现代对天麻气味的定义有一定差异,气味由“辛”变“甘”,主要出现在近现代本草著作或官方药典中。结合文献报道发现古今天麻性味辨识的差异可能有多种原因。中药功效复杂,古人对天麻药性的认识存在局限与不完善。辛味主发散、甘味多补虚,气味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药材主要功效[52]。天麻药理、药效研究显示其同时具有辛味药和甘味药对应的多种功效与化学成分[11,52]。如作为祛风湿类药使用时,天麻主要发挥发散、行气、活血、开窍的功效,这些功效与“辛”味特征有关[19,52]。天麻用于提高机体免疫力或作安神药使用时,主要发挥补益、调和、缓急止痛的功效,上述功效多与“甘”味特征相关联[52]。中药气味描述具有一定模糊性,加之天麻药效多样,其在方剂中的用药模式与对应病证各有不同,以上原因可能促使古代医家对天麻气味辨识未能统一[19,52]。现代天麻除作平肝息风药外,滋补食疗功效逐渐被世人熟知并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味甘、性平与天麻补益作用相契合,也可能是当前多数医药文献将天麻气味描述为“甘”的原因之一[52,58-59]。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与古方整理,认为用“甘、辛,性平”描述天麻性味更为客观准确,同时强调天麻性味较复杂,用药需辨证施治,当医治血虚眩晕、因热生风等导致的头痛、头晕时,天麻要慎用[60]。随着中药性味理论的发展与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深入,天麻性味科学辨识与相关理论仍有待发展完善。
1.2.2 药用功效 古籍记载天麻功效多围绕息风止痉、平抑肝阳和祛风通络3方面叙述。从“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治小儿风痫惊悸”“止惊恐恍惚”“治善惊失志”等效用描述发现,天麻是我国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传统药物[6,19,22,31]。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天麻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抗抑郁等功效[11-13]。其块茎中含有的天麻素、香草醛、4-羟基苄醇、巴利森苷等是天麻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也是抗焦虑、抗癫痫、镇静催眠、保护神经元细胞、改善学习记忆、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药效成分[11-13]。治疗头痛晕眩是天麻的另一主要功效。传统认为天麻归肝经,可缓肝急、息肝风,因此能平肝潜阳,用于治疗头痛、晕眩、耳鸣、腰膝酸软、言语不利等病证[52]。此外,天麻能祛外风、通经络,宋代以前就被广泛用于治疗痈肿、肢体麻木、手足不遂等病证[16]。宋金时期《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有“天麻主头眩,祛风之药”的药赋[29];明代《雷公炮制药性解》总结天麻具“主瘫痪语言不遂,利腰膝,强筋力,活血脉,通九窍,利周身”的功效[61]。Yin等[62]研究证实天麻素可改善与急性心肌梗死相关的损伤并对心脏有保护作用。药效学和代谢组学分析发现,天麻治疗脑缺血的机制不仅与有效成分的抗炎、抗氧化、抗神经毒性、抑制细胞凋亡等活性关系紧密,还与天麻对生物体花生四烯酸代谢、组氨酸代谢、嘧啶代谢、甘油磷脂代谢等代谢途径的调控及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63]。此外,天麻多糖对促进生物体一氧化氮等内源性血管活性成分产生,抑制血浆内皮素等内源性血管收缩剂释放,提升机体免疫调节机能,促进脑神经恢复、提高体内氧化代谢相关酶活性等具有明显作用[12]。上述研究和发现为天麻传统功效的现代释义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民族药中天麻的效用与传统中药非常接近,治疗头痛、偏头痛、肢体麻木是少数民族地区天麻的常见用法[39]。苗族、哈尼族、仡佬族和毛南族还用天麻治疗胃痛[41]。瑶族天麻全草入药用于治疗高血压、眩晕、疮疖肿痛等病证[41]。苗族天麻地上茎主治高血压、头痛、眩晕,块茎则用于治疗急慢性惊风、抽搐痉挛、胃痛等疾病[41]。民族药天麻功效与用法见表2。
表2 民族药中的天麻功效
Table 2 Effects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ethnic medicine
民族功效药用部位 藏族头痛、头晕目眩、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小儿惊风、僵直、止痛块茎 蒙古族头痛、眩晕、口眼歪斜、中风、风湿痹痛、破伤风、小儿惊风块茎 彝族头痛块茎 白族头痛、高血压、眩晕块茎 纳西族偏头痛、肢体麻木、口眼歪斜、言语不利、小儿惊风、半身不遂块茎 哈尼族胃病块茎 德昂族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块茎 苗族偏头痛、头晕目眩、肢体麻木、小儿惊风、胃痛、破伤风块茎 苗族高血压、头痛眩晕、口眼歪斜全草 瑶族头痛、眩晕、口眼歪斜、小儿惊风、疮疖肿痛全草 阿昌族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块茎 侗族头痛、头晕、肢体麻木、风湿瘫痪块茎 仡佬族头痛、胃病(温酒吞服)块茎 景颇族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块茎 傈僳族头风头痛、眩晕、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小儿惊痫动风块茎 毛南族头痛、胃病块茎 怒族头晕、风湿麻木块茎 羌族头痛、头晕、眼花、风寒湿痹、小儿惊风、中风块茎 土家族偏头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癫痫、口眼歪斜、破伤风块茎
1.2.3 食用方法 古人在秦汉时期对天麻养生、保健功效就有较高评价,然而以天麻为主的食养方剂和食用方法历史上却鲜有记载,仅见《新修本草》《本草图经》和《本草乘雅半偈》等有少量记录与描述[17,37,64]。中国不同朝代天麻食用方法各有差异,唐代天麻作为食物,采后即刻趁鲜生吃,未有加工[17]。到宋代天麻除生吃外,还有2种食用方法。一种为蜜煎也做蜜渍,即将新鲜天麻采收后用红糖或蜂蜜腌制加工成蜜饯、果脯食用[27-28]。《证类本草》天麻条目下有“嵩山、衡山人,或取生者,蜜煎作果食,甚珍之”的记载[28]。宋代设有蜜煎局专为皇公贵族提供果脯甜食,北方契丹人也善做蜜渍果品作为朝贡礼品[65]。蜜渍天麻的出现反映了宋代果脯制作工艺的发达,也体现出当时天麻的珍贵。蒸煮是宋代天麻的另一种食用方法,最早见于宋朝寇宗奭撰写的《本草衍义》,书中有“天麻用根,人或蜜渍为果,或蒸煮之”的介绍[27]。明代《本草乘雅半偈》记载有外出作战军人,食用煮熟天麻,用于抵御饥饿并提升气力和精力[64]。由于缺少古籍支撑,除中原地区外,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天麻的食用历史也难以确定。现代民族药用植物学研究显示,天麻与其他食物一起烹煮是彝族、苗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治疗疾病、康养身体的传统方法[66-68]。如天麻与鸡肉、猪肉炖食是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的传统食用方法,类似烹饪方式在贵州黔南、黔西南及云南滇东、滇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较常见[42]。此外,贵州分布的仡佬族喜将天麻泡酒饮用[67];喜马拉雅山南麓分布的藏族则将天麻切片后做茶饮或与肉一起熬汤服用,该方法是当地治疗头痛和心脏疾病的传统食疗方法[68]。结合文献报道天麻在中国食用历史悠久,但古代其资源长期处于稀缺状态,导致天麻主要作名贵药材使用,食用方法和食疗功效未能发展普及[4,58]。伴随人工栽培天麻的出现,天麻药用资源稀缺性已有所改善,食养价值逐渐凸显,相关保健食品开发与食疗方法也随之迅速发展[59]。
2 当代天麻资源利用与问题探讨
2.1 产地变迁对药材品质的影响
现代天麻药材产地与古代相比已有较大变化。经国内研究者考证发现,从汉代至今约2000年的药用历史中,天麻主产地由最初的黄河流域逐渐南移至长江流域,最后又西迁到长江上游地区[4]。药材最佳产地也由唐宋时期的山东郓城,演变为现今的云南昭通、四川青川、贵州大方等地[4]。古代天麻产地变迁诱因较多,作为一种野生药材,除分布区生境气候改变、交通运输限制、国家疆域变化等影响因素外,原有分布区野生天麻过度采掘和资源耗尽是导致历史上天麻产地不断变迁的重要诱因[4,58]。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工栽培天麻技术获得突破,药材生产和资源利用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69]。在近代川滇黔野生天麻产地基础上,相继形成云南(以昭通为核心)、四川(川西与川西北)、贵州(赫章、大方等地)、湖北(武昌、恩施)、陕西(汉中)、安徽(大别山区)、吉林(长白山)、西藏(林芝)等栽培天麻主产区[4]。其中6省市15个县区生产的天麻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获批地理标志保护(http://www.mofcom.gov.cn/),见表3。
表3 天麻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Tabl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for Gastrodiae Rhizoma
产品名称地理标志类型代表性产地 昭通天麻地理标志商标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小草坝镇 大方天麻地理标志商标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辖区 雷山乌杆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辖区 德江天麻地理标志保护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辖区 青川天麻地理标志保护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辖区 金口河乌天麻地理标志商标四川省乐山市市辖区辖区 平武天麻地理标志保护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辖区 荥经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辖区 罗田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辖区 英山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辖区 郧阳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辖区 宜昌天麻地理标志商标湖北省宜昌市市辖区辖区 略阳天麻地理标志保护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辖区 波密天麻地理标志农产品与商标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波密县辖区 林芝天麻地理标志保护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以波密县为主)
栽培天麻产业发展可有效保护野生天麻,初步缓解了药材供应紧张局面,但优质天麻的需求仍较迫切。研究发现,产地水热气候条件、物种生长海拔、土壤矿质元素含量、共生菌种等均对天麻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药用部位产量、药材含水量等品质相关性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0-74]。杨婧等[72]发现,生长海拔1600 m左右的乌红杂交天麻其块茎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均最高。Wang等[74]研究也认为较高的生长海拔(1900 m)更有利于天麻中对羟基苯甲醇的积累,并推测随生长海拔降低,生境温度升高可能促使羟基苯甲醇转变为天麻素。昭通彝良小草坝栽培天麻研究发现,杂木林较荒坡更适宜开展天麻生产[70]。适量增施磷肥后天麻产量明显提高,但土壤中磷含量过高又会抑制药用部位天麻多糖和天麻素的积累[71]。对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天麻中矿质元素分析发现,不同产地天麻磷、铁等矿质元素的计量特征不同[75]。与天麻共生的蜜环菌属真菌随产地变化其物种也有所不同,菌种变化影响着天麻对钠、铝、锰、钙、锌等元素的吸收、积累,改变天麻生境土壤菌群结构与天麻体内生物代谢过程,导致药材产量与质量发生变化[74]。
课题组前期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报道分析发现[4],由南向北、自西向东栽培天麻主产区平均海拔总体呈降低趋势(<0.05、0.01,图2-A)。不同产区依据海拔可聚为3类,其中云南、西藏天麻主产区海拔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多在1700 m以上),与之相比湖北、安徽等地天麻种植区海拔相对较低(多在1000 m以下,图2-B)。“昭通天麻”“波密天麻”“大方天麻”“青川天麻”等受地理标志保护的优质天麻,由于生长海拔的明显差异,其种植条件和种植模式必然发生变化,药材品质也可能受到影响[21]。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从青藏高原到长白山区,海拔、经纬度变化显著影响年平均地温、年平均气温、年日照时数、年均降水量等水热指标(<0.05、0.01,图2-A),上述指标也是天麻药材生产的关键气候指标[21]。面对复杂的产地环境,天麻药材品质在经向、纬向及垂直方向上的地带性变化规律尚不明确;不同产地优质天麻区域品质特征有待阐明;药材优良品质形成的驱动因子与相关生态学机制鲜有报道。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天麻药材同种异质问题的科学认识,对后续药材生产区划、种源筛选、地理溯源等具有重要意义。

A-地理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B-基于海拔的产地聚类分析
2.2 天麻加工炮制技术及其现代发展
2.2.1 天麻加工与炮制方法演变概述 现代天麻采收后多制成干品,但唐代《新修本草》中仍有“得根即生啖之,无干服法也”的记载[17];据此推测至少在唐代天麻采后干燥加工方法尚未普及。宋朝天麻产地加工技术有所发展,出现将新鲜天麻去皮、沸水略煮(断生)、暴晒晾干的加工方法,类似加工方法在宋朝后一直沿用至近代[37,76]。民国时期天麻加工方法又增加了烘干[76]。20世纪60年代后,经过《中国药典》的不断修订,天麻的加工方法趋于统一,形成净制、蒸煮断生、干燥等系列工艺[1,76]。
天麻入药前需经炮制加工为饮片。蒺藜子煨是天麻较早的炮制方法,始见于《雷公炮炙论》[24]。唐代出现了酒浸天麻,宋代后天麻炮制工艺逐渐丰富,出现了热灰煨、浆水煮、炙等工艺[76]。明代在宋代炮制工艺基础上还发展了湿纸包煨后酒浸、细剉、麸炒黄、火煅、焙、酒煮等炮制方法[19,76-77]。清代则出现了姜制[77]。近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天麻炮制方法主要有净制、切制、煨天麻、炒天麻和姜天麻[55-56,77]。此外湖南和上海有麸炒天麻或蜜麸炒天麻,福建仍有酒天麻炮制法[56]。姜天麻始见于清代《幼幼集成》,现云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仍有使用,炮制过程都涉及焖、蒸等工序,并发展出“樟树帮”“建昌帮”等各具特色的炮制流派[56,77-79]。湖南姜天麻炮制方法与各地差异最大,为姜炙法更接近于古籍中的炮制方法[56,77]。结合文献报道天麻炮制可能始于南北朝时期,在宋代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炮制工艺和用药理论趋于完善[76-77]。新中国成立后天麻炮制主要涉及单炒、加固体辅料炒、炙法、蒸、煨等[55-56];《中国药典》2020版收载的炮制方法为净制、切制[1]。近年伴随药材加工方法进步,还有冻干、发酵等新工艺用于天麻饮片及相关衍生品的制作加工[80-81]。
2.2.2 天麻加工炮制现代发展与问题探讨 断生是药材采后防止天麻褐变的关键环节,蒸制杀酶和水煮杀酶均是传统断生方法[52]。考虑到水煮会导致水溶性成分的流失,目前蒸制已成为天麻断生及提升药材质量的主要方法[52,82-83]。Li等[84]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研究天麻蒸制前后25种化学成分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蒸煮可促进天麻多种化学成分转化,提高天麻素、羟基苯甲醇含量。进一步结合动物模型与代谢组学分析发现,与鲜天麻相比,蒸制天麻中有效成分更容易被生物体所吸收,其生物活性也显著优于鲜天麻[85]。研究还显示蒸煮与热风干燥2种加工方法对天麻质量的形成具有互补效应,新鲜天麻蒸制后其总酚、总黄酮、腺苷、巴利森苷C等成分含量显著下降,进一步使用热风干燥处理又能使上述成分含量及抗氧化活性提高,因此,先蒸后热风干燥的加工能有效提升天麻药用价值[85]。以上研究为揭示天麻传统“断生处理”及“蒸煮-干燥”加工技术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干燥是天麻断生后的重要加工环节。当前热风干燥、微波干燥、冻干等药材干燥技术发展迅速[80,86]。Li等[87]通过实验与模型分析发现药材干燥过程中温度和风速是影响天麻素含量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天麻热风干燥温度、风速、切片厚度、相对湿度等参数进行优化,设计出适合工业生产的高效药材干燥方法。Subramaniam等[44]研发了天麻微波干燥技术,该技术提高了药材中总酚含量并有效防止天麻素水解,在保证药材品质的同时,大大缩短了药材干燥时间,节约了加工成本。低场脉冲核磁共振可评估天麻干燥过程中水分状态变化,核磁共振成像则能呈现天麻水分空间分布特征,Chen等[88]将二者联用,研发了天麻干燥水分变化无损监测技术,为天麻干燥工艺水分精准控制提供新方法。
硫熏是改善天麻外观、延长药材贮藏时间的传统加工方法[52]。研究发现蒸制与硫熏相结合可引起天麻中支链淀粉降解产生直链淀粉,从而使天麻口感发生变化[89]。硫熏处理是一种简便、低成本的药材防虫、防霉变加工方法,但不利于天麻品质提升,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药材有效成分含量降低并导致潜在的安全隐患[90-92]。硫熏天麻二氧化硫残留量与加工方法、存储时间、硫磺用量等紧密相关[91,93]。天麻带皮整体硫熏后二氧化硫残留量较天麻切片硫熏更高,同时硫熏过的药材存储4个月后二氧化硫残留有降低趋势[93];调节硫磺与天麻用量比,控制熏烤时间有助于药材二氧化硫残留量下降[91]。硫熏加工具有一定科学性,但天麻二氧化硫限量标准制定、食品安全评估、药材质量控制与鉴别仍有待发展[91,94]。康传志[94]从硫熏工艺、硫熏标志物等方面对硫熏天麻药材质量与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Zhang等[95]则基于硫熏与非硫熏天麻的色泽、纹理、形貌特征结合机器视觉技术开发了2种天麻的鉴别方法。红外光谱指纹图谱被广泛应用于中药材质量评价,硫熏生姜、硫熏人参的光谱鉴别已有报道[96-97];与之相比硫熏天麻光谱快检技术研究仍较缺乏。
依据文献分析天麻炮制目的主要涉及2方面:(1)通过物理加工除去杂质,便于进一步炮制或制剂服用,如净制、闷润软化、切片、细剉等[55-56]。(2)通过火制、水火共制及不同辅料的加入达到改善药性、引药归经、增强特定药效的目的,如煨天麻,主要目的是改善药性、减少药物刺激,使药效发挥更为和缓[55-56];蜜麸炒天麻亦可达到类似效果并增加天麻滋补功效[55-56];文火炒天麻有助于饮片变得酥松,煎煮过程中成分能更好溶出[55-56];天麻性平,酒制天麻可使药材药效成分通达血脉,从而增强天麻祛风通络止痛的作用[77-79];姜制天麻也以增效为目的,但作用与酒天麻有差异,经姜汁炮制后天麻温中散寒、祛痰息风、定眩止痛的功效被增强[77-79]。天麻自古被认为是无毒药材,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古代炮制天麻作用多以增强药效为主。现代药理、药效研究认为经炮制加工,天麻中天麻素、巴利森苷、对羟基苯甲醇、对羟基苯甲醛等有效成分含量升高,炮制天麻药用价值优于生天麻[98-101]。祝洪艳等[99]依据古法用蒺藜炮制天麻,发现药材中天麻素、天麻多糖含量高于常见的蒸制天麻。Cheng等[100]详细对比了酒蒸天麻与生天麻间的成分差异,发现天麻酒蒸后药材中巴利森苷A、巴利森苷E含量降低,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B和巴利森苷C含量升高;通过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睡眠实验与慢性束缚应激模型研究发现,酒蒸天麻具有促进睡眠与抗焦虑作用[100]。上述研究为现代天麻炮制工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姜制是清代后天麻重要炮制方法[77]。陆平等[101]研究发现姜天麻的天麻素含量高于生天麻及硫熏天麻。Ye等[102]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分析,从姜天麻及未炮制的天麻样品中筛选出20种差异性化学成分,为后续姜天麻质量控制与药效差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传统认为姜制能增强天麻祛痰息风功效[78]。范晖等[103]利用小鼠动物模型开展系列研究发现,用姜炮制天麻明显提高了天麻的抗眩晕作用。张霞等[104]研究发现,大鼠服用姜天麻后可有效缓解硝酸甘油诱导的偏头痛,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大鼠血浆中一氧化氮及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含量,上调大鼠脑组织中5-羟色胺、多巴胺及血浆中内皮素含量,改善大鼠血管微循环,进而缓解偏头痛。上述研究为揭示姜制天麻增效机制提供更多理论依据。尽管自古炮制就是提高天麻临床药效的重要环节,然而多数炮制方法目前仅限文字记载,实际生产中应用较少[77-79]。天麻炮制前后药效变化及辅料作用规律不清,增效机制不明仍是阻碍当前天麻炮制工艺守正创新与技艺传承的关键瓶颈[52,77]。后续还需借助现代药理学进一步完善天麻炮制理论,深入揭示炮制方法对药材质量和效用的影响[105]。在此基础上针对天麻用药需求,挖掘传统炮制工艺,优化炮制过程,灵活运用不同炮制方法增强天麻药用功效与食用价值,通过理论与技术创新推动传统炮制工艺适应现代中药材规模化生产,以实现天麻药用、食用资源的高效利用。
3 结语与展望
本草考证发现天麻是多民族药材,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有悠久的药用和食用历史。以天麻为纽带,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在经贸、医药和传统文化方面相互联结;在此过程中天麻也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及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发展的重要药材资源(http://www.scio.gov.cn)。历史上天麻均为野生药源,药材长期处于稀缺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人工栽培天麻的研发使天麻药用资源的持续利用得到保障;天麻相关专利研发发展迅速,并在医疗卫生、康养保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06]。
现代天麻资源利用与评价面临新趋势和新问题。天麻质量评价仍以少数有效成分定量评价为主,药材质量标志物、化学指纹图谱及谱效关系缺乏深入探讨。中红外、近红外等多光谱技术与机器学习尚未充分融合应用于天麻药材种源、产地、真伪、加工炮制的鉴别与质控。基于现代分析化学、药理学的天麻炮制理论研究有限,炮制工艺传承以经验描述为主,缺乏有效的现代化质控手段和标准。上述问题阻碍了天麻加工技术进步与规范化生产,不利于天麻饮片的质量控制与用药安全。此外,食养理念的普及促使市场鲜食天麻需求量逐年增加,如何延长鲜切天麻贮藏时间,保障其药用和食用价值成为天麻产地加工的新问题。当前天麻保鲜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后续提高天麻保鲜工艺稳定性,消除保鲜制剂不良反应,发展低成本高效保鲜技术,建立符合药用、食用标准的鲜天麻质量评价体系仍是亟待解决的科学与技术难题。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1] 中国药典 [S]. 一部. 2020: 59.
[2] Chen S C, Liu Z J, Zhu G H,.Vol. 25 [M]. Beijing &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Science Press, 2009: 204.
[3] 陈心启, 吉占和, 罗毅波. 中国野生兰科植物彩色图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234.
[4] 刘大会, 龚文玲, 詹志来, 等. 天麻道地产区的形成与变迁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18): 3639-3644.
[5] 龚文玲, 詹志来, 江维克, 等. 天麻本草再考证 [J]. 中国现代中药, 2018, 20(3): 355-362.
[6] 顾观光. 神农本草经 [M]. 于童蒙编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 38-40.
[7] Makino T, Yasui H, Namiki T. Comparison of the names and origins of crude drugs used in ethical kampo extract formulation and listed in the western pharmacopoeias with those in the pharmacopoeia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J]., 2021, 72(4): 402-414.
[8]. 18 [S]. Crude drugs and related drugs. 2021: 2007-2008.
[9] MFDS.[S/OL]. (2019-09-01) [2023-07-14]. https://nedrug.mfds.go.kr/pbp/CCEKP14/selectEkpPopupList.
[10] Teoh E S.,[M].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2019: 55-57.
[11] 于涵, 张俊, 陈碧清, 等. 天麻化学成分分类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2, 53(17): 5553-5564.
[12] Zhu H D, Liu C, Hou J J,.Blume polysaccharides: A review of their acquisition, analysis, modifica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J]., 2019, 24(13): 2436.
[13] 付亚轩, 孟宪钰, 李明超, 等. 天麻抗抑郁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0, 51(21): 5622-5630.
[14] 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尚志钧辑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13.
[15] 吴普. 吴普本草 [M]. 尚志钧辑.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20.
[16]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M]. 尚志钧, 尚元胜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186.
[17] 苏敬. 新修本草 [M]. 胡方林整理.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38.
[18] 甄权. 药性论 [M]. 尚志钧辑释.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5-16.
[19]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校点本(第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730-732.
[20] 葛洪. 抱朴子内篇 [M]. 张松辉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47.
[21] 李世, 苏淑欣. 天麻高产栽培技术 [M].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8.
[22] 张锐. 秦汉行政体制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3] 芦笛. 天麻、赤箭、徐长卿、鬼督邮名实考 [J]. 中医文献杂志, 2009, 27(4): 31-34.
[24] 雷敩. 雷公炮炙论通解 [M]. 顿宝生, 王盛民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1: 138-139.
[25] 卢多逊, 李昉. 开宝本草 [M]. 尚志钧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146.
[26] 掌禹锡. 嘉祐本草 [M]. 尚志钧辑复.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133.
[27] 寇宗奭. 本草衍义 [M]. 张丽君, 丁侃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30.
[28] 唐慎微. 证类本草 [M]. 郭君双, 金秀梅, 赵益梅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184.
[29] 李东垣.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白话解读本 [M]. 常章富编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257.
[30] 王好古. 汤液本草 [M]. 张永鹏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43.
[31] 张介宾. 景岳全书(上) [M]. 李继明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217-648.
[32] 张志聪. 本草崇原 [M]. 张淼, 伍悦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20.
[33] 汪昂. 本草备要 [M]. 郑金生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46.
[34] 吴仪洛. 本草从新 [M]. 朱建平, 吴文清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1: 10.
[35]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M]. 苏礼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22-376.
[36] 凌奂. 本草害利评按 [M]. 钱俊华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51.
[37] 苏颂. 本草图经 [M]. 尚志钧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64.
[38] 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53.
[39] 岩崎常正. 本草图谱 [M]. 影印本.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72-73.
[40] 钱信忠, 楼之岑, 肖培根.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 (常用中药篇)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49-47.
[41] 贾敏如, 李星炜. 中国民族药志要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 287.
[42] Wang J, Seyler B C, Ticktin T,. An ethnobotanical survey of wild edible plants used by the Yi people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China [J]., 2020, 16: 10.
[43] 谢宗万. 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169.
[44] Subramaniam S, Wen X Y, Jing P. One-step microwave curing-dehydration ofBlum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tochemicals, water states and morp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J]., 2020, 153: 112579.
[45] Chapagain A. An overview of Nepalese medicinal plant trade with China [J]., 2021, 28(1): 556228.
[46] He J, Yang B, Dong M,. Crossing the roof of the world: Trade in medicinal plants from Nepal to China [J]., 2018, 224: 100-110.
[47] Jo W S, Lee S, Choi H,. Studies on the technique of cultivatingusing small diameter log [J]., 2017, 15(2): 69-72.
[48] 沈忱, 陈卫平. 《本草纲目》对日本、朝鲜医药学界影响的比较研究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0(2): 183-185.
[49] Watanabe H, Shindo S, Matsubara K,. Domestic production of kampo herbal medicines in medicinal plant gardens during the Edo period-efficient cultivation and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medicinal plants in Japan [J]., 2016, 91(Suppl): 396-411.
[50] Kuchta K. Traditional Japanese kampo medicine-History of ideas and practice; Part 1: From ancient shamanic practice to the medical academies of Edo [J]., 2019, 6(2): 49-56.
[51] Liu S H, Matsuo T, Matsuo 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prescriptions brought from China to Japan by a monk (Jianzhen, Japanese: Ganjin): A historical review [J]., 2022, 2(4): 267-284.
[52] 彭成. 系统中药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134-135.
[53] 朱艳玲, 郭瑞华. 天麻四性变迁的本草考证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35(5): 423-425.
[54] 日华子. 日华子本草[M]. 常敏毅辑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46.
[55] 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中药炮炙经验集成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33.
[56] 云南省卫生厅. 云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86: 43.
[57] 中国药材公司.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539.
[58] 单锋, 周良云, 蒋长顺, 等. 天麻的食用历史及发展建议 [J].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21(3): 110-115.
[59] 郭佳欣, 谢佳, 蒋丽施, 等. 天麻保健食品开发现状分析 [J]. 中草药, 2022, 53(7): 2247-2254.
[60] 李杲. 用药珍珠囊 [M]. 王今觉, 王嫣点校辑补.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0: 7.
[61] 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 [M]. 张家玮, 赵文慧校注,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68.
[62] Yin Q, Yan R, Wang Y,. Gastrodin fromattenuate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by suppressing autophagy: Key role of the miR-30a-5p/ATG5 pathway [J]., 2023, 102: 105429.
[63] Wang D X, Wang Q, Chen R H,.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Blume on the treatment of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using UPLC-Q/TOF-MS-based plasma metabolomics [J]., 2019, 10(11): 7204-7215.
[64]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 [M]. 刘更生, 蔡群, 朱姝, 等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28-29.
[65] 邵万宽. 我国古代食物的加工与贮藏技术 [J]. 农业考古, 2017(4): 201-207.
[66] Wang Q H, Zhao L, Gao C,.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herbal market a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f Chuanqing people in China [J]., 2021, 17(1): 19.
[67] Xie J, Liu F S, Jia X H,. Ethnobotanical study of the wild edible and healthy functional plant resources of the Gelao people in northern Guizhou, China [J]., 2022, 18(1): 72.
[68] Guo C G, Ding X Y, Hu H B,. An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wild plants used by Tibetan people in Gyirong Valley, Tibet, China [J]., 2022, 18(1): 67.
[69] 郭怡博, 张悦, 陈莹, 等. 天麻人工栽培模式调查分析及发展建议 [J]. 中国现代中药, 2021, 23(10): 1692-1699.
[70] 王佩, 孟广云, 毛如志, 等. 不同环境栽培对天麻土壤理化性质、微生物、代谢物的影响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1, 27(14): 164-174.
[71] 熊万, 唐成林, 王以兴, 等. 不同氮磷钾配比对天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 2020, 39(3): 61-66.
[72] 杨婧, 王传华, 曾春函, 等. 海拔对乌红杂交天麻产量与品质的影响及其酶学作用机制 [J]. 西北植物学报, 2021, 41(2): 281-289.
[73] Yu E, Gao Y G, Li Y Q,. An exploration of mechanism of high quality and yield ofBl. f.by the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J]., 2022, 22(1): 621.
[74] Wang C H, Zeng Y J, Hou Y B,. Effects ofspecies on growth and quantity of active medicinal components ofBlf.tubers along an altitude gradient: Evidence from empirical experiments [J]., 2023, 54: 101-106.
[75] 龚文玲. 天麻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建立及其质量评价[D]. 武汉: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9.
[76] 赵禾笛, 王丹, 翟小林, 等. 天麻“产地加工-炮制-质量评价”相关性的本草考证 [J]. 中药材, 2020, 43(10): 2577-2584.
[77] 李玉清. 本草古籍常用药物采收加工与炮制考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348-350.
[78] 胡志方, 陈建章. 建昌帮中药炮制技术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840-845.
[79] 范崔生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樟树药帮中药传统炮制法经验集成及饮片图鉴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67-68.
[80] 付伟, 杨群, 薄雯映, 等. 基于Box-Behnken法的天麻冻干工艺优化研究 [J]. 中南药学, 2021, 19(1): 20-24.
[81] 陈刚, 高晴, 和劲松, 等. 响应面法优化天麻发酵液发酵工艺 [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3, 44(4): 162-167.
[82] Xie Y K, Li X Y, Chen C,. Effects of steam and water blanching on drying characteristics, water distribution, microstructure, and bioactive components of[J]., 2023, 12(6): 1372.
[83] Xie Y K, Li X Y, Zhang Y,. Effects of high-humidity hot air impingement steaming on: Steaming degree, weight loss, texture, drying kinetics, microstructure and active components [J]., 2021, 127: 255-265.
[84] Li Y, Liu X Q, Liu S 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hemical ingredients in steaming process ofBlume [J]., 2019, 24(17): 3159.
[85] Wu Z, Gao R P, Li H,. How steaming and drying processes affect the active compounds and antioxidant types ofBlf[J]., 2022, 157: 111277.
[86] 肖伟香, 张士齐, 杜洪志, 等. 天麻产地加工及其质量评价研究进展 [J]. 农业技术与装备, 2023(2): 55-60.
[87] Li K, Zhang Y, Wang Y F,. Effects of drying variables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ot air drying for: Experiments and multi-variable model [J]., 2021, 222: 119982.
[88] Chen Y N, Dong H J, Li J K,. Evaluation of a nondestructive NMR and MRI method for monitoring the drying process ofBlume [J]., 2019, 24(2): 236.
[89] Guan J J, Chen Z W, Guo L P,. Evaluate how steaming and sulfur fumigation change the microstructur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digestibility ofBl. starch [J]., 2023, 9: 1087453.
[90] Zhang X R, Ning Z W, Ji D,. Approach based on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ingerprint coupled with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J]., 2015, 38(22): 3825-3831.
[91] Kang C Z, Lai C J S, Zhao D,. A practical protocol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ulfur-fumigation ofusing metabolome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alysis [J]., 2017, 340: 221-230.
[92] 薛鹏仙, 龙泽荣, 袁辉, 等. 硫熏中药材品质及其毒理学研究进展 [J]. 化学通报, 2019, 82(7): 598-605.
[93] 康传志, 蒋靖怡, 杨婉珍, 等. 不同贮藏时间硫熏天麻化学成分及二氧化硫变化规律研究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8, 43(2): 261-266.
[94] 康传志. 硫磺熏蒸对天麻和牛膝药材质量的影响 [D].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8.
[95] Zhang Z M, Zheng Z A, Li A C,.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Blume has been fumigated by sulfur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A] // 2021 ASABE Annual International Virtual Meeting [C]. Michigan: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s, 2021: 2-11.
[96] Yan H, Li P H, Zhou G S,. Rapid and practica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non-fumigated ginger and sulfur-fumigated ginger via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chemometric methods [J]., 2021, 341: 128241.
[97] Li P, Zhang Y N, Ding Y,. Discrimination of raw and sulfur-fumigated ginseng based on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coupled with chemometrics [J]., 2022, 181: 107767.
[98] 杨飞, 王信, 马传江, 等. 天麻加工炮制、成分分析与体内代谢研究进展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8, 43(11): 2207-2215.
[99] 祝洪艳, 蒋然, 何忠梅, 等. 不同乌天麻炮制品中天麻素、天麻苷元和天麻多糖的含量分析 [J]. 中国药学杂志, 2017, 52(23): 2062-2065.
[100] Cheng L J, Wang H, Ma K J,. A novel alcohol steamed preparation fromBlume: Pharmacological assessment of a functional food [J]., 2023, 14: 1092693.
[101] 陆平, 金镭, 贾彩虹, 等. 江西建昌帮姜天麻与其他炮制品中天麻素的含量差异 [J]. 中国医药导报, 2018, 15(4): 27-30.
[102] Ye X D, Wang Y H, Zhao J P,.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key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processedusing UHPLC-MS/MS and chemometric methods [J]., 2019, 2019: 1-10.
[103] 范晖, 王丽华, 刘琪琳, 等. 建昌帮姜天麻中苯丙素类对小鼠抗晕眩作用的影响 [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20, 20(16): 157-159.
[104] 张霞, 高慧, 阿丽牙·阿布来提, 等. 江西“建昌帮”姜天麻对硝酸甘油诱导的大鼠偏头痛的作用 [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020, 31(8): 887-891.
[105] 唐文文, 孟艳林, 陈垣. 基于多指标成分优化天麻产地“发汗”加工工艺 [J]. 中草药, 2021, 52(23): 7185-7191.
[106] 上官晨虹, 全毅恒, 陈琛. 基于专利计量的天麻药品研发态势分析 [J]. 中草药, 2022, 53(15): 4915-4924.
Herbal textual and key problems discussion in modern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HEN Tao1, LIU Hong-gao2, WANG Yuan-zhong3
1. College of Chemistry,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 China 2.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Gastrodia and Fungi Symbiotic Biology,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3.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s,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unming 650200, China
Tianm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herb with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healthcare and wellnes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name, effectiveness, orig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ocessing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were summarized. Meanwhile, the new trends and problems du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were discussed.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future evaluation system of medicinal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and deeply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dicatio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of, and establish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for quality control, origin traceability, preservation and storage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and it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 herbal textual; changes of producing areas; processing technology; resource evaluation
R282
A
0253 - 2670(2023)18 - 6106 - 12
10.7501/j.issn.0253-2670.2023.18.028
2023-04-11
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202202AE090001);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项目(202205AC160088)
沈 涛,男,博士,从事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研究。E-mail: st_yxnu@126.com
王元忠,男,博士,副研究员,从事药用植物和真菌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E-mail: boletus@126.com
[责任编辑 赵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