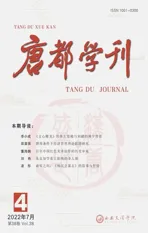从良知学看王阳明的圣人观
2022-11-21刘艳
刘 艳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39)
王阳明的所有思想皆围绕其良知学而展开,良知学指的是以人先天所具有的德性——“良知”为核心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王阳明的理想人格正是在其良知学的基础上构建的。“君子”“大人”“狂者”都是王阳明极为赞赏和推崇的人格,而“圣人”才是其终极的理想人格。“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1]43,只有“圣人”才是完满的。但圣人并非普通人不可及,王阳明认为人人皆可为圣,“满街人都是圣人”[1]132,圣人与“愚夫愚妇同”[1]121。基于此,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王阳明将“圣人”世俗化、大众化了。然而这一通行的观点忽视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个体性、特殊性。其实,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圣人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个体性,每个人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或者个性“量身打造”圣人之身,即满街都是不同的圣人。“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1]43,此“性”此“道”皆与良知相关,而良知人人具有。那么,王阳明是如何在良知学的基础上构建其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体性的圣人观呢?本文试图通过对良知、致良知的多重内涵以及逻辑考察来阐述王阳明的理想人格,展现其思想中圣人的形象。
一、“三变”:王阳明圣人观的成型历程
阳明之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1711,与之相应,其成圣之路的探寻也经历了“三变”,并蕴含在其为学之“三变”的过程中。王阳明自幼有志于圣人之学,将学为圣贤视为人生第一等事,并且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不断探索。18岁时大儒娄谅与其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可学而至”,王阳明对此“深契之”,于是开启了一段艰辛的探索成圣之路。其“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1]1711,在程朱理学官学化的背景下,这是王阳明寻求成圣之境的首要途径。然而,21岁在父亲官署中格竹受挫,27岁循序格物旧疾复发,王阳明颇感心与理“终若判而为二”,两次格物失败使其“益委圣贤有分”[1]1350。于是转向佛老之学,直到31岁时“渐悟仙、释二氏之非”[1]1351,成圣之路又一次受阻。程朱、佛老之学都没有实现王阳明的成圣之志,其原因何在?程朱理学主张向外求索,认为理在心外,析心与理为二。在朱子的思想中,“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2]2830,所以将穷极天下之物视为成圣之途。而其现实路径就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少积多,达至豁然贯通。显然,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学习能力有别,通过“格物”或者说“格”同一“物”所获得的“天理”各不相同,对物之理的认识也是深浅各异,以至于从“格物”到“豁然贯通”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参差不齐,且长时间地格物会劳神成疾,精力不足者劳思致疾,甚至部分后学者因缺乏良师指导在格物的过程中容易走向歧路。所以,朱子所谓的全能圣人并不现实,且难以实现,甚至可以说不能实现。在王阳明看来,格“天下之物”,从“物”的向度出发,以“物之理”为出发点无法安顿人之身心,即宋儒“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者也”[1]1711,难以达到天人合一、心理合一之境。换句话说,外在之物没有“主动性”,很难与人心相契合,一味地逐外物,往往会忽视内心的真实感受,使得理在心外、心理分离,导致人灵魂空虚,成圣受挫。总之,从物到心,以物来启发人心获取天理委实困难。就连朱子也感叹圣人难为,“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2]2611所以,王阳明认为朱子眼中的圣贤是“做不得”的。
在遵循朱子格物而“无所得入”之时,王阳明开始出入于佛、老,泛滥于二氏之学。然而,佛、老之学超然于世累之外,“遣弃其人伦事物之常”[1]273,“不染”[1]1301世间一切情欲之私,对于常思“祖母鞠育之恩”[1]1399,听闻父亲病危“欲弃职逃归”[1]1410的王阳明来说这是“断灭种性”。出世的佛、老之学无法尽孝道,与王阳明内心的真实感情极为不符。除此之外,内以修己、外以治国平天下是圣贤之举,而佛老“一切都不管”“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1]11,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佛家“欲求宁静,欲念无生”[1]76,将天地万物之理置之度外,老氏讲养生,皆是“自私自利”。二氏之学斩断人的情感,远离社会关系,逃避父子、君臣、夫妇之伦常,隔断了人与万物的关系,视人为独立于万物的单个个体。以我之身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难免有“遗外”“义外”之嫌。显然,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佛老之学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圣贤之学差之千里,佛老之路不但不能成圣,反而使人远离社会,成为脱离社会关系的独立个体。正因如此,王阳明“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1]1708。看来,以佛老之学来实现成圣之志也是行不通的。
直至谪龙场时,面对“穷荒无书”之境,王阳明并没有放弃成圣之志,而是在“日绎旧闻”的过程中忽悟格物致知之旨乃“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1]1708,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1]1711,此“性”乃人先天之良知。“日绎旧闻”暗含着王阳明对宋儒、佛老思想的反思:宋儒“不恃此明觉”[1]1711,“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1]1712;释氏“尽绝事物”“止守此明觉”[1]1711,渐入虚寂;老庄“外礼以言性”[1]172“清净自守”[1]257,有“空虚漭荡”之弊,与释氏一般。儒释道各有所偏倚,而王阳明“归理于天地万物,归明觉于吾心,则一也”[1]1711-1712,认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1]1712,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主张“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1]51。从人之先天“良知”出发来明“天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良知与天理打通,不弃本心,不遗人伦,在致良知过程中成就理想人格,这是王阳明在“患难幽独”中寻找到的成圣之路。宋儒从外在之物出发,缺乏对内在本心的体认;佛老从内在之身心出发,抛弃外在人伦之事。而王阳明成圣之径既无宋儒格物的繁琐,也无佛老静坐的虚寂;既没有“忘内”之嫌,也没有“遗外”之弊,而是兼宋儒和佛老之长,主张内外合一,正所谓“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1]1423。不难发现,王阳明在吸收宋儒、佛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良知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良知学也是王阳明成就理想人格之学。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主张满街人都是圣人,增强了“人人皆可成圣”的自信心,打破了“圣人难做、圣人做不得”的传统观点,消解了圣人遥不可及的崇高性。
二、“良知”:王阳明圣人观的理论内核
“良知”二字是王阳明思想的精髓,经过百死千难的生活磨练,他深刻地认识到“良知”乃“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1]1412,这一点滴骨血是古圣先贤和今人共同的特质,或者说这是“人”的特质,因为“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90。正是人人具有良知,所以“众人亦是生知”[1]108,人的这一点先天之良知构成了成圣的前提。易言之,“良知”是成圣的必要条件,没有“良知”的存在就没有王阳明满街圣人的观点。所以,良知是王阳明圣人观的内在根据,在其理想人格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良知的具体意涵是什么,它在评判善恶是非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研究王阳明理想人格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良知与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1]31,圣人之心纯乎天理的依据在于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之在人心”[1]78,而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纯乎天理是良知的本然状态,所以“良知即天理”。天理乃良知的首要内涵,良知是人先天本有,良知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1]78,这便为人人皆可成圣提供了先天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具有内在性,是不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以往学者追求圣人人格,视圣人为万人敬仰之模范,先识“圣人气象”,从圣人气象上寻求天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准的”[1]66,然后去学习和模仿。这种圣人之途往往导致学者只是从仪节上求得是当,追求外在气象,甚者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矫揉造作之态,似与戏子一般。圣人气象是此心纯乎天理在人形象气质中的外在表现,是人之良知的自然而然,来不得半点效仿。所以,王阳明称“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1]66,他人无处“识认”,往日学者先识圣人气象,其行为乃本末倒置,是“欠有头脑”,犹如无星之称权轻重,未开之镜照妍媸。求圣之工夫只能从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1]66,都是以天理作为内容,是至善无恶的,如果能够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认真体认自己良知,那么“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66。正所谓成圣由己不由人、求圣在己不在人。“有源者由己,无源者从物”[1]172,成圣由己源于人人皆有纯天理而无人欲的良知,天理在我之心,存我良知之中,我本自足一切,成圣何待向外求!良知的天理内涵成就了满街都是圣人,只是这个“圣人”是潜在的,通过人对良知的体认和推致才能够变为现成圣人。“满街人都是圣人”指的是人人具有成圣的潜能,都是潜在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满街圣人无有不同。但实际上现成圣人却是气象各异,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即使是尧舜禹,其外在气象表现也各有不同。以人人具有天理良知而言,“我”本圣人,“我”这个圣人随“我”的才力而发,以“我”的才力展现天理。圣人才力有大小之别,犹如“金之分两有轻重”[1]31,才力的大小并不影响人之为圣,因为圣人“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犹如黄金“在足色而不在分两”[1]32。然而,王阳明以金之分两喻圣人之才力存在漏洞。圣人才力不同,在不同的境遇中表现不同,即使在同一境遇中才力不同的圣人呈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也可能不同,也就是说,道德主体从自身才力出发在日用动静之间体现天理良知,才力大小导致其言行各有不同。工农士贾皆为圣人,才力和生活境遇的不同致使其圣人的表现形式有异。没有相同的人生,更没有相同的圣人。而足金分两虽有差别,但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形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其形式的同与异并非由分两的多少而决定,即足金的分两与其形式没有关联性。所以,王阳明以金之分两喻圣人之才力存在不足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天理先天存在于人心之中,圣人因纯乎天理而称为圣人,精金因足色无杂而成为精金。天理乃形上之本,万古不变;气象乃形下之末,不拘一格,圣人气象是形而上之天理所展现出来的形而下之景象。各随才力,皆有所至,王阳明所谓的圣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个体,满街圣人各不相同,气象各异,充分地彰显了人的个性自由。王阳明认为,作为一个现实的圣人,追求功业也是“理”所当然,“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1]109,圣人不以功业闻名天下,只是循着天理而已,其功业是形上之天理的体现。所以,人人都可以建功立业,且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来追求功名。换言之,功业并不与天理矛盾,相反只要遵循天理,在建功立业中同样能够成圣成贤。当然,不同的人建功立业的形式和表现各不相同,成就的圣人也是气象各异。因而,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各随才力建功立业造就不同外在气象的圣人,使得圣人具有了各自的个性特征。天理纯善无恶,人先天具有的良知是天理的化身,无论何种才力之人,“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1]36,则“人人自有,个个圆成”[1]36。良知因天理而具有完满性,使曾经遥不可及的圣人变得触手可得,填补了圣人与普通人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了“心之良知是谓圣”的观点。
其次,良知与天道。“良知即天道”[1]298,良知蕴含着天道之意。我们往往将天理等同于天道,其实天理与天道是有区别的,特别在王阳明这里尤为突出。王阳明言“天理即是‘明德’”[1]7,天理指人先天所具有的本然之性,构成了人人皆可成圣的首要基础,作为良知的内涵其存在形式是静态的。天理与人欲相对,多指人的伦常道德。而天道与人道相对,多指自然现象、自然运行规律等。日月之所以能昼夜往复、照临不穷,四时之所以能循环更替、生运不穷,皆因“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1]1078。天道虽多与自然相关,但修人事以达天道,其与人事也是息息相连,如圣人“能成而化,化而复成”[1]1078,妙用不穷,源于天道“常久不已”。王阳明认为“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1]298,天道具有运行不息的特征,与之相应,圣人循天理而行,教化万众不止,展现了天道之运动,即圣人之行合乎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是本然也是应然。“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1]298,良知本身是动态的,其运行合乎天理,呈现天道的运行不息,从运动的意义上来说,良知即天道。但不可谓之良知“亦”天道,因为“亦”字“则犹二之矣”。可见,良知与天道本为一,良知的无一息之停本就是天道。“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1]1438成为现实圣人的途径即致良知,致良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良知即天道也蕴含着致良知即天道的意思。天道作为良知的内涵其存在形式是动态的,较天理而言内涵也更为广泛。如果以知为静,以行为动,那么圣人之知多与天理相关,圣人之行多与天道相关,也可以说圣人之知乃天理,圣人之行乃天道。虽然良知不“可以言动静”,但其本身内在的存在着动与静,王阳明言良知“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1]72,只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所以动即静、静即动,不可以严加区分。从动与静的角度来说,良知包括天道和天理的双重内涵,天理使人人成为潜在圣人,天道使得人人在日用常行的动态生活中成就圣人,故而,天道成为人人成圣的第二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天道的内涵使得良知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这个动态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天道如何在圣人行为中落实?如果说是循理而行,理、天理纯善而无恶,那么圣人之行皆善行。但是有善必有恶,圣人为何在循天理之时能辨别善恶而后从善弃恶?无疑其辨别善恶的能力是先天所具有的良知之本有,善与恶“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1]1070,而能够自知善恶皆因良知是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不假外求。良知作为是非之心“是尔自家底准则”[1]105,这里的准则更多地指道德评价标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范导意义。一方面,良知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另一方面,良知具有判断、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能力。王阳明认为愚人与圣人“虽有昏明不同”,但因良知人皆有之,所以“其能辨黑白则一”[1]126,即能够当下判断孰善孰恶、孰是孰非。“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1]126,可以判断善恶,即使有人做了恶事,以至于“逆理乱常之极”,而“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1]1112,小人也不例外。小人行为不善,无所不止,但“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1]1070,说明小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善,试图在君子面前掩饰恶行、彰显善行。小人知其自身行为不善,表明其良知“不容于自昧者也”[1]1070,换言之,良知作为是非之心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且不会欺骗任何人,尽管做了恶事,良知也会明示小人其恶行是不被认可的。但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小人知善不行、知善行恶,这是分知行为两事,属于“知而不行”,对于这种情况,王阳明认为这是“未知”。“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1]1711,小人私欲泛滥,自欺本心,其知非真知,非真知即未知。是非之心辨善恶,普通人却难以在现实行为中择善去恶,所以需要不断致良知,只要能致良知,愚不肖者也会“与圣人无异”[1]312。辨是非善恶是一种理性的分辨,择善去恶则是一种感性的认同。是非之心在王阳明这里不仅可以辨善恶、明是非,而且蕴含着道德情感原则。“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126好即喜爱、喜欢,恶即憎恶、厌恶。在理性辨别善恶之时存在着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所以是非之心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人人皆好善恶恶,但是只有圣人至诚无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1]110,致其本然之良知,在辨善恶之时就择善去恶了,其道德判断、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之间不经任何干预而具有天然的一贯性,因为圣人致良知是“自然而致之”,一切都是本心所发,愚人“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1]312,难以在现实行为上真正做到行善去恶。是非之心使人人具有先天辨别善恶的能力,为进一步择善去恶成为现实圣人提供基础,也许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有“知善知恶是良知”[1]312之语。
三、“致良知”:王阳明圣人观的实现路径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现实的圣人不是天生的,如果说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那也只是从“义理”方面而言。“义理”是“天理”的题中之义,所以人人具有。王阳明所言的“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1]60,主要指的是从良知之虚灵明觉、心之虚灵明觉的角度谓圣人之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能够自然顺应天理,在行为上以此良知而行,使得内在于己心的天理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将天理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状态,将本然之良知通过致良知转化为明觉之良知。普通人虽先天具有天理,但是会被私欲遮掩,其致良知要么“勉然而致之”[1]312,要么“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1]312,与圣人“自然而致之”[1]312相差甚远。“自然”意味着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人可以谓之“生而知之”者,这里的“知”也可以理解为“致”,即“生而致之”。可以看出,以现成而言,圣人也需要致良知才能在现实行为中做到择善去恶,达到知行合一。所以“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1]247,只有通过致良知才能将潜在圣人化为现成圣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圣人是先天良知与后天努力的结果,“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1]311良知是人先天所有而非后天能为,能为的只是“致”良知。先天良知是成圣之本,后天致良知才是成就圣人的现实途径。致良知的过程,是潜在圣人化为现成圣人的过程,是良知从本然走向明觉的过程,也是道德本原走向现实德性的过程。所以,“致良知之外无学矣”[1]312。“致良知”是作圣为贤之要,即使是“昏暗之士”,只要能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1]53。
从理论意义上而言,良知具有两种存在状态,即本然状态和明觉状态。本然状态之良知具有先天性,其普遍性决定了人人成圣的可能性;明觉状态之良知是对本然之良知的自觉,是现成圣人的表现,需要通过后天“致”的工夫才能达到。“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1]312,潜在圣人走向现成圣人,致良知是唯一方法。致良知重在“致”字上,什么是“致”?“致者,至也”,至有到达之义,又蕴含极点之义。“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1]1071,“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1]136,致良知是要达到良知之极,使良知无私欲遮掩,也即扩充良知之全体,良知之全体指的是良知本体、本然之良知,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1]53,所以良知之极其实就是良知的明觉状态。此种状态之下,“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1]1746,明觉良知是本然良知之发用流行,良知明觉与否,决定着现成的善与恶、是与非,只要处于明觉状态的良知,则一切现成行为纯善无恶。所以,致良知指的是要达到对本然之良知的自觉,即良知之明觉状态,化本然良知为现实德性、德行,使此心纯天理而无人欲。王阳明又言:“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1]1070,遇丧则应哀,这是一种道德情感的表达,说明致良知中包含有道德情感的认同,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践履的统一。那么如何够达到良知之极,使得本然良知化为明觉良知?王阳明曾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1]109致良知说到底就是去除障蔽良知本体的私欲,恢复心之本体,展现本然良知。“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1]136,“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极”[1]1316,存天理,无私欲遮蔽,良知才能“致其极”,呈露全体。以“至”训“致”更多地指向致良知的目标,蕴含存天理、去人欲的现实方法,这是消级方面的致良知。从积极方面而言,致良知是依良知而行,“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1]311,“致”有实行、实践之意。良知是先天的道德准则,是非善恶“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1]105,按照本然之良知去做,现实行为则纯善无恶。“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1]308致知包含“为之”“行之”的意思,遵照良知去实践,把良知贯穿于各个行为中,才是圣人之举。“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1]56,“行”是致良知的内在规定。正因为“致”有“行”之义,所以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1]308,知行合一是致良知的精神实质。但是知行工夫有深浅难易之殊,“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1]126王阳明将人分为三个层次,生知安行者圣人也,学知利行者贤人也,困知勉行者学者也,只有圣人能做到依良知而行,贤人需要时刻警觉醒悟,避免私欲侵染,促使自己按照良知去行,一般学者受私欲遮蔽较多,必须下更大功夫,以百倍千倍的努力才能拨开云雾见白日,使人欲消失天理自现,顺良知而为。可见,除圣人之外,其他人皆因私欲遮掩需要不断增强自我主观意识,通过现实的主观努力才能不违背良知且依良知而行。前文所言小人,其逆良知而为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主观上向善的努力,任由私欲泛滥,所谓良知不欺小人,小人自欺也。圣人之行自然而然,被称之为生知安行者,但是其不敢自称生知之人,反而“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1]127,时刻保全良知,“兢兢业业,亹亹翼翼”,使本然良知昭然不昧,所以可以说“圣人亦是‘学知’”[1]108。致良知作为一种工夫,既是潜在圣人转化为现成圣人的途径,又是现成圣人维持圣人气象的根本,而无论是潜在圣人还是现成圣人,后天的主观努力是致良知的关键。
从现实意义而言,致良知着重从主体自身出发通过经验性活动来完成,先验性良知以经验性的实践活动来展现其作用。而经验性活动不仅包括实实在在的直接性行动,还包括具有间接性质的见闻,所以如何对待见闻是致良知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王阳明认为先验性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1]80,见闻是良知之用,良知是见闻之体,良知与见闻是体用、本末的关系。“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80,这里的良知其实是就致良知而言,王阳明的意思是说致良知活动不受经验性的见闻所局限,但是要通过当下的所见所闻来决定符合良知和天理的具体行为,即要在具体的见闻中来实现自己。视、听、言、动皆为经验性活动,视、听是见闻,言、动是行为,按王阳明的理解,当下所行离不开当下见闻,当下见闻可以看作是致良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们不必“专求之见闻之末”,否则就是“失却头脑”[1]80。“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1]80-81,强化致良知的主观意念,一心一意致良知,则任何见闻中都体现致良知之功,那么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1]81当然,“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1]81,致良知“不是悬空的致知”[1]136,是实实在在的成圣工夫,要在日常的见闻酬酢中来实现,不离人之日用常行,就如在俗世中修行才是真修行一样,于闻见之中致良知才是真圣人之行。人非槁木死灰,闻见乃生活之常,如欲不闻见,除非“耳聋目盲”,既然见闻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对待?王阳明言“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1]104,不被所闻所见左右,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从心而行,做到不悖逆良知。总之,任何成圣工夫都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进行。
从伦理意义上而言,圣人之行依照良知天理,符合现实伦理道德,其所作所为是必然,也是应然。所以致良知亦包含应然之义,“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1]239,致良知是具体的,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是“在实事上格”[1]136,而“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1]17,随“事”而变,随“时”而变才是真正的致良知。“素富贵行乎富贵”[1]24,“行乎富贵”包括适“时”地“弃富贵”。富贵乃人之所好,但是不义之富贵与天理良知相左,此富贵应当弃之。除此之外,“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1]1424,外在富贵名利牵绊着学者之本心,使其少了洒脱之境,所以当富贵成为成圣成贤路上的羁绊时,应该弃之。然而,王阳明所言的“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也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当求富贵即求富贵也是致良知,求富贵、好富贵是人之常情,只要求富贵发自本然之良知,是天理的自然流行即可。可见,王阳明笔下的圣人并非无思无虑、清心寡欲之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人,可以说王阳明缩小了普通人与圣人之间的距离。另外,适“时”而为才是致良知的真谛,违逆父兄之命与儒家纲常伦理相悖,所以理学家倡导人人应遵从父兄之命,王阳明也言“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但是“当”字意味深刻,蕴含着从父兄之命并非绝对,也存在不从父兄之命的情况。如果父兄之命不符合天理良知,那么“不从”父兄之命就是理所应当,就是致良知。王阳明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不从”违背天理的父兄之命,而一个“当”字已经隐晦地表达其弦外有音,此弦外之音不得不说是对封建权威的挑战。弃富贵与求富贵、从父兄之命与逆父兄之命都是致良知的内容,按王阳明的理解,现实生活中事事物物皆是相对的,只有内在之良知天理是绝对的,所以圣人唯“天理”是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从客观外在的生活现象而言,依良知而行,人的一切言行皆符合天理,从主观个体自身而言,致良知能够让主体精神上安然自足,即“无入而不自得”[1]279,具体而言就是“自快吾心”。王阳明言“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1]1018,生活处处是致良知之地,致良知所获得的愉悦之情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体验,来自于主体自觉循良知而行时精神充实所产生的自我快乐感,这种快乐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感性满足。总之,无处不是致良知之地,致良知不仅使人的行为与天理一致,而且能够给主体带来内心的自足与快乐,从侧面也反映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纯理性之人,而是一个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现实的人,是一个内在之情与外在之行相统一、相融合的现实的人。
圣人在现实生活中致良知,其言行合乎天理,但是并不意味着圣人是全能、全知的。恰恰相反,圣人有所能有所不能,且也会像一般人一样有过错。正是这“不足”之处才使得人人成圣变得更加真实,增强了普通人成圣的自信心,成圣之路才具有了可操作性。圣人所能、所知的只是天理,所不能、不知的是礼乐名物、节文度数等具体的知识,对其所不能、不知之事也是“必待学而后能知”[1]60的。圣人不患无过,唯患不改过,“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1]893。可以看出,王阳明心中的“圣人”并非一个完美之人,而是“可学而至”的,是在生活中追求天理、不断磨练的现实的人。圣人的“不足”之处使成圣具有了可实现性,理想人格的理想之处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具有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