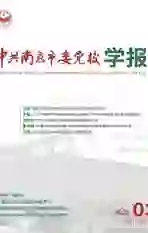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吗?
2022-07-11严斌剑靳振忠
严斌剑 靳振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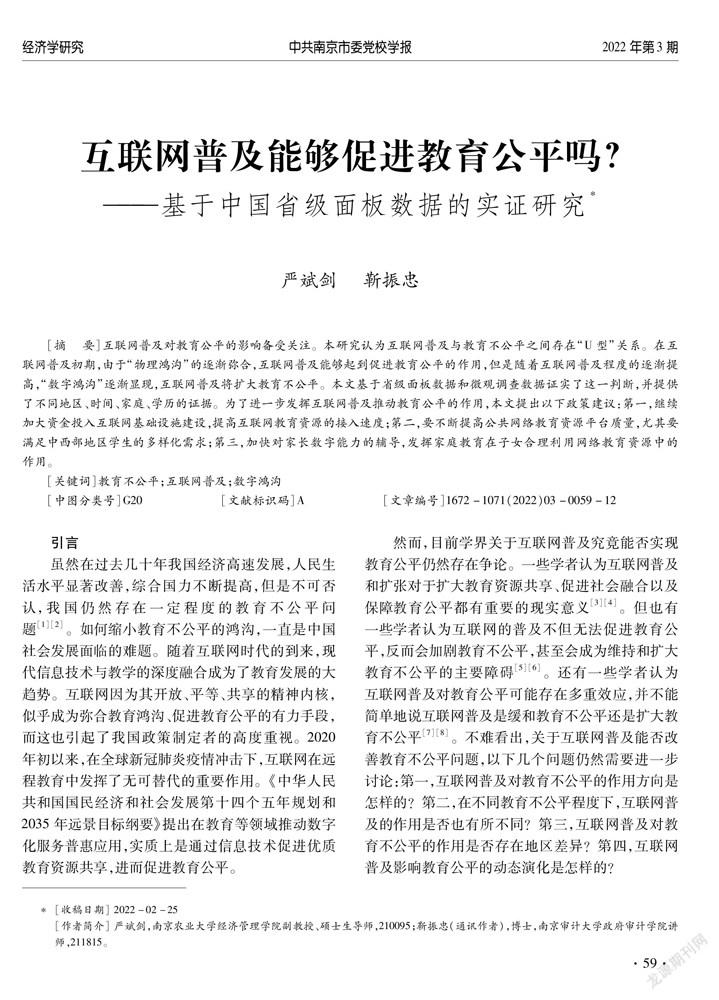

[摘 要]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备受关注。本研究认为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由于“物理鸿沟”的逐渐弥合,互联网普及能够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但是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逐渐提高,“数字鸿沟”逐渐显现,互联网普及将扩大教育不公平。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判断,并提供了不同地区、时间、家庭、学历的证据。为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普及推动教育公平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教育资源的接入速度;第二,要不断提高公共网络教育资源平台质量,尤其要满足中西部地区学生的多样化需求;第三,加快对家长数字能力的辅导,发挥家庭教育在子女合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中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不公平;互联网普及;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2)03-0059-12
引言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是不可否认,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问题[1][2]。如何缩小教育不公平的鸿沟,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互联网因为其开放、平等、共享的精神内核,似乎成为弥合教育鸿沟、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手段,而这也引起了我国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2020年初以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互联网在远程教育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教育等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实质上是通过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进而促进教育公平。
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互联网普及究竟能否实现教育公平仍然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普及和扩张对于扩大教育资源共享、促进社会融合以及保障教育公平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4]。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不但无法促进教育公平,反而会加剧教育不公平,甚至会成为维持和扩大教育不公平的主要障碍[5][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可能存在多重效应,并不能简单地说互联网普及是缓和教育不公平还是扩大教育不公平[7][8]。不难看出,关于互联网普及能否改善教育不公平问题,以下几个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一,互联网普及对教育不公平的作用方向是怎样的?第二,在不同教育不公平程度下,互联网普及的作用是否也有所不同?第三,互联网普及对教育不公平的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第四,互联网普及影响教育公平的动态演化是怎样的?
因此,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全国及各省教育基尼系数的基础上,研究互联网普及能否改善教育公平这一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以教育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更为直观的关系;其次,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系统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影响的地区差异与时间差异;不仅如此,本文还考察了在不同教育不公平程度下,互联网普及的作用差异;最后,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动态面板方法进行了弥补,以期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稳健。
本文主体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说,第二部分为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的描述性统计,第三部分介绍了研究方法与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数字鸿沟”的微观证据,第六部分为政策建议。
一、 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影响的机理分析
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之一,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是社会公平的延伸,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教育公平对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9]。然而由于目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教育不公平始终是教育领域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教育公平长期难以实现。这导致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可能存在多种影响。
第一,互联网普及能够通过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来促进教育公平。互联网普及对教育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缩小教育资源的“物理鸿沟”,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10]。由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征,再加上数字化资源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特性[11],使得互联网能够让原先封闭于校园之中的知识以低成本、远距离、灵活自主的方式被个体所获得,进而使得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摆脱时间、空间、人力的限制,为缩小教育资源供给与教育资源需求间的巨大鸿沟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将意味着互联网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12]。
第二,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与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有关。如果教育资源不同的地区存在较大互联网使用技能差距,特别是倘若教育资源好的地区个体的互联網使用技能更好,那么,互联网普及就会使得教育资源较好的地区获得更多改善,而教育资源较差的地区改善较少,这样就会扩大教育不公平。也就是说,缺乏数字生存技能的“数字弱势”群体与“数字优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多表现为信息技术技能水平上的差异,即“数字鸿沟”[12]。根据新兴技术普及的一般规律,“数字鸿沟”往往随着新兴技术普及率的提高而扩大,因而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数字鸿沟”对教育公平的抑制作用会逐步抵消甚至超过“物理鸿沟”弥合带来的教育公平效应。
第三,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与人们的家庭教育有关。有研究表明,在互联网普及度较高的荷兰,低学历家庭子女在闲暇时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高学历家庭子女,前者使用互联网的时间是后者的1.2倍,前者平均每天3.2小时,而后者平均每天2.6小时[13]。而Park等的研究表明,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导致青少年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导致学生学习时间减少、学业成绩下滑、家庭矛盾冲突激化和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导致青少年体质下降[14]。也就是说,过度使用互联网不仅对学业无益,而且损害学生健康,因为它减少了学生用于运动、睡眠和学习的时间。心理学研究发现,过度使用互联网不但会降低学生学习能力,而且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和意志力受损,同时还减少他们学习的内在激励。学历和收入较高的父母往往对子女进行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投入,也即更加注重对子女互联网使用方式的监督和引导[15]。这就使得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子女更多使用互联网的“严肃类应用”(serious application),较好地发挥互联网在学习、社会参与等相关领域的优势效应。而低学历、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则多使用互联网的“娱乐化应用”(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如进行在线聊天或在线游戏等,因而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效应。美国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即相较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电视以及其他电子设备上投入的时间更多,并且时间大多用在了视频、游戏以及浏览社交网站等“娱乐化”的应用上[13]。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具体来说,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由于“物理鸿沟”的逐渐弥合,互联网普及能够起到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但是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逐渐提高,“数字鸿沟”逐渐显现,互联网普及将起到扩大教育不公平的作用,即本文认为互联网普及与教育公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试图利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维度系统地探索互联网普及与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加深我们对互联网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关系的认识和了解,最终希望能够为扩大互联网在教育公平中的积极作用、缩小其消极作用提供一些理论支撑。
二、 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描述性统计
(一) 教育不公平及其演变趋势
要研究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要对教育不公平程度进行测算。教育标准差和教育基尼系数是测度教育公平程度的常用指标。Thomes等认为,教育标准差缺乏稳定性,有时会得到误导结果。与教育标准差相比,教育基尼系数被认为是衡量在时间序列上各国家和地区教育公平发展变化程度的更有效指标[16]。基尼系数是广义的分析工具,不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且可以用于一切分配问题和均衡程度的分析。同基尼系数类似,教育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也是[0,1],教育基尼系数的数值越大,教育不公平程度越高。目前,教育基尼系数已经逐渐成为国际上测度教育公平程度的通用指标,为此本文也选择使用教育基尼系数作为教育不公平程度的衡量指标。
根据已有研究的方法[16][17],我们使用如下公式计算教育基尼系数:
由于大部分研究倾向于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基础来测算教育基尼系数[18],所以我们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为基础来测算教育基尼系数。按照我国教育体系的实际情况以及教育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我国教育层次分为5级,分别是:未上学,处于该层次的人群受教育年限为0年;小学,处于该层次的人群受教育年限为6年;初中,处于该层次的人群受教育年限为9年;高中或中专,处于该层次的人群受教育年限为12年;大专及以上,处于该层次的人群受教育年限为16年。
表1中给出了2003—2019年间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以及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基尼系数情况②。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亦或是从性别角度,我国教育不公平程度整体在保持小范围波动的态势下呈下降趋势。从全国层面看,教育不公平程度从2003年的0.244下降至2019年的0.223,下降了8.6%。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教育不公平程度相差不大,西部地区的教育不公平程度最高,三大地区的教育不公平程度分别下降了10.8%、4.6%及11.4%。也就是说,教育不公平的改善情况是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从性别层面看,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教育不公平程度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男性教育不公平程度明显要低于同期女性的教育不公平程度,这可能与我国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有一定关系。由于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男性普遍能够获得较多的家庭资源,而女性能够获得的家庭资源则分化较为严重。但可以发现,近年来女性教育不公平情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不过其不公平程度依旧高于男性。
(二) 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关系的描述性统计
图1描述了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公平的二次拟合关系图。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互联网普及能够降低教育不公平程度;第二,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呈现出微弱的“U型”曲线形态,即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教育不公平程度下降速度逐渐降低,甚至表现出些许提高趋势。同时这也初步表明,初期互联网的“物理接入”可能有利于降低教育不公平程度,但是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数字鸿沟”愈发显现,导致其对教育不公平产生了一些助推作用。不过该关系仅仅是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影响中国教育公平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在没有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这种拟合关系并不能精确地反映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之间的真实关系。基于此,本文余下部分将通过计量分析方法,進一步探析中国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三、 研究方法
(一) 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文献回顾及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到,互联网普及和教育不公平之间可能存在“U型”关系。为了更加客观地检验这一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二) 变量设置与测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教育不公平程度采用教育基尼系数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普及率。另外,影响教育不公平的因素是较为复杂的,为此,为了估计的准确性,我们还选择了如下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LnGDP)。在微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家庭的消费结构,进而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增长水平;在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地区对教育的投入,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有条件为当地教育提供更多的经费以改善教育教学条件,从而拉大与落后地区的教育差距[19]。因此,本文加入各省人均生产总值对数作为控制变量。(2)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化发展阶段或城镇化水平对教育不公平的影响已经被学者们广泛关注[20][21][22]。本文采用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数除以总人口数来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3)经济开放程度(Open)。地区开放程度作为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社会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并将其纳入本文的控制变量。(4)由于抚养比高低常常影响着财政支出中公共资源的分配,较高的抚养比可能会对教育投资产生挤出作用[23]。因此在有关教育的研究中,抚养比常常被纳入其中。本文分别采用0—14岁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少儿抚养比(Dr)和老年抚养比(Or),并将二者纳入到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中。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2003—2019年期间除港澳台、西藏以外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各省的教育程度、GDP、进出口总额、抚养比、年末常住人口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年鉴汇编》。而互联网普及程度分别采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上网人数占本地区年末总人数的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GDP数据分别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转化为2003年不变的可比价格,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观察表2可见,各个变量都有较大的变化区间,较好地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表明检验互联网普及率和教育不公平关系的基础数据是良好的。
四、 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互联网普及对教育不公平的“U型”影响
本文首先在全国层面上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属于面板数据,而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通常有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为此本文分别采用了这三种模型进行回归,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混合OLS模型,模型(3)和模型(4)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模型(5)和模型(6)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表3可以发现,三种模型无论采用哪一种模型,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模型估计结果中的R2总是大于不加入控制变量时的R2,说明加入控制变量是必要的。此外,面板固定效应的两个估计结果中,F检验的P值均为0,拒绝原假设,即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中应该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而两个Hausman检验的结果又均表明应该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而不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为此,我们将基于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互联网普及缩小了我国教育不公平程度。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在1%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为正,表明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同时,这两个结论在不同模型中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均是如此,说明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该结论表明,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由于互联网所具备的共享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教育资源供给与教育資源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缩小了教育不公平程度。然而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群体间在互联网使用上的差异逐渐显现,从而产生了新的“数字鸿沟”,进而使得互联网反而成为了教育公平的阻碍,这也说明了我们在强调互联网普及时不能仅考虑“物理接入”的鸿沟,同时也应当考虑互联网使用差异造成的“数字鸿沟”。
进一步分析表3中模型(6)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第一,城镇化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0.039,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化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城市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因此应当重视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问题[20]。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0.00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缓和教育不公平程度,这说明发展仍然是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途径之一。第三,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它们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不但是我国应对人口红利不断耗散的需求,同时也是推动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
(二) 不同教育公平水平下互联网普及对教育不公平的差异化影响
全国层面的随机效应模型仅能给出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一般影响”的有限信息,而分位数回归方法不仅能有效解决数据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不稳健的影响,还能大大提高数据信息的丰富程度。根据以往文献的做法,本文选择了0.10、0.25、0.50、0.75以及0.90五个分位点进行面板分位数估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发现,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到的互联网普及的系数符号与全国层面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大体相似,但系数估计值随着教育不公平程度在条件分布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从表4的结果中不难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介于-0.131和0.001之间,且至少都在5%水平上显著。单就面板分位数回归下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变化特征可以发现,随着教育不公平程度的逐渐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估计值由正变为负,并且其数值一直在减小,这说明在不同教育不公平程度下,互联网普及对教育的公平效应是有所不同的。具体而言,当教育较为公平时,互联网普及不仅不能缩小教育不公平程度,反而会扩大教育不公平的作用。当教育越不公平时,互联网普及对教育的公平效应也越大。这一结论启示我们应当更多的关注教育不公平地区的“物理接入”问题。此外,不同分位点的互联网普及率的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说明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不以分位点的变化而改变,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与此同时,其二次项系数整体随教育不公平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说明在注重落后地区“物理接入”的同时,应该注意其潜在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
(三) 互联网普及对东中西部地区教育公平的差异化影响
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各地区教育发展现状、信息化程度都具有较大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公平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将基于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三大地区,利用2003—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同样,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确定各模型应当采用哪种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同时,为了方便比较分析,我们将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也一同列于表5中。
从表5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首先,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并且分别在10%、1%和5%水平上显著,同时可以看到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的大小在依次增加,表明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在依次提高,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同时教育不公平程度较低,导致互联网普及的公平效应相对较低。其次,就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并且系数估计值大小依然表现为依次递增,这不仅从区域层面上证明了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的“U型”关系,同时也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我们更应当警惕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最后,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情况整体上未发生较大变化,说明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 互联网普及对教育公平影响的动态演化
为了进一步刻画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公平影响的动态特征,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普及率一次项,并加入互联网普及率和年份的交互项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基期2003年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不公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0.20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此时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是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的,表明此时处于“U型”曲线拐点的左侧。而与基期2003年相比,从2008年开始,互联网普及率与时间的交互项系数开始变得显著,且系数均为正。不过,从2008年到2019年,互联网普及率与时间的交互项系数绝对值仍小于基期,表明直到2019年,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的关系仍然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说明互联网普及的教育公平效应仍存在上升空间。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互联网普及的教育公平效应是随时间缩小的。再次说明,在推广互联网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利用互联网来促进教育公平。
(五) 稳健性检验
虽然本文已经通过多种方法(混合OLS、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并通过多个视角(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位数趋势及时间趋势)研究了互联网普及对教育不公平的影响,并且研究结论总体上都是一致的,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但是由于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依然可能存在,而这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此我们将使用动态面板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以进一步考察研究结论稳健与否。表7列出了静态面板的基准回归结果,同时给出了动态面板中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表7的结果中不难看出,考虑到互联网普及率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没有产生明显变化,因此,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之间的“U型”关系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不仅如此,本文还借鉴黄群慧等[24]的做法,选取各省份1985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究其原因,互联网作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交互实现的基础,是傳统通信技术的延续发展,各地区以往的通信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后续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影响进一步的互联网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固定电话作为传统的通信工具,其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排他性需求。但是本文研究使用的是面板数据,而该工具变量仅仅是截面数据,因此并不能直接作为工具变量。为此,参考赵涛等[25]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同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与1985年各省份每万人固话数量的交互项,作为该省互联网普及率的工具变量。从表7的结果中可以看到,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对互联网普及率的估计系数显著,并且F统计值为451.06,远高于10,说明该工具变量是较为有效的。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引入工具变量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仍未产生明显变化。因此,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与教育不公平之间的“U型”关系得到了再次验证。
五、 “数字鸿沟”的微观证据
在上文的研究中,我们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互联网普及与教育不公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且本文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其背后可能是由于“数字鸿沟”造成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本文并未对“数字鸿沟”是否真实存在进行验证,因而缺少微观证据来支持本文的观点和结论,为此,我们在本部分将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考察不同家庭背景下,学生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是否真的存在“数据鸿沟”。根据前文的分析,“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使用方式、使用时长和使用技能三个方面。由于问卷中没有关于使用技能的量化指标,我们假定使用技能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关。为此,我们将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不同家庭背景下,学生个体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是否有差异;第二,不同家庭背景下,学生个体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时长是否有差异。如果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个体在使用互联网玩游戏概率及时长存在明显差异,则我们认为确实存在“数字鸿沟”,方面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中可以看到:第一,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和时长都相对越低;第二,相较于女性,男性学生在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和时长都更高;第三,农村学生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要高于城镇学生,但是游戏时长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第四,家庭经济社会背景越好,其子女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和时长都相对越低。通过微观数据的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家庭背景下,个体在互联网使用方式及使用时长方面确实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可以认为本文讨论的“数字鸿沟”切实存在。那么,这就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一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合理性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醒我们要警惕“数字鸿沟”。
六、 发挥互联网普及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互联网普及对于推动教育公平具有非线性影响,当前正向作用正在下降,且中西部地区、低学历家庭“数字鸿沟”效应下的劣势日益突出。为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普及推动教育公平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教育资源的接入速度。提高落后地区和教育不公平程度较高地区的互联网“物理接入”,让更多的个体可以接触到高质量的互联网。不断提高网络速度,以满足个体正常使用的需要。
第二,要不断提高公共网络教育资源平台质量,尤其是满足中西部地区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不同地区、不同知识背景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资源,并且提高网络平台中师生双向互动水平,让偏远地区的学生通过网络能获得与发达地区优质课堂一样的学习体验。
第三,加快对家长数字能力的辅导,发挥家庭教育在子女合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中的作用。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契机,一方面积极开展家长成长培训教育,尤其关注低学历家长的教育培训,注重对互联网、数字资源的利用能力培训,让其子女掌握正确的网络使用方法;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媒体宣传等方式,让家长意识到科学合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在子女学习成长中的重要性。
注释:
①由于2010年和2020年的统计数据中教育指标的统计口径与其他年份出入较大,并且相关控制变量存在缺失,因此在本研究中暂不考虑2010年和2020年的数据。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信息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等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等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等11个省份。
③根据被解释变量的类型,我们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估计了不同家庭背景对学生个体使用互联网玩游戏的概率和时长的影响,并且前者在表中给出的是边际效应,因此常数项为空。同时,是否是精英家庭的划分方法,参考了吴愈晓和黄超(2016)以及靳振忠等(2019)。
参考文献:
[1]靳振忠,王亮,严斌剑.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测度与分解[J].经济评论,2018(4):133-145.
[2]靳振忠,严斌剑,王亮.家庭背景、学校质量与子女教育期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9(12):107-121.
[3] Beltran D, Das K, Fairlie R. Home Computer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NLSY97 and CPS[J]. Economic Inquiry,2010,48 (3):771-792..
[4]Ludwig M. Measuring ICT Use and Learning Outcomes: Evidence from Recent Econometric Studies[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3,48(1):28-42.
[5]Willis S and Tranter B. 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Diffusion and Inequality in Australia[J]. Journal of Sociology,2006,42(1):43-59.
[6]罗小茗.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例[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4):63-76+186-187.
[7]Hargittai E,Hinnant A. Digital Inequality[J].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3,35(5):602-621.
[8]陈纯槿,顾小清.互联网是否扩大了教育结果不平等——基于PISA上海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140-153+191-192.
[9]龙安邦,范蔚.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及特点[J].现代教育管理,2013(1):16-21.
[10]徐继存.“互联网+”时代教育公平的推进[J].教育研究,2016(6):10-12.
[11]A Goldfarb and C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 57(1):3-43.
[12]王美,徐光涛,任友群.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一剂良药抑或一把双刃剑[J].全球教育展望,2014(2):39-49.
[13]Dijk.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Digital Divide Turns to Inequality of Skills and Usage[M].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book, Amsterdam: IOS Press,2012.
[14]Park S, Kang M,Kim E. Social Relationship on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 Korea: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ntrol[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38(3):349-357.
[15]周春燕,萬丽君,宋静静,黄海,李林,刘陈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自尊的关系:父母卷入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6):1186-1190.
[16]Thomes V, Wang Yan,Fan Xibo. Measuring Education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s of Education for 140 Corntries,1960-2000[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2003,17(1):5-33.
[17]张菀洺.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分析及政策选择——基于教育基尼系数的测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4):89-97.
[18]孙百才,刘云鹏.中国地区间与性别间的教育公平测度:2002-2012年——基于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3):87-95.
[19]孙继红,杨晓江.我国教育公平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2009(9):56-61.
[20]刘善槐.我国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J].教育研究,2015(11):103-110.
[21]曾水兵,万文涛.农村“小微学校”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5(24):24-29.
[22]陈爱雪.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2017(3):81-82.
[23]Dridi M.Corruption and Education: Empirical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ial Issues,2014, 4(3):476-493.
[24]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25]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10):65-76.
(责任编辑:田青)
(校对: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