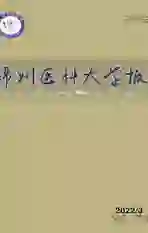萨特:自我的超越性
2022-06-06魏士国
【关键词】萨特,马克思主义,自由,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G6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6-5328(2022)03--02
理解萨特是困难的。因为,萨特不仅以文学上的成就著称,他也往往以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讨论萨特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结合他的哲学思想上的经历与转变,是不得要领的,即便不是不得要领,也是很难认清萨特作品的整个面目。纵观萨特作品,最早的成功见于他的文学作品《恶心》(1938)。萨特早期关注的是个人意识,这些意识大多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对自由意识的威胁,比如在他成功开始的《恶心》之中对一些负面心理的刻画,这些心理处于一些“荒谬的”、“没有存在理由的”、“多余的”事物的背景之下,甚至,呕吐是无缘无故地发生,哪怕是捡起一颗光滑湿润的石子。还有一类文献似乎佐证了萨特这个时期的困惑,“脱离存在的人类精神是自由的,但是没有力量去完成这一综合,真理与知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神话”。问题是,1933年,萨特开始接触胡塞尔现象学,并对现象学深深着迷,并利用现象学的方法解决他困惑的哲学问题,因此,按照这个思路,1938年的《恶心》既然已经是在萨特接触现象学之后的文学尝试,它就不应该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现象学并没有拯救萨特的“颓废”。不过,萨特在《恶心》的最后提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当形而上学的患者认识到在令人呕吐事物面前的失败即是在走上一条治疗疾病的路上。
通过萨特对于意识、自由、存在与超越等概念的阐释,能够解读萨特在其哲学之中是如何贯穿施皮格伯格所称的萨特哲学风格——“未来创造现在的意义”。萨特很容易被误解的是他关于意识的描写,往往引起非议的是他关于负面意识的描写,比如焦虑这类的主题。发表于1938年的《恶心》,萨特是从1931年开始写作,1936年完成。从时间上看,整个写作的过程贯穿萨特接触胡塞尔的现象学。很多国内的评论家认为,萨特的《恶心》反映的是当时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里,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彷徨苦闷,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评论家们在某一层面上可能是对的,当萨特被限制在法国哲学的狭小的圈子里,他和同时代的人具有同样的思想:幻灭、厌倦、无力。关于这一点,萨特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为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完全把自己放进去。”过分地渲染小说反映了某一时期人们的整体心态,也会带来一个深度的问题,萨特说的是“没有完全放入”,也即是说萨特此时在作品里并非没有对于自我意识体验的放入,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因此,当评论家的这样的意见即会忽略萨特此时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的体验,以及萨特何以如此的哲学原因。参照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说法,在前现象学时期,尽管萨特写了很多东西,出版的只是少数不太重要的作品,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文献表明萨特此时的“困惑与幻灭的心情”,这是由于“萨特在求学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法国哲学显然无法改变他的形而上学的失败主义与悲观主义所致”。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在萨特之前的法国哲学家对于意识的解决方案都不能令萨特满意的,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柏格森。萨特的哲学是创造的、具有生成性质的哲学。萨特在他的童年自传《词语》中就发出了对传统惰性的抗议,他说,“为什么是过去使我变得丰富呢?它并没有造就我,相反是从我早已成为灰烬的过去中苏醒的我不断以创造性的行动从虚无那里夺回我的记忆。”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又引用了一段话,萨特“想在每一种现象的把握中看到与存在本身的某种接触,即在相对的事物中看到绝对的东西;他所相信的是一般人除非逃避开人类的相对状态,否则不能个成为人”。
当萨特写作本科毕业论文《意象》之时,萨特的主要引路人是“康德、柏拉图和笛卡尔”,但是萨特把自己看做一个笛卡尔主义者。的确,笛卡尔对于萨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在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中,哪怕笛卡尔是被以批判的视角出现,笛卡尔的“我思”仍然是萨特哲学的出发点。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构建了一个抽象化的“我思”,“我思”具有自明的、清楚的特点,在“我思”的基础上才能够构建整个现代哲学或知识的基础。笛卡尔的哲学开启了将我思与世界、显象与本质二元对立,从此哲学的主题演变为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哲学。在萨特看来,笛卡尔的信条“我思故我在”,割裂了意识、思想与生存、存在的关系,这种哲学思维并不能解决萨特对于自由、存在这些主题的思考,因为这样的思考方式“将自由与存在陷入互不相关和无法调和的境地”。柏格森提出意识是绵延的方案似乎避免了二元论的问题,在意识的连续性方面给了萨特很大的启示。但在萨特看来,柏格森除了混淆了事物的状态和意识之外,并未提出任何主张,只是一种“欺骗性的肤浅的快乐”。
1933年以后,萨特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上的“意向性”对意识进行重新解读。萨特认为,意向性这一概念将意识从受到世界的干扰解放出来。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意识就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萨特改造了胡塞尔的“意向性”。在他看来,意向性指的是意识的方向性。意识是不可还原的。如果按照现象学的方法,笛卡尔的我思顶多是一种描述性的或者解释性的术语。萨特指出笛卡尔唯理论的错误就在于以实在先于本质来定义,将自我完全地设置为绝对的实体。萨特断言:包括自我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 并且不能被我们的意识所吸收;我们是在我思之外, 在世界中, 在他人中间,才发现我们自身的;我的“自我”并非实体, 而是我必须通过我在世上的行动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去加以构建的一个对象。借用海德格爾的说法就是, “现象就是显示自身的东西”。萨特进一步提出,现象就是本质。
萨特的意向性解读是在胡塞尔的启发下进行的,在我看来,但是关于意识与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在海德格尔对“此在”的解读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萨特对意识的处理体现了法国传统的微妙的精神所在,并不以简单二元对立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对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的克服。在对二元论的克服的过程中,不得不借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指明意识的发生。萨特拒绝意识的主体性。意识是被动发生的,类似于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解释,人本身被“抛入”世界的。人的意识完全是具有直接指向世界的的特点(萨特将“自为的我思”一度理解为反映-反映者结构)。在《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海德格尔的术语,如“在世”、“领会”、“共在”等。自我就是“在世”世界的許多现象中的一个。当人具有恐惧、愤怒或焦虑等意识是介入了世界的结果。当然,海德格尔很不满意的是,萨特将海德格尔本体论的存在哲学改造为具体的人化的哲学。
关于意识的微妙精神体现在萨特对意识否定作用的超越上。意识并非是抽象的实体,不具备绝对的超验地位。首先,在萨特看来,意识能进行认识和认识自己,但他本身不是回归自我的认识,而是朝向一个对象,意识本身没有内容。意识必须是自我与自我之间的一种直接的,而非认识关系。按照萨特的意思,按照现象学构造的人或者存在,是存在人的世界,这个存在产生于对自我的超越向外开拓出意识的世界。
接下来,意识如何朝向一个对象?萨特提出,意识朝向不在场的所在。“意识是它所不是的那种东西,又不是它所是的那种东西。”按照萨特的解读,“存在和非存在不再是空洞地抽象”,存在包含着对虚无的“领会”,人对的实在的认识通过世界的虚无化显示出来。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萨特否认虚无并非是简单的否定关系,存在并非预设本质,而是存在超越自身过渡到本质。存在与虚无并不如黑格尔的断言,存在与虚无构成两个对立面。意识并非总是对立,虚无产生于自为的存在,萨特说:“自在的世界不可能产生这种尘世的虚无:充满了肯定性的存在概念并没有把虚无作为它的结构之一包含咋自身中”。关于意识问题的回答包含着至少是“双重的虚无化运动”,虚无起源于人的存在某种活动、某种期望、某种谋划,在意识的连续性断裂的时刻产生。依照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规则,严格说来, “对象”总是相对于某个意识而言的。相应地,由于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因而只有面对超越的对象时,才可能有意识产生。用萨特自己的话说,“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在萨特提出的由反思前的“我思”和反思后的“我思”构成的意识结构之中,“反思一点也不比被反思优越:并非反思想自己揭示出被反思的意识。”。
在反思前的我思与反思后的我思这两种意识的区分之中,前者是怎么样过渡到后者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理解“超越”这个术语就成为十分关键的环节。本来,在萨特看来,反思前的我思对于我们来讲,并非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明清楚的,反而是不透明的,甚至在大多时候,人们往往处于一种真诚地自欺的状态。自欺的态度指的是,意识并非将它所面对的否定指向外部,而是回过头来转向自身,这些意识往往诉诸相信曾经所是。比如,社会加诸我们的角色,咖啡馆的侍者,食品店的店主,裁缝店的店主,我们扮演这些角色,以求别人相信我是咖啡馆的侍者,食品店的店主,裁缝店的店主。这种自欺,反映的是意识的惰性。
意识自身具有的超越性质在“反思前的我思”向“反思后的我思”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意识朝向不是自身的对象的基础上,要解释清楚意识具有的超越性含义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意识朝向的不是自身的角度讲,超越描述的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在语法上,起到类似现在分词的作用,意思接近滑向、滑入,从A点过渡到B点。在反思前的我思阶段,处于自欺时,也具有从意识中躲避的意思。当意识处于自为阶段,意识的超越在引入了时间的因素,从过去到未来,具有连续性。
通过对萨特的意识学说的分析,可以看出,萨特的哲学一方面是向外扩展的,是朝向外部的,他人的,不在场的;在另一方面,他的学说尽管是大谈特谈外部的、他人的、不在场的,但仍旧回到对法国传统的意识“我思”、“自我”的考察,这种“我思”或“自我”一种十分精妙乃至精细的以朝向“不在场的”、“他者”的方式呈现,不仅论述了意识的连续性、半透明性、超越性这些特点,而且沿着这条思路,也不难解释萨特为何由战前的不问政治,何以到战后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或演说家,何以到战后亲近马克思主义。
魏士国,男,汉族 天津人,197805,博士,助理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100101),研究方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制度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首都抗疫斗争中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2022C725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首都抗疫斗争中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逻辑及实践路径研究》(2022C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