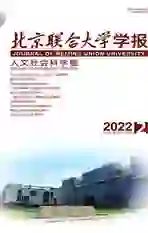关于社区治理动力机制问题的概念性思考
2022-04-27陈星
陈星
[摘要]社区是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以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为目标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成为社区治理外生动力的主要来源;社会个体则以优化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功能的诉求为基点,逐渐建构出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以社区社会资本为关键媒介,消除上述兩种治理动力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二者成功耦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制度建构与优化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社区治理;动力耦合;社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2-0117-08
社区治理系指相关组织与机构为保证社区良性秩序的建构与维护,持续完善相应的社区管理制度体系,推动社区内部结构功能实现和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贯彻国家的发展与治理理念,将社区治理纳入整体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①推动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驱动力及这些驱动力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区治理动力机制的基本内容。经过几十年实践,我国社区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社区治理动力机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优化。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这是未来较长时期内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的基层治理体系逐步成熟,社区治理进一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②新时期社会治理工作对社区治理动力机制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立足当前社区治理实践,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党领导下的多元参与社区治理动力机制是提升社区治理效率进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
一、社区治理动力机制的历史维度:社会重构与社会治理
社区治理动力甚至“社区”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本身从根本上说均来自社会发展引发的社会结构解组及随这种社会解组产生的社会治理新需求。社会解组是指社会结构在某些因素的冲击下裂解,原有的社会结构被逐渐打破,新的社会结构在冲突与混乱中被逐步创立起来。以社会发展的宏大视角来看,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发展约束构成了“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并在整体上决定了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结构解组与重构提供了初始动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信任关系的重构以及立足于此上的社会规则重建则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
社区治理及其理论研究围绕社会解组与重构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问题展开。一般认为,社区治理理论滥觞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又译《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一书。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联合,在这种社会联合中,情感的、自然的意志占优势,个体的或个人的意志被感情的、共同的意志所抵制。与此相对应,他将人们由契约关系和“理性意志”所形成的联合体称为“社会”。他认为社区的特征是:“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他们重感情、重传统,彼此之间全面了解。”[3]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在概念内涵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反而是他所说的“社会”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有更多相似性。结合滕尼斯开展社区研究的时间阶段来看,工业发展引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应对为其社区研究铺设了厚重的理论底色。社区研究在西方工业化背景下展开,工业化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性增加成为社区研究的基本语境并形成了特定的理论预设,只不过这些预设在当时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常识”,故在当时的社区研究中较少被着重提及,但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一问题,却需要溯本清源,因为这个预设涉及社区治理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逻辑起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结构变动情形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适应性调整,这是社区治理外源性动力的重要来源。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与优化的过程,社区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行为与社区自组织能力长期互动并取得平衡的过程。就社区治理模式而言,一般认为主要存在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模式等三种类型。[4]不过这种类型划分本身隐含着“政府与社区互动及平衡”的逻辑前提,而社区治理类型的差异,主要也是以上述两种主体互动类型差异作为划分的依据与标准。研究者一般依据政府与社区的互动方式差异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类型划分,因此也有学者将上述三种类型称为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新加坡为代表)、自治型治理模式(英、美为代表)、混合型治理模式(日本、以色列为代表)。见刘娴静:《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公权力部门推动社区治理的动力主要来自其依托社区解决社会问题的初衷,而这些问题是单个社区无法解决的。更进一步说,国家介入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完成基层政治结构的建构并优化整体社会治理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治理的有效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权力介入与参与是社区治理外部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均承认这一事实,所不同者不过是社区治理中政府介入的程度以及形式有所差异而已。
英美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治传统,因而其社区治理模式被定位为“自下而上型”,不过即使在这种类型的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的作用也越来越强。美国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快速工业化带来了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剧变,这一过程与美国当时的向外拓殖过程相叠加,推动了社区组织的快速形成。不同的人群带着不同的习俗与文化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如何治理这些“陌生人社会”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美国社区治理实践中,以社区为基础完成社会秩序重构是核心内容。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归纳了社区的本质:“大量人口聚集于某一地区,形成了受地域约束同时具有地域特征的人际关系,经过若干时间的积淀,这种人际关系形成了社区发展的外在环境。”[3]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对社区治理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约翰逊总统1964年发起的“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运动成为社区发展运动的开端。“向贫困开战”聚焦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服务,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和社区变革。[5]英国1960年代兴起的“社区运动”主要目的则在于创造更具有效用的地方服务,以及探索具有鼓励性自助精神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处理社区各项事务。其中,在社区环境恶化、内城贫困等议题上,城市社区得到政府的大量支持。[6]可以看出,较强的社会自治传统与公权力对社区治理介入的加强并非不能共存,公权力处理的是超越社区范围但又对社区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因而两者在很多时候是互补的关系,公权力介入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动力源。
相较而言,欧洲大陆及后来的东亚社会社区发展过程中公权力广泛介入的情况更为普遍。对美国来说,社区的建构及治理是在广袤大陆上创建新秩序的过程,殖民者初到在这片土地时,少有原初的社会秩序,此后他们创造的秩序经历了一个约束力由弱到强的过程。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原有的政治結构和社会秩序非常强势,这种社会结构下的社区治理事实上就变成了公权力如何处理工业化及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解组与重构的问题。联合国1955年通过的《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出的社区发展基本原则中,既强调了公权力部门对社会发展的扶助责任,同时也强调了社区居民参与以提高行政效能的作用。[7]这个论述体系中,国家介入社区发展并将社区整合进社会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对许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来说,社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可以用“国家推动社区建构或重构→社区逐渐形成内生治理动力→内外动力共同推动社区治理进化”的基本逻辑理路进行描述。
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是我国社区治理体系进化较为直接的推动力。1980—1990年代是我国社区治理理论及实践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单位体制逐步弱化,整个社会的人员流动性增加,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居住地联结的稳定性被打破。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要承接单位制改革和市场化转移问题,社区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社区功能重构工作逐步推开。[8]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被打破,居民的组织形式必须有相应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下市场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意味着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许多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工作所在地,通过何种方式保证他们融入当地社区并推动社区平衡和谐发展一直是社区建设重点要解决的问题。[9]于是,在传统的街居体制基础上,通过组织功能重组,社会治理逐步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社区治理模式渐次向乡村渗透。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引发的社会组织结构改变是推动社区治理体制发展的终极动力。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针对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发挥着重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建设社区文化心理的重要功能,成为整体社会治理体系优化的重要支点。对于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来说,公权力系统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进化中扮演了引导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对社区治理介入甚深。以此而言,所谓社区治理的“自主性”只能是相对的,其不能背离社会治理系统优化的前提而单独存在,推动社区治理体系持续进化的内生动力机制也只能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产生并发挥作用。
二、基于“生活共同体”视角的社区治理内生动力机制
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系指发源于社区内部并能驱动社区治理结构持续进化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的动力及其机制。与整体社会层面的社区治理宏大叙事不同,社区治理内生动力首先是因应生活需求而出现的,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建构与优化社会生活网络和降低社会生活交往成本的需求。就目前讨论比较多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来说,大部分居民只有意识到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将有利于社区建设与发展,也有利于满足自己的个人生活需要,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才会呈现出积极的参与热情。[10]与社区的“被组织”相比,“自组织”显然更加复杂一些,需要通过激发社区内部的积极性,建构起社区内部资源动员机制,优化社区治理机制及形成促进社区持续发展动力来达成。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涉及多元主体的观念与行为整合以及稳定性机制建构等问题,与公权力主导的自上而下动力机制运行逻辑有较大差异。
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主要依托于社区的功能实现展开。由于社区生活是工业化社会到来及社会流动增加情况下社会大众主要的生活组织方式,社区首先满足的是居住和生活功能,因此2000年民政部印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把“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将城市社区的范围界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而“社区建设”则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0年11月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在“生活共同体”的功能约束下,社区成为具有共同地缘的居民生产、生活、交往和互动的空间。[11]社区发展与治理的目标设定就是在这种空间定位中展开的,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也是在上述社区功能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形成与加强的。
从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功能实现角度来看,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很难独立发挥作用。社区的许多功能是由外源性动力系统实施完成的。公权力治理所要实现的社区功能主要有管理功能、服务功能、保障功能、教育功能和安全稳定功能等,[12]具体来说社区要在经济上实现生产-分配-消费功能;在政治上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保障社区居民安全;在教育上实现对社区居民的教化;在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层面,实现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功能等。[13]这些功能大部分都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设定功能,并非社区本身能够单独实施完成的。就社区功能定位而言,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及生活质量的提升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建构的重要支点,如动员社区力量有效解决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离散、社会疏远、社会失序、社会失控等问题;充分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培育社区公益组织并使其充分发挥公益作用;积极引导社区精英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建构能为社区普通居民提供充分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等。[14]上述社区治理行为依托社区自身资源,围绕“生活共同体”功能实现与提升而展开,既可以增加居民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又可以提高社区治理参与的积极性,可以为社区交往网络及信任网络建构提供有效支撑。
社区治理内生动力来源于社区居民提升生活品质的诉求,依托于社区信任网络展开,兼具利益诉求与情感诉求的内涵。从社区发展的实践来看,社区形成之后其社会交往网络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场域”,这一场域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虽然这一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15]正是因为社会交往网络与信任网络的存在,社区具备一定自组织能力,也因此具备一定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这些能力叠加于社区功能实现目标诉求升级与进化之上,共同建构起了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体系。从社会关系网络的一般特征来说,虽然“利益”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分析的主要面向,但情感同样也是影响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指出,虽然旧有的熟人社会被社会现代化发展所打破,但社区治理仍保留一定的“半熟人社会”特征,情感作用在社区治理中的发挥方式从通过舆论约束塑造居民行为,转向以“情感+利益互惠”方式形塑社区规范。[16]此外,习俗以及特定时期的文化对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存在样态也会有一定影响。
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与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还是有内涵上的差别,可以认为是“不完全共同体”。“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分歧较多。《辞海》采用了滕尼斯的说法,“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见《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页。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社区”与“共同体”均译自community,为同一个概念,该书将“以共同的地域为基础,体现出团结的观念,并赋予个人以意义感”作为“共同体”最低限度的定义。见[英]戴维·米勒等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4页。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主要指涉“亲族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联合”,比较而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共同体”的描述与当下现实更为接近。社区因为其“限制性参与”的特征及“基本生活组织”的功能设定,其“意义赋予”的功能只能是部分的,因而本文将其称为“不完全共同体”。究其原因,社区居民的参与是“限制性”的,大部分情况下局限于生活层次,尤其是在社区正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更是如此。于是在社区治理中出现了所谓“共同体困境”,具体而言就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社区居民、社区内市场主体普遍缺乏主动参与治理、维护共同家园的意识和动力。[17]同时,社区治理内生动力来源于“居民对社区的生活需求←→社区回应”这一循环反馈结构,在某一特定阶段社区居民对社区的需求决定了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基本样态,社区对这些需求的持续回应过程则决定了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基本进化路径。王德福在社区研究中提出了“社区良性秩序”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社区良性秩序”,系指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秩序,它直接关系到居民在社区中的居住与生活品质,它往往与社区中频繁发生的日常性小事有关。[18]从本质上说,这种“秩序”其实就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秩序结构。这些需求是社区作为人群聚合的“生活场域”的内生性需求,社区以对这种秩序需求的回应的形式与社区居民持续互动,形成推动社区发展的连续性动力。
三、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与外源性动力的互动机制
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结构逐步成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主流。社区以及社区治理是人类自身对社会结构变迁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改变而进行的适应性探索与实践,也可以说社区及其发展本身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一部分。从简化的社区治理结构来看,社区治理动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上的作用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即国家将现代治理体系延伸到基层社会;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建设”,即社区基层组织自觉且自主地组织与动员基层社会力量,并将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18]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區的社会变迁进程都是在国家的主导下完成的,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初始阶段以外源性动力推动为主。因此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外源性动力是原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则相对来说具有派生性,即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系统是在社区形成及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易言之,外源性动力决定了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基本方向与路径。行政机关从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通过政策规范、机构设置、资源注入等方面对社区发展进行引导,形成了社区治理结构演进方向与路径的强约束,这种约束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推动社区治理向国家设定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社区发展过程中,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外部资源是社区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在目前的社区治理结构中,资源挹注以“服务”的形式进入社区治理系统,对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服务是最好的社区治理”,认为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和普惠化是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社区治理科学化,就必须全领域整合社会资源、无差异高质量增加服务供给,推动社区治理资源服务供给现代化。[19]以服务为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以回应居民生活需求为支点,全面形塑社区治理体系,在这种治理体系中,外源性动力的强度基本上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与绩效的基本样貌。
社区内生动力及其运行样态则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形式及精细化程度。社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更不是大家庭,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基本上是以法定社区作为施政单位,在实际确定社区这一实体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标准是地域界限,居民之间没有太多的直接经济利益和血缘关系。[10]与传统社会相比,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显然是随机的和弱化的。同时,共同的地域生活又决定了社区居民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方面,其中最显著者是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系统的需要。[20]在回应生活需求的过程中,社区的互动网络逐步形成,并开始对社区治理产生推动作用。一旦形成这种规则系统,社区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再生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内部的稳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我复制。一般来说,社区规则来源于社区日常生活交往经验的沉淀,并以此为基础形塑出社区民众的思维模式与行为取向。这些思维模式与行为取向构成了社区交往网络与信任结构的重要基础,也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生长的深厚土壤。当这些行为取向和思维模式经由社区治理过程的不断实践,或基于外来的协助进一步进化为规则系统,便能够形成具有治理功能的社区公约。社区公约来源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又受到来自外部的公权力等因素影响,是综合了社区基本行为规范的规则系统;其涵盖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路径,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物化形式,也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社区治理的内外动力体系是互补与协调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公权力主导的外源性动力提供了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向并提供了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基本秩序;内生动力系统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参与社区治理,补强了外源性动力的治理效果,推动社区治理走向精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度非常流行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自20世纪90年代“国家-社会”研究范式引进以来,一度成为分析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范式,但这一范式的问题在于将国家与社会设定于二元对立的框架,甚至设想社会可以作为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形成与国家的平衡,[21]西方理论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与此也有非常大的关联。从我国社区治理的历程来看,社区的内生动力显然会逐步增加,但与外源性动力之间的耦合程度也会不断加强,可以形成和谐与自洽的治理体系,公权力部门作为社区治理行为主体,遵循“社区需求让居民表达、社区问题让居民讨论、社区事务让居民参与”的原则,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行于民、问效于民。[14]社区群众和社区组织则在社会治理整体框架约束下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4]于是,内外两个动力系统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建构出稳定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与外源性动力耦合的核心问题在于消除两个动力体制之间的张力并推动二者整合成较为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两者的耦合程度决定了社区治理效率。在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社区已经成为城市甚至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系统的重要节点。随着社区交往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社区组织的出现,社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社区多元主体随着社区的发展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在社区治理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区的这种自主性能力与外部治理体系之间的张力会逐步显现出来,如果两者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则社区治理成本会不断增大,社区治理绩效的天花板会被压低。因而社区治理动力整合有消除社区交往网络内部张力和将社区自主性能力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两个方面的内涵。有学者提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是社区治理动力的力量源泉,公权力的主导作用有助于不同力量的有机整合,而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合力生成的根本途径。[22]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就是社区自主性能力与外部治理体系整合、协调与适应的过程,基于社区发展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四、内外动力的耦合枢纽:社区社会资本
学界目前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意涵未有定论。刘琳在其文章中归纳出几种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1)认同前人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通过居民的社会参与、邻里间互惠及信任度等来测量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2)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首要表现为人情浓密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邻里、家庭、朋友及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的居民参与、社区信任和自治组织也是现代性社区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3)以社区为依托或载体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称为“社区社会资本”,指人们在社区这一具有明确边界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信任、规范、积极的情感等。[23]上述社区社会资本的定义虽稍有差异,但都没有脱离信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核心内涵。概而言之,社区社会资本概念涵盖了社区成员之间信任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稳定行为模式等多方面意涵,社会资本的存在样态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成员互动的交易成本,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社区治理的成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与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伴生形成的情感结构,是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程度和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依托。社区社会资本建构立基于社区社会交往网络,主要包括社区意识、社区认同和社区信任网络等方面的内容。现代社区是对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一次重组,非血缘的人际关系及程度比较高的人口流动性是社区组织结构的显著特征。社区在物质上表现为推动交往关系重构的重要平台。居民群众在社区这个平台之上,互相交往联系,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产生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从抽象的“社会人”转化成了“社区人”。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既有个体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网络,同时也具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和意义的精神内核。因此说,社会治理“基础在基层、根本在社区”,在社会治理的众多路径中,依托社区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既是必然也是必须。[24]在现代社会“社区化”的过程中,居民互动经验以文化或者规则的方式沉淀下来,形成行为取向的稳定性影响因素,并进而成为居民行为和社区治理中比较稳定的约束性框架,成为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的情感与文化基础。
社区治理公权力机构的引导与干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发展样态会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社区内部的社会信任往往形成于居民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是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多次博弈的结果。日常生活中的这类社会交往与互动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石。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外化形式,社区规范正是在这一长期博弈中形成的,遵守契约与规则的社区意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伴生形成的。社区治理机关往往是通过建构社会交往结构及引导社区规则形成等途径完成对社区社会资本建构过程的干预,实践中一般通过“使命框架的设定→持续动员(互动)”的逻辑路径来达成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目标。社区治理机关从社区发展的目标设定需求出发,找出符合社区民众经验和认知的行动目标,再持续透过相关实践的故事、事件之诠释和扩增,同时根据社区资源状况制定动员策略,逐步推展服务方案,增加上述实践的感染力并试图唤起参与者热情。这一逻辑路径的要义在于按照社区发展愿景组织居民参与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居民良性互动,进而建构出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调动行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的重要依托。上文已经述及,滕尼斯当初在对社区概念的讨论中尤其强调社区精神结构与精神内核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区存在于传统乡村,在社区中人们基于血缘、地缘等共同的利益关系,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拥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认同共同的价值规范。[25]虽然滕尼斯的社区概念与现代社区概念指涉涵义不同,但在强调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生活中核心地位这一点上却没有太大差异,二者均指涉社区社会的精神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认知、居民对社区生活的基本态度、居民社区观念系统的稳定结构等,以及这些结构与方式如何进化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日常行为规则等内涵。社区治理必须深入社区文化心态系统的核心,即社会资本本身,顺势而为,实现社区治理模式建構与社会资本的充分融合,进而浑然一体,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将居民与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实现社区治理措施效用的最大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支点。社区发展初期的社区治理工作多注重制度建构,比较侧重于从制度框架层面建构社区治理的基本规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社区治理工作日益走向深入,社区治理必然向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层面延伸,社区治理内外动力机制以社区社会资本为纽带全面整合是社区治理的必然趋势。以北京的社区治理工作为例。经过20多年发展,北京社区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逐步从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向多元社区治理模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社区复合治理”模式。[26]这个模式突出“五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分别指涉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的内涵。于文认为“社区复合治理模式”“具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其中“四位”似乎指涉社区党委、社会组织、居委会以及社区服务站,“一体”指社区居民参与这一枢纽。不过作为社区治理参与方的社区居民,与前面四个基础性主体的地位应该同等重要,因此这种模式称“五位一体”应该更为恰当。上述“五位一体”中前面“四位”涉及社区治理结构中内生与外源性动力两个系统,其联结与耦合的媒介则为社区居民参与这一“主体”。在这一治理模式中,社区社会资本提供了信任资源,决定了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动力系统的耦合方式,对社区治理的实施路径及精细化程度会产生较大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治理绩效。
五、结语
社区治理内外动力系统经过功能性整合即形成了社区治理动力机制。通过这一整合过程,社区获得发展动力,社区治理结构得以优化。因此社区治理动力机制的建构与强化更多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其基础不是控制和支配,而是协调。[27]社区治理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社区治理结构则涵盖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系统、涉及公私部门等治理机构及其持续的互动过程等内容。社区治理动力机制推动着上述互动过程不断迭代,并推动着社区治理结构的持续进化。因此,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优化社区治理动力机制,才能推动社区治理良性发展,实现社区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整体社会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202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12日。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401页。
[4]张若冰、祝歆、李雪岩:《智慧城市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实践创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5]吴晓林、李一:《全球视野下的社区发展模式比较》,《行政论坛》2021年第5期。
[6]边防、吕斌:《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第4期。
[7]胡申生主编:《社区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8]高莉娟主编:《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应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9]杨清:《常住外来人口城市融入进程中福建社区教育的发展与推进》,《教育评论》2016年第2期。
[10]申可君:《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11]潘泽泉、辛星:《政党整合社会: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国实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2]潘士君:《社区教育工作者实用手册》,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13]胡俊生主编:《社会学教程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14]刘晓丽:《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微循环——社区公民的生成机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15]闵兢:《场域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动力研究》,《科教导刊(上旬刊)》2016年第19期。
[16]李兆瑞:《社区治理结构“逆扁平化”层级扩张的逻辑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17]陈晓春、肖雪:《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
[18]王德福:《社区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7期。
[19]王木森、唐鸣:《社区治理现代化:时代取向、实践脉向与未来走向——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政策-实践”图景分析》,《江淮论坛》2018年第5期。
[20]陆平贵编:《中国和谐社区-鼓楼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 第116页。
[21]田先红:《新时代的互联网与基层社区治理:机遇、挑战与超越》,《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2]王东、王木森:《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3]刘琳:《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居住因素分析:居住隔离抑或社区社会资本?》,《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4]姚迈新:《城市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25]郑广永:《论城市社区文化的功能及限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6]于燕燕:《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前线》2014年第8期。
[27]冯猛:《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启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Conceptual Thinking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HEN Xing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human society after entering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becomes the main source of exogenous power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dividuals gradually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demand of optimizing the function of community as “life community.” Tak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s the key medium to elimina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above two governance force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ccessful coupling between them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not only the basic goal to construct and optimize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construct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community governance; dynamic coupl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責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