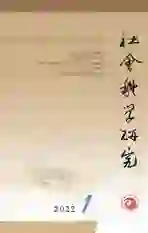论儒家哲学的“超越”与“感通”问题
2022-03-22黄玉顺
〔摘要〕 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严重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主体,即“天”是外在的、超凡的,而“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的、超验的。“感通现象学”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康德与牟宗三的问题意识;而其观念背景,在西方哲学中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哲学中是主张“心即天”“性即天”,因而“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宋明理学。因此,作为“感通本体论”的“感通现象学”其实并非现象学,而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
〔关键词〕 儒家哲学;超越;感通;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150-10
〔作者简介〕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① 蔡祥元:《从内在超越到感通——从牟宗三“内在超越”说起》,《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
学界近来关于儒家哲学“超越”观念问题的热议,与牟宗三提出的中国哲学“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之说密切相关。对此,蔡祥元教授的文章《从内在超越到感通》进行了一种概括:“当前学界对于内在超越说有两大典型批评。一是張汝伦、黄玉顺等学者着眼于外部世界的超越性视野出发提出的批评。另一个是杨泽波着眼于牟宗三与康德哲学的思想关系提出的批评……这两个批评,可以说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去‘终结’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对我们理解、评估牟宗三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提出了两个重要挑战。”①(以下简称“蔡文”,引文不再注明出处)蔡文旨在维护和发展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其路径是以某种现象学的视域来诠释中国哲学的“感通”观念,姑名之曰“感通现象学”。其中,蔡文对笔者观点的评述不无中肯之处,然而也存在着若干可以商榷之点。鉴于问题重大,不仅关乎怎样理解和评估“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问题,而且“关乎当下儒学发展的思想方向”问题,笔者特在此对蔡文作出回应,以期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关于“内在超越”问题
与牟宗三一样,蔡文所关注的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哲理特征”,认为这个特征就是“内在超越”。因此,蔡文的宗旨是通过“重新考察智的直觉如何可能的问题”,以“感通”视角来“表明内在超越如何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为此,针对笔者对牟宗三的批评,蔡文提出了反批评。
蔡文归纳笔者对牟宗三的批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内在超越的消解及其思想后果的批评……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也有内在超越,因此它并不构成中国哲学特质。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内在超越的思想模式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具有某种平行关系,后者是造成现代价值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对外在超越的诉求。在指出内在超越的问题之后,他们都转向中国古代‘天’的观念,表明其中蕴涵着外在超越的维度”。
这样的归纳大致不差:笔者确实着重指出了“西方哲学传统也有内在超越”,并强调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儒学的“外在超越的诉求”即“‘天’的观念”。然而,尽管蔡文认为笔者的意图是要“‘终结’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这是没错的,但蔡文说笔者的批评是“对内在超越的消解”,则是不对的。笔者其实承认儒家哲学存在着内在超越的维度,但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维度,而是指出儒家哲学同时存在着外在超越的维度。笔者的意图是要破除“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即破除中国哲学是内在超越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前者区别于后者并且优越于后者的臆见。
(一)康德哲学的内在超越
确实,笔者强调“西方哲学传统也有内在超越”。蔡文写道:“张汝伦[参见张汝伦:《论“内在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与黄玉顺也都看到了康德与牟宗三的思想关联。他们都指出,在康德那里,上帝是一种理智的假设,不是理性直观的对象。黄玉顺为了证成西方近代哲学同样具有内在超越的维度,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他指出,既然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公设,而实践理性乃是人的理性,这就表明‘上帝’终究也是内在于人的理性之中的。”这样的理解基本符合笔者的原意,即证明康德哲学是内在超越的。
蔡文对此提出反驳:“虽然他们都注意了德国古典哲学中有个超越者的内在化维度,但都没有明确意识到它与儒家传统中形上本体的‘内在化’有关键不同。康德那里的上帝关涉的只是一种理性‘设定’,因此是一种理性设定的‘内在’”。蔡文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等于承认了康德哲学是内在超越的,亦即承认了笔者的观点。
蔡文批评笔者“没有对中西两种不同的‘超越’作出回应”,其实是偷换了论题:笔者的意图在于揭示康德哲学是内在超越的,而蔡文的意思是指出康德的内在超越不同于儒家的内在超越。诚然,儒家的内在超越不同于康德的内在超越,中西双方的内在超越之间存在着差异,笔者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点;不仅中西之间,中国哲学内部亦然,例如,孔孟儒学的内在超越与宋明理学的内在超越就是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后者之中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内在超越也是颇为不同的。但尽管不同,它们毕竟都属于“内在超越”,这才是笔者的关注点。
(二)“内在”“外在”概念的澄清
当然,蔡文的意图是要否定西方哲学也有内在超越,否定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也是内在超越的,意在证明唯有中国哲学、儒家哲学才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与上引蔡文“康德那里的上帝关涉的只是一种理性‘设定’,因此是一种理性设定的‘内在’”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蔡文写道:“正是这种理性或理性的设定,在熊、牟看来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儒家的形上本体与此不同,它是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可以为我们所直接体认。……也因此,不仅仅康德,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在熊、牟看来,都可以视作为某种形式的‘外在超越’,从而有别于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传统中)那种可以在生命中获得直接体认的‘内在超越’。”
这其实是偷换了“内在”“外在”的概念。事实上,在“超越”问题的讨论中,“内在”和“外在”并不是蔡文所说的“内在于生命”和“外在于人的生命”。所谓“内在”是说的内在于这个凡俗世界(the secular world),乃至内在于人的心灵,不论康德的“理性”还是儒家的“心性”都是这样的“内在”;而所谓“外在”则是说的外在于人的心灵,乃至外在于这个凡俗世界,这里的观念前提乃是凡俗世界与超凡世界(the transcendent world)的划分。[参见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这是因为,“超越”(transcendence)原是西方话语,有一个从宗教的“超凡”(transcendent,或译“超验”)概念到哲学的“超验”(transcendental,或译“先验”)概念的历史转换。刘述先根据《韦氏大辞典》而指出:“宗教所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也相信人有了这样的信仰,乃会在精神上得到慰藉。这样的说法……兼顾超越(神)与内在(人)两层……”[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二十一世纪》总第50期(1998年12月号)。]这就是说,当时的“超越”观念,既有外在的超凡性(“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即外在于人与凡俗世界),也有内在的超验性(“信仰”即内在于凡俗世界与人的心灵)。后来,“以康德为分水岭,使我们看到在西方古典时期与近现代的神本与人本的对立;这既是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也是古代与近现代的转折。以后的哲学,不管是有神的还是无神的,都开始在人的主体内寻找超越的根据”;于是,“从康德开始,西方‘超越’(transcendence)就已转变为‘超验’(transcendental)了,即原来的‘跨过界限达致本体’的含义已变为在主体内的一种提升活动”。[耿开君:《“超越”问题:“内在”与“外在”》, 《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 这其实就是我所讲的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内在超越”。
而蔡文所谓“内在”与“外在”,却是说的“内在于人的生命”与“外在于生命”。那么,何谓“生命”?蔡文特意引证了熊十力的说法:“吾人与天地万物,从本体上说是同体,即是同此大生命。”[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这个“大生命”观念显然来自宋明理学,却也不禁令人想到西方的生命哲学,而蔡文说,“甚至叔本华、柏格森那种注重体验、注重直觉的生命哲学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观”。诚然,熊十力的生命哲学不同于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它们都诉诸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大生命”。然而:
其一,熊十力说的是“人与天地万物……同此大生命”,而蔡文说的是“人的生命”,这并不是同一概念。
其二,这个所谓“大生命”,其实等于根本取消了“内在”与“外在”的划分,即无所谓“内在”了,试想:在这个涵盖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大生命体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存在呢?可见无论是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是熊十力的“大生命”哲学,都属于近代以来的内在超越的哲学,而这种所谓“内在超越”其实已经无所谓“内在”,因为“外在”的东西都已经被“悬搁”起来了。
其三,进一步的追问是:在这个大生命体之“内”,毕竟人与天地万物并存,那么,天地万物究竟是在人之内,还是在人之外?对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儒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的回答。其实,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孟讲“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3页。]“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十三经注疏》,第2753页。],天显然是外在于人的至上存在者,乃是“天本主义”,而宋明理学则大讲“心即天”[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1,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页;《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3,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第105页;《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卷6,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第228页;《谨斋说》,《王阳明全集》卷7,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第280页。]“性即天”[参见张载:《张子语录》上,《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11页;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8页;《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04页;《河南程氏遗书》卷25,《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318页;朱熹:《朱子语类》卷6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4、1428页。],于是,天就成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者了,这其实是“以人代天”,即是所谓“人本主义”。这是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
二、关于“外在超越”问题
诚如蔡文所说,笔者确实强调中国哲学“外在超越的诉求”即“‘天’的观念”。其实,蔡文有时也承认中国哲学有外在超越的传统,如说:“中国古代的‘天’或‘天命’与西方的上帝在超越维度方面是相似的”“西方哲学宗教传统中的超越者,无论是上帝还是实体,整体上言,都具有一种超出自然界或現实世界的存在方式。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的天或天道同样也具有这个维度”。这实际上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
(一)中西古今共有的天人沟通
但是,蔡文却是要维护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于是再次偷换了论题,认为:“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哲人,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在寻求如何把此外在的天跟人心打通。‘内在超越’标识的就是这一哲理特征。”注意:我们原来的论题是“中国哲学有没有外在超越的观念”?现在的论题变成了“中国哲学的外在超越与西方的外在超越之间有何区别”?
蔡文认为,这个区别就是:中国哲学“寻求如何把此外在的天跟人心打通”。言下之意,西方没有这种天人沟通的寻求,这个判断显然不能成立。试问:难道西方宗教就不“寻求如何把外在的天跟人心打通”吗?难道西方宗教就不寻求人与上帝的沟通吗?
再者,既然谈天人之间的“打通”,其前提当然是天人二分,即承认天与人是两种独立的實体,亦即承认天是外在超越的,否则,也就无须什么沟通了。
然而蔡文要否定西方的天人沟通,其论证方式仍然是牟宗三式的,认为:尽管“中国古代的‘天’或‘天命’与西方的上帝在超越维度方面是相似的,但是它与人的德性一开始就有某种关联,这是它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的区别所在”。[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页。]这个判断大可商榷。按照这种说法,西方的上帝与人的德性之间没有“某种关联”。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研究西方哲学与宗教学的学者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至于中国哲学方面,蔡文自己也在下文提到,西周时代尽管已有“以德配天的理路”,但“还没有达到与天命相贯通”。其实,这个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早在西周之前,“德”就已经是一个重要观念,即蔡文所说的天“与人的德性一开始就有某种关联”。例如《今文尚书·周书》之前的记载,有《虞书》中的“克明俊德”“否德忝帝位”(《尧典》)、“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让于德”“惇德允元”(《舜典》)、“允迪厥德”“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日宣三德”“日严祗敬六德”“九德咸事”“天命有德”(《皋陶谟》)、“迪朕德”“群后德让”(《益稷》)、“祗台德先”(《禹贡》)[参见《尚书》,《十三经注疏》,第119、123、125、126、130、138、139、143、144、152页。],有《商书》中的“夏德若兹”(《汤誓》)、“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施实德于民”“汝有积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用德彰厥善”(《盘庚上》)、“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盘庚中》)、“用降我凶德”“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式敷民德”(《盘庚下》)、“用乱败厥德于下”(《微子》)。[参见《尚书》,《十三经注疏》,第160、169、170、171、172、177页。]可见过去通常认为到周公才开始重视“德”的看法是错误的,“德”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并且一开始就与“上帝”“天”和“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而绝非“还没有达到与天命相贯通”。
这种古老观念被以周公思想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继承下来,见于《尚书·周书》对外在超越性的“天”的尊崇。[参见黄玉顺:《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权力话语——〈尚书·金縢〉的政治哲学解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然而,这种“以德配天”的观念前提,恰恰是天人二分,而不是什么“天人合一”,即不是什么“内在超越”。蔡文其实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转述牟宗三的观点:“周人的天命观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高高在上,决定人间吉凶,掌控人类的命运,这是古代人对超越者的通常领会,中西无异;另一方面,在如何对待天命方面,出现了以德配天的理路,通过敬德修德,来获得天命的庇佑。”
然而对于中国上古时代的这种“外在超越”,蔡文不以为然,而完全采纳了牟宗三的叙述,认为孔孟开始改变了这种“外在超越”观念,儒家转向“内在超越”的路数:“孔子在实践仁的过程中,又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天,一种跟仁也即人的德性有内在关系的‘天’或‘天命’”“如此一来,践仁以通天命的思想路子就打开了。孟子将孔子那里隐含着的‘践仁知天’发展为‘尽心知天’,这个维度就得到了进一步突显”“这种意义上的天,与超越的上帝或实体相比,它相对于人心而言,已经具有明显的‘内在性’特征了”“到《中庸》这里,超越的遥契转变成了内在的遥契,消除了超越之天的宗教意味”。
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孔子之前的“外在超越”就已经是与“人的德性有内在关系的‘天’或‘天命’”了。这且不论。蔡文所说,其实就是余英时所谓孔子的“轴心突破”(The Axial Breakthrough)[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2、221—229页。],转向所谓“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李怀宇:《余英时谈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精神归宿于“内向超越”》,《时代周报》“时代在线”,www.time-weekly.com/index.php/post/2434,2014年3月27日。]余英时说:“孔子创建‘仁礼一体’的新说是内向超越在中国思想史上破天荒之举;他将作为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第一次从外在的‘天’移入人的内心并取得高度的成功。”[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229页。]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是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孟子的“此天之所与我者”,还是《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第1625页。],从诸如此类关于“天人之际”的命题中,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天”已经“内在化”的结论,恰恰相反,它们都承认“天”乃是外在超越性的、终极创生性的。[参见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
(二)两种超越主体的混同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的根子还是在牟宗三那里:他谈“超越”问题的时候,完全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不同的主体。本来,他所否定的所谓西方的“外在超越”,主体是“上帝”或“天”,即上帝是“超凡的”(transcendent)(牟译为“超绝”或“超离”),而他所肯定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主体则是“人”,即人的心性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参见黄玉顺:《“超验”还是“超凡”——儒家超越观念省思》。]孔孟儒学其实也是这样的观念,即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间并不矛盾。然而在牟宗三那里,无论超验者,还是超凡者,主体都是“人”,而具有所谓“智的直觉”。
牟宗三对两种超越主体的这种严重混淆,既有康德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背景,也有中国的宋明理学的背景,都是以“人”取代“上帝”“以人代天”,这在西方哲学是“上帝死了”,而在宋明理学则是“天死了”。蔡文所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样的路数,即是“接着讲”康德哲学和牟宗三哲学。应当承认,蔡文对康德哲学和牟宗三哲学的分析与把握是颇为精准的,作者自己在这个基础上的推进也是富有创意的,但这一切的前设都已经是“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立场,然而这种预设观念在今天恰恰是亟须反思的。
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关系
上文讨论的中西共有的天人沟通,实际上就是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间的关系,这里再作伸说。
蔡文认为,孔子的“天”与“天命”仍然是“一种外在超越的天”,因而“义理上就不通透”;“牟宗三据此指出,孔子通过‘下学而上达’达到了与天命的‘遥契’,从而作出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尽管如此,牟宗三依然指出,孔子对天命的遥契中包含着敬畏,因而还保留(外在)超越的维度”。蔡文这样的判断实在令人惊讶:承认天是外在超越的,人对天应当是“敬畏”的,为什么“义理上就不通透”?
这里所涉及的就是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关系问题,亦即“天人之际”的问题。蔡文认为,到孟子才把这个道理讲“通透”了:“孟子将孔子那里隐含着的‘践仁知天’发展为‘尽心知天’,这个维度就得到了进一步突显。……这种意义上的天,与超越的上帝或实体相比,它相对于人心而言,已经具有明显的‘内在性’特征了。”这当然根据的是孟子关于“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论述。[参见《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第2764页。]但这其实是对孟子的误解,事实上,孟子那里仍然坚持孔子的外在超越的“天”。[参见黄玉顺:《天吏:孟子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孟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否则,就真的是“不通透”了:无论如何“知天”,也不可能使外在的“天”具有“内在性”,即不可能使“天”内在于人。这就犹如我认识了一个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被我内在化了,这个人仍然是,并且始终是一个外在于我的存在者。
其实,孟子的“知天”并不是要使天内在于人,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人“事天”,即侍奉上天,而这种侍奉的基本情感态度,正是“敬畏”,即孔子所讲的“畏天命”。[参见《论语·季氏》,《十三经注疏》,第2522页。]孟子也讲“畏天”,他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孟子·梁惠王下》,《十三经注疏》,第2674页。] 孟子讲的“畏天之威”,与孔子讲的“畏天命”是完全一致的。要之,在孔孟的思想观念中,天人之际的要点有三:天是外在的、至上的;人是天生的;人对天要敬畏。
蔡文在论证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批评西方的“外在超越”时,还是采取了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方式,即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在寻求如何把此外在的天跟人心打通”,而康德哲学及西方的宗教与哲学则不能沟通天人,即不能打通现象界与物自身。然而上文说过,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事实上,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神学家、哲学家“都在寻求如何把此外在的天跟人心打通”,或者说,都在寻求沟通“天人之际”,只是沟通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这就涉及如何最终确定“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间关系的问题了。更确切地说,这是内在超验者(心性或理性)与外在超凡者(天或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承认天的外在超越性的前提下,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是并不矛盾的:这是两种不同主体的超越,即天是外在而超凡的,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而超验的,然而这种内在的超验性正是指向外在的超凡者的,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事天”。
四、关于“感通”观念的讨论
上文谈到,蔡文的问题意识和基本路数还是康德和牟宗三的,然而蔡文却尝试以某种现象学的方法来继承和发展这种思路。这一点可以说是蔡文的独到之处,因为现象学恰恰是超越康德哲学的。蔡文用以消弭这种紧张关系的途径,就是引入中国哲学的“感通”观念。确实,“感通”是蔡文作者这些年的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特色,且颇具创造性。不过,说实话,蔡文的这种“现象学”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现象学,乃至究竟是不是现象学,笔者心存疑虑。
(一)“情感”观念的澄清
蔡文的“感通”之思,基于几年之前的一种批判意识:
当代儒家学者已經开始尝试以一种更加理性化的方式来重构儒家道统,实体论与情感论是其中两种典型思路。实体论的主要代表是陈来的仁学本体思想,情感论则包括李泽厚的原始情感论、蒙培元的普遍情感论与黄玉顺的纯粹情感论等不同主张。下面的考察将表明,这两种思路都难以真正跨越康德给形而上学思辨划下的界限。实体论失于概念思辨,而沦为抽象的形而上实体,情感论虽然反对实体建构,意欲返回情感本源,但却无法走出经验论的困境。[蔡祥元:《感通本体引论——兼论当代儒学的实体论与情感论》,载《当代儒学》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这里且不讨论李泽厚的“情本论”,因为他的情感论其实并不属于儒家哲学。[参见黄玉顺:《关于“情感儒学”与“情本论”的一段公案》,载《当代儒学》第12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3—177页。]这里只讨论蔡文所说的“蒙培元的普遍情感论与黄玉顺的纯粹情感论”的所谓“经验论的困境”。
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参见黄玉顺:《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被归结为“经验论”,这是不对的。这里仅以蔡文作者所引的蒙培元的一段话为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仁作为心灵境界,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志。它虽以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又必须超越情感,成为普遍的存在方式,这样,就同个别的心理现象、个人的情感欲望有了区别。只有从超越的层面上看,仁才是境界,否则,便只是一些个别具体的情感活动,没有普遍意义。[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显然,这里的“情感”不仅仅是感性经验层面的,而恰恰是超越这种经验情感的。蒙培元的“情感”概念是在境界论的意义上讲的,包含三个层级的境界:感性情感、理性情感、超越感性与理性之对立的形上情感。[参见黄玉顺:《“情感超越”对“内在超越”的超越——论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哲学动态》2020年第10期。]其中,只有“感性情感”或“心理情感”才是经验论层级的。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的情感观念,也被归结为经验论,这更是不对的。蔡文作者是这样讲的:“纯粹情感虽然克服了观念化的困境,它由此却可能走向观念的对立面,也即走向经验,因为这种‘真切的仁爱情感’很容易被看作一种仁爱的‘纯粹经验’。”[蔡祥元:《感通本体引论——兼论当代儒学的实体论与情感论》,第108页。]蔡文这里的“纯粹经验”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概念。[参见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50页。] 但事实上,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的所谓“纯粹经验”并不那么“纯粹”,因为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英美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先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相对立而存在的,但两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基于海德格尔所要解构的“主体性”。[参见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页。]然而生活儒学的“生活情感”观念,恰恰是要追溯“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生活情感,从而超越经验论与先验论的紧张、情感与理性的紧张。且看蔡文作者所引的黄玉顺的话:
儒家所说的“仁爱”也在观念的三个层级中显现为截然不同的三种样态:(1)本源之仁,乃是原初的真切的生活情感的存在,这是存在的直接显现,是前存在者化、前对象化、前概念化的事情;仁爱之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乃是在这个层级上而言的;(2)形而下之仁,则是被理解为道德情感、甚至道德原则的那种形而下者的存在,是某种相对主体性的事情;(3)形上之仁,又是更进一步被理解为本体之“性”、甚或类似“上帝之爱”的那种形而上者的存在,是某种绝对主体性的事情。[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生活儒学的“生活情感”观念正是“本源之仁,乃是原初的真切的生活情感的存在,这是存在的直接显现,是前存在者化、前对象化、前概念化的事情”。这也正是蔡文作者所希冀的“既立足仁爱情感,又能超出情感經验的主体性限制”。
顺便说说:蔡文将笔者的观点归为“反对实体建构”以防止“沦为抽象的形而上实体”,这也失之片面。事实上,笔者已经致力于建构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Change Ontology)[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此文详尽地讨论了中西“实体”概念),近来又致力于建构一种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Transcendent Ontology)。[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只是笔者的这种形而上学建构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乃是渊源于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生活情感的,宗旨是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蔡文作者试图建构一种本体论,谓之“感通本体论”。而一说到“本体”,思想视域的问题便立即赫然凸显出来。所以,蔡文作者首先澄清这个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本体”不应当是西方“ontology”的译名,而应当是“道”或“仁道”的另一种表达,因此,应当“把中国形而上学传统称为‘道本论’(Dao-ology)”。[参见蔡祥元:《感通本体引论——兼论当代儒学的实体论与情感论》,第109页。]然而我们注意到这里的表述:作者所说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讲,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这样一来,“感通”岂不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者化的概念?进而,“感通本体论”的“本体论”概念与西方的“ontology”概念,尽管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岂不是同一观念层级上的概念?这样一来,这岂不是前现象学的观念?
蔡文提出:“仁学本体或仁道的关键就在于,这种看起来源自人心的情感发用,何以能够超出自身的主体性限制,而成为贯通物我的天人之道。这是感通本体论要回答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本体意义上的感通,不只是显示出那潜在的存在,而是生成存在,如此才是本体。”[蔡祥元:《感通本体引论——兼论当代儒学的实体论与情感论》,第95—118页。]说实话,这样的“本体生成存在”的表述是令人困惑的:既然本体是形而上学的范畴,即标识的形而上者,也就是一种存在者,那么,“本体生成存在”岂不等于是说“存在者生成存在”,然而当代思想前沿的观念正好相反,是要追问“存在者何以可能”,其回答恰恰是“存在生成存在者”。
蔡文作者在这样的观念上理解“感通”,是因为他的思想视域其实还是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所以他大量引证周敦颐、程颢、程颐和朱熹的言论来谈论“感通”,即“本体意义上的感通”。
(二)“感通”本义的前现象学性质
我们知道,“感通”的观念最初直接来自《易传》: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1页。]
这段话里的“易”有两重含义(整篇《系辞传》里的“易”皆然):
加书名号,指《周易》这部书,涉及“其辞”“其变”“其象”“其占”。其中涉及两层意思:一是“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是说的筮者通过询问《周易》来决定其行为;二是“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是说的《周易》这部书本身是如何构成的。
而不加书名号,指《易》这部书所蕴含的“易”之道,即“易道”。正是这里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句话,直接导出了“感通”概念。那么,何谓“易道”?一方面,“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78、83页。],即这里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乃是说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而另一方面,“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78页。],即这里所说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是说的这个“一阴一阳”的形上本体的运行,可以由“感通”而“生成”天下万事万物,诸如:自然界方面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第87页。];人类社会界方面的“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第91页。]等等。总之,“感通”是讲的形而上的本体论,属于轴心时代以来的存在者化的思维。
那么,这个感通的本体由何得来?来自圣人的经验归纳:“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第86页。]这种经验观察,最突出的是男女交媾的现象,这是许多学者一致的看法。可以说,“感通”观念其实最初是来自《咸卦》[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6—200页。],故《咸彖传》说: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是以亨也。止而说(悦),故“利贞”也。男下女,“取女吉”也。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咸彖传》,《十三经注疏》,第46页。]
这是从男与女之“感”而“通”引伸到圣人与人心之“感”而“通”,再引伸到天与地之“感”而“通”,再抽象为阴与阳之“感”而“通”,最终落实到《周易》乾与坤之“感”而“通”。于是,“阴阳”或“乾坤”即“天地”就是《周易》哲学的形上本体。[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所以,“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第89页。]“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现)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2页。]
这里有两个属于前现象学的观念架构值得注意:
(1)“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此即所谓“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3页。]所谓“易道”就是这样的“形上-形下”之道,而有种种表现,诸如“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泰彖传》,《十三经注疏》,第28页。]“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否彖传》,《十三经注疏》,第29页。]“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周易·睽彖传》,《十三经注疏》,第50页。]等等。
最典型的是《象传》中的“大象传”,其“形上-形下”的关系表现为“天道-人事”的关系,那是一套君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天道”即对每卦的卦象(上下卦)的解释;“人事”即讲地上的帝王君主应当如何仿效天道,诸如“天行,健(乾);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豫卦)“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卦)“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卦)“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姤卦)等等。这些“君子”“后”“先王”“上”“大人”之類,皆指帝王君主。
(2)“本体-现象”或者“本质-现象”的观念架构。笔者已专文讨论过这个问题,指出:“汉语‘现象’出自《周易》‘见象’(‘见’读为‘xiàn’),对应于西语的‘phenomenon’或‘appearance’,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1)形下实体的本质的显现;(2)形上本体的显现。但这些都是前现象学的‘现象’观念。”[黄玉顺:《中国哲学的“现象”观念——〈周易〉“见象”与“观”的考察》,《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
具体来说,汉语的“现象”出自《易传》:“天垂象,见吉凶”“见(现)乃谓之象”。[《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2页。] 两个“见”字都读为“现”(xiàn)。汉字的“现”字产生很晚,乃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还没有“现”字,直到唐宋的《广韵》,才在“见”(xiàn)字之后列出“现”字,而注为“俗”[《钜宋广韵·去声卷第四·三十二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314页。],即“现”字乃是“见”的俗体字。这就是说,汉语的“现象”原作“见象”。
在“天垂象”这个表述中,“天”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万物的终极本质;“象”即现象,即“天”这个本体的显现。要注意的是:《易传》有时以“天”指称本体,如“乾元用九,乃见(现)天则”[《周易·乾文言传》,《十三经注疏》,第17页。];有时以“天地”指称本体,如“复,其见(现)天地之心乎?”[《周易·复彖传》,《十三经注疏》,第39页。]“天地”在《周易》里就是“乾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现)矣”[《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75—76页。]“乾坤毀,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第82页。]而“乾坤”即“阴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周易·说卦传》,《十三经注疏》,第93页。]“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第89页。]这就是说,“阴阳”乃是“有体”的,即是本体。
在这种观念下,所谓“感通”只可能有三层意义:要么是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的自我感通,即阴与阳的感通,或天与地的感通,或乾与坤的感通;要么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感通,即天与人的感通;要么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之间的感通,即人与人的感通、人与物的感通。然而无论哪种意义的“感通”,显而易见,它们都是存在者化的观念,即典型的前现象学的观念,而不是现象学的观念。
综上所述,牟宗三的“内在超越”之说,严重混淆了超越的两种不同主体,即主体“天”是外在而超凡的,而主体“人”的心性或理性是内在而超验的。两者本来并不矛盾,人的内在超验性指向外在超凡性的天,即“知天”而“事天”。然而蔡文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康德、牟宗三的问题意识,而其观念背景,在西方哲学是近代“认识论转向”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哲学是主张“心即天”“性即天”,因而“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的宋明理学。因此,“感通现象学”作为所谓“感通本体论”,并非现象学,而是一种前现象学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感通”是不可能在现象学的视域下来讲的,但只能这样来讲:如果“感通”导致新的存在者的生成,那么,对于新的存在者来说,“感通”就是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事情,即是“无”,而非“有”,更非什么存在者化的“本体”。为此,现象学本身也有待反思。
(责任编辑:颜 冲)
sdjzdx20220323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