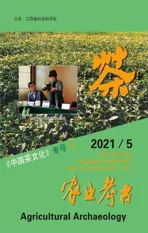论中国茶书中关于茶树种植的生态智慧*
2021-11-04杨源禾
杨源禾
朱自振先生和沈冬梅女士主编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把历代问世的茶书按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分类,共收录近120种茶书。本文主要对《集成》中所收录的茶书进行研究,找寻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智慧。
一、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环境的生态意蕴
中国古代先民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在茶树种植的环境选择上,就处处体现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及生态实践,有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环境的生态意蕴主要体现在符合茶树生长条件的科学客观的自然空间结构,即古代常说的因地制宜。
(一)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适宜性
根据朱自振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可以发现,茶的产地全国各处都有,而茶的品质有高下之分。到底以什么因素来判定茶叶品质的好坏?首先,茶叶品质一定和特定生产区域相关联,这是农产品的特性。然而,茶的品性又不止于农产品,它又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生产,才能形成最终的成品形式。但种植环境是茶叶品质好坏的先决条件,以下主要从区域地理、地势、土壤、气候等自然环境讨论茶叶原料的优劣。
1.适宜茶树生长的区域地理
据古茶书记载:唐代最有名的是阳羡茶(江苏宜兴),宋人则重建州茶(福建建州),明清时期,罗岕茶(浙江长兴)和松萝茶(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成为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名茶。明以后至今,武夷山一直是中国的名茶产区,除此之外,蜀地所产的蒙顶茶(四川雅安),楚地所产的宝庆茶(湖南邵阳),云南所产的五华茶(云南昆明),还有庐州所产的六安茶(安徽合肥),这些茶都名声卓异(图1)。今天来看,北回归线(23°26′N)以北至北纬30度附近是适宜中国古代茶树生长的黄金地带。
2.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势
适宜茶树生长的海拔高度为针叶林和阔叶林的交界地带。古茶书中大多记载生长于高山的茶叶,品质优良。如胡秉枢在《茶务佥载》记载:“植茶,以高山、大岭及穷谷中至高之处为宜。”[1](P834)宋子安在描写东望建安茶山之高时说道“丛然而秀,高峙数百丈。”[1](P107)根据古代度量单位,一丈十尺,三尺一米,百丈大概是333.33米,由此可大致推算“数百丈”为1000米以上、3000米以下。陈师的《茶考》有关于蜀茶的记载:“我闻蒙顶之巅多秀岭,恶草不生生淑茗。”[1](P242)蒙顶山最高峰上清峰,海拔约1456米,今雅安市蒙顶山茶园种植的海拔高度为1200—1456米。曹学佺在《茶谱》提到“蜀茶之极品”在“玉垒关宝唐山”[1](P446)。根据地理位置来看,现在的玉垒关宝唐山可能是与玉垒山相邻的灵岩山,主峰海拔1432米。熊明遇在《罗岕茶记》中记载了明清时期的贡茶:“岕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1](P317)岕茶产于宜兴南部山区,即唐宋时期的阳羡茶,据宜兴县志载:“章山有茗岭,以产茗得名……茗岭,于宜兴西南七十里。”宜兴最高峰海拔为611.5米。
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差异,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海拔高度从几百米到上千米分布不等,但从生态环境和生物条件方面考虑,最适宜茶树生长的海拔高度为针阔混交林地带。在针阔混交林地带的茶区植被、植物群落、动物群落等自然生态的构成对维系茶树生长和茶叶品质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3.适宜茶树生长的土壤
茶树种植的土壤以肥沃的黑土为佳,并且土壤透气性好。早在宋代,宋子安就比较了生长在两种不同土壤中茶叶品质的区别:若茶树种植在山的阳面,土为红壤,那么种出来的茶叶黄白,没有茶香味;若是茶树种在山的阴面,土为黑壤,生长出来的茶叶则色香俱佳[1](P107)。后文又写道:若是种在贫瘠的土地上,茶树则营养不良,“土瘠而芽 短”[1](P109),茶 叶 细 小,芽 头 不 肥 硕,内 含 成 分低,冲泡出来的茶汤、茶味都差强人意。相对而言,胡秉枢在《茶务佥载》则提出植茶之地,“其土性愈厚,则茶树愈壮”[1](P834),叶片也更加肥厚、宽大。
据《茶经》,陆羽把种茶的土壤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他认为最好的茶叶是从“烂石”中种植出来的[2](卷一《茶经·一之源》)。这里的“烂石”笔者认为主要强调的是土壤的透气性。林馥泉在武夷山对茶叶进行调查时,提到“山腹岩罅之处,每多腐质肥土流入,肥分既多,气水透通,此均适宜于根深植物如茶树之丛生。”[3]“烂石”“岩罅”可以使根深类的植物保持“气水透通”,避免肥分过多。
4.适宜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
茶树喜欢温暖湿润、富含紫外线的气候特征。许次纾在《茶疏》记述:“江南地暖,故独宜茶。”[4](卷二《茶疏·产茶》)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所以特别适宜产茶。《九州记》载:“蒙着,沐也。言雨露常沐,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香芳。”[1](P446)茶树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多云雾的环境中,这样易形成对茶树生长有利的漫射光,且湿度大。所以才会有“茶之为物,其感雾露愈深,其味愈浓”[1](P834)的说法。在这样的光、热、水、湿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微域气候条件,是优质茶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
虽然笔者找出了古代茶书中适宜茶树生长的区域地理、地势、土壤和气候条件等因素,但茶叶品质的好坏是随着时间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宋代赵佶在《大观茶论》“品名”篇中就谈到茶人的茶:“固有前优而后劣、昔负而今胜者”[5](P46),明代黄龙德在《茶说》中也表示赞同往昔被当作佳品的茶,到了今天还有更胜一筹的。这说明种植茶树的园地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适宜茶树种植的自然环境改变了,茶叶品质及名茶产地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了。
(二)生态意蕴
1.生态实践
(1)有利于茶树生长的生态实践
历代文人士绅与底层社会都在不断对茶树种植的地势、土壤进行划分,这种对不同环境中栽培出来的茶叶等级的分类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从特殊的个人经验中抽取出来的整体图式,把感知安置进一种相对的文化系统之中去。程用宾在《茶录》中提到“上种茶”应“生于幽野,或出烂石,不俟浇培,至时自茂。”[1](P311)这 里 的“幽野”“烂石”“不俟浇培”“至时自茂”即指纯粹的自然状态,象征着自然的秩序,这里有着自然的原本面貌,是生态之根。黄儒在《品茶要录》记载了“壑源”“沙溪”两地:“而中隔一岭,其势无数里之远,然茶产顿殊。”[1](P113)这是因为茶树这种草木植物“其势必由得地而后异”。茶树因栽培地点不同,茶叶的售价有着天壤之别。这是长期以来,古人对茶树培植地点的地势环境等既定的物理因素中总结出了一套与自身文化体系相匹配的生态实践。
(2)不利于茶树生长的生态实践
在明代,人们就认识到了人类的生产活动会限制或影响自然环境,对生态造成破坏,如许次纾在《茶疏》“虎林水”篇就提到了人类造纸活动对玉泉造成的破坏:“玉泉往时颇佳,近以纸局坏之矣。”[4](P143)而没有人迹,或人烟稀少、仍在自然规律主导下的生态环境——湿地、溪流,“则澄深而无荡漾之漓耳”。
2.朴素的生态观念
形容茶山之高的“数百丈、巅、悬崖”等用词,大量对茶山中云、雾、雨、露等自然景观的描写,清、灵、柔秀等感官用词,这些字词不断地反复闪现。通过对词汇的选择、搭配和重组,这些文字不仅勾勒出了一种高山厚土、云雾缭绕、林木茂密、阳光充足的自然环境,这种自然环境孕育了古人对天地、山川、林木、野生动物的亲切感与敬畏感。“古人本身对自然万物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解,不同于学者科学的态度与认知”[6]。例如《东斋纪事》载:“常有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7]这种对自然景观的崇拜、敬畏,并以之为圣神、尊贵的象征,是古代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源自于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与神灵联系在一起,产生自然崇拜。古人对于难以控制和征服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借助神灵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朴素的生态观。“这种朴素的生态观不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提升了人们对茶山、茶园保护的集体认同和行为自觉,更对茶农的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渗入到茶农们的实际行为中”[8]。这是一条以古人对茶山自然的“感知—敬畏—信仰—规范”[9]为线索而形成的朴素自然的生态观念。
以万物有灵的观念展开阐述是古人解释自然的途径,他们相信周围的世界由神灵组成,在这种古朴观念的影响下,古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之前,少不了要面对神灵。《神异记》《异苑》中都大同小异地记录了凡人偶遇神灵后获得茶叶、或以茶茗祭祀祖先获得钱币的传说[2](P124-125、P136)。 祭 祀 作 为 先 民 与 神 灵 沟 通 联 系 的 方式,其本质是协调其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人们对神灵虔诚的态度和隆重的仪式体现了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和顺从。《广陵耆老传》更是将提着器茗、卖茶叶的老姥神化,她不仅乐善好施,将卖茶叶所得钱币散给路边穷人,被捕入狱后,半夜执茗器从狱中飞出,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老姥是拟人化的、被赋予灵性的茶树[2](P137)。“天育万物,皆有至妙”[2](P98),世间万物被赋予灵性,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现。《坤元录》载:“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2](P148)古代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信仰万物有灵,茶树有树神,茶叶有茶祖,等到吉庆的日子,就会聚集到茶山上载歌载舞。“并且在今天云南的革登、莽枝等各地茶山,茶农还依然保留着在古茶树旁举行祭祀‘茶祖’的活动”[10]。中国传统的茶山祭祀仪式的存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对待自然应该保持尊重的态度。
二、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多样性
与现代农业追求经济效益推行的单一化、规模化种植不同,中国古代传统茶树种植不以单一作物的经济效益为目标,在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智慧及生命多元化自然组成观念的指导下,茶树种植表现为种群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以及茶树种植与种养结合的多样性。
(一)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种群多样性
“一个茶种是由多个性状大不相同的类群组成的,这种不同的类群,可能是变种、生态种,甚至是更高一级的可以成为物种的种”[11],在清代英国高葆真摘译的《种茶良法》“茶种”篇记载:“茶树大要分二类:一为中国茶树;一为亚撒玛(Assam)茶树。”[1](P931)这里的亚撒玛茶树就是今天所说的阿萨姆种(Camellia sinensis var.assamica)。虽然古代中国茶种数量尚不明确,但我国地势复杂,为适应不同光温和土壤条件差异,不同茶区种植有不同的茶种,每个种都可形成种群,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茶树种群的多样性。茶树的种群多样性不仅使茶树在不同地域得以生长,也满足了人们对茶叶的需要。明代陈继儒在《茶话》中就有提到琅琊山出产小叶种,其叶片“类桑叶而小”[1](P267)。多样的茶种再加上不同的茶叶加工工艺,造就了“茶有千万状,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襜然……”[1](P40)
(二)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生物多样性
某种或几种茶树类群在自然界,常与多种其他植物、多种动物、多种微生物自由组合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某一特定的气候下和土壤里,从而构成一种生态系统。如云南大叶种的茶与杉树等亚热带针叶林及相关的动物、微生物,在亚热带气候下组成的生态系统。据中国古代茶书记载,茶树多生长在高山、泉边,由于茶树喜欢湿润温暖、富含紫外线的气候特征,造就了我国名优茶产区皆具有“高山”“邻水”特征。陈师在《茶考》中就描写了在这样人迹罕至的茶山环境中可以见到“虎豹龙蛇”等动物的身影。李白《答族侄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写到生长在玉泉山中的“茗”,这里“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玉泉流不歇”,这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茶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选择机会,为茶种发展进化,扩大种族,以及栽培种的品种多样化,创造了前提。宋代赵汝砺在《北苑别录》描写御园九窼十二陇中提到了苦竹园、鸡薮窠、鼯鼠窠……鸡薮窠里“疏竹蓊翳,多飞雉”,这里“时有峰鸡百飞翔,雄者类鹧鸪”;苦竹园里顾名思义,因为茶园中多栽种苦竹而闻名;鼯鼠窠里泉流积水、潮湿阴暗的地方多有鼯鼠出没[1](P149)。不难看出,将茶树种在苦竹园、鸡薮窠、鼯鼠窠等地,为茶树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环境,为其生态种、变种形成提供了环境资源,促进了茶树的多样化发展。“苦竹”“飞雉”“鼯鼠”不仅为茶叶提供了生存竞争对手,推动茶树种族的进化,扩大其适应性;还提供了种间竞争的帮手,这些害虫天敌和蔽荫植物保护茶树种族能够延续、繁衍,帮助茶树更好地生长。
(三)中国古代茶树种植与种养结合的多样性
在中国古代的混林茶园中,就已经形成了以茶树为主体,乔、灌、草共生的植物体系。宋代赵汝砺《北苑别录》说:桐木与茶树最宜合种,冬天茶树畏寒,秋天桐木落叶,掉落的叶片可为茶树御寒保暖;夏天茶树害怕烈日直射,春天桐木发芽,等到夏天枝繁叶茂便能为茶树提供荫蔽[1](P155)。罗廪《茶解》中写道:茶园惟有桂树、梅树、木兰、苍松、翠竹之类的植物,与茶树间作,才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茶树下可移栽芳兰、幽菊之类的“清芬之品”[1](P322)。《茶解》中的记载将古人对混林茶园生态系统的构思跃然纸上:其中高层乔木如“桐木”“苍松”“翠竹”一类,夏季可以避免阳光对茶树的直射,冬季可以蔽覆霜雪,为茶树保温,抵御严寒;底层草本植物如“草”“芳兰”“幽菊”一类,有利于固土,减少雨水对土壤的冲刷。同样地,叶清臣在《述煮茶泉品》中提到“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荈”[1](P94)。这里的“草”即指底层草本植物,“木”即为高层乔木,整体的植物体系成为可以保持茶园水土的生物墙,对调节茶园气候、改良土壤质量、促进茶树的生长、保障茶叶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智慧依然指导着当代的茶树种植,在《茶树与泡桐间作能提高生产效益》一文中,吴天荣等人(1996)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温圳茶场就采取茶树与泡桐(桐木的一种)间作,对改变茶园的生态环境有积极作用。“茶树有喜温、喜湿、喜漫射光、耐荫的特性。”[12](P88)但在炎热的夏秋季,人工栽培的灌木型茶树大都缺乏湿、荫的自然环境,在高温、强光、低湿情况下,导致茶叶的自然品质差。茶树与泡桐间作——由于泡桐为乔木型,有宽大的树枝和叶片,在夏、秋季能使茶园荫蔽,改善了茶园的局部生态环境,变直射光为漫射光,有利于新梢中的氨基酸形成与积累,能达到提高茶叶品质和产值的目的[13],如图2所示。
在中国古代混林茶园中,茶树种植不仅与其他林木结合兼具协同性和多样性,就连茶叶与其他草木叶片合制也体现出多样性。古茶书中记载着用皂荚芽、槐芽、柳芽和茶叶一起制作成茶,香椿、柿叶与茶叶合制味道尤为奇特。谢肇淛《鼓山采茶曲》记载了鼓山(今福建省福州市鼓山镇)“竹林-茶园-村落”的空间关系,展现出茶园与竹、桑、麻等作物种植和鸡犬动物养殖协同的多样性,并维系了人与茶紧密的联系[14](P134-135)。人、茶、林和谐共生,使得鼓山涌泉寺的半山茶园留存至今。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的生活十分贴近大自然,人与茶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而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
三、中国古代茶树种植的生态规律性
对古代先民而言,人们的利益来自于自然的恩赐,茶树种植不仅具有农作物生产所需的耕作、播种、施肥、管理、收获等生产环节,还需要生产活动服从于自然的秩序。这种自然秩序表现为茶树种植生产环节中顺应时节的生态观,体现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15](卷九《荀子·王制》)顺应时节的生态观,尊重大自然的种植规律。
茶树初次新梢的生长一般来说集中在大地复苏,气温回暖之时,“春夏之交,方发萌茎”[1](P458),根据自然物候的变化和茶树生长规律严格规定了采茶的时间。黄龙德认为“采茶,应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1](P415)。许次纾提出“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赵汝砺在《北苑别录》中记载:待到夏天,草木生长最盛之时,每年六月开始对茶园进行除草。《建安志》云,古代对茶园除草有一专有名词“开畲”——“茶园恶草,每遇夏日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名曰开畲”[1](P155)。草本植物与茶园混生,平日里可以固土,减少水土流失,但到夏日最烈时,茶树需要大量水分,便开畲除草,“以渗雨露之泽”,调节茶园水分;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茶园有机质。夏秋季翻地三四次后,若觉茶园土壤不肥沃,可“用米泔浇之”[1](P272)。“米泔”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稻》中释义:“米泔,甘,凉,无毒。”[16](P186)亦称“糯米泔”,即淘米水。秋燥后,待到茶籽成熟时期,茶农们开始摘茶籽,并对摘下来的茶籽进行选择、处理,为了使茶种达到“勿令冷损”,以便过冬的目的,晒后的茶籽应用沙子拌匀后贮藏在竹篓里,等到来年春天再进行播种[1](P271-272)。
古代茶农依据草木枯荣等规律性自然变化安排生产活动——“春采茶、夏除茶、秋摘籽、冬藏种”,蕴含着“顺应天道,万物自然”的生产观。在漫长岁月中当地人与大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态智慧被祖祖辈辈的茶农世代继承,这种茶树种植的生态规律性也就演变成了坚实且规范的生态自觉性。
四、小结
以中国古代的茶树种植为例,茶农们在茶籽的播种、茶叶的采摘、茶树的生长、茶籽的收藏、茶园的管理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一些重复性的、连贯性的动作,找到了茶树种植的规律性和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环境,并且在生命多元化自然组成观念的指导下,茶树种植表现出种生态多样性,展现了中国古代茶树种植丰富的生态智慧。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茶书中记载的遇神灵得茗的传说、卖茶老姥的故事、祭拜茶祖的仪式,也内嵌于茶叶的生产过程之中,融入到茶农们的日常生活中,化作茶树栽培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仪式及传说虽然表面上看是属于脱离实践的形而上的心理及观念层面,但在茶树栽培的过程中,对茶祖的信仰及对茶神的敬畏等观念均实实在在地渗入到茶农们的实际行为中,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有序的茶树栽培的生态智慧[17](P141)。
中国古代茶树种植所体现的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朴素的生态观念、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传统的生态实践等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8],有别于现代众多规模化的台地茶种植园,对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