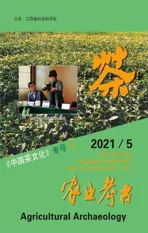论宋元禅寺中的节庆饮茶*——以端午、重阳为例
2021-11-04纪雪娟
纪雪娟
端午节、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菖蒲、茱萸这两种植物在节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人们在端午日、重阳日或祝祭祈愿,或纪念缅怀,或宴饮娱乐,同时装饰、佩戴以及食用菖蒲、茱萸,祈求驱邪禳灾、蠲除病疾。宋代禅寺中,端午日、重阳日由住持上堂烧香说法,并首创饮用菖蒲茶、茱萸茶。至元代,更将此仪轨写入《敕修百丈清规》,正式确立了菖蒲茶、茱萸茶在寺院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考察宋元禅寺节庆饮用菖蒲茶、茱萸茶的文化现象,可以透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寺院生活,更好地理解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
一、寺院节庆饮茶的文献记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最早种植并饮用茶叶的地区之一。随着茶叶种植技术、制茶工艺的提高与精进,烹茶、饮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尚。茶与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唐宋以来,饮茶成为禅寺修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僧人栽培茶树,传习茶艺。结夏、解夏、冬至、新年是寺院内最重要的节日,四节茶会也成为节日中最为庄重的仪式。除此四节外,宋元禅寺开始在中国传统节庆——端午节、重阳节说法品茗,说法偈颂成为记载寺院内节庆饮茶的重要文献。
(一)宋元禅师语录
宋元寺院内,于端午日、重阳日由住持长老上堂说法、阐发佛理,内容多贴近节庆生活,说法结束后,集众饮茶。禅师说法内容以偈颂形式被记录下来,后被弟子收入语录、灯录,保留了诸多关于端午饮菖蒲茶、重阳饮茱萸茶的历史记载。目前可知较早的文献是北宋惟白所编《建中靖国续灯录》,记载了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龙安山慧照禅师于端午上堂说法并品饮菖蒲茶的事迹:
上堂。举拂子曰:端午龙安亦鼓桡,青山云里得逍遥。饥餐渴饮无穷乐,谁爱争先夺锦标。却向干地上划船,高山头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铁旗。一盏菖蒲茶,数个砂糖棕。且移取北郁单越来,与南阎浮提斗额看。[1](卷25,P333)
慧照禅师曾于隆兴府兜率寺担任住持,为南岳下十四世兜率从悦禅师法嗣。南宋晦堂师明所编《续古尊宿语要》保存有从悦禅师端午饮菖蒲茶的偈颂:
端午龙安何所有,一瓯山茗泛菖蒲。
且无百索缠人手,只有摧邪肘后符。[2](第一集《兜率悦禅师语》,P867)
宋廷南渡后,节庆饮茶的习俗广泛流传于江浙、江西一带的禅寺之中。镇江府焦山普济禅寺住持无门慧开、隆兴府泐潭山宝峰禅寺住持环溪惟一、庆元府雪窦资圣禅寺住持希叟绍昙、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无准师范等禅师皆有相关偈颂存世。南宋灭亡后,元代禅寺仍延续此传统,平江路灵岩禅寺住持了庵清欲、庆元路天宁禅寺住持了堂惟一、灵岩报国永祚禅寺住持南石文琸、明州天童禅寺住持平石如砥等禅师亦有节庆饮用菖蒲茶、茱萸茶的事例(详次页附表)。
(二)《敕修百丈清规》
崇宁二年(1103)由宗赜编集而成的《禅苑清规》,为现存成书时间最早的清规,记端午节、重阳节作斋会,尚未出现“节庆饮茶”的记载。南宋咸淳十年(1274)由僧人惟勉编次而成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与元代延祐四年(1317)僧人中峰明本编写的《幻住庵清规》所保留的《月分须知》规定,五月作青苗会,亦未见上堂说法、点茶的记载。可见,虽然宋代禅寺内饮用菖蒲茶、茱萸茶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仍作为一种地方饮茶风尚在江浙、江西一带流传,并未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茶礼。元代至元二年(1336),蒙元顺宗之敕,由僧人德辉集三种清规编修而成《敕修百丈清规》,首次出现端午日、重阳日烧香点茶的规定:
五月 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内烧香,点菖蒲茶。
九月 重阳日早晨,知事烧香,点茱萸茶。[3](卷八,P1155)
《敕修百丈清规》成书后,诏天下僧人悉依此清规修行。由上可知,《敕修百丈清规》出台之后,端午日饮菖蒲茶、重阳日饮茱萸茶,由一种寺院饮茶风尚变为了全国寺院内僧人必须人人遵守的准则。至明代洪武年间,朝廷规定“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永乐年间,规定“僧人务要遵依旧例”[3](序,P1109),可见,《敕修百丈清规》之后,禅寺于端午、重阳日点饮菖蒲茶、茱萸茶的规定被延续至明代。
(三)明清禅师语录
节庆饮菖蒲茶、茱萸茶的规定被明清禅师所传承。例如,明初《松隐唯庵然和尚语录》言:“黄米粽吃一钵,菖蒲茶吃半瓯。个是衲僧好时节,大家相见饱齁齁。”[4](卷1,P32)清代《法玺印禅师语录》言:“雄黄酒,菖蒲茶,无限馨香生两颊。艾虎符,善财药,亦能杀人亦能活。”[5](卷3,P789)《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收录《赠凌云杨居士》云:“菖蒲浮水面, 角黍腻人牙。”[6](卷10,P348)《东山梅溪度禅师语录》言:“倘若未见茱萸茶,且莫饮黄栗粽。”[7](卷5,P395)《神鼎一揆禅师语录》云:“若在今日,山僧热炙盏子,点茱萸茶,令他各各知有,且道知有个甚么,重阳九日菊花新。”[8](卷2,P456)
二、宋元禅寺节庆饮茶缘由考
(一)以茶代酒,准于世礼
端午,又称为重五节、正阳节、天中节等,宋代始以五月五日为端午节,是为纪念诗人屈原兼具驱邪禳灾的复合性节日①。端午节纪念屈原从楚俗扩大至全国,但在不同地区,端午驱邪禳灾的风俗仍占主要地位,或为主要内容[9](P552)。百姓于端午节赛龙舟、食粽子,同时悬挂艾草,塑张天师像,并饮用菖蒲酒、雄黄酒,以蠲除毒气、禳灾祈福。饮用菖蒲酒的习俗由来已久,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10](P47)唐代殷尧藩甚至认为菖蒲酒比艾符 更 具功效:“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11](卷492《端午日》,P5567)宋代文人亦曾创作大量端午宴饮菖蒲酒的诗词,如欧阳修《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12](卷132,P2028);元绛“菖酒朝觞满,兰汤晓浴温”[13](前集卷16);苏轼《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14](P329);王之道《南歌子·端午二首》“一尊菖歜泛清醇”[15](卷17);史浩《花心动·槐夏阴浓》“菖歜碎琼,角黍堆金,又赏一年佳节”[16](卷48)等。人们依照荆楚风俗,将菖蒲切成缕或屑,渍酒饮之,或加雄黄少许,可“除一切恶”[17](卷19)。
重阳节,亦称重九节。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称,古人以九为阳数,“日月并应,俗嘉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燕高”[18](卷34)。旧时重阳日登高宴饮,同时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晋代《西京杂记》卷三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19](卷3,P20)《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10](P60)至宋代,人们开始饮用茱萸酒以辟邪消厄,《梦粱录》卷五《九月》记载:“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20](卷5,P164)宋人诗词中同样保留大量茱萸酒的嘉言丽句,如谢薖《虞美人·答金钗尽醉何须伴》“萸糁浮杯乱”[21];周紫芝《九日竹坡昼睡二首·其一》“紫萸香度酒杯空,分付重阳一枕中”[22](卷31);韩淲《玉田道中得诗二句因足之》“萸糁人家皆取醉,菊花篱槛亦争妍”[23](卷11)等。
众所周知,佛教戒律严禁饮酒,因此如何在节庆中既合世俗,又不突破戒律,成为宋元僧人思考的重要议题。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云:“此日饮菖蒲酒,僧家以茶代之,准世礼也。”[24](卷25,P675)由此可知,宋僧以茶代酒欢度节日,因时制宜,既不触犯佛教戒律,又不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抵牾,维护了教团与世俗社会的和谐。以茶代酒,遵循了儒家的礼法精神的同时秉承了怀海禅师倡导的“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25](卷6,P251)的原则。宋代僧人语录中,了堂惟一提出端午节世俗百姓欢饮共庆,僧人当然也要懂得时序更迭,“灰头土面衲僧家, 无端也要知时序”[26](卷1,P899)。了庵清欲提倡万物随时,以茱萸茶代替菊花酒,“今朝九月九,万物随时候。满泛茱萸茶,何用菊花酒”[27](卷三,P654)。 南石文琸认为虽然僧众以茶代酒,但是风流更胜一筹:“是处人家悬艾虎,灵岩但吃菖蒲茶。莫言淡薄无滋味,毕竟风流出当家。”[28](卷1,P381)
(二)预防瘴疠,养生健体
菖蒲,又名“白蒲”“石菖蒲”,根茎可入药,有健胃强身、理气活血、散风祛湿的功效。《圣济总录纂要》记载了菖蒲丸以及石菖蒲丸的具体药效。食用菖蒲,据说可以延年益寿,保持青春,如李白《嵩山采菖蒲者》言“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29](卷25,P1162);张籍《寄菖蒲》言“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头青面如雪”[30](卷7,P834)。菖蒲味道甘辛,《摩诃止观》中称“如服菖蒲,将得药力而多瞋”[31](卷9,P119), 因此在僧人日常生活中被禁止食用。但《十诵律》规定:“尽形药者,五种根药。何等五种?一舍利、二姜、三附子、四波提毘沙、五菖蒲根,是药尽形寿共房宿无罪。”[32](卷26,P194)菖蒲根被定为五种根药之一,指代因病可随时食用的药物。禅僧将菖蒲以药物形式加入茶饮,既遵从了菖蒲的药性,同时饱含了希望蠲除疾病、祈求邪气不侵的愿望,如希叟绍昙认为菖蒲茶虽然“嗅着鼻头辛,咬得牙关肿”,但“佛病祖病蠲除,妖星怪星惊悚”[33](卷3,P225);再如恕中无愠提出“共啜菖蒲茶,无限馨香生颊舌。百病消除,千妖殄灭”[34](卷1,P815)。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具有温中理气、止痛除湿的功效。历史上,长江流域多瘴疠之气,当地人以茱萸入茶同煎,防御瘴疠。如李复《潏水集》卷六《夔州药记》载“人无老幼,不问冬夏,饮茱萸茶一两杯,以御山气”[35](卷6);陆游《荆州歌》云“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36](卷19,P1480);元代曹伯启《舟至常德出陆由辰抵沅书事三首·其二》道:“囊无薏苡防私论,茶有茱萸敌瘴烟。”[37](卷5)三峡附近的居民也靠饮用茱萸茶抵御蚯蚓瘴,如项安世《茱萸茶》言:“峡中有蚯蚓瘴,饮此茶御之”,“城郭千山隘,晨昏二气并。乍如水底宿,忽似甑中行。蚯蚓方雄长,茱萸可捍城。龙团宁小忍,异味且同倾”[38](卷3)。又如邢凯《坦斋通编》提及“夔门有曲鳝瘴,以茱萸煎茶,饮之良愈,谓之辣茶”[39]。再如,范成大《入秭归界》云:“蚯蚓祟人能作瘴,茱萸随俗强煎茶。”[40](卷16)在今广西一带,当地人在煎茶时亦加入茱萸,饮用后身热出汗,可有效缓解瘴疠导致的疾病。如元代陈孚《邕州》诗中便提到“驿吏煎茶茱萸浓,槟榔口吐猩血红。飒然毛窍汗为雨,病骨似觉收奇功”[41];南宋赵蕃《早过兴福寺》诗云“僧劝茱萸饮,身能瘴疠祛”[42](卷8),说明地方僧人早已知晓茱萸茶有抵御瘴疠的功效。
由次页附表可知,饮用菖蒲茶、茱萸茶的禅师大多来自今江浙、江西地区。端午节、重阳节正值季节更迭之时,饮用菖蒲茶、茱萸茶主要是为了缓解瘴疠,强身健体。菖蒲、茱萸并非珍稀药材,在南方是常见之物,宋元禅师有关菖蒲茶、茱萸茶的偈颂中大量引用“文殊令善财采药”“杜顺灸猪左膊”的公案,突出菖蒲、茱萸药效的同时,更旨在揭示世间万物重在如何应用,不要拘泥于因果逻辑而忽略事物普遍的联系性。宋元禅师将医病疗愈与开示顿悟联系起来,因时说法,更具禅意。比如月磵和尚言:“佛病祖病,正在膏肓。文殊是药采将来,都用不着。杜顺灸猪左膊上,亦错商量。东湖水点菖蒲茶。”[43](卷1,P1048)天目文礼上堂说法云:“山中药草信手拈来,举拂子云:见么,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其或未然,菖蒲浮苦茗,角黍腻人牙。”[44](卷40,P762)无门慧开说道:“善财能采,文殊解用。虽然眼辨手亲,检点将来漏逗不少。焦山今日终不效他先圣,只是各人喫一杯菖蒲茶。任是贪病、嗔病、痴病、身病、心病、佛病、祖病,一时顿愈。虽然如是,知恩者少,负恩者多。”[45](卷上,P510)希叟和尚言:“苦涩菖蒲茶,胶黏青蒻粽……善才采药,扬在壁根;天师书符,抗藏衣笼。”[33](卷3,P225)恕中无愠道:“文殊令善财采药,善财拈草度与文殊,石上栽华。文殊接得示众云: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34](卷1,P815)
三、宋元禅寺菖蒲茶、茱萸茶的饮用形式
(一)点饮或煮饮
通过分析宋元禅师偈颂,可以发现,菖蒲茶、茱萸茶的饮用形式复杂多样,尤以点饮法最为普遍。宋代多种饮茶方式并存的局面在蔡襄《茶录》之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②。南宋之后,禅寺中多以点茶的形式冲点茶汤,该法既可以增加茶饮风味,又可增添茶汤的白腻之色。如“茭粽叶包蒸米饭,埜山茶点石菖蒲”[46](P173),“箨包角黍,茶点菖蒲”[33](卷2,P214),“蒻包粳米粽, 茶点石菖蒲”[33](卷3,P235),便是将菖蒲与茶叶碾碎后注汤击沸点饮。另外,还可以在茶中加入菖蒲煮饮。如率庵梵琮“却把山茶,以替竹叶。角黍满盘,菖蒲细切”[47](P110);了庵清欲“细切菖蒲泛酽茶”[27](卷2,P625);千岩元长禅师“今朝端午节……擎出一杯茶,满泛菖蒲玉”[44](卷40,P760)等,描写的便是将菖蒲切碎投入茶汤之中共同煮饮。不过,煮饮前只是将茶饼与菖蒲碾成茶末,末如点茶时会过罗细筛,因此植物颗粒并不像粉末一般细碎,饮茶时会将其咬破,正如双杉元禅师所言:“今朝依旧点盏茶与伊湿口,蓦然咬破菖蒲。出身冷汗,失声道哑。”[48](卷下,P180)
有关茱萸茶的味道,如无准师范“苦苦涩涩茱萸茶”[49](卷1,P862);西岩了惠“始信茱萸茶苦涩,展眉人少皱眉多”[50](卷上,P351);希叟绍昙“不向东篱赏菊花,只点茱萸茶一啜。苦涩难尝舌如絶努,更吞栗棘蓬肝肠裂”[33](卷3,P236)所言,茱萸茶味道苦涩,但饮用后会周身发汗,通体舒畅,“香浮毛孔,清透肌肤”[33](卷2,P214)。虽然菖蒲茶味道单薄,但在宋元僧人的眼中,茶饮所带来的感观体验,远不及人情心暖给予人们的情感依托,千岩元长以及愚庵智及巧妙地引用释妙伦的经典偈颂说道:“擎出一杯茶,满泛菖蒲玉。且道成得甚么事。人情若好,吃水也甜”[44](卷40,P760);“潦倒径山无法说,大家喫盏菖蒲茶。一般滋味休分别,分别则任汝诸人。且道毕竟是何滋味,良久云:人情若好,吃水也肥”[44](卷40,P762)。
(二)配食粽子
端午节食用粽子是传统习俗,“陈元靓《岁时广记》二十一引《岁时杂记》:端五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51](P204)。宋元寺院内端午节饮用菖蒲茶时也会配合食用各式各样的粽子,如兜率从悦“一盏菖蒲茶,数个沙糖粽”[1](卷25,P333);希叟绍昙“大家相聚喫盏菖蒲茶, 几枚茭粽子”[33](卷2,P207),“茭粽叶包蒸米饭, 埜山茶点石菖蒲”[46](P173),“苦涩菖蒲茶,胶粘青蒻粽”[33](卷3,P225),“箨包角黍,茶点菖蒲”[33](卷2,P214),“蒻包粳米粽,茶点石菖蒲”[33](卷3,P235);双杉元“吃着三角粽子,便道是端午”[48](卷下,P180);唯庵松隐“黄米粽吃一钵,菖蒲茶吃半瓯”[44](卷40,P760);天目文礼“菖蒲浮苦茗,角黍腻人牙”[44](卷40,P762);环溪惟一“蒲饮先春雪,粽餐明月珠”[52](卷上,P106)等,可知宋元寺院内粽子式样繁多,粽叶、形制、馅料各不相同,有茭粽、青蒻粽、角粽、三角粽、粳米粽、黄米粽、砂糖粽等。
宋元时期,江浙一带重阳节会食用栗粽,如《(绍定)吴郡志》记载,“重九以菊花、茱萸尝新酒,食栗粽、花糕”[53](卷2);《(嘉泰)会稽志》记载,“重九亦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54](卷13)。江浙寺院内也因时因地制宜,重阳节在饮用茱萸茶的同时配合食用黄栗粽,如无准师范住持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时上堂言“胶胶黏黏黄栗粽,苦苦涩涩茱萸茶”[49](卷1,P862);西岩了惠住持瑞岩山开善禅寺时亦云“一十二峰黄栗粽,东大洋海茱萸茶”[50](卷上,P353)。
四、余论
茶中添加其他植物或调味品共同煮饮的方式由来已久,陆羽在《茶经》中提倡单煮茶茗,推崇保留茶的自然真香,“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55](卷下,P97)。直到宋代,点茶法流行,清饮遂成为饮茶的主要形式。然而,宋代禅寺却开始在端午节、重阳节饮用菖蒲茶、茱萸茶,元代被收入《敕修百丈清规》,令天下僧人共同遵行,由一种地方习俗演变为全国性准则。寺院内节庆饮茶,成为宋元时期独特的文化场景。宋元僧人以茶代酒,准于世礼,共同庆祝中华传统节日,反映了佛教徒希望消弭灾祸、祈求健康顺遂的美好意愿,可谓宋元僧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言,“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中国化”[56](P74)。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方面带来了新知识,形成了新节日,如腊八节、盂兰盆节等;另一方面,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接受中土文化,调适相似,改造自身,以求更好地与中华传统文化融摄交会。重阳日,除饮用茱萸茶,宋元僧人还会登高赏菊,如剑关子益言“登高双眼空,独步乾坤窄。只手未曾举,黄菊已盈握。好彩从来奔龊家,随分一盏茱萸茶”[57](P85);又如平石如砥云“茱萸满泛一瓯茶,冷淡家风亦自佳。不用登临追往事,眼前随分有黄花”[58](P386)。
宋元僧人饮用菖蒲茶、茱萸茶,也逐渐影响到宋元文人的饮茶习俗。如宋祁《答朱彭州惠茶长句》云:“饮萸闻药录,奴酪笑伧人。”[59](卷20)其中“饮萸闻药录”注“《本草》:茗以茱萸饮佳”。上文提到的赵蕃老年患病后仍怀念茱萸茶,在《初二日蚤发亲捷》说道:“颇忆茱萸饮,还思薏苡赉。异乡逢物色,老病益清羸。”[42](卷8)元末明初刘崧在《九月八日述怀》中感叹“清尊久覆无烦问,拟折茱萸试煮茶”。
通过考察宋元禅寺内饮用菖蒲茶、茱萸茶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重阳节已经深刻影响到寺院僧人的日常生活。佛教与中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感染与认同,共同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影响并改造着中原文化,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中原文化也在影响着佛教文化,佛教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中土文化,不仅逐渐消弭了儒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为自己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禅宗产生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了新的高度,宋元时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原因即在于此。极具创造性、包容性、开放性的多元一体、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附表:
注释:
①参见朱瑞熙等著《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1998年版,第423页;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2页。
②参见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