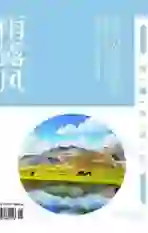祖殇
2021-08-09辛春喜


生、老、病、死,笔画如此简单的四个字,却概括了人的一生。我们不得不佩服于中华文字的神奇。其实,这四个字也在警醒着我们,做人其实要简单些,不要有过多的繁杂。
人到中年,不得不开始面临与祖上的生离死别,我们前面那生命的大山少了一座又一座。在我的脑海里,祖父去世时的印象已经全无,就像灰茫茫的一片晨雾里,无论心里多么想看清,可那永远是个模糊的影子。有时伸手去抓,抓到的只是一把晶莹的眼泪。
不过与外祖父、祖母离别的那段日子,抑或片刻,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内心。不管过去多久,他们紧闭双眼的脸庞,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于是,那人世间的亲情冷暖,犹如那一丝丝水波,在面前荡漾、荡漾。
外祖父过世的日子太清晰,那是我高考的年份——1997年。这一年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亲人外祖父的离开,还有邓小平爷爷的远去,喜的是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因为经历的大喜大悲太多,那年的高考发挥得不甚理想。
外祖父过世的那天天气还很冷,我穿着厚厚的毛线衫。我没有住宿,所以放学后仍然回家。高三放学比较晚,我骑行半个多小时后到家,天色已经快暗了。记得那天打着车铃一路转弯进了家里院子,等候在大门口的母亲就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快点吃饭,吃好了马上去外祖父家。母亲遇事向来镇定,我看她这样子感到奇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说,外祖父身体抱恙,村喇叭里都在喊,让子女们快点去看看。母亲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说,小阿姨、大阿姨她们都已经去了,姨父们与父亲也赶去了,母亲怕我回家一个人也不见会担心,所以就留了下来。
因为事情紧急,我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说吃饱了,便与母亲出了门。那时没有汽车、摩托车啥的,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也载不动肥胖的母亲,所以两人就步行前往。一个年轻气盛,一个中年体健,而且都挂念着外祖父的病情,所以我们的脚下都像生了风一样。夜色已经降临,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犬吠,那15瓦的灯光映射出来的光芒有些吓人。不久前刚下过大雨,泥路上还有一些深深的脚印,现在干了,留下了坑,我们走得快,几乎都不看脚下的路,好几次差点崴了脚。快到外祖父家的时候,我们小跑起来。跨进大门时,我们都气喘吁吁,额头上冒出汗来。
舅舅家造了楼房,时间不长,估计没啥余钱,房子也没有装修。那简单粉刷的墙壁有些角落已经发黑,估计是受了雨气受潮发霉。灯光昏暗,那时连瓦数高一点的灯都不舍得,为的就是节电。外祖父睡在底楼最西面那一间,上楼要经过他的这间房门。我走近房门,里面黑压压一大片,到处都是人。阿姨们、姨父们、表哥表嫂们,或站或坐,挤满了一间房。几个男人在聊天,女人们在哭泣,母亲进了房间,叫了一声“阿爸”,我则叫了一声“大大”,外祖父的眼皮动了一下,嘴里轻声吭了一下,示意听到了我们的话。
外祖父睡的床是老式旧床,蚊帐还没有拿下来,帐子也黑黑的,是老式的麻布做的。天还冷,穿的衣服都是深色的,这屋子里就更黑了。外祖父半躺着,看不清他的真实脸色,他正在挂水,盐水慢慢地经过筋脉渗入到他的血液里。不知是谁坐在他的床沿上,一个劲地抚着他的手。村里的医生坐在一边,阿姨们正在问他要不要送医院去,他模糊地应答着,叫阿姨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送还是不送。
我退出了屋子,那里太压抑了,我快喘不过气来。在这一屋子人里,我的辈分最小,外祖父该怎么治疗,没有我说话的份。我走到前屋,看到舅舅他们正在厨房里说着什么,大概的意思是说,这是外祖父气喘的老毛病了,挂点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以前也发作过。后来我又知道,那天下午,外祖父简单吃了午饭后,去村部的活动室搓麻将。在搓了一个多小时后,突然晕倒在桌子上。所以,村里工作人员用喇叭喊外祖父的子女快点来,当时最近的小阿姨夫妇第一个到了现场,将外祖父背回了家里,再请了村里医生来医治。
大人们一直在聊天商量,要不要将外祖父送医院。外祖母后来发了话,说不用送出去,就在家里好了。她说这话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是听天由命的无奈,还是重回健康的信心。于是,所有人都有了台阶,都说观察一下再说。
因为我第二天還要上学,而且要迎接人生最重要的高考,所以母亲就陪着我回家了。一路上,母亲对我说,舅舅在做保安,舅妈也在厂里,都是打工的,收入不多,家里经济压力大,所以都不敢提出送医院去。当时我想回驳母亲,你是大女儿,你应该做主的,治疗费用我们家可以出。但最终,我还是息了口。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看书,但脑子里只有外祖父的影子。我不知道躺在那黑黑的床上的外祖父,此时是否好了一些;明天的阳光,是否依然能照耀在外祖父的身上;乐观的外祖父,是否还能呼吸到第二天的新鲜空气……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呼喊声:“寄爸(干妈)、寄爸!”这叫声急促不已,是表哥的声音,一听这语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母亲猛地奔到阳台上,急呼而出:“明官(表哥小名),阿爸怎么啦?”“大大走啦!他们叫您快去!”母亲听到这话,一下子愣了两三秒,突然大哭起来:“我苦命的阿爸呀!”她滚也似地冲下楼梯,跟着表哥走了。
我就这样静静地靠在床上,心里突然无比宁静,但眼泪却偷偷地溜了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也不知道母亲是何时回家的,依稀在睡梦里,听到母亲轻轻的哭声,这哭声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响起。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晚我们离开后,外祖父突然要拔针头,可女婿们不同意,还把他的手系在床沿上。外祖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无法再救他了”,随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大阿姨发现盐水没有滴下去的痕迹,一探外祖父的鼻息,才发现外祖父已经去世了。这样算来,我们只是走到半路,外祖父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来送我们回家。
外祖父走了,出殡那天,我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昏倒了过去,父亲也因此没有去殡仪馆,留在舅舅家里照顾我。等我醒来时,听着身边人关切地说着“没事了,没事了”,我木然地看着眼前人,心里酸痛不已:我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外祖父了。
我心里是一直埋怨母亲的,怪她没有做主送外祖父去医院。如果到了医院,外祖父应该不会离世,因为他只是气喘罢了。“他当时看到我来了,心里肯定想没事了,会送他去医院的。当他看到我们离开时,他就知道没有希望了。”母親一直很内疚,但内疚有用吗?
祖母身体健朗,从不生病。在我印象里,我甚至没看到过她吃药。姑妈们说,那是祖父把自己的健康留给了祖母,所以小辈们才这么省心,不用为她的身体担忧。
说实话,我们姐弟与祖母的关系并不亲厚,这其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祖母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却在父亲结婚后,毅然与父亲分了家,自己与未出阁的几个女儿住一边屋子。从我们懂事起,我们就在吃好晚饭后绕个圈子回前屋睡觉,遇到刮风下雨,还必须打伞才行。后来父亲在正屋那开了个后门,我们才少走了一段弯路。后来姑妈们出嫁的出嫁,回城的回城,祖母也经常在城里帮姑妈们带孩子,回家的时间非常少,我们难得见到。没有交流的亲情,很容易湮没在隔阂的长河里。直到外孙们都成年长大,祖母年事渐长,她才回乡下家里来定居。可她脾气很犟,拒绝了我们邀请她同吃一桌,仍然独自一人烧饭起居。日子久了,我们也习惯了。
我工作结婚之后,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虽然离老家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路程,也难得回家。特别是母亲来到城里跟我们居住,帮我们带女儿后,回家的次数更是少得很。这也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生活的常态。父亲不愿意进城居住,还要耕耘着几亩田地,同时照看着年老的祖母。我们逢年过节回去,都会请祖母一起吃饭,祖母没有拒绝,跟我们一起吃着饭,聊着天。
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祖母到底是老了,后来因为摔了一跤,养好腿后就拄了拐杖。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的行走,屋后大路上时常看到她的身影。居住在不远的姐姐说,每天都会看到祖母出来散步,心里也就放心了些。姐姐还说,祖母会到她那儿去坐坐,陪她聊天,劝姐姐不要做得太劳累,否则年纪大了吃亏的还是自己。祖母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和,神情慈祥,就像《知否》里的祖母。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涌起伤感,看来人之将老,其行也善,这话真的不假。
在八年前的清明节前夕,祖母突然病倒了,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连忙问祖母的病情,母亲说,应该是受凉了,感冒了。现在每天由中姑妈从市区配好盐水拿来,再请乡村医生来挂。“那些盐水都挺好的,应该问题不大。”听到母亲这样说,我也放下了心。确实,清明时节气温变化大,年纪大了感冒也是正常的,相信过不了多久,祖母就会恢复健康的。
清明节那天,按惯例,姑妈们都会回来,给去世30多年的祖父上坟。我也会在这一天回去,我除了做菜,也要一起上坟。那天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烧猪蹄,我一进屋就问祖母怎么样了。母亲说,昨天回来时给祖母送了饭,吃得还可以。我稍微放下了心,便去祖母的屋子看看。
我一边进屋,一边叫着“亲妈”,这是我们当地对祖母的称呼。我连叫了两声,并没有听到祖母的回复。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房间,看到一碗面条掉在地上,碗已经碎了,面条也已经干了,祖母则躺在床上不说话。她闭着眼睛,神情十分疲惫,一阵子不见,想不到祖母竟然憔悴如斯。我再次呼唤着,祖母终于微微睁开了眼睛,看到我之后,原本暗淡无光的眼里发出了一丝光亮。她轻轻叫了我的名字,我一个劲地点头,眼泪都快到流下来。“亲妈,这些面条是你打翻的吗?你是不是饿了?”我急切地问。可祖母含糊不清,不知道说些什么。
祖母病得太严重了,不送医院怎么行?我飞快跑到厨房,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对她说,祖母一定要送医院,否则要出事。母亲说,送就送吧,不过姑妈们马上要来了,让他们一起商量下。
我来到屋后,在蔬菜大棚里找到了父亲。我对父亲说,祖母应该马上送医院,否则后果严重。正在这时,居住在城里的中姑妈与小姑妈来了,我也说了自己的想法。两位姑妈一听我的话,当即说好,请父亲在三轮车上铺上被子,立即送祖母去医院。
我又来到了祖母的屋子里,凑在她耳边说:“亲妈,我们送你去医院看病好吗?”祖母听了顿时有了劲,拉着我的手指指衣服口袋,似乎想说什么。后来姑妈告诉说,祖母是想说里面还有2000元。从这可以看出,祖母其实很想去医院看病,只是没有子女们提出,她无力也无法提出来。
父亲与姑妈们火急火燎地将祖母送到了医院。母亲说,我是晚辈,这事让父亲与姑妈们去处理,到医院就不要紧了。我与母亲则在家里先把清明祭祀的一些事做好。哪知过了没多久,中姑妈打电话来说,祖母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已经插上了管子。“医生建议的,说里面痰太多,要插管吸出来,而这也是祖母自己同意的。”中姑妈说。
一位已经89岁的老太太插管进重症监护室,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天,轮到我探视时,无论我如何呼唤,她都在沉睡之中。护士告诉我,给老人上了安定,否则她的手要乱动。护士还安慰我,祖母其他体征都不错,尽可放心。
但我出来后,我提出让祖母出重症监护室,我怕祖母对呼吸机有依赖,以后反而会害了她。姑妈们与父亲很为难,此时子女一多,谁都不敢做主了,因为谁提出来转普通病房,谁就会被套上“担心重症监护室费用太高”的帽子。所以,家境并不好的他们,只能硬撑着,今天你拿两三千交进去,明天我拿两三千维持。谁也不知道,这个无底洞到底要填到什么时候。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是多么地矛盾。
我后来再也没有进重症监护室去探望祖母,母亲一次也没有进去过。姑妈们说,探视时间太短,还是让他们进去好了。于是,所有的信息也都是小姑妈传达的,一会儿说病菌查到了,可以对症下药了;一会儿说已经有起色了。但没想到第六天的时候,医院突然通知出院——这样还能留一口气到家里。
这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因为治疗费用的事大家都有些不开心,但还是一直怀着希望。事实确实是,祖母在氧气泵的辅助下,把最后一口气留到了家里。当她躺到床上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咽下,手臂上的盐水也渐渐滴不进去了。
我抚摸着祖母的脸,依然留有余温,皮肤光滑,脸色犹如一个婴孩。哭声开始在耳边响起,家里人一边清理着房间,一边哭泣,大家乱作了一团。
我安静地坐在床沿上,盯着这位陌生又熟悉的老人。我不知道她的灵魂是否已经远去,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有最后的意识听得到周边的哭声,我只知道,随着哭声的响起,大家心头最重的那块石头成了齑粉,飘然而去了。
外祖母是遠近闻名的巧手,一双巧手会养蚕,会针线,特别是会剪花。一张红纸拿在手里,一把剪刀在红纸间游走,很快便剪出了一朵朵形态逼真的花。这些花的样子在外祖母的心里,无论何时,只要给她红纸与剪刀,她都能随意剪出大小一样的花来。这就是她的神奇之处,也是文化工作者的佩服之处。正因此,外祖母上过央视四套——过了十多年,她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央视编导拍摄时的情景。
外祖母的身体也一向硬朗,在我印象里,她只去过一次医院。那时,舅舅家已经拆迁,经济条件好了许多,外祖母自己也有了养老金,一个月有1000多元。对于从不出门的乡下老太太来说,这些钱根本花不掉,也一直由舅舅保管。因为有了外祖父的前车之鉴,舅舅他们对外祖母的身体状况也更加重视,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医院送。那天我正在上班,舅舅打电话来,说是外祖母身体有些不适,我马上叫车把她接到市区医院医治,母亲与阿姨们全部来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外祖母只是有些受寒,并没什么大碍,所以挂了盐水就回家了。果然,外祖母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邻里之间又看到她步履矫健的身影。
祖母去世的时候,外祖母还来相送,她心情很差,直说没想到亲家走在了她的前头。众人相劝,生死无常,谁先谁后又没人规定,自己保重身体就好。外祖母的身体倒一直挺好,快九十岁的人了,连感冒也没有了,子女们都觉得挺幸福。就在她发病的前一个月,我还特地跑到外祖母家去看她,请她剪一些花样出来,说是为她举办一个手工展览。外祖母听了十分高兴,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她就拿起来剪几朵花,有几朵还特别大,舅舅说她剪的时候手都有些发抖。看来,年龄毕竟是大了,剪大花对她而言是件累活了。
这些也都是后来听说的,我由此觉得十分内疚,怀疑是让外祖母剪花而发病的。不过医生告诉我,外祖母得的是尿毒症,跟剪花啥的没有任何关系,我这才稍感安慰。只记得那天母亲对我说,舅舅说外祖母最近记性很差,有时还胡乱说话,说过什么很快就忘记了,小腿也有些肿,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听了就与舅舅联系,确定要送医院后,我马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外祖母家里。
外祖母已经准备妥当,她也希望到医院去看看。她梳着一个小小的发髻,头发挼得整齐,衣服也穿得妥帖,她仍然把自己穿戴得十分利落。这哪像是去医院看病,这分明是要去走亲戚。外祖母有一个孙子,在广州读硕士,另外两个外孙也在其他城市,只有我留在当地,这也成了她的一个依靠。只要一声呼唤,我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尽力帮她解决问题。所以,她看到我来了,就很是放心,坦然地上车,我们全都去了医院。
医院是认识的朋友开的,服务不错。外祖母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们想着住院输液,就当作疗养好了,因此心情也都十分放松。哪知第二天下午,我正上班,母亲打电话来,急促地对说我,你知道亲亲(外祖母的称呼)得了什么病吗?估计没法救了!母亲都快哭出来了。我还不信,精神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一入院就不行了呢?母亲接着说,外祖母得的是尿毒症,已经是晚期了。一听尿毒症,我也一时惊呆了,这确实是很危险的病了,更何况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但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对母亲说,尿毒症还有医治的办法,那就是透析,你对舅舅说,无论多少医药费,我们都可以分摊,让他不要有压力。
外祖母得尿毒症的事所有子女都知道了,大家商量着怎么治疗。医生说,依外祖母目前的状况,只有透析能续命,否则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没命。那要不要透析?子女们的意见又不统一,大家都有着各自的顾虑。最后,我对舅舅说,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的意见吧。舅舅同意了,我们一起来到了治疗尿毒症的权威专家那里。这位专家分析了情况,他也说只有透析一条路,但这么大的年龄是否会有风险,他也不能保证。
舅舅开始是同意透析的,子女们开始算治疗的费用,因为有养老金,所以后续每月的透析也花不了多少钱,子女们都能承受。只是大家还有一点顾虑,万一外祖母瘫痪在床怎么办?后续谁来照顾?有人甚至对母亲说,就由母亲来照顾,他们给母亲工资。母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照顾母亲是自己的责任,不要他们一分钱。
但是,只隔了一个晚上,舅舅就放弃了给外祖母透析的决定,他自己也突然痛风发作,自顾而不暇。没有舅舅的决定,出嫁的女儿没有一个站出来,有人甚至快要打退堂鼓了。我也只能干着急,但我只是一个外孙,我又能做什么重大决定呢?
外祖母开始自己拔针头,这与外祖父去世前的举动一模一样。陪夜的女儿们不让她拔,她便开始大骂起来。外祖母出身大家,自幼庭训,从来没有骂过自己的子女,这反常的行为让女儿们泪流不止。没有人知道外祖母此时的想法,她健康时曾经对母亲说过,她在去世前会把自己的一些不顺告诉母亲,但最终,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只说,子女们之间一定要团结。
没有做透析,留在医院也是无用,盐水挂下去,肚子就要涨起来。最后,子女们决定接外祖母回家。我没有亲自接外祖母回去,我只是联系好了车子。我不忍心看到这凄凉的一幕,因为这次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送出来了。
只过了两天,我们就接到了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当时陪同在床边的小阿姨说,外祖母一直在等孙子回来,她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这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从来没有叫过名字,一口一个“金宝囝”“银宝囝”地叫。可是,当她听到孙子不会回来时,她再也没有了期盼,一口气吐出来,就此离开。后来孙子的哭泣,不知道外祖母听到了没有。
三位祖上已经离去多年,但他们的离世,我始终有些不舍。或许,如果晚辈们再努力些,他们可能还会有更长的生命,能够看到子女们日益幸福的生活,最起码能够喝到外孙们的喜酒。这应该是他们完整的人生,否则就有缺憾。
祖上的事,我毕竟做不了主。但父母这辈的事,我是能做主的。只要他们在,我依然是孩子,还属于自己的青年。
作者简介:辛春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平湖市作家协会理会,《南湖晚报平湖周刊》主编,在《散文选刊》(原创版)、《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参花》、《海外文摘》、《名家名作》等发表散文作品,出版纪实文学《铭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