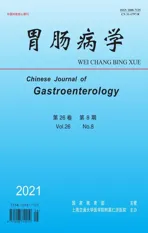重症溃疡性结肠炎合并急性心肌梗死1例并文献复习
2021-07-06毛宇娟
毛宇娟 叶 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消化内科(430071)
病例:患者男性,41岁,因“反复腹痛、腹泻伴黏液脓血便3年余,加重1个月”于2020-08-12收治入院。患者于2018年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确诊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广泛结肠型),规律口服美沙拉嗪治疗并门诊随诊,病情间断复发,2018年和2019年结肠镜检查均提示广泛结肠病变(横结肠至直肠),Mayo内镜评分2分。本次入院前近1个月腹痛加重,每天解稀糊状黏液脓血便7~8次。
既往史:2018-06-21因ST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行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左前降支近段闭塞,左旋支中段狭窄60%,右冠状动脉近中段狭窄20%,远段狭窄30%,左室后支开口狭窄50%,于左前降支行支架植入(图1),术后规律抗血小板和调脂治疗。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烟酒史和心血管疾病家族史。

LAD:左前降支;LCX:左旋支图1 2018-06-21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前降支近段闭塞, 左旋支中段狭窄60%
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4 ℃,脉搏100 次/min,呼吸18次/min,血压126/82 mm Hg(1 mm Hg=0.133 kPa);神清,精神欠佳,面色苍白;心、肺无异常;腹软,左下腹压痛,无反跳痛,全腹未及包块。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2.12×109/L(↑),血红蛋白122.3 g/L(↓),血小板计数353×109/L(↑),红细胞沉降率(ESR)25 mm/h(↑),C反应蛋白(CRP)104.0 mg/L(↑);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PT)13.9 s(↑),凝血酶原时间活动度(PTA)67%(↓),纤维蛋白原(FIB-C)5.02 g/L(↑),D-二聚体608 ng/mL(↑);EB病毒DNA阳性;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实验阴性;心肌酶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结肠镜检查示直肠至横结肠黏膜弥漫性、连续性充血水肿、糜烂、溃疡形成(图2)。入院诊断:UC(慢性复发型,广泛结肠型,活动期,重度),UC Sutherland疾病活动指数(UCDAI)12分。予氢化可的松300 mg/d静脉滴注,美沙拉嗪4 g/d口服,腹痛减轻,糊状便6~7次/d,时有便中带血,复查CRP 37.0 mg/L(较前下降),UCDAI评分10分。1周后激素改为口服泼尼松50 mg/d,继续口服美沙拉嗪4 g/d,拟2020-08-22出院。

A:回盲部;B:横结肠;C:乙状结肠;D:直肠图2 2020-08-11结肠镜检查示直肠至横结肠黏膜弥漫性、连续性充血水肿、糜烂、溃疡形成(Mayo内镜评分3分)
2020-08-22凌晨3时,患者突发心前区隐痛,伴大汗淋漓、胸闷,急查心电图示窦性心律不齐,Ⅱ、Ⅲ、avF导联ST-T改变(图3)。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16.80×109/L(↑),中性粒细胞85.2%(↑),血红蛋白102 g/L(↓),CRP 52.6 mg/L(↑),D-二聚体992 ng/mL(↑);心肌酶:肌酸激酶(CK)640 U/L(↑),CK同工酶(CK-MB)55 U/L(↑),肌钙蛋白Ⅰ(TnⅠ)391.4 pg/mL(↑),2 h后复查TnⅠ1 807.3 pg/mL(为之前数倍)。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左心扩大,左室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考虑后间隔和左室下壁AMI。

图3 2020-08-22 4∶52 a.m.心电图检查示Ⅱ、Ⅲ、avF导联ST-T改变,考虑下壁AMI
患者发生AMI后1 h便血明显加重,每1~2 h一次,鲜血便,无明显粪质,与心内科沟通后认为急诊冠状动脉造影+必要时支架植入术存在出血和血栓栓塞双重风险,且溶栓或抗凝可加重出血,建议药物保守治疗。予扩冠(硝酸甘油10 mg, 2 mL/h持续泵入)、调脂稳定斑块(阿托伐他汀20 mg qn)、控制心率(酒石酸美托洛尔47.5 mg qd)等处理,患者胸闷、胸痛症状减轻,复查TnⅠ下降;心电图Ⅱ、Ⅲ、avF导联ST段回落至正常。心肌梗死急性期仍予口服泼尼松50 mg/d,因便血加重,病情稳定后于2020-08-26再次静脉应用氢化可的松300 mg/d,但症状改善不明显,UCDAI评分12分。2020-08-28转换为英夫利西单抗治疗(类克®,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5 mg/kg,患者体质量70 kg,400 mg静脉滴注),临床应答不明显;2020-09-01予强化治疗(10 mg/kg,700 mg静脉滴注)。强化治疗后血便较前明显减轻(7~8次/d),2020-09-09静脉激素改为口服泼尼松 50 mg/d,2020-09-12予出院。2周后复诊,无腹痛,软便2次/d,无黏液血便;复查CRP 0.42 mg/L,ESR 12 mm/h,予第3次英夫利西单抗700 mg静脉滴注。泼尼松自出院起足量50 mg/d口服1个月,之后逐渐减量至停用。继续英夫利西单抗(700 mg静脉滴注)每8周一次维持治疗。出院6个月后复查结肠镜,UCDAI评分1分,UC维持缓解,无胸闷、胸痛症状。
讨论:UC属于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典型临床症状为腹痛和黏液血便,病情多呈复发与缓解交替。冠状动脉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原因。AMI具有起病急、病情复杂、进展快、病死率高等特点,是CAD中的严重类型。目前已有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被证实与CAD相关,然而IBD与CAD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CRP和同型半胱氨酸(Hcy)作为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在IBD患者中亦明显升高[1-3]。此外,IBD患者存在系统性炎症反应,白细胞介素-1(IL-1)、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可能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功能障碍,进而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研究表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动脉僵硬度[以颈动脉-股动脉脉波速度(PWV)等参数反映]等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标志物在IBD患者中较对照者显著增高[4]。活动期IBD患者处于血栓前状态,表现为血小板和组织因子(凝血因子Ⅲ)增多,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降低,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增高,导致纤溶功能受损,血栓形成风险增加[5]。一项meta分析表明IBD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VTE)风险约为非IBD患者的2倍,以UC患者为著,60%~80%的血栓栓塞事件发生于活动期[6]。Kaiko等[7]的研究发现活动期IBD患者肠黏膜PAI-1表达显著上调,通过阻断tPa介导的抗炎细胞因子活化促进结肠炎症进展,而PAI-1基因多态性已被证实与CAD易感性相关[8]。此外,短链脂肪酸(SCFAs)被认为参与了IBD的发生机制,IBD患者肠黏膜和粪便中SCFAs含量降低[9];同时,SCFAs可通过预防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对心血管疾病发挥一定保护作用[10-11]。上述研究均提示了IBD与CAD之间的联系。来自丹麦的全国性队列研究发现,IBD患者的AMI风险高于一般人群,以活动期患者为著[12];IBD确诊后第一年的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风险增加约2倍[13]。Kristensen等[14]对首次发生AMI的住院患者的调查显示,IBD活动期患者的AMI复发风险亦较非IBD患者显著增加。Choi等[15]在韩国开展的全国性队列研究显示,克罗恩病患者的AMI风险约为非IBD患者的2倍,以年龄<40岁者和女性为著;但UC患者仅女性表现为AMI风险增加。近期国内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16]发现,18~35岁的年轻IBD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IHD风险增加更为显著。
本例患者无传统心血管相关高危因素,于UC确诊后约6个月出现急性胸痛,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左前降支闭塞并行支架植入,术后规律抗血小板和调脂治疗。本次于UC重度活动期内再发AMI,结合上述研究结论,考虑UC可能在本例患者的AMI发生中起有一定促进作用。
关于IBD治疗药物是否会增加AMI的发生风险,目前尚无定论。5-氨基水杨酸(5-ASA)制剂是轻中度UC的一线治疗药物。丹麦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显示5-ASA可降低IBD患者的IHD风险[13];但也有学者指出5-ASA并未显示出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并有个案报道其可能导致心肌损害[4,17]。糖皮质激素是IBD,特别是急性重度UC治疗方案中的关键药物。据报道,使用激素治疗的IBD患者AMI发生风险是对照组的5倍以上,而不使用激素者仅为1.79倍[18]。英国一项人群队列研究[19]显示,即使是较低剂量的激素(<5 mg/d泼尼松龙)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然而一项纳入177例IBD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20]却发现激素使用可降低IBD患者包括AMI在内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生风险。生物制剂TNF-α抗体是急性重度UC重要的转换药物。一项法国人群队列研究[21]评估了TNF-α单抗对IBD患者急性动脉事件(包括IHD、脑血管疾病和外周动脉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与未暴露者相比,TNF-α单抗可降低近50%男性CD患者的急性动脉事件风险。但TNF-α抗体的作用同样存在争议。国内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16]发现TNF-α单抗治疗与IHD风险无关,但这一结论可能与过去数十年中我国TNF-α单抗使用率相对较低有关,两者间的相关性还需更多高质量研究加以明确。
也有较多研究关注了心血管药物对IBD的影响。低剂量阿司匹林常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非甾体抗炎药可通过抑制环氧合酶(COX)引起肠黏膜损伤,可能使IBD加重或复发,但也有研究表明低剂量阿司匹林应用于IBD患者并不会影响其临床结局,尤其是对于具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患者,可降低AMI风险[22-23]。他汀类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s)类药物可能具有控制IBD和防治CAD的双重作用[23]。肝素可通过抑制血栓形成降低AMI再发风险,研究发现除抗凝外,其对IBD还可发挥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24]。一项小样本病例分析显示,激素难治性UC患者接受普通肝素治疗后,大部分获得临床改善,甚至可达到完全缓解,且无严重并发症发生[25]。加拿大胃肠病学会发布的IBD患者VTE风险及其防治共识建议住院治疗的中重度活动期、不伴严重出血的IBD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低剂量普通肝素等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26]。
综上,本文通过对1例重症UC合并AMI病例的报道和文献分析,期望引起临床医师对IBD并发AMI风险的重视。对处于活动期,特别是年轻、无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急性重度IBD患者,应警惕心血管事件风险,予心血管相关生物学指标以及IMT、PWV等筛查。存在心血管高危因素或既往有心血管事件史、临床证实外周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更高,应予高度重视,必要时应加用抗血小板、他汀类等药物加以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