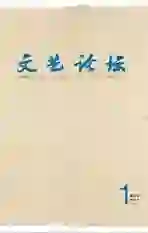中西思想交汇中文化主体性的保持途径
2021-05-17田淑晶
田淑晶
摘 要:在中西思想交汇中不丧失积极活跃的出自自我、指向自我、为着自我之思,避免失语、迷失或异化,应当关注和审思文化主体性的保持途径。思想文化交汇场域中存在着自我、自我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这三重主体及其之间的两重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三重主体之间的两重关系处于何种结构。这种结构取决于自我的理性取位。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实质上是自我应该如何理性取位以避免被他者控制、影响或者同化的问题。结合史上的胡、汉思想交汇及汉化思想之生成,“超主体”是可能而有效的理性取位,其中内蕴着超越的思维,超越的对象包括取位者自身。它具体涉及话语层、思想义理层和社会意识中的“超主体”取位。“自我”在交汇场域中始终“在”,自我所面对的自身与他者在“我处”平等共在、俱为“我”之思想资源,是自我由超主体取位保持自身、实现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超主体”;理性取位;思想话语
二十世纪末,文艺理论界有学人提出西方思想接受导致“失语”的现象,这种看法被很多人认同,由此引出关于如何摆脱失语的热烈讨论。本世纪,有关文论话语建设的呼吁反映出中国文论还没有走出失语。“失语”表面看来源于接受者言说能力的不足,其背后则是致思能力的贫弱。无论是言说能力,还是致思能力,都与接受者的主体性紧密相关。在具体行为活动中,个体不必然拥有主体性。而拥有主体性,个体才能保持自我以及自我处于活跃状态。对于外来思想接受而言,接受者丧失主体性,意味着他在接受活动场域中自我缺席,这种缺席使他无法进行指向自身或包含“我性”的理解和思考,以致除了复述他者,无有可说或有意义的言说。显然,对外来思想的接受不是导致接受者主体性丧失或贫弱的根本原因。外来思想能够给予发展与进步以灵感和启发,思想文化发展不能拒斥外来思想,鉴于此,应当关注和审思的是外来思想接受中接受者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接受者如何既使外来思想成为发展的助力和动力,又保持主体性,不失语、不异化,立足于一个民族而言,即:在试图通过借鉴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推动发展的时候,抑或在全球化背景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外来的思想文化处于交汇状态的情形当中,应当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使外来思想成为具有借鉴、启发作用的正向力量,同时不丧失积极活跃的出自自我、指向自我、为着自我之思,最终融通外来文化、发展传统。
当下备受关注、引起中西各方学者讨论的是中西思想文化交汇。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汇场域中共存在三重主体,交汇所发生的地理空间所属的文化之主体为其中之一。如果立足于该主体、将其置于“我”位来探讨,那么由于思想文化的交汇,自我同时面对着自身和他者。自我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都具有鲜明和突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只是源于二者各有其民族源出和文化特质,而且基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本身等方面的原因,二者中至少会有一方具有影響、控制、同化另一方的势能,并且可能表现出此类倾向或欲望。交汇场域中共存的三重主体之间存在两重关系:一为自我与自我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的关系,一为自我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自我是否能够保持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三重主体之间的两重关系处于何种结构。如中国文艺理论学界忧虑和汲汲想摆脱的失语,即因于关系的结构性残损。具体说来,在自我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中,他者控制了自身,导致自我与其所面对的自身和他者的关系中,自身失去主体性能与主体地位,自我的双重思想来源变为单重,只能依照他者、运用他者进行思维和言说。故而,思想交汇所发生的地理空间中文化的主体能否保持主体性,关键在于交汇场域中三重主体之间的两重关系处于何种结构,而这种结构取决于该文化主体的理性取位。由此,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实质上是自我应该如何理性取位以避免被他者控制或者同化的问题。“间位”为现代西方主体间性哲学提供的一种可供选择和细阐的主体取位,除此之外,从史上胡、汉思想交汇及汉化思想的生成看,“超主体”之位颇值得关注和详论。
一、话语层的“超主体”取位
“话语”有其主体权属。中西思想交汇场域中存在分属于“中”和“西”的两种话语,超越这两种主体权属,为话语层的“超主体”取位。由史上胡、汉思想交汇及其汉化看,交汇所发生的地理空间中文化的主体能够通过民族权属之外的话语聚焦,在自我之中缔造一个“亦我亦他”“非我非他”的话语系统。
胡、汉思想交汇中在胡籍的翻译方面存在是否“从汉”的分别,这种分别隐含在史上对来自“胡”的典籍翻译的“文质”之别当中。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谓支谦重译支谶译本的原因:“恐是越嫌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所异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②支谶、支谦都是著名的胡文翻译家,但支谶的译文“了不加饰”③,属“质”者一派,支谦的翻译则颇“文”。两人翻译的文、质之别与他们对汉语的精熟程度有密切关联。支谶、支谦皆为胡人,然而,他们对汉语的精熟程度有很大不同。支谶在汉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之间传译胡文。④据此推判,汉语应该不是支谶的第一语言,支谶的汉语能力在遣字铺文方面相当有限,故而,他的翻译只能注重本旨传译,这种情况在其他偏于“质”的翻译者那里亦有明确说明。史载《法句经》的翻译者竺将炎不擅长汉语,其翻译“近于质实”⑤。支谦与支谶、竺将炎等不同。支谦的祖辈已经移居中土。他十岁学汉书,十三岁学胡书。⑥据此看,支谦首先学习的应是汉籍。支谦非常聪敏,也十分勤奋用功,史载其“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⑦。由此推判,支谦应当精熟汉语,并且受汉地文风濡染至深,而这当是他在翻译中重“文”的原因。以其汉语水平,支谦的翻译亦能“文”,实际上也颇“文”。支谦以及与其相类的译家翻译之“文”,具体说来,是随顺了当时中土丽而不朴的文风。从汉者“文”。“从汉”的追求与分别,转化为纯粹文章学上的“文”还是“质”的追求与分别,话语的民族权属已非注意的焦点。
在翻译观念上,史上也存在“从胡”还是“从汉”之争,只是这种纷争的着眼点并非话语的民族权属,而是应当如何传译、何为有效的译语等纯粹翻译问题。如:面对时人对竺将炎所译《法句经》质实而不雅丽的指摘,携此经来中土的天竺人维祇难言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⑧当时共座的人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⑨在维祇难那里,翻译“从胡”是遵循圣人语、“依义”而译。座中人应当或为汉人,或为对汉文化有深解的胡人,故而从道家、儒家的言意观念指出直接传译胡义的缘由。无论是依据释教圣人语而主张“从胡”,还是依据儒、道阐释的言意关系主张“从胡”,都不是为了争夺话语的民族权属,而是为了有效传译。支谦翻译之重“文”在观念层面的原因亦然。支谦翻译胡籍之所以重“文”,是为了使翻译符合中土士子文人的文章习惯。对中土士子文人而言,随顺中土文风的翻译显然更易被接受和欣赏。另一著名译家鸠摩罗什也是从翻译接受的角度考虑文体应该“从胡”还是“从汉”。史料载,鸠摩罗什与僧叡论中、西文体的差异:“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⑩在鸠摩罗什看来,改梵为秦会使文辞失去藻蔚,进而会让人丧失愉悦的阅读体验。尽管鸠摩罗什此处主张“从胡”,然而,其与支谦的“从汉”在缘由与目的上根本无别,都是为了创造有效的译语。
概念是思想的纽结。胡、汉思想交汇中,超越话语的民族权属、但为精准传义的概念翻译在中土文化场域中创造出一个非胡非汉、亦胡亦汉的概念系统。由胡、汉思想交汇生成的概念系统包括直接音译的概念、改造本土词汇生成的概念和新创的概念。如:“般若”是梵文praij ā的音译,含义是智慧。中国本土语汇中并非没有“智慧”一词,《孟子·公孙丑上》谓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11}《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述贾谊《过秦论》中言道:“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12}西来的佛学中的“智慧”与中土不同。《大智度论》释“般若”:“般若者,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穷尽到边;如一切众生中佛为第一,一切诸法中涅槃为第一,一切众中比丘僧为第一。”{13}“般若”所指称的智慧,唯佛才有,佛典载一国王立下誓愿:“我今求法,为成佛道,后得佛时,当以智慧光明照悟众生结缚黑暗。”{14}“佛”为中土文化中没有的圣人,唯佛才有的无上、无比、无等的智慧自然也在中土“智慧”一语的含义之外,直接音译为“般若”表意更精准。在这个意义维度上,“般若”成为普遍流行的译语,不是话语权属争竞的结果,而是精准表意的意图和目的作用的结果。而似“般若”这样的直接音译,运用、组合汉字表达西来之义,其概念的民族权属非胡非汉、亦胡亦汉。
如果说音译本身都具有“亦我亦他”“非我非他”的性征,那么基于意义对本土词汇的改造则无论改造的缘由还是概念本身,“亦我亦他”“非我非他”都是其独有的性征。最初的《般若经》翻译并立“本无”与“空”两个概念,其后“本无”在翻译中渐次退场,“空”成为般若学核心而稳定的概念标树。“无”为本土哲学范畴,老子哲学以“无”为宇宙之始,魏晋玄学以“无”为宇宙之本。梵文中并没有独立的、可作为宇宙之源始和本体的“无”字,般若学也不是以“无”为世界本体。“本无”的退场、“空”成为核心而稳定的概念标树缘于精准传义的诉求,并成就了一种恰当的传义。而佛学传入之前作为一般语词的“空”与其对应的梵文 ūnya含义相应。 ūnya的梵文语义为空虚、空旷、非存在、零等{15}。日本学者立川武藏指出, ūnya表示的“空虚”“非存在”是“某物(y)中没有某物(x)存在”。在使用中,“ ūnya”一词一般用于“对于x、y是空的”这种语言形式,意思是“y中欠缺x”“y中没含有x”。{16}这种意义的“空虚”为胡、汉思想交汇之前本土“空”字的常用义。《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毛诗正义》:“空,尽也。”{17}高亨《诗经今注》详释为:“织布的原料被搜刮一空。”{18}《管子·幼官第八》:“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19}概念范畴不同于一般语词,其中内蕴着思想。作为般若学概念的“空”内蕴的“性空”思想,简要说来,是宇宙欠缺自性实体。这种思想与作为一般语词的“空”字的“空虚”之义之间存在着语义承续关系。上升为概念范畴的“空”的思想蕴含与中土(和梵文)作为一般语词的“空”的语义承续关系,使得因胡、汉思想交汇而上升为概念范畴的“空”,其语义权属非胡非汉、亦胡亦汉。其他一些广为流布的语汇虽然与“空”字情形不同,但概念的民族权属与“空”概念無别。如:“空空如也”初见于《论语·子罕》,“空诸所有”为中土居士所造,两词的本土源出在后来的发展中都渐次被遗忘,仿似它们是自西而来的语汇。根究这类概念的权属,也是非胡非汉、亦胡亦汉。
从史上胡、汉思想交汇看,话语层的超主体之位具体表现为聚焦于如何有效传译、精准传义,换言之,聚焦于话语的表义功能而不虑及概念语汇、文辞表达的民族权属,这种“超主体”取位能够在“我”之思想文化域中缔造“亦我亦他”“非我非他”的概念系统以至话语系统。
二、思想义理层的“超主体”之位
思想义理亦有主体权属。在中西思想交汇的场域中,思想分属“中”与“西”两种主体,并且,由于思想发源、思维角度、问题与视域以及观念主张等的相异,思想义理愈发凸显民族权属的不同。从史上胡、汉思想交汇看,基于文化的优越感或保守主义而执于自身难以发现或重视他者的异质性,其结果要么无视他者,要么使他者沦为“我”的注脚,这两种行为态度对于思想发展毫无意义。执于他者亦然。超越思想义理的民族权属,自我能够在交汇中保持自身,借由与他者的相遇发展自我。
在胡、汉思想交汇中,“道”“理”为专注点。《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段:“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否?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20}僧意与王修讨论“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自始至终都在论“理”,完全不涉“理”的民族权属,更不必论自我主体权属丧失的忧虑和争夺主体权属的意识。中土士子对于西来之理或叹服、或批驳的着眼点也都是在“理”的层面,没有进一步延及“理”的民族权属。如《世说新语》载殷浩阅读佛经的感受:“理亦应阿堵上。”{21}余嘉锡参考前人考证,谓“阿堵”犹言“者个”。{22}据此看,殷浩所观为佛经所宣之理,其叹服的也是“理”。道安曾经对慧远在西来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特别的肯定,感叹道:“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23}在道安的感叹中,不是“西来的思想”流入东国,而是“道”流入东国。
无论是中土士子还是西来的胡人,无论所论是中土思想还是西来的思想,都但为“求理”,于“理”之外的要素或无视或不屑。《世说新语》载当时诸名贤关于《庄子·逍遥游》未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遁与冯怀共语论及《逍遥游》,“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时人遂用“支理”。{24}许询因不忿时人将其比王修而与王修论辩。论辩中许询屡屡使王修词穷理屈。论辩结束后,许询问支遁自己辩论得如何,支遁回答道:“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25}“道”“理”为普遍存在,专注于“理”、着眼于“道”而不延及其民族归属,则民族权属在思维视域之外。
胡、汉思想交汇中并非不涉及“理”的主体权属,只是所涉及的主体权属在民族权属之外。如不论胡、汉之别而论释、俗之异。在印度,与俗有别为释理被强调、被认可的特点之一。如佛典载昙柯迦罗未阅佛典之前博览善学,自认为“天下文理毕己心腹”{26},及至晓畅佛籍,“始知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27}。中土论及西来思想亦每代之于释、俗之异。《高僧传》载殷浩向康僧渊请教佛典的深远之理,康僧渊“却辩俗书性情之义”{28}。为使中土人士理解西来的思想,以中土概念拟配释典中的概念为西来思想讲说者运用的方法之一。慧远讲说释典的时候,曾经有人不能理解“实相”的含义。慧远“往复移时,弥增疑昧”{29},及至引《庄子》义为连类,才使惑者晓然。对于慧远的中西概念连类,道安的反应是赞赏慧远“不废俗书”{30}。
除了不论胡、汉之别而论释、俗之异,还有不论胡、汉之别而论释与儒、释与道之异。在中土士子那里,是否倡导“空”为儒、释的分别。如关于《论语·子罕》中空空如也者是孔子还是“鄙夫”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空空如也者是孔子,有的人认为是“鄙夫”。对于第一种理解,一些人“疑其近禅”{31}。一些孔子空空论者在理解中确乎代入了释教的思想,或认为儒、释相通不二,或隐然以释学思想理解孔子的空空{32},然而,“疑其近禅”者另有一种根据,他们认为“释氏谈空”{33}。在这种观念理路上,“空空如也”儒家语源被遗忘、发展成为释教色彩浓厚的语汇,不是缘于西来思想对中土思想的控制或影响,而只涉及儒、释两种思想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影响,也是释学对儒学的话语侵占。立足于民族发源,儒、道为本土的思想,释学为西来的思想。但儒与释、道与释之异仅有思想义理的相异,无关思想的民族发源以及由此建立的主体权属。
胡、汉之外的主体权属归置,无论是释与俗,还是释与儒、道,实质上都是专注于思想义理而悬置或旁置思想的民族权属。而在“理”的层次上,胡、汉各为“理”之分殊,被考量、被审视的是“理”而不是理自何来、归属于谁,“理”是进行价值评判进而展开思维和思想建构活动的全部根据。作为价值评判根据的“理”不是基于民族发源和主体权属的“一”,而是“复数”意义的存在。从理论上讲,超越民族发源与民族权属的主体权属归置更有助于思想义理的分剖、深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融通、综合等思想活动。
三、社会意识中的“超主体”之位
社会意识是否专注于思想文化的民族发源、并且由此清楚界分和时刻铭记其民族归属,直接关系到交汇是走向融通发展还是始终各自保持独立乃至终止交汇状态。从史上胡、汉思想的交汇看,中土很早就有非道弘人而是人弘道的观念,在思想发展发挥正向作用的社会意识中,对于弘传西来思想之“人”往往由其所弘传之道、讲说之理和对道的弘传、对理的讲说来评判。
中土所谓“胡人”是西来思想的重要弘传者。从相关史料看,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建构群体——士子文人那里,胡人不会因其异族身份而只会因“理”获得声名。康僧渊是西来思想的著名弘传者之一。由当时称谓姓氏的习惯推测,他可能与康僧会同族。康僧会的传记载其先祖“世居天竺”{34}。康僧渊不是中土人氏,其身体形貌与中土人氏差别很大,他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載录:“琅瑘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35}人们通常首先通过身体形貌辨认是否为同一个民族,故而,身体形貌是民族身份相异的突出标志和提醒。康僧渊的相貌被特别提及,其中没有夹杂任何有关民族身份的敌对或蔑视,而只有因彼此之间相熟的戏谑。更值得注意的是,戏谑以时人对其机敏回答的赞叹告终。《世说新语》载康僧渊初过江的时候不为人知,因在殷浩处论理才获得声名。{36}由这些载录看,康僧渊的胡人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特别的关注,时人所重是他是否机敏擅理,而这是当时普遍的品评人物的准则和方式。
胡人身份并非都无效应,但是,胡人在中西思想交汇场域中因其异族身份获得的特别重视,几乎都是为了更好的解“理”弘“道”。如慧远对中土内化西来思想颇有功绩,其传记载:“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求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载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37}与此相类的还有:昙摩流支到关中后,慧远听说他“既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书通好”{38};佛驮跋陀罗不被秦地僧所容,南向庐山,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若旧”{39};听说鸠摩罗什入关,慧远出于诚恳咨访玄道之意而遣书通好。凡此种种,慧远对胡人典籍、胡人的特别重视完全是为弥补“道缺”、深解与正解“胡义”,也因于此,慧远虽然令弟子艰苦远求胡书、与学丰识高的胡人通好,但是未有丧失自我的见解,其传记载他“常因支竺旧义,未穷妙实,乃著《法性论》,理奥文诣”{40}。
不只是胡人,西来思想的中土弘传者同样不会因其所传为西来思想而被特别关注,评判其人及其理的依据为是否擅理、所论之理通还是不通。支遁为魏晋时期声名在外、积极活跃的西来思想的信仰者和弘传者。《世说新语》载支遁分判三乘佛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41}。有人向王羲之推荐支遁,王羲之自负才隽“殊自轻之”{42},与支遁会面时亦不与其言语,直到支遁主动与其攀谈,“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43},王羲之才大为折服,“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44}。谢灵运对慧远的钦佩与此相近。据慧远传,谢灵运负才傲俗,及见到慧远方肃然心服{45}。推揣谢灵运何以见到慧远方肃然心服,情形大概与王羲之见支遁大致相同,皆是折服其所弘传之道及其对道的讲说。
由所弘传之道、讲说之理和对道的弘传、对理的讲说来评判弘传西来思想之人、之道,其人的民族身份、其所弘传之道的民族权属完全在意识与思维之外。在这种意识状态和思维方式中,只有“道”的不同和对“道”的阐释的不同,思维者思维着来自自身和他者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