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翅翼
2021-04-18吕峰
1
村庄在大运河畔,是人的村庄,也是植物的村庄,鸟儿的村庄。
村里人对鸟儿有着极深的情谊,这种情谊有着漫长的时间基础,可能随着第一户人家的落戶,可能随着第一棵树的栽种,那些鸟儿便在此居住、生息、繁衍。对村里人来说,每一种、每一只鸟儿都是朋友,甚至是家人。黎明时分,鸟儿的叫声掀开了村子一天生活的序幕,像赤脚的农夫在软软的耕地上辛勤撒种。
对于那些鸟儿,我只熟悉寥寥的几种,如麻雀、燕子、啄木鸟、斑鸠等,更多的是不知名的鸟儿,也不知它们藏于何处,颇为神秘。那些鸟儿各有各的领地,麻雀、燕子等是属于村子里的鸟,和人相依相伴;乌鸦、喜鹊、啄木鸟是属于林子的鸟,至于翠鸟、白鹭、野鸭则是属于河滩的鸟。无论是村子里的鸟,还是林子里的鸟,或是河滩上的鸟,都是真正的国王,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当它们在天空起伏着身姿,空中开始充满生动的舞蹈。
麻雀是鸟类中的平民,它迷恋乡村,最能够与人和谐相处、同存共荣。在潜意识中,一看到鸟字,立刻会想到体形娇小、毛色灰土、鸣声短促的麻雀,它是跟鸡鸭猫狗一样深入生活日常的飞禽。麻雀习惯于守护,不习惯远飞,一旦选择了一座村庄,它们会乐此不疲地在此留守。
麻雀喜欢随处安家,屋檐下,墙洞里,草垛中,只要有个挡风遮雨的地方就好,巢的材料就地取材,在房前屋后随随便便叼些散落的鸡鸭鹅毛即可。事实上,一个巢窝可反复使用,让一代又一代的麻雀居住下去。即便多年后,在那些高低不一的墙洞中,每年春天依旧有麻雀飞进飞出的身影。
麻雀自由自在,恣肆洒脱,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路口抵达另一个路口,从一家的房顶抵达另一家的房顶,从一方树丛抵达另一方树丛。麻雀也是快乐的鸟儿,自由自在地飞,自由自在地唱,把细碎的欢乐如细雨般播洒。你高兴也好,悲伤也罢,都会跟它一起乐呵呵地忙碌着,一起忙忙碌碌地乐呵着。
一天到晚,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单一的音调不停歇地平衡着乡村生活的动与静。“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雀。”幼时,父母到田间劳作,我在寂静的院子里,可与一群前来凑热闹的麻雀,度过一段冗长的时光。看它们在屋顶蹦跶,看它们在天空疾飞,成为生活中熟悉、亲切的场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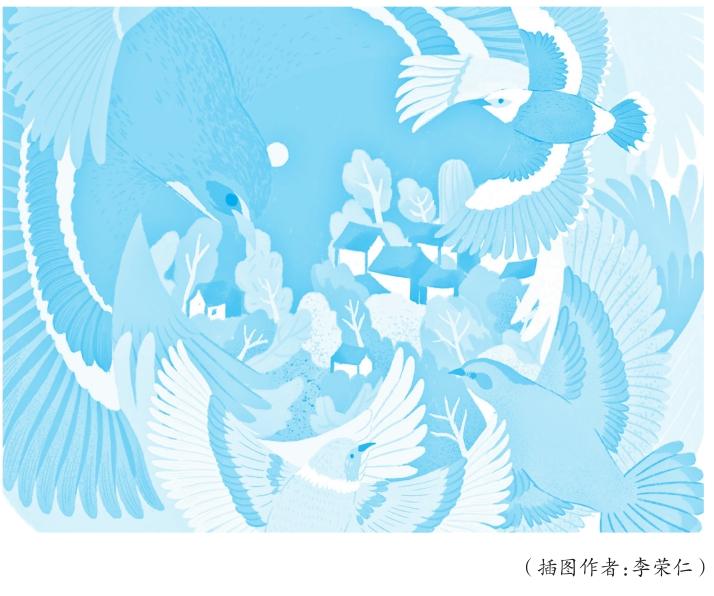
如果说麻雀是散养的鸟儿,燕子则是家雀。燕子,羽毛黑白分明,双尾似剪刀,如迎春花般被视为春来的象征。当大地走出寂寞的寒冬,燕子便从南方赶来迎接春天。它们一个个迈着轻快的步伐,沉湎在春风里,时而几只、时而几十只地蹦跳在树枝上,错落有致,划出一条条的五线谱,演奏起春天的大合唱。
运河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人还没从冰天雪地的寒冬里完全回过神来,在南方潜伏的燕子便陆续回来了,它们“啁啾啁啾”地叫着,在低空中四处飞着,寻找能筑巢繁育的地方。燕子喜欢把巢筑在檐下或屋梁上,它们在前屋后屋的屋檐下旋转,有时多达十余只,整个院子内外呈现出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气氛。
眨眼间,一群群突然冒出来的春燕,往返穿梭于麦田的沟渠、河流的岸边,衔起一口口细细粘粘的泥土,再飞到屋檐下或走廊里,然后,一粒粘一粒,要不多久,一个漂漂亮亮的燕窝便出现在房梁上。它们开始与人毗邻而居,开始在这个堪称伟大建筑的巢里生儿育女,繁衍下一代。
燕儿只捡旺家飞。有燕子来筑巢,那是兴旺发达的征兆。穷家小户,旺宅高门,都在意燕子的光临,把燕子在自家的房屋中筑巢、繁育,看成是一件喜庆事儿。檐下添了一对喜气洋洋的燕子,心里便平添了一份舒悦的吉祥。谁家燕子开始筑巢,谁家燕子哺出了新燕,谁家新燕开始试飞,都是被孩子们热烈关注的大事,像大人们谈论天气和年成,燕子的生活细节也被孩子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
每年春天都有燕子来我家的檐下筑巢,这巢,家里人从不让乱动,它们在檐下安稳地坐着。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摆着乱七八糟农具的屋中,看成燕给雏燕喂食。雏燕从巢中伸出头来,张着红红的小嘴,“叽叽”地叫着。我好奇地注意到,燕子喂食的顺序从未错过,谁也不多吃,谁也不会被饿着。
燕子是登堂入室勤劳无比的家庭成员,每天早早出去觅食,捕捉害虫。祖母经常哼唱一首儿歌:“我不吃你的谷,我不吃你的米,我只借你的房檐避避雨。请你别打我,请你别骂我,我会为你把害虫除!”在童稚的心中,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燕子飞舞呢喃的春天会是什么样子。
到了深秋,燕子开始盛大的集会。在那些纷纷扬扬、飘飘荡荡的树上,厚厚密密、重重叠叠的燕群在飞翔。初升的朝阳,被罩上燕群织成的一张巨网,只漏下疏疏朗朗稍纵即逝的光。一群群燕子相继在村子里消失,融入云间,融入蓝天。院子开始冷冷清清,山林也空空荡荡,天空变得寂寞荒凉。
老鹰是少见的猛禽,也是村子的稀客。当有老鹰飞过时,大人小孩,都会停下手中的事儿,仰着脸看半天,直到它消失在天尽头。幼时,我对老鹰有一种毫无理由的喜爱与痴迷。一有时间,就爬上树,或坐在田梗上,昂首望天,期待一只老鹰从眼前飞过。运气好时,会看见一两只盘旋飞翔的鹰,像一粒种子那么大的黑点,穿过白晃晃的阳光,落到翻耕过的土地上,或落在高高的树梢上,寻找猎物。
老鹰是空中的王者,两只硕大的翅膀,让它可随心所欲的飞翔,可肆无忌惮地捕捉猎物。遇到了猎物,它像一支激射的箭矢,“嗖”地冲向地面。等你再看时,它已腾空而起,鹰爪上挂着一只正在挣扎的猎物。记忆里,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老鹰抓野兔。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老鹰与野兔的殊死搏杀,看得心惊胆寒。
村里人不喜欢老鹰,因为它总是趁人不备时,叼走一只鸡或鸭。谁家的鸡鸭要是莫名其妙地丢了,都会怀疑被老鹰叼走了,并诅咒它。我亲眼见过一只老鹰叼走鸡的情形,它停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先选中地上的美味,然后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看到没有什么危险,“嗖”地一下腾空而起,冲向猎物。在一阵鸡飞狗叫中,它抓起一只鸡飞走了。看着它抓鸡的情形,我发现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是另外一回事,母鸡哪有保护小鸡的能力啊!
对村里人来说,每一种鸟儿都是灵异之物,它们持有神秘的身份,不停地飞翔,不停地用歌唱的方式来与万物沟通交流。因为它们的飞翔、鸣唱,村子也生出了千双万双翅膀,翼翼然欲翔欲飛,似乎在下一个瞬间,也会振翅飞去。
2
村子外树多,林子大,鸟也多,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名字,有着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形貌,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有翅膀,都会飞。它们在天空、在原野、在丛林,穿梭如织。喜鹊和乌鸦是林子里最多的鸟,或者说林子就是它们的地盘。人在村子里刨食,喜鹊和乌鸦在林子里叼食,人与鸟相互厮守,相安无事。
喜鹊喜欢“喳喳喳”地叫,虽然叫声粗糙,却是吉祥的鸟,俗语说“喜鹊叫,喜事到”。村里人对喜鹊有着莫名的好感,幻想着每天都有它的光临,以期带来好运。祖母常说,你出生的那天早晨,好几只喜鹊站在门前那棵槐树上,“喳喳喳”地叫个不停,把初冬清冷的早晨,叫得温暖如春,格外生动。在喜鹊的欢叫声里,一个生命“呱呱”坠地了。
燕子把巢安在檐下或屋梁上,与人毗邻而居,享受着人的殷勤照拂。喜鹊不然,它喜欢将巢筑在高高的树梢,生怕别人惊扰了它。在人开始春忙时,喜鹊也开始筑巢孵蛋。喜鹊垒窝很讲究,堪称鸟中的建筑师。它不辞辛苦地叼来树枝、泥巴,把窝垒得牢固、美观,且有顶棚遮天,真正能起到遮风挡雨的效果。喜鹊的窝都不小,一个窝拆下来,树枝能煮三大锅稀饭。
冬天,一场北风呼啸着到来了,给林子披上了一身的霜,地面上的草也枯了,在风中瑟瑟地颤抖着,人看了,也禁不住地瑟瑟发抖。落尽叶子的树梢、树干、树林,像一张七疮八孔的渔网,网不住过往的风,任它“咣当”作响,任风呼啸而过。一棵棵树站在河滩上,平时隐藏在繁枝茂叶中的鸟巢凸显在了眼前。鸟巢数不胜数,呈盆状,在空旷的林子里,很容易引起人的敬畏。
一年冬天,日暮时分,夕阳的余晖在树梢上跳起了舞,闪耀着点点金光。林子里不见人声,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从林子中经过。突然,天上传来“喳喳喳”的叫声,那是喜鹊的叫声,开始只是一声两声,孤独而嘹亮。紧接着,一只只、一群群喜鹊从巢洞中,从林子深处,从我不知道的地方,从四面八方飞来,密密麻麻停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梢,把寂静的林子弄得一片喧闹。眼前的景象令我心惊,突如其来的鹊群像一场始料不及的风暴,仿佛是精灵在聚会,黑压压闪动在天地之间,让我想起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传说。
乌鸦,村人俗称老鸹,全身乌黑,如同巫师的斗篷,泛着绿光,会做木工的祖父常在嘴里念叨,这老鸹比墨斗还黑。黑色是一种带有神秘性的色彩,蕴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乌鸦一身的黑羽,让它拥有了无限的神秘感,让人惶恐不安。事实上,人们之所以怕见乌鸦,是怕那紧跟其后的神秘与未知。以至于在随后的日子里,只要听到乌鸦的叫声,尚来不及捕捉到它的身影,都会习惯性地先吐口水,如同条件反射般。在那天接下去的时间里,心上似乎挂了一个水桶,七上八下,说话、行事都小心翼翼,生怕惹祸上身。
乌鸦很少光临村子,似乎在遵守某种秘不可宣的约定。有一次,一只乌鸦不知为何闯到了村子里,或者说闯入了家中。它披着一身令人发怵的黑羽,煽动着翅膀,在院子的上空不停地飞着。最后,它落在了窗外。当时,我刚从睡梦中醒来,它对我瞪着一双黑黝黝的眼睛。在它的注视下,我的头上、背上都是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最后,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只乌鸦无动于衷,黑亮的眼睛依然瞪着我。直到哭声将母亲唤来,它才“嗖”地消失在天空深处。
一个不知害怕为何物的少年,竟然被一只乌鸦吓哭了,现在想来,颇为可笑。后来,常去给守林子的聋子爷送吃的,乌鸦见得多了,也就见多不怪了。那些乌鸦或立在树桠上,目光像一阵风,扫过山野;或用翅膀拍打周围的空气,如海浪拍打礁石,“啪啪”作响,打破这方天地的静谧;或从远处衔来食物,在巢里进进出出。
啄木鸟也是林子里的常客,它敲打树干的声音密集、有力,像打击乐队的演奏,“咚咚咚”,那音律和节奏里深含着天才的创意。每一次,我都奇怪木头在啄木鸟的嘴下,竟会发出如此奇妙的声音。每一个音节是如此精巧,众多鸟儿发出了庞大的和声,以至于让我感到所处之地就是一座阔大的音乐厅。
每年都有猫头鹰在树洞里孵蛋。有一年,我从树洞里逮了两只猫头鹰的幼鸟。傍晚,我正逗它们,猫头鹰竟顺着幼鸟的气息,来到了我家。它站在院墙外的桑树上,使劲地叫着,“咕咕咪咕咕咪”。后来见我无动于衷,竟像老鹰般俯冲而下,向我啄来。母亲听到动静,忙从屋子里出来,见此情形,狠狠地骂了我一通,“造孽啊,造孽啊”,边骂边让我把幼鸟送了回去。
再后来,在聋子爷那里见过一只濒临死亡的猫头鹰。那曾经自由飞翔的翅膀,毫无生气地瘫作一团,尖锐的爪子弯缩着,仿佛发出痉挛之声,眼睛睁得大大的,威严的目光里埋着深深的遗憾和不甘。那一刻,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怎么也不能把它同那个用利爪尖嘴攻击我的猫头鹰联系在一起。
林子里的鸟很少光临村子,只有冬天下雪了,才飞到村子里觅食。它们落在墙头上,院子里,屋檐下,捡拾撒落的谷物,啄食人们遗留在树上的柿子、石榴,以及挂在屋檐下的玉米、柿饼、大枣等。村里人也不吝啬,常常扫去积雪,撒上些谷子,那些鸟儿也不怕人,慢悠悠地吃着,人过来了,最多飞到院子边的树上或屋脊上,待人离开,继续享受它们的饕餮盛宴。
3
运河的水是自由散漫的,运河里的鱼是自由散漫的,河滩上的鸟儿也是自由散漫的。
荡漾的清波,潮润的河风,葱茏的丛林,给鸟儿的繁衍提供了条件,提供了庇护。河滩上的鸟儿很多,成群结队在水面游弋、追逐、戏水,像一艘艘战舰在列阵、在攻歼、在追击,给河滩、给天空带来无限生机。
秧鸡、野鸭、翠鸟是河滩上常见的鸟儿,也是熟悉的鸟儿。秧鸡的数量很多,几乎每一处河滩都有它的踪影。秧鸡,黑黑的,小小的,头顶有一撮红色肉冠,像一簇小小的火焰燃烧在黑炭似的身体上。秧鸡喜欢栖居在苇丛中,用芦苇来掩蔽它的身影,然后“咕咕咕咕”地叫着,那声音与众不同,让人从心里生出一份喜悦。
野鸭学名水凫,嘴扁,脚短,趾间有蹼,头和颈是灰绿色,颈部有白色的领环,上身黑褐色,腰和尾上的覆羽为黑色。雌的野鸭为灰褐色,一点儿不漂亮,只有雄的野鸭才有漂亮的羽毛,似乎鸟儿都是如此,如孔雀、野鸡等。人与鸟不一样,女人才喜欢华丽的衣裳,花花绿绿的,在风中招展。男人们很少见鲜亮的衣服,黑、白、蓝、灰四种色就囊括了一年四季。印象中,祖父和父亲常年都是黑色或藏青色的粗布大褂,一如他们黝黑的面孔。
野鸭虽以鸭名,却能飞翔。它们喜欢成群结队栖息在河滩上,像一群即将出席宴会的乡村绅士。一只挨着一只,浮于河面,一有声响,便“哗啦”一声,向深处群起而飞,黑压压的,像天边卷来的一大团乌云,颇有遮天蔽日的味道。冬天是野鸭最难熬的季节,闲下来的村里人常捕来打牙祭。
捕野鸭的网和捕鱼的网不一样,网眼有一定的弹性,大小刚好钻进鸭头。野鸭觅食,好扎猛子,遇见喜欢的水草,争先恐后,一个猛子扎下去,鸭头钻进了网眼里,后退退不得,往前则越窜越深,常看到十几只野鸭在水中扑棱乱窜。用网捕野鸭也有招数,网的中间常放些媒鸭,也就是家鸭。那些媒鸭的脚上拴了砖块,不能游远,也不能逃走,不停地游動着、叫唤着,“嘎——嘎——”野鸭听到伙伴的呼唤,信以为真,敛翅落下,真可谓是自投罗网。捕回家的鸭子,可与地瓜粉皮、栗子同煮。如果是煲汤,味鲜且美。
翠鸟是河滩上最漂亮的鸟,飞起来,像一块移动着的翡翠,带给人想象的空间。翠鸟的羽毛油润有光泽,尾部有尾腺,能分泌出油脂,沾水不湿。它的叫声脆生生的,听得人浑身透彻爽快,像夏天吃拔过凉的西瓜。翠鸟机灵,根本捉不住,甚至都不能靠近看个仔细,稍微一点声响,它便一个转身,“嗖”地飞进苇丛中,空留清脆的叫声在水面飘荡。翠鸟是捕鱼的高手,它喜欢站在一截水中的树桩上,眼睛盯视着河面的动静。一有目标,迅疾地夹紧羽翼,俯冲下来,叼起鱼,快速飞走。
春水涨起,白鹭整日在水面转悠。白鹭天生丽质,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恰到好处。它们带有几分忧郁几分孤傲,或如智者般屹立水际,或与爱侣款款偕行,或展翅飞翔迂缓,姿势随意、自然、闲适。在如镜的水面上,它们汲水而舞,轻歌萦绕,倩影婆娑。
春天的河滩除了鸟,还可以拔茅针。茅针是茅草的幼芽,上面是略带紫色的叶子,下面是嫩绿的芽。剥掉外面的皮,白白的,嫩嫩的,吃到嘴里甜丝丝的,要化了一般。后来长大了吃棉花糖,也没有它好吃。整个春天,每个孩子的口袋里,都时刻装着茅针,嘴边自然也充溢着春天的味道。
到了夏天,河水泛滥,水退去后,河滩上长出了一片片地角皮,黑黑的,滑滑的,嫩嫩的,散发着水汽。村里人称地角皮是大地的耳朵,我不知道它们能听到什么,是风和水的和弦,是星和月的对话,还是鸟儿和鸟儿的交谈。苇荡中时不时地擎起一个个粗大的黄色花柱,那是香蒲草,又称水烛,嫩芽称蒲菜,是有名的水生芽菜。
夏日的阳光烘烤着大地,人也没有了精气神,河滩边的树荫就成了避暑的绝佳去处。阳光洒落下来是慢的,水面缓缓涌动是慢的,林木轻轻摇曳是慢的,躺在树荫下,一边听着蝉声,一边看鸟儿游弋。游弋是飞翔的另一种姿势,那些鸟儿一只只拥簇在水面上,慢慢融入河面上落日金黄的影子,人也好像变成了一只慵懒的鸟儿。
到了秋天,有些鸟儿要南飞,我们就可去芦苇丛中捡拾鸟蛋,这些遗留下来的鸟蛋是孵不出幼鸟的。野鸭的蛋最多,白皮的,青皮的,捡回来,怎么吃都是美味。母亲好用来腌咸鸭蛋,蛋白如嫩豆腐,橘红色的蛋黄溢出金黄色的油,晶莹剔透,颜色像初夏的落日,吃在嘴里细腻绵密、油润醇香。
咸鸭蛋的腌制有两种方法,一种将粗盐溶于清水中,再把鸭蛋放入盐水中浸泡;另一种将粗盐用水化后,与黄泥拌成糊状,将鸭蛋包裹住,放入一个密封的坛子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即可食用。
咸鸭蛋的吃法是用筷子戳开一个小口子,掏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地一声,红油就冒出来了。吃完,我习惯性地拿过来再瞅一瞅,里面残留的蛋白,也会抠出来吃干净。若是见到那黄澄澄、亮晶晶、油腻腻的咸蛋油,渗透到了蛋壳外面,会不自觉伸长舌头,“吱溜”一圈,舔了又舔,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觉得美味。
招待客人宜带壳切着吃,切好的咸鸭蛋围成一圈,摆在盘子里,青色的蛋壳,白色的蛋白,橘红色的蛋黄,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切咸鸭蛋也有技巧,切之前先用刀尖在蛋中间磕个小缝,再切开就不容易变形,且蛋壳边缘整齐,没有碎屑。
说起吃咸鸭蛋,还有一个笑话。一位城里的姑娘到村子里相亲,男方家备了一桌子丰盛的菜。姑娘独独对咸鸭蛋的蛋黄情有独钟,最后所有的蛋黄全进了姑娘的嘴里,只剩下如小船般的蛋白,让人哭笑不得。后来,姑娘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咸鸭蛋能成就一段姻缘,也算是一件美事。
捡拾鸟蛋之余,可采摘菱角,把椭圆形的长木澡盆拖进水里,双手先揪住岸边裸露的树根,人轻轻地坐入盆中,松开手,划一划水,采菱的小船儿便荡漾起来,水波一圈又一圈,消失在远处。嫩菱,皮脆内嫩,鲜美爽口。老菱,肉质洁白如玉,粉而不腻,烧炖煮无一不可。乌菱的两角铁钩般翘起,皮巨硬如铁。吃的时候像劈柴,拿起菜刀,手起刀落,乌菱被劈成两半儿,剥出里面的肉,有一种软香,生食,熟吃,均可,且是不一样的味道。
河滩上,更多的水鸟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它们像跟人捉迷藏似的,全藏在芦苇深处,只用叫声逗着你放下心事,陪它们玩耍。有时,你蹑手蹑脚循声而去,只看到一个个影子惊飞远遁,留下惊鸿一瞥。
鱼老大是捕鱼高手,也是河滩上鸟儿的守护者。大风袭来,鱼老大夫妇就沿着河岸,深一脚浅一脚地把跌落的幼鸟送进巢里,或带回家饲养,小鱼小虾足够鸟儿吃的了,养再多的鸟儿也不怕。在鱼老大那里,可见多种多样的鱼,也可见平时只听闻名字的鸟儿。那些鸟儿长大了,鱼老大也不留,随它们来去自由。
河滩的天空一派神秘,水面幽深,一道道鸟影肆意飞翔,一声声鸟鸣肆意传播,随着它们的起起落落,人的想象也被安上了翅膀,开始任意飞翔、驰骋。
4
鸟声,蝉声,虫声,雪声,松声,水声,都是大自然奇妙的声音,让人觉得不虚此生。鸟声最妙不可言,在某个曙光从远方显现、大地氤氲着薄纱似的雾气的清晨,或在夕阳西坠、余光染红整个天际的黄昏,它突然响彻在耳边,传递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语。
从幼年开始,每天都在鸟鸣中醒来,光阴也在鸟鸣中倏然而过,如白驹过隙。黎明,鸟声如定了铃的闹钟,准时把我从睡梦中唤醒。鸟声透着细瓷的质感,清清纯纯地穿窗而过,落在枕边。大自然最黑暗的那段时光也被它惊醒,黎明在惊讶里一下子张开了眼,开始变得白白的、亮亮的。
鸟声此起彼伏,我也睁开了惺忪的双眼,依稀看到窗外的树上有无数的鸟儿。它们不甘寂寞,各占枝头,或来回飞舞,或敛翅静立;或啁啁啾啾,短促而明快;或唧唧喳喳,粗糙凝重;或吱吱扭扭,柔弱婉转;或鸣啼百啭,清脆悠扬。它们各有声调,各有情趣,让人耳不暇接,如听音乐会。那些活泼泼的鸟儿在一种哨音的引奏下,用嘹亮的歌喉,为清晨的到来抒情歌唱。
鸟鸣像一道道清泉倏地流过心田,像洒落的音符陡地种在情感的罅地上,心胸变得舒缓、开阔、悠然。因为鸟儿,我对村庄有了一個诗意的构想,树荫丛里,简约的村庄在熹微白光中显现出模糊轮廓,四周雾霭萦绕,看不出具体影像,只有院子里的枝叶间,成群的鸟儿跳跃啁啾,细碎的叫声催醒了昨晚贪玩迟睡的顽皮儿郎。
有鸟儿的日子是温馨的,有鸟儿的日子是快乐的。鸟儿的叫声是鸟儿的语言,是一只鸟儿与另一只鸟儿的交谈,是一只鸟儿对另一只鸟儿的呼唤。人与鸟,也是生命和生命的交谈,欢乐与欢乐的交融。鸟儿的语言纯净、透明,从它的鸣啭里,我听到了蓝天白云的对话,听到了清风细雨的对话。一只只鸟儿是来自天空的信使,带来了云间的消息。
鸟儿是树的花朵,哪怕是隔着暮霭,也能听到鸟儿在夜风中歌唱。
布谷鸟是受人优待、惹人怜爱的鸟儿,体形大小和鸽子相仿,较细长,上体暗灰色,腹部布满了横斑,飞行急速无声。淳朴的农人,将它看作是一种提醒农时、催生丰收的吉祥之鸟。在紧要的农事时节,村里人祈祷它的叫声能更欢畅些、更紧凑些,这样,当年的庄稼丰收就大有希望。
我对布谷鸟的情愫自小滋生。天清气爽,鸟鸣虫啁,兴致勃勃地盯蚂蚁搬家外,还喜欢听布谷鸟吟唱。立夏过后,基本上昼夜都能听到那高一声低一声、远一声近一声的鸣叫,“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在薄雾笼罩的清晨,在旭日当空的正午,在晚霞如织的黄昏,清脆、激昂、悦耳的声音,和着谷雨的气息,扑面而来,催人奋进,不经意的几声清音,如沐天籁,如聆梵音,那种酣畅淋漓,让人难忘。
那时,只要一听闻布谷鸟的叫声,我即莫名地欢快、兴奋,全身带劲,赶紧丢下手中的活计,堂前屋后、漫山遍野地去寻它,只为一睹它的姿容。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与追寻中,布谷鸟早已掠了翅膀,飞过树林,掠过河滩,匿了踪影。在我难过得想要哭时,在远处的树梢之巅,又传来了宏亮的“布谷布谷”声,委屈的心灵才算有了一丝慰藉。
布谷鸟的别名不少,如杜鹃、子规等。相传,古代的一位帝王,因德才不够,只能在闭塞的蜀中盘踞一片天地,最后,这个羞愧的帝王化作子规鸟,飞天而去。如是,布谷鸟才总是唱着“不如归去”的歌儿,唱着它失去的一切,唱着它向往的一切。后来,听祖父讲,布谷鸟喜欢倒吊在树枝上叫,到最后,血从舌头上滴下来,滴到杜鹃花上,花就染红了。
可能是因为此,布谷鸟虽长得不漂亮,却深受人们喜爱。每个人会根据心境的不同,把它的叫声也演绎得有所不同。对于祖祖辈辈同泥土打交道的农人来说,布谷鸟的叫声是在督促人“下地干活,下地干活”。在我看来,布谷鸟的叫声代表着一个忙种忙收的节令,也代表着某种离别、相思的幽怨,带有一种亘古的凄美,古老又苍凉。
幼时,村里人喜欢养鸽子。屋檐下,房顶上,悬挂或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鸽子笼,灰鸽子、白鸽子都有,进进出出,极为热闹。早晨和傍晚,一群群鸽子或在蓝天上飞翔,或在屋顶上驻足,或在树梢间盘旋,伴随着的是鸽哨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平静祥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让人不由地驻足观望。
第一次养鸽子是在十岁左右,它是一位远房亲戚送我的礼物。当我看到四只可爱的小灰鸽转着圆溜溜的黑眼睛怯怯地望着我时,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欢迎它们。我赶紧找来纸盒、木棍、木板、铁丝,做了一个粪便可以漏到下边的简易鸟箱。从此,放学后照顾鸽子成了我的一件大事,喂食、喂水、洗毛、清理鸽笼,且乐此不疲。
鸽子慢慢长大,身体一天天结实起来,体态修长丰满,羽毛油光发亮,泛着荧荧的彩虹的光芒。这时,可以给鸽子戴鸽哨了。我便提着笼子去找眼镜爷。眼镜爷读过私塾,喜欢遛鸟、斗蛐蛐,也是做鸽哨的高手,能做出好几种形状的哨子。眼镜爷一边做,一边讲鸽哨的知识,什么四筒哨、五联哨、梅花哨、九星哨之类的。没多大工夫儿,一个精美的梅花哨就做好了。
鸽哨做好了,系鸽哨也有讲究。眼镜爷让我按住鸽子的翅膀,他小心翼翼地把鸽哨穿在中间四根尾翎的根部,然后用一根细铁丝穿过哨鼻,两端一搭一扣,鸽哨就牢牢系好了,任鸽子怎样翻飞回旋,都不会掉。从此,每天早上,放鸽子、听鸽哨成了一件雷打不动的事情。看着那自由自在的身影,听着那无拘无束的腔调,仿佛有甘甜的酵母粉末断断续续撒进心房,渗透到心底,一颗心变得柔软、松弛起来。
在暮暮朝朝的陪伴中,那些鸟儿如潮水般,荡漾出无限的风情,氤氲出无数的念想。漂泊异乡,对故园的记忆是乡风乡俗,是河鲜鱼肴,当然也少不了鸟儿。念起时,那些动人眼目的身影,那些略带暖意的鸟声,像朝雾、像海水、像音波,在无风的清晨,在寂寥的黑夜,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作者简介】吕峰,1979年生。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现已发表出版作品200余万字,见于《人民日报》《大地文学》《中国铁路文艺》《雪莲》《散文百家》《当代人》等报刊,著有《屋头青瓦是谁家》《梦里天堂:一城一景一味》《一器一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