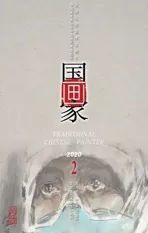“铁锈未眠”:中国当代工业题材绘画中的废墟景观研究
2020-12-08
中国当代工业绘画不乏表现“废墟”之作。并且,依照目前的创作样态看,“工业废墟”的主题创作还将一直持续下去并引发新的社会关注。本文认为,当美术家将视线聚焦于工业废墟时,他极有可能是在表达一种对宏大工业景观的审慎观察,形成一种对历史的鲜明反诘和另类阐释,并隐含着重建时代核心价值体系的愿望。
一、当代美术家为何要表现工业废墟?
近年来,一些工业主题的美术展览相继开幕。例如2009年,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国工业主题美术作品展”;2010年,UCCA与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刘小东个展“金城小子”;2012年,“锈永未眠——崔国泰个展”;2013年,北京德山艺术空间举办的“‘铁锈未眠’赵晓佳大工业作品20年回顾展”;2015年,湖北美术馆举办的“‘工业在场’2015中国工业版画三年展”;2016年-2017年,重庆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工业美术展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日俱增的工业题材创作往往对废弃的工厂情有独钟。美术家总是刻意地回避“人”的在场,不遗余力地描绘着工厂的“废墟”身份,即使它可能还没有那么破旧。这就不得不使人思考:当代美术家为何热衷于表现工业废墟?这些废墟形象到底给我们呈现了什么?
(一)借助工业废墟叩问历史
工业废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企业转型之中,千千万万的工人告别了旧址。昔日热火朝天的工厂渐渐变成了无人的废墟,即使留有巨大的体量,也已经成为被遗忘的杂草丛生的角落。在这种语境下,“废墟”成为传统工业所面临的现实难题的影射,它对“光荣工厂”的历史补位颠覆了人们无比坚定的社会观念,反映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和时代的焦灼感。应该说,工厂不仅是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也是光荣的工人们的精神场所。这个重要而特殊的场所因时代的革新而湮没,关于工厂的所有记忆便都成为一种无所依托的倏忽的存在。
当然,对于原来工作其中的工人来讲,他们或许更关心自己的生计,而不是这种“工业废墟”的意义,但是这种因历史变革而带来的情感变化和特殊景观,却会引起美术家们的反思和叩问。他们能够展现出极为敏感的艺术嗅觉,容易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其背后的重大历史变迁进行反思,并利用擅长的艺术语言将废墟意象表现出来。2013年,赵晓佳举办了“铁锈未眠——大工业作品20年回顾展”,作品采用了黑色和红色的基调。正如栗宪庭所说:“黑色既是大工业风景的衰败、废墟和黯淡,也是美术家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内心压抑和痛苦。红色既是大工业风景的动荡、挣扎和燃烧,也是美术家体会到这个时代的热血、怒气和焦灼。”[1]这当中就寄寓着知识分子一种探古寻幽的反思情怀。
如同古人登高总要怀古成诗一样,当美术家凝视着这样一座座废弃的厂房和工业遗迹时,“面对着历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沉默的空无,观者会感到自己直面往昔,既与它丝丝相连,却又无望地和它分离”[2]。换言之,在这些美术家的笔下,工业废墟确实与时人所熟悉的工厂息息相通,但那种只属于工人群体的特殊空间性质已经变得遥远,而公共猎奇的空间性质开始掺杂其中,成为一种“置于异质混杂的符号之下”的特殊场域,也就是福柯所谓的“异托邦”[3]。这种工厂“异托邦”是多种时空或时空性质的共存,具有片段化、矛盾化、破碎化的样态特征。正是工厂“异托邦”的“异质混杂性”触动了美术家并使之表现出来:一方面,它仍然借助工厂之名存在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主体的缺失和岁月的痕迹又使其脱离工厂之实,成为外来猎奇者的关注对象。
一些美术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在画面中加入了“在场”的观者元素,更鲜明地揭示了工业废墟的异质性和辩证性,观照了历史进程的衔接和意识形态演变。例如在2017年“第二届全国工业美术作品展”中,刘德才的《静谧之秋》抓取了田野间两只小羊横跨废弃铁道的场景,小羊的介入致使工厂的空间性质发生转变,从封闭的工作空间转换为空旷的田野空间。董喜喜的《存在之路过》对此表现得更明显。废弃的火车头横在背景中,前方同样利用一只羊羔来表现工厂空间的公共性。另外,正是画面中拍照的少女,促使其公共猎奇空间的性质得以强化,只有那没有坍塌的钢架还表现出最后的倔强,成为两种时空的见证者和调和者。
(二)实现一种对话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叩问式的“废墟”作品呈现出一种“对话”关系:对话身处其中的自己或者对话当下社会。对于前者,曾经的特定人群所使用之空间变成一个毫无遮拦的场所,美术家成为闯入这一空间的“外人”。在“外人”的眼中,工业废墟就静止在那里,它既不属于任何人,又被所有人观赏。它们不属于任何人,是因为其使用主体已经形成历史性缺席,而其自身却尚未蜕变成新的形态空间。这种有别于当下的空间性质被敏锐的美术家所捕获,并在历史性与当下性的错位中形成一种空间的扭曲,产生一种非当代的当代性。驻足其中的美术家似乎察觉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又该继续走向何处?
这种审慎的发问实现了自我对话,也必将成为与社会对话的艺术方式。中国当代工业题材美术所演绎的叙事冲突,来自美术家对往昔工业建设与当下工业废墟所形成的历史落差的思考,是通过视觉叙事的方式将“异托邦”的强烈冲突性引向了文化史的层面。巫鸿认为:“当代艺术对工业废墟的表现多是对社会主义往昔的回眸,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视角。在风格上,这种视角被外化为宏大的景观。与他们表现城市拆迁有别,美术家从不把自己融进废墟,而是谨慎地保持着和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迫使观众必须把整幅图像作为宏观客体来观察。”[4]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工业废墟成为一种当下想象的历史文本,工业废墟的描绘成为一种冷静而审慎的阐释行为,是一种与自我和社会的对话,蕴含着对时代生活的关注。
二、对当代工业题材绘画之目标设定的思考
工业废墟与往日每一位工人的思想情感都息息相关。每一套落满灰尘的旧设备都保留着最鲜活的工人生活的回忆。它展现的是旧工业基地与精神家园之间的符号互动,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勾连。但是薄薄的灰尘将成为阻断这种精神勾连的利器,伴随着灰尘的积攒和时空的流转,这些回忆所依存的物质基础必将湮灭无踪,使“工业废墟”彻底孤立为詹姆逊所说的“碎片化”和“无深度化”,进而拒绝人们(尤其是老工人)寻觅精神信仰的请求。
如果说工业是整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工厂则是精神象征的代表。当象征时代精神的工厂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铜烂铁并不断消逝于人前时,人们对曾经的历程和自我必会感慨万千。“为钢铁而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工业精神是否还值得延续?赵晓佳说:“大工业题材我持续画了二十年……我突然发现工业不死,就是未眠的意思。铁锈还是跟大工业有关。在近期的作品中,我希望表达死亡中孕育新生。”[5]“工业废墟”的文化史意义可能就在于此。如果说“工业”是一种超越工人群体而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意象,那么美术家对“工业废墟”的热衷,正是意图对精神家园的呼吁和重建,具体而言就是围绕工业建立的时代核心价值体系。在这种上下文中,我们才可以理解陈丹青所说的工业废墟的“伟大”之处。[6]
应该说,美术家通过绘画构建的,不仅仅是工业废墟的现实,更是一种对时代核心价值的讨论。工业废墟,以其急遽消退的现实感和难以摆脱的沉重感使观者茫然无措,逐渐成为流浪者。当孤独的流浪者突然遭遇工业废墟,便会选择逃避,但是后者又不断地证明着流浪者的存在,遂将人们重新拉回现实。美术家的创作不正是在现实中直面“工业废墟”并企图呼唤核心价值体系的壮举吗?
结语
美术创作中对工业废墟的描绘,是当代“废墟”意义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美术家通过描绘颓败的工业废墟,揭示了工业“异托邦”的特殊空间性质,以对话自我和对话社会的方式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多重思考,凸显出美术家们试图重建时代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由此看来,“工业废墟”不仅是一种绘画题材,而且兼具了文化史层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