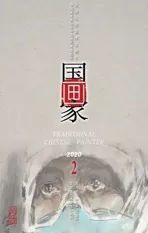从情景交融到超以象外
——浅谈石鲁中期到晚期绘画风格的蜕变
2020-12-08
石鲁的艺术创作若从时间和风格演变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入陕北公学院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中期阶段、“文革”后至去世前的晚期阶段。早期阶段石鲁艺术创作主要为了配合党革命路线宣传,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以版画创作为主,内容多表现劳苦大众,形式朴素,画面单纯,通俗写实,带有叙事情节,群众能够快速明了其创作用意,如版画作品《群英会》《打倒封建》《说理》等。此时,石鲁艺术创作思想尚未成熟,画面主要表现昂扬炙热的革命情感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目标。其身份不仅是一位个体艺术家,更像是肩负宣传党的方针路线重要职责的艺术战士。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实情况的转变,石鲁开始将创作重心由版画转为中国画。他与赵望云等共同开创了长安画派,提出“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创作观念,期望通过汲取生活中的养分,对传统中国画笔墨造型进行大胆革新与改造。因受石涛不拘一格艺术思想及特立独行艺术品格的影响,其创作逐渐表现出构图奇绝、境界高迈、千奇万状的个性面貌,从而步入创作的中期阶段。
一、情景交融,意与象通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自豪感中,创作都围绕着讴歌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进行构思和立意。如1952年创作的《幸福婚姻》年画,描绘了妇女婚姻自由的巨变;1953年创作的《祁连山下的工地》塑造了西北大建设的壮美场景;1954年创作的《古城墙外》刻画了新修铁路穿过古老长城的伟大事件;1955年创作的《梯田人家》描写了黄土高原的焕发生机等等。我们能够清晰体会到石鲁这一时期炙热的情感和政治上的奋进。这一时期石鲁主观精神状态虽激昂向上,但还是屈从于时代政治的需要,手法写实,内容叙事,情节明了,有意识地将内在情感服务于客观需要,忽视了探求自我心灵的自由和自我情绪的宣泄。作品中,艺术家的“自我”表现与政治的“他者”需求出现统一又分离的矛盾现象。就像他倡导的“新国画运动”,改造中国画,就是要具有写实精神,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服务于人民。
可以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石鲁中国画创作一直在尝试如何将客观生活与主观情感融为一体,其创作的一大批作品都清晰呈现出以景生情、借景畅情的艺术风格。1959年,其为国家博物馆创作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无疑是诸多创作中的一座丰碑。《转战陕北》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转战陕北的革命事件为创作背景,表现了革命伟人身在高原,却胸怀天下的不凡气度。画面初观如一幅山水画,大面积的黄土高原,人物很小,仿佛点景之用。但细观,目光则不由自主地被人物吸引过去,大面积赭红的黄土高原似乎成为伟人身体的一部分,滋养着主席的形象不断升腾,变得越来越伟岸。画面中毛主席是侧身伫立,观者却依然能感觉到主席深邃的目光,感受到主席心系国家、情系民众的深沉情感,感触到主席对于开创新中国的决心与自信。在画面构图上石鲁可谓下足功夫,主席基本位于画面上下居中、左右偏右三分之一位置,恰好在赤红色的高原近景与淡赭色的高原远景形成的一个弧线的顶端,形成强烈的动态视觉效果。笔墨运用也匠心独具,将浑厚坚硬的线条都置于主席背后,将纤细浅淡的线条置于主席下方和前方,象征着主席得到人民爱戴、拥有着无穷力量的气势,也彰显革命前路无可阻挡、尽在掌握之中的气魄。画面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来凸显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张力。画面高原虽以红色为主调,但浓淡反差很大,近景壁立的高原用浓重的朱砂和赭石敷在粗硬的墨线上,远景皱褶起伏的沟壑则用淡赭色和金黄色敷在浅淡的墨线上,拉深了画面的层次,强化了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同时毛主席前方的一片光明,如初升太阳般神圣,使画面雕刻般凝重、史诗般震撼,象征着革命成功后所拥有的美好未来。本幅作品中,石鲁将黄土高原客观的地质物象与自己主观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艺术地熔于一炉,生动自然,寓意深远,看似写景,实则写情,用黄土高原承载自己对主席炙热深厚的情感,达到了情景交融、意与象通的艺术境界。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对传统中国画不断深研,石鲁在中国画笔墨运用和审美境界上有了更多的理解,“新国画运动”的固有认知也产生了改变。1964年其创作的历史巨制《东渡》,就在人物造型和色彩上进行了夸张,初步显现了由具象转意象的蜕变。石鲁这种超前的审美形式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但仍为其后期形式更加自由、情感更加浓烈的绘画风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超以象外,笔简意深
尽管石鲁及长安画派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很大成功,其杰出的艺术才华也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广泛认可,但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来袭,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如上文所述的其丰碑创作《转战陕北》即被污为影射领袖“悬崖勒马”和“走投无路”,《东渡》也被污为丑化领袖,因此石鲁被以“黑画”罪关进牛棚,不得不中断了高涨的艺术创作。“文革”期间,石鲁身心俱残,艺术思想与精神体悟变得更加沉郁尖锐。惨烈的社会现状和无以寄托的情感,让其痛苦难受,只能于笔端倾泻出来。但受环境限制,必须压抑这种痛苦,所以这个阶段他以书入画,创作了大量浓彩重墨、笔简意足的花鸟画和跌宕起伏、瘦硬锐利的书法,来表现自己不屈的决心。
花鸟画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多,如《雨荷图》《骄雪图》《与世无争》《兰宜乎瘦土》等,以荷之高洁、兰之清幽、竹之有节、菊之凌寒,将自己的心志表露无遗。如《兰宜乎瘦土》画面中,石鲁简化了兰花客观物象的结构,全凭主观情绪驱使笔意,尽力挥洒着沉重扭曲的线条,似乎要刻进纸里,刻入心里。整个画面非常简单,但笔势丰富,展现出兰花的高洁典雅和劲挺坚韧,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余地。从本幅作品可以观察到,此时的石鲁已不再关切兰花的形似,只注重自己情绪在画面的充分表达,超越了现实艺术形象的制约,直抵内心。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讲到雄浑风格时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指创作已超越物体表象,直指事物本质,而石鲁的晚期创作无疑已进入此境界。
“文革”期间石鲁也画过一些山水画,如画过多幅《华山图》,均忽略掉华山的山石细貌,只强化华山整体的险峻奇崛,是石鲁高迈精神的现实观照。再如《陕北夕照》,以纯色朱砂描绘出黄土高原的黄昏,画面没有中期创作时黄土高原的坚实厚重,显得恍惚不定,好像隔着时光,就像记忆里的旧照片,带有深切的感怀往事之情,也带有回不去的忧伤之情。由此可见,石鲁艺术创作的晚期,大多借物抒怀,以景寄情,简于象而尊于意,是艺术语言的成熟,也是精神天地的升华。他用锋芒毕露、生涩扭曲、跌宕纵横的线条,发泄着内心磅礴澎湃的愤懑与苦痛,彰显着他对现实的抗争,隐藏着对前途无法消除的绝望。
现在对石鲁后期绘画有一些神秘主义说法,认为其创作受精神病影响,主要依据是1970年石鲁根据退回的其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时的写生稿,创作的《古城堡》《印度神王》《林中少女》《赶车人》《红鹿》等一批作品。这批作品的寓意一直令人费解,加之石鲁后来回忆其创作过程时,说自己是在幻觉中创作的这批作品,似乎每幅画都在描述一个故事,但又记不起故事的具体情节。我认为,石鲁创作时肯定是清醒的,在艺术上是可控的,只是无力挣脱那个特殊社会环境,心有不甘,于是选择彻底颠覆与嘲讽,试图在颠覆与嘲讽一切固有中寻找新生力量。石鲁通过作品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超越了客观物象,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肆意发泄,尽情狂欢。
三、时代丰碑,艺术巨匠
在石鲁短短61年的生命里,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留下大量具有长久感染力的经典作品,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艺术巨匠。他与赵望云等共同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成为当前中国画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艺术观点,也是众多艺术家汲取创作灵感,探寻创作源泉的重要途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熟起来的艺术家,石鲁不但打破了苏式艺术创作的雷同僵化,也对传统中国绘画精神与时代结合做出有益推进,以形式与情感融合的方式为传统绘画的时代新生提供出选择之路。石鲁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取决于他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身处的复杂历史时期,敏锐的艺术感觉赋予他一双慧眼,让他在生活和传统中可以寻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养分,而复杂历史时期带来的变化和反差,促使石鲁不断颠覆旧有观念,不断突破陈规,不断用不合常规的审美视角来观照现实,从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丰碑。
新闻链接
“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
2019年12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
2019年是石鲁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石鲁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多艺术领域皆有建树,其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独创一格,作品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时值石鲁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对于研究和纪念石鲁先生,以及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展览分为革命史诗、时代礼赞、长安新画、风神兼彩四个单元。作品选择着眼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史与美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所形成的语境与情境,呈现石鲁先生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中的创作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以及经典作品创作过程中的速写、手稿和创作草稿。
石鲁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代表之一。1940年起的十年间,他先后在延安的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并创作过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同时他也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30岁的石鲁胸中涌动着激情和强烈的创作冲动,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他深入青海地区、宝成铁路和兰新铁路建筑工地、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
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这是石鲁在5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大问题。1955—1956年的印度、埃及写生之旅,使石鲁认识到: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活跃于陕西美术战线的石鲁始终怀念年轻时参加革命和战争的亲身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创作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石鲁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场景再现,需要艺术家认真思考造型艺术的规律,力求在构思立意上新颖、丰富、含蓄,并对特殊形象和历史事件有具体的感悟,赋予作品革命史诗般的价值。
共和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他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创作的指导思想。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引发了长达两年多的关于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大讨论,“长安画派”由此得名。
长安画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它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其中,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的石鲁功不可没。
1970年之后,经历过肉体和精神折磨几度死里逃生的石鲁,重新拿起画笔。虽然石鲁后期没有再画主题性创作,但在艺术风格和笔墨表现上却更加精到,境界体悟上也更加深远。他的艺术从理想转向精神,从抒情明朗的浪漫转向孤愤苍劲的沉雄,从现实的诗意描写转向形而上自然大道的畅神。他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意,是其后期艺术的神髓。石鲁借助于传统文人画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语言来体现其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以及在特殊年代敢于捍卫真知真理的信念和坚持艺术理念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