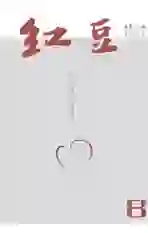写作是沉思的生活
2020-08-19胡弦
胡弦
写作,是触摸生活深处那并非人人可及的零散片段,并把那感觉留住。
生活有种严厉的幽默,类似写作者的孤独。
诗歌强有力地介入公众生活是很偶然的事情。生活是现实的,诗歌是超现实的,在两者之间,诗人应当保持怪诞的安详。
生活的价值,在于它被看见、被注视,不然,它就是白白流失的生活。
诗歌的价值,在于诗人给生活打下个人烙印的能力,也即诗人在自己所处语境中对生活本质的表达能力。但厘清大众身份和个人身份间的区别并不容易,稍一混淆,诗歌就会陷入机械性的泥潭。
对于生活,诗人必须是个亲密的知情者。被理解的生活,远比正朝前滚动的生活重要。
如果只是复述生活而毫无见地,就是盲目的写作。诗歌必须深入精神领域,寻求那高贵的东西。诗人应当直面这个时代的精神,挖掘并整理它们,而不是交给其他人来处理。
要写好一首诗,得对生活有点紧张感才行。要用新的命名進行暗示,从中寻找新的道路和无限性。
相信实证,相信物质,但不要轻信社会意义。要发现被忽视的视角,精确地捕捉到物象,并触及其中蕴藏的精神实质,写出无法归类的东西。
真实性与个性密切相连,它取决于观察者而不是生活。
诗人对生活应当持有强烈兴趣,但对于身边的喧响,诗人不是和大家一起欢呼,而是要去寻求那些声音的源头。
写作,需要生活顺从地保持静止状态。只有浮躁者才认为生活目不暇接,世界并没有变,它仍然是人的世界。但生活的复杂性,往往会使人的标准失效。写作,则是重拾人的标准。
人性没有清晰的轮廓。在生活中,事有始终,人性的开始与结束却不容易辨别。在事件、物象的联系中,准定与模糊是混合的。这不是公众生活的深度,而是写作的深度。写作所触及的,是深层情感的对等物,是存在的神秘性。
诗,是生活的起诉书。
不可能有纯粹的静观,不可能抒写悲伤而无动于衷。
生活中的小人物是被忽视的社会力量,人性弱点更容易不加掩藏地暴露,因而看上去会让人更揪心,要写他们对卑微尊严的寻求,哪怕是带有绝望味道的追求。虚空中仍有人性的意义存在,而且更有不驯之美,能让我们明白,生活的永恒性在于,受苦是不可避免的,救赎总是与苦难相连。这是生活的宗教,也是写作者的宗教,
生活没有征得一些人的同意,就把他们裹了进去。诗歌要表现这些人为之忍受的东西。
诗歌描写危机,提出问题,但不必给出答案。
诗歌可以选择温和的表达方式,但不能没有强硬的立场。
用诗歌描写节日、大型庆典活动是一种坏习惯,它容易使写作者的紧张感被弱化或消失掉。
诗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其永恒性,也即历史纪念意义。
文字有留证和艺术两种功能,诗歌主要对后者负责。
在生活中,发现诗意和写好一首诗是两码事。
任何被描写的对象都有眼睛和心灵。诗要找到它们,表现那眼睛里的恐惧,或眼睛闭上时心脏的跳动。
要让古老的眼睛出现在新的画面中,并传达出不一样的眼神。
诗歌不是一种流行性、潮流性很强的艺术,它和生活的滚动有一定距离。它不一定非要寻求和生活同步,而是可以独立自足地发展。
急于寻找筛选标准和急于断代都是轻率的。感觉比公式重要,年龄则毫无意义。
诗人不必担心自己被公众生活抛弃。寂寞和隔离永远都是幻觉,就像没有完全的世外,即便是一个避世者,山野也会参与他的生活。
诗人不必为自己的声音找不到回声而自责,因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自己的心灵镜像。为诗歌不被公众关注而焦虑是不必要的,因为诗人的坐标在语言中,而不在生活中。
边缘是一个更加广大的空间。实际上,不管生活怎么变化,对诗歌的需求永无止境。
诗,归根结底是极其单纯的艺术,是对生活和语言的嗅觉、洞察力。敏锐的感觉是基本的诗歌哲学。
生活的信息量过于繁复巨大,深思的目的在于学会牺牲。
诗是一种罕见的艺术。诗人的精神世界,在生活那里,是无名或罕为人知的。即便在评论家那里,也常常体现为一种主观叙事。
生活出现在一首诗里的时候需要包含的要素:一是判断性细节,二是物象在其物理之外的特性,三要寄寓于外部世界的写作者的个人隐喻,四具有把物象联系起来的那些关键性的东西,五是表达方式。
知道一种诗歌理论只需要几分钟或几个小时,而知道怎样去写,一生还是显得太短。最难的是对词语的感觉,不同的词以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效果,和对这种效果的理解。
写作应当是一种挑衅行为,哪怕是自己正持有的写作观。
一首诗,应该有一个不能被描述的内部,但词语可以暗示出它的存在,并把它置于注视之下。
物象是一种情感器官。物象更明了它和写作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它会左右一首诗的成败。
发现错觉恍如在制造错觉。要研究哪些是应该被重视的。要理解,并理解理解的局限性。
细节越具体,一首诗就越概括。在深层体验区域,人们的认同感更有一致性。
要有一种训练有素的意识,并以此来确定要写什么,意义何在。一首诗不但要表达出作者的见解,还要让人看到不容置疑的事实。
必须同写作对象决斗。此中过程,任何画意般的修饰都是污蔑。被过度拔高的善良更具欺骗性。诗应当诚实,不能让一个成年人降低到以儿童的心智来接受某种幻觉。
诗,不是激情,是怎样处理激情。
哲思是更高形式的抒情。
诗人是自己心灵的偷窥者。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诗人也是偶尔才能看见自己的秘密。
所有的公众生活都是写作者的个人生活,诗人应当安心地呆在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在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时代,寻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片段,并借以界定人的位置和人性的继续存在。
责任编辑 丘晓兰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