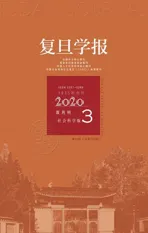契合与超越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现象学原则的关系
2020-06-04刘少明
刘少明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实践”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对这种地位的阐释有多种方式。有的学者从现象学的原初性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构造了一个先于主客二分的“前概念”的生存世界,从而突破了哲学上的知识论局限。贺来教授就认为“生存实践活动作为人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体现和构成了人与世界本体论的原初关系,拥有着优先于人与世界的抽象逻辑认知关系的基础性地位”。(1)贺来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有的学者从具体性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一种类似现象学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哲学(如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时间性显现哲学),从人的生存的历史性的角度看待现实生活世界。

那么实践理论与现象学原则是契合的吗?如果不是契合的话,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呢?目前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够系统。持有肯定观点的学者没有对现象学原则和追求进行细致区分,或者仅仅是从某一两个现象学家(如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角度去比附或比较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持有反对观点的学者的批判对现象学原则的内涵尚未做出更为细致的阐述,同时也未将这个原则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做出更为细致的比较。如王德峰教授所说,马克思哲学对现象学原则既包含又超越的关系,也只不过是对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原则进行了“包含和超越”,而且他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对先验意识的超越的角度来说的。(4)王德峰 :《 论马克思哲学对现象学原则的包含与超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所以学术界尚未回答现象学原则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否契合的问题,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实践理论对于现象学原则的优势。
回答此问题,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阐明现象学的追求和原则。在将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现象学理论进行对比时,不知道原则就没有比较对象。如果仅仅只比较一个或两个现象学家的观点,难免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不仅如此,假如用一些现象学家的理论与实践理论进行比较时,可能出现分歧与差异。但是理论上的不同并不能说明用现象学解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些差异很可能不是涉及原则的,而是细枝末节的。所以抓住现象学的原则才能树立一个核心的标准。第二,用现象学的原则和追求来衡量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看看两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回答两者是否契合的问题。第三,在找到契合点与差异性的基础上,说明实践理论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和超越性。
一、 现象学的原则与精神
现象学作为一个从胡塞尔开始的传统,在一百多年间经历很大的变化。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列维纳斯的伦理现象学、马里翁的溢满性现象学、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等,虽然都是在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传统里面展开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或修改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比如“海德格尔虽然完全承认了现象学的洞见对于哲学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在1927年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中,宣称‘没有唯一的现象学这回事’”。(5)Dermot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如果没有唯一的现象学,我们如何说现象学有其核心精神与原则呢?即使有的话,我们如何在众多的现象学家的学说和形态中把握现象学的核心精神与方法呢?这里我们选取胡塞尔、海德格尔、马里翁这三位对现象学原则进行了细致区分的现象学家的观点,看看他们如何论述自己的现象学原则和方法,然后去发现这些原则与方法的共同点。
第一,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胡塞尔最为人所知的现象学理论是他的现象学方法,即为了回到事实本身而进行的对于客观世界存在性的悬置、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现象学描述和对生活世界的阐述。那么他的现象学原则是什么呢?当代著名现象学家马里翁将他的现象学原则归结为三点 :“第一,‘显现即存在’……第二个原则是‘回到事物本身’……第三个原则是……‘每一个被给予的直观是知识的合理源泉,所有的知识都在直观中被原初给予’。”(6)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on, trans. Robyn Horner andVincent Berrau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2) 16-17.从这三个原则能够看出,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就是通过现象学的悬置和还原,在先验自我的层面,利用本质直观探讨事物和世界如何被显现和被构造的问题。“通过现象学还原,每一个心理过程都对应着一个纯粹的现象,这个纯粹现象都展示了作为绝对要素的内在本质。”(7)Edmund Husserl,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trans. William P. Alston and Geogre Nakhnikian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35.这也就是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的双管齐下,从而实现对于认知如何可能的问题的解决,并通过这种现象学的还原,为科学真理的可能奠定了基础。
第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原则。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看法是同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的追求一致的,即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让“原初”的世界和事物显现出来,从而解决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是,他对胡塞尔从意识的角度来描述现象学的方法表示反对。他认为“‘现象’就是显现,它意味着在自身之中显示自身”。(8)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2) 51.即现象的显现不是通过先验意识的还原和构造完成的,而是它自身的显现。海德格尔所使用的“此在”是一种关系性的范畴,代表着此在原初地生存于世界之中,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关系整体。“这个先在的整体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其形式化的生存论表达就是‘在之中-存在’。它没有指出一个居住在意识中的同一化的自我而解释了同一性——同一性仅仅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才能出现。”(9)宋继杰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这个同一性就是在自身之中显示自身的现象学原则的体现。因此,海德格尔现象学中也存在着一种还原,即还原到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原初关系。当然,海德格尔哲学中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根本的还原,那就是通过“畏”的情绪带来的彻底的悬置,从而在通过面向死亡的筹划中展现的对于世界的重新构造。这种‘在-世界-中-存在’是先于反思性的科学理论研究,也比形而上学的研究更为原初。
第三,马里翁的现象学原则。他提出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三条原则,但他认为胡塞尔的三条原则之间有矛盾。因为第二原则是回到事物本身,第三原则是“直观让现象显现”。(10)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on, trans. Robyn Horner and Vincent Berrau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2) 18.但是回到事物本身的本质还原,本身也是一种被给予。所以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还原,因为还原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被给予。“我提出现象学的第四条,同时也可能是现象学的最终的第一原则 :‘还原越多,给予越多’。”(11)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on, trans. Robyn Horner and Vincent Berrau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2) 17.所以马里翁的现象学走向了一种给予现象学。自我仅仅是一个接受性的自我,接受那个难以被彻底接受的“溢满性现象”。但是马里翁的“接受”理论接受的仍然是原初的进行了现象学还原的世界,一个先于主客二分的先验世界。因为“给予就等于现象”(12)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on, trans. Robyn Horner and Vincent Berrau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2) 21.,这时候尚无主客二分,因为“接收者在接受的东西中接受了自己”(13)Jean-Luc Marion, In Excess: Studies of Saturated Phenomenon, trans. Robyn Horner and Vincent Berrau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2002) 48.,所以在开端处,接收者与被给予之物是融合的。因此马里翁的现象学原则仍然是对于事物本身的追求、对于原初性的追求。原初性的给予先于任何反思性的科学研究。
总的说来,尽管三位现象学家对于现象学的“现象”的看法如此不一致,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最终的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初性的追求。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萨特的非位置意识、列维纳斯的他者都是这种被还原之后的现象学起点,都是遵循着回到事物本身的还原与悬置的方法。尽管还原的方法不一样,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悬置“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理论和“客观世界”的预设,从“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来看待事物本身,从而为突破形而上学、为科学性的反思奠定基础。所以悬置和还原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悬置的是抽象的客观世界的预设和概念化的抽象世界建构,还原是回到事物自身。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原初性的追求。且这种原初性的给予就是一种“显现”,是“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之所以说是一种显现,是因为反思性的方式会毁坏其原初性,所以显现就成了事物自身开放的方式。所以原初之物的给予也可以说成是事物本身的显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现象学的基本的方法就是还原和悬置的方法。
不仅如此,现象学原初显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时间性。时间性对胡塞尔来说是先验意识显现对象的条件,时间性对海德格尔来说是存在之意义,对萨特来说,“人的实在本身被看作是时间性的……其超越的意义是它的时间性”(14)萨特 :《存在与虚无》, 北京 :三联书店,2008年,第145页。,对梅洛-庞蒂来说,“主体性在知觉的层面上除了时间性,什么也不是”(15)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2) 214.,对马里翁来说,“时间作为一个给予,保证了所有受益于它的事物的给予和重新给予他们自身的可能性”。(16)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rans. Jeffrey L. Kosk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245.所以尽管还原之后的原初给予如此不同,时间性仍然被现象学家们一致称为事物显现的先在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现象学的核心精神是让原初之物显现,核心的方法是还原和悬置的方法,还原之后的原初给予显现的共同条件是时间性。这三条标准共同构成现象学的原则。有了这三个标准之后,就可以对现象学原则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对比,从而回答本文的问题。
二、 马克思实践理论的原则与现象学精神是否契合?
(一) 两者的契合点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也有其自身的还原方法,也有对于还原之后的原初给予物的追求,也是对于面向事物自身的追求。但是对于他来说,事物自身取决于不同的还原方法。不同的还原方法会导致不同的“事物自身”的显现。那么他进行还原的方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他实际上进行了至少两重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阐述了现实的感性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两种原初给予之物。同时,时间性和历史性作为被还原之物的共同特征,是马克思实践理论的原则与现象学原则的另外一个契合点。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马克思的实践的原初性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一种对原初性感性活动的描述,反映了超越主客二分的原初性。实践对于马克思来是“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或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这句话里面的“感性”和“世界”两个词非常关键。一般来说,感性是人的感觉和知觉等主体性范畴,而世界是一个多种对象的集合。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将一个代表主体的词汇与代表对象的词汇合在一起,展现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这种还原就如海德格尔的“此在”、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是一种主观和客观在原初实践的活动中所展现的被给予物的统一。“存在物的存在便是对象性关系本身,因为若没有这种作为原初关联的对象性关系,就谈不上任何存在物。”(18)吴晓明 :《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需要注意的是原初感性世界实践活动自身对自身的显现。“人的和自然的这种统一立足于实践,但不是抽象的、还原为抽象‘物质过程’的实践,而是具体生动的感性活动的实践。”(19)邓晓芒 :《 实践唯物论新解 :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这说明现象学还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还原,不是将实践当成自然世界的组成要素,也不是形而上学所谈到的精神对于主观客观在概念意义上的综合,更不是将人的精神进行客观化的解释,而是一种显现意义上的关系。因为是这种生产活动让感性世界显现。而活动就是感性的活动,作为原初之物的感性世界就是在这个活动中被显现的,与这个活动难分你我。从现象学上来说,感性活动是显现条件,而感性世界是显现者。如果将两者分离,就会产生反思性的概念分析,从而陷入二元论之中。因此感性活动与感性世界实际上是一体的,感性世界实际上是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感性实践活动对于感性世界的显现,实现了现象学原则——事物本身的自我显现。离开实践活动,就没有事物本身,而是反思性和异化的“事物”。
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对于原初性的追求还表现在对于抽象概念的拒斥。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和现象学都追求对具体现实的人的生活的描述,反对以抽象的概念为前提。人的活动必须是现实的感性活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感觉,比如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世界也不是单纯的“客观”对象,“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地,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类说也是无”(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自然界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真正被显现。马克思是回到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类似于胡塞尔回到人的纯粹意识的描述,海德格尔回到此在的“在世界之中”的生存,梅洛-庞蒂的知觉对意识和世界的统摄,都是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还原和悬置之后,回到原初被给予之物,然后进行描述与构造。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生存论导向比较强烈,很多学者也正是从具体个人生活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因为具体性最后导向的就是个人的具体的生存。

2. 将实践还原到社会生产关系
将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个人实践的条件,是比将实践还原到个人感性活动更为根本的一重还原。如果马克思对于事物自身,对于原初被给予之物的追求类似于现象学的阐述,从而实现了感性活动自身对于自身的显现的话,那么实践仅仅能从现实个人感性活动层面来理解吗?当然不是的,马克思还面临着交互主体性问题,即个人活动与他人活动之间的问题。因此现实的感性活动是个体的活动,而个体的实践活动又要与他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如何看待个人感性活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呢?显然马克思不认为社会关系就是个体的相加,反而是已经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社会生产关系就是马克思的第二个现象学还原后的“原初给予物”或“事物自身”。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bestimmte)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马克思之所以将人与人之间的原初关系解释为生产关系,是因为它是“先在”的,是一切生产的出发点,“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生产”。(24)亨利希·库诺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517页。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其他关系的解释的出发点,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因此马克思通过对实践活动的显现条件的进一步追溯,实现了另外一重更为根本的还原。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原后的“剩余物”描述为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与胡塞尔的不可还原的“生活世界”,与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共在”、天命,与梅洛-庞蒂所讨论的文化和历史一样,都说明了原初给予之物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是“个体”已经被抛入的那个世界,是他逃避不了的,并作为个体的条件而呈现。
所以,社会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交互主体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马克思的还原是双重的还原。一方面他在破除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将实践当作原初的现实感性活动;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个人的感性活动当成是处于社会经济联系中的活动,也即是个人与他人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当胡塞尔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时,发现“他者”是不能完全被个人构造出来时,这已经模糊地承认了将他人还原到个人构造的不可能性。当然,海德格尔所提到的“与他人共在”实际上也与马克思社会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对于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解释相类似,即承认交互主体性的关系本身就是不能在完全还原到个体的感受之后被建构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个体活动显现的条件,或者也类似列维纳斯的“他者”具有一种不能从自我进行建构的优先性一样,承认社会关系对于个人感性活动的优先性和显现条件的地位。“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这说明还原到社会生产关系的现象学描述是不能用还原到个人的感性活动代替的。
尽管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更多的是指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与其他现象学家对与“个体”相异的不可还原者的阐述(“共在”、“他者”、“文化”与“历史”)不一样,但这里体现的精神是一样的 :追溯不可继续被还原之物的显现及其显现条件。在马克思这里,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显现为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上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且社会关系自身就是那个不可被继续还原和悬置之物,即原初之物。
3. 对作为事物显现条件的原初时间的追问
与还原基础上的原初性的讨论一样,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在时间层面上仍然与现象学一样有着共同点 :追求时间本身,为异化的时间和变异的时间找到原初的时间基础。这个原初时间是原初感性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样态,是它们显现的条件。马克思对于时间的讨论包括了个人时间和社会的时间。
首先,个人的时间性。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将真实的时间建立在个人感性的活动,即劳动过程之上。马克思对于劳动与劳动时间的区分展示了原初的时间是人的实践而不是数字化的时间,更不是表现为价值的时间。经济学的时间是对于原初人的劳动的一种社会交往化的变异。而这个原初的人的劳动就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当然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最原初状态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异化与本质的关系问题这里暂时不考虑,这里只考虑感性实践活动与抽象时间之间的关系)。感性实践活动表现为一种原初的过程性,也就是原初的实践。“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179页。因为实践活动是人去改变对象的过程,改变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所以实践也就表现为时间性的实践,而不是一种图像化的摄影。
之所以称这里的过程为时间性,是因为它为一般的计数的时间奠定了逻辑基础。一般数字化的时间是人的实践过程的抽象化和凝固化。“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知识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的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的知识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9、179页。所以,真实的质的劳动时间变成了量的劳动时间。而现象学的时间也倾向于回到个人的意识、生存、知觉等原初的时间之上,认为数字化的时间是对原初时间的变形和抽象。比如胡塞尔的时间性是原初的“感觉滞留-当下-前摄”的统一体,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是此在筹划性地重演历史而做出抉择的时间性,梅洛-庞蒂的时间是“过去-知觉-筹划”的统一性时间。现象学家们在阐明自己的时间时,都认为科学化和数字化的时间时原初时间是变异和抽象化。因此在个人时间性的阐述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仍然遵循着回到“时间本身”的原则,将实践原初看成是质的过程。
其次,从社会时间来说,作为显现条件的时间性,本身也是一个原初的统一时间整体。当下的实践是在历史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也是被未来的理想所牵引的。过去的维度表现为历史视域。实践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生产关系下的历史。历史对于马克思的实践来说是一个条件,而现象学的具体性也与历史性紧密相连,历史总是现象显现的条件。这与上面探讨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实践活动显现条件是一样的。
从社会时间的未来维度来讲,“真正的时间性乃是实践对人的未来可能性的开启,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诞生活动”。(28)何中华 :《历史地思》,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人们实践活动的一个显现条件就是未来维度对于人的实践的引导和显现作用,也即是实践本身仍然是有其指向性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168页。所以社会实践一方面显示为过去的历史积累出来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又是被未来所牵引。社会历史的过去和未来就在当下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原初的时间性统一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料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168页。原初性的时间统一体是一种显现条件,是自然化时间的显现条件,而非反思性的自然化的编年时间和数学性的时间。
(二) 二者的不同点
虽然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包含双重还原的原则,与现象学的还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先于主客二分的原初之物的追求,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作显现的先在条件而不能进一步被还原来看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感性实践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的阐释与现象学精神有一定的差异。差异的核心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所以他没有将现象学原则贯穿到底来构建一个体系,仅仅是树立了一个对于原初的感性实践活动和原初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追求。所以在具体的阐述时,他更多的是从反思性的概念出发来进行的,从而与现象学的原初之物的显现原则发生偏离。同时,马克思对于时间与历史的论述也因为现象学原则的不明确性,同时受到改变世界的迫切性要求,从而与现象学时间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下面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1. 对待科学化和反思化的真理观的态度不同
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主要是反对观念形而上学的以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世界的真理观,但他并不认为哲学的真理为科学的真理奠定基础。他用实践真理去反对形而上学的真理的核心在于“证明”,从而有类似实证主义的符合论真理的特色。验证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提前设想了一个世界,然后用感性实践活动去证实已有的对于世界的设想的正确性。而设想是一种反思性的概念与理论。通过验证和证明,人的思维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得以可能。因此,在阐述了原初性实践性活动的同时,他对于真理的阐述并不是在原初性层面来进行的。因为原初性的感性实践活动本来应该是反思性的概念的基础,是先于反思性概念真理的,而这时候反而成为了一种去验证反思性概念真理的方法和手段。这种通过建立概念然后去验证的符合论真理是一种经验科学的反思化与实证化的真理。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的最终目标不是为科学化的和反思化真理建立一种基础,反而是认为实践真理就是一种科学化和反思化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规律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它追求的是对于客观规律的描述,哲学真理因此被科学化。
而现象学更多的是去回答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认为反思性的概念和理论有一个前概念的世界作为真理的基础。就如胡塞尔所说“生活在这个生活世界中的人(包括自然科学家),仅能将他所有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放置于这个世界之上”。(32)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David Carr (Evans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海德格尔也认为反思性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原初“在-世界-中-存在”的真理的揭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区别在前期表现为“应手之物”和“现成在手之物”之间的区别,表现为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后期表现为存在的揭示对于反思性真理和符合性真理的优先性。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的真理观,都表现出现象学真理对于科学真理的原初性。所以马克思在真理观上,并没有将对原初性的追求的现象学原则贯彻到底,而是采用了一种经验科学的实证真理观。从而,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与现象学的真理观就分道扬镳了。当有学者认为“思维的真理性有待于实践去检验,不能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这一点,而是应该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看,实践的思维是特定实践的自身意识,是被意识到的人的存在状况”(33)李君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存在论》,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时,表面上是对马克思的真理观的原初性意蕴的揭示,但这种说法恰恰说明马克思对于原初性真理与科学化真理之间的区分不够明确,而是将原初性的存在论与衍生性的认识论不加区分地使用了。实践理论在真理观上并没有将现象学式对原初实践活动的追求贯彻到底。
2. 马克思贯彻现象学原则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在实践理论上是有着很强的现象学式的还原精神的,那就是对于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客观世界”的悬置,对于离开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人的感性活动的悬置。马克思的这双重还原现象学让他在实践理论的核心处与现象学有着同样的追求。但是马克思在还原层面并没有对“客观世界”的悬置贯彻到底。原初性感性活动对于感性世界的显现,是主客二分的基础。那么主观和客观如何统一在一起的呢?“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客体也在不断的主观化。这个阐述中,虽然主体和客体通过实践活动统一在一起,但这个表述中已经有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客体’的模式并不是被彻底抛弃了,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35)李志 :《马克思的个人概念》,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实践在这里更多的是充当一个中介的作用,而不能成为哲学上的主客二分的逻辑基础与显现基础。或者至少说,马克思并无意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构建一个世界的显现体系。那么为什么在具体的阐述中马克思没有将现象学原则贯彻到底呢?
第一个原因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的现象学原则,不会在每一个哲学阐述中都自觉从如何先于主客二分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来构建世界、历史和社会,容易滑入“自然状态”,也就是容易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阐述世界。“悬置的本质特点就是施加一个改变,或者‘态度的转变’(Einstellungändererung),让我们从关于世界的自然假设中抽离开。这个自然假设包括我们日常行为指向的对象,也包括我们工作于其中的复杂的自然科学。”(36)Dermot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47.马克思在具体的表述中,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悬置“客观世界”的现象学原则,也就很容易进入一种自然状态。这从他对费尔巴哈的自然界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这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先于人的自然界是未被人开发的自然界,是未打上人的实践色彩的自然界。这恰恰是设定了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因为那个珊瑚岛毕竟被发现了,只是仍然未被开发。同时,由于他无意对自然科学的知识进行悬置,所以也无意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先于主客二分的彻底的实践现象学的构建。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目标是为了去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谈世界如何在感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显现和被构建。在历史观念上,马克思持有的是同样的态度。现象学的历史性是一种显现,而马克思虽然认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是生产性的条件和逻辑基础,他更多的是希望去改变历史,改变世界,并非仅仅是为了让存在者在历史的角度上显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搜集资料,总结规律,指出人类的方向,指导人的实践行动。“规律”只可能是在反思层面才能得以完成。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实践理论的反思性和第三人称特征比较明显,即将社会与人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所以他并不反对从概念出发,反而认为只要概念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就能真正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点反而也揭示了现象学的一个缺点 :用概念的表述来追求原初的先于反思的源初之物的显现。实际上马克思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原初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虽然作为哲学基础能够去解释世界,但是有效果的还是对象化思维的规律总结。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可能仅仅志在实现现象学哲学的体系化。
3. 在自然态度中构建理论
马克思的实践时间理论方面,往往是将原初感性时间和自然时间混用的。他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保留了自然态度和自然科学时间,所以他经常是站在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时间和历史的。这种自然的历史关系表现为用因果关系、用编年史关系来看待历史。比如在对待社会关系的态度上,“这种关系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成员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38)亨利希·库诺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517页。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是现在的关系显现了过去的生产。将现在的关系当作过去生产的结果是在显现关系基础之上的知识重构的结果。所以尽管他在哲学基础上看到了原初时间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性,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显现的条件,但他并没有将对于原初的时间性显现的现象学原则贯彻到理论的所有角落。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与马克思对于原初之物的态度是一样的。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没有明确的现象学还原的原则。所以尽管他指出了原初的时间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提出了个人感性活动对于经济学时间的奠基作用,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所有实践活动的基础,更是反思性的基础,但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中,他更愿意使用自然化和编年的历史时间,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在原则不是自觉的和明确的时候,就不会应用到理论的全部细节,也没必要应用到全部细节。
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去发现历史的规律,论证实践活动的未来导向,并因此预言历史的具体走向。比如,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39)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61页。显然,单纯地由历史与未来的时间统一性是难以表达这种时间过程的。这里的“时间顺序”是一种自然编年时间,它更有效地表达了原始积累的地点转移和积累方式的变化。或者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时,当然是从量化的数学时间出发来谈资产阶级的实践活动,这时候量化显然更为有效,更具有冲击力。所以,很多时候“自然”态度比单纯地谈论历史和实践的显现更有力量,更有效果。尽管这两种时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时间,但马克思无意在原初显现层面停留太久,而需要在编年时间的世界里解决实际问题。
三、 马克思实践理论对现象学原则的契合与超越
从马克思实践理论与现象学原则在对原初性的追求来看,两者都追求回到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现实感性活动和先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两者是先于主客二分的还原“剩余物”,是一切思考和活动的起点。马克思通过对原初性的追求超越了抽象唯物主义和概念性的形而上学。同时原初之物本身是时间性的,对于原初之物的追求也展现了作为原初之物显现条件的时间性。因此他在时间性的问题上仍然遵循的是回到时间本身的现象学态度。因此,从原初性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双重现象学还原是现象学式的,这与现象学原则是契合的。
但是,由于他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他的实践哲学并不追求将对“客观世界”的悬置原则和原初性的追求贯彻到底,因此在很多的阐述中仍然使用的是自然态度,即主观与对象的矛盾及其解决的模式进行的。在时间问题上他也更多采用的是自然历史的时间,而不是原初的感性活动的原初时间,也不是仅仅让过去在现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显现。即使在将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作为显现的条件时,“由于马克思是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所构建的历史现象学,始终是伴随着他的经济学科学的创造性思想实验发生发展的,他并没有在经济学之外以纯粹的话语直接表述历史现象学”(41)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5页。,所以他的实践更多的是经济关系上的实践。因此,马克思没有在经济实践之外构建他的更广意义上的实践现象学,而是去完成改造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体系。
马克思实践理论对于现象学原则的“半坚持”,恰恰展现了实践理论对于现象学原则的超越和优势。因为现象学原则仅仅追求回到事实本身,仅仅是让事物显现的一种解释性理论,没有更好地提出改造世界的力量。但是实践的对象化阐述更有利于达到他的目标,因为实践是在对象化世界中改变世界的力量,从而能够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这也是马克思对于一般哲学理论的超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