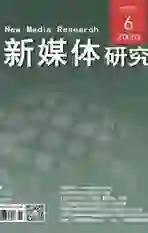数字劳工理论视域下网络用户的情感劳动
2020-05-28江颖
江颖
摘 要 Web3.0时代悄然到来,用户在互联网中的自主创造能力也不断提高,逐渐呈现出“劳工化”趋势。文章基于“数字劳工”理论,聚焦数字劳工的情感劳动,创新性归纳了情感劳动的三种类型,即表演规制类、间接引导类、搭台唱戏类,揭示了当下的互联网行业将用户的情感劳动化与商品化、剥削网民劳动成果、规制用户情感表达来实现资本积累的根本目的,同时辩证承认情感劳动的社会价值。因此,情感劳动区别于传统的劳动剥削,是剥削与赋权的交织与结合。最后从微观层面强调用户应提升媒介素养,避免情感异化。
关键词 数字劳工;情感劳动;剥削;赋权
“众包”一词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是一个褒义词,是集体智慧的体现。尤查·本克勒在《网络的财富》中追溯了网络价值的产生过程,互联网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平台,允许用户利用自身特长、知识与资源生成内容,为其他用户提供服务。实际上,在互联网内容的大规模生产中,大部分是由互联网用户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内部员工的劳动,数十亿网民都成为托夫勒口中的“产消者”。用户在微博、微信、知乎、B站等社交平台、资讯平台发布心情、分享经验时,都扮演着“线上工人”的角色,为平台带来流量与价值。因此,在互联网技术带动下,新时代劳动形式发生了变迁,网民变成了数字劳工,内容消费变成了数字劳动。
1 数字劳工与情感劳动
1.1 数字劳工概念的提出
互联网使得传统封闭式生产向开放共享式生产转变,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产消合一者(Prosumer)”概念,他预言消费者与生产者将融为一体[1]。“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则最早出现在2000年,由意大利的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中提出,他将互联网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免费劳动”定义为“数字劳动”[2]。2014年,英国学者福克斯又提出了“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概念[3],来指那些在互联网中进行内容生产的用户,他们从事数字内容生产的行为往往繁琐而又卑微,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却不被视为“工作”。
“数字劳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达拉斯·斯密塞1951年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的延伸。用户沉迷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表面上是在享受免费的消遣和娱乐,实则却是在为互联网平台免费生产内容,进行无偿或者收益与付出极其不对称的数字劳动。学者吴鼎铭指出在Web2.0技术加持下,互联网产业将网民的“集体智慧”进一步劳动化与商品化[4]。
1.2 情感劳动概念的演变
上述的数字劳动实质上也是一种非物质劳动,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种形式,其中一种非物质劳动就涉及感情的生产和控制,并要求虚拟或实际的人际接触。这里的情感劳动就囊括了生产或操纵娱乐、轻松、快乐、兴奋等情绪的劳动[5]。在信息资本主义下,“情感参与”与“用户影响”是价值的来源[6],人的情感劳动具备了劳动力价值属性。美国情感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一概念:“为了收入,员工按照组织要求控制自己的情感,进行符合标准的面部表情或身体表演”[7]。在之后的研究中,“情感劳动”的适用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企业员工的情感劳动。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就将情感劳动概念延伸开来,指代真实或虚拟的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实践[8]。
综上,“数字劳工”超越了“受众商品论”,将受众的研究视角转移到受众的劳动上来,这种转变不是将受众的时间直接看成一种商品,而是将其产生的价值看成一种商品。“情感劳动”则延伸了“数字劳动”概念。但是,国内大部分情感劳动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对象多聚焦家政、教育、养老、酒店、医疗等传统服务业,比如关注企业管理中的情感劳动以及社会分工中女性的情感劳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影响情感劳动的因素、影响以及应对策略上。目前少数几位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行业的情感劳动,但是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批判或是对情感劳动的理论渊源进行梳理。学者陈璐认为粉丝所参加的集资应援活动是娱乐工业对粉丝情感劳动的利用和剥削[9]。胡鹏辉等学者认为网络主播直播过程就是一种情感劳动,其实质就是资本对情感的控制[10],但是尚未对数字劳工的情感劳动这一现象进行综合性的分类和总结,也未肯定理解数字劳工情感劳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合理性。本文将总结数字劳工的三种情感劳动类型,并从正负两方面对情感劳动进行评价。
2 数字劳工的三种情感劳动类型
在数字劳工理论视域下,用户的社交行为和情感表达、粉丝的忠诚度以及网络主播的情感展等情感行为都可转化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数字化资本,本文根据平台、资本等因素对“数字劳工”情感劳动影响大小的不同,总结了数字劳工的三种情感劳动类型。
2.1 表演规制类
表演规制即用户作为数字劳工在互联网中并非自由,其行为和情感表达会受到平台显性或隐形的控制。霍克希尔德提出“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两种情感展示策略,也间接说明情感表达并不是一种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表达,任何有策略指导的、带目的性的情感表达都是缺乏真诚的表演。在这类情感劳动中,平台的作用较大。
网络直播的魅力就在于博主与观众之间的实时互动性,扩展了博主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表达空间。网络直播平台吸引用户成为主播并无偿、自愿炮制各种免费内容供其他用户消费,观众无需付费订阅,可自由决定打赏[11]。在打赏机制和成名的想象驱动下,大量用户又加入主动生产内容的行列,成为“产消者”。网络主播的博主和观众都是为网络平台增值的数字劳工。
为了在利润分成、流量扶持和IP培养方面更有优势,直播博主往往要加入直播工会。直播工会会对主播的情感表演策略進行指导,对主播本身的情感展示规则也有一定的约束,如主播的服道化、开播时间点、直播时长、内容策划等方面,同时柔性控制主播在适当的节点“释放”自己的情感,获取用户的共鸣。胡鹏辉和余志强的研究表明,加入直播工会的网络主播往往采用标准化、模式化的方式与观众互动,其深层表演策略是影响主播与观众互动频词的重要因素。同时直播工会会引导主播进行不同的情感表演策略来展现符合要求的情感状态,以更好地满足观众的期待,这一过程会削弱主播个性化,加快主播情感耗竭[10]。
由此看来,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也契合阿多诺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工业”的概念,同机械复制的工业生产模式类似,网络传播时代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标准化、复制化、统一化的倾向。
2.2 间接引导类
这类情感劳动是指平台抓住用户的情感,通过制定规则引导用户进行情感输出或为情感付费等,间接将情感“劳工化”。如随着粉丝文化兴起,平台通过点击打榜、捆绑产品销售来吸引粉丝为爱豆助力。费斯克在上世纪就粉丝文化的经济价值,粉丝在其追星活动中对爱豆的情感投入,能够让粉丝群体产生快感,粉丝文化因此具有了商业价值。资本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将粉丝文化的经济价值挖掘出来。
一方面,粉丝群体深谙流量数据是互联网时代的不二法则,流量的存在将无形的情感劳动进行量化。粉丝为周杰伦数据打榜数据,就是这种粉丝与爱豆之间情感联结的量化表达,这种情感的联结成为一种无形的数字资本,粉丝的情感输出就是一种无形劳动,为微博供流、增值。
另一方面,“销量=带货能力=艺人商业价值”这一等式在数字资本逻辑下已成了黄金法则。因此除了打榜之外,平台还联合品牌方,借势爱豆的应援活动提高产品销量。如《创造营2019》节目方将打榜通道与产品销售捆绑起来,粉丝要想为偶像投票,就必须购买指定产品,资本方就这样间接将粉丝对爱豆热衷产品销量挂钩。其他涉及明星营销的应援活动还包括各种在线投票、提升在线视听资源的点击率、参加网络讨论以提升明星曝光率等活动。这些粉丝自愿进行的活动而今都是在平台的引导、粉丝群背后的娱乐公司的支配下完成的,自愿参与的背后仍摆脱不了规制的隐形强迫、粉丝群的群体压力,粉丝在参加应援活动时,就间接成为平台、娱乐公司等资本群体的无薪员工[12]。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粉丝或者情感本身并非天然存在的,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虚假欲求和自我想象,激发了粉丝们的消费欲望、意义生产,特别是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对偶像、对技术的情感投入或狂热追求,更多是以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本或商品的面目出现。
2.3 搭台唱戏类
此类情感劳动中,平台对用户的影响最小。表面上,平台本身不对用户进行刻意的引导和规制,只是用户情感输出和表达的渠道。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用户在平台上的情感劳动成果,会成为平台吸引用户、品牌营销和变现的资本。
以网易云音乐为例,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就是用户UGC创作的平台,往往有“网易故事会”之称,受众在评论区点评、分享、点赞,都是在不断为平台制造内容,同时这些内容又起到拉新、促活、留存、转化的作用。此外,网易云音乐还曾利用用户的评论进行营销,将UGC印刷在地铁站和农夫山泉瓶身上,将无偿内容变现,成为自身营销资本,扩大品牌资产,同时更加激发了用户写评论的激情[13]。
小米也不断吸引米粉无偿贡献自己的需求和创意,使得用户参与到小米产品的设计和口碑传播过程中。评论、弹幕、树洞类App的倾诉内容都是用户在内容使用过程中的情感表达,零碎的情感输出也在不经意间成为网络平台吸引用户、活跃社区的工具。斯迈兹的“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的论说在此也适用,放松与娱乐也是为工作赋能。用户听歌看剧等休闲活动中的所想所感都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工具。
3 情感劳动:剥削与赋权的交织
学者冯建三曾提出:互联网技术所催生的参与与分享的生产模式,究竟是資本剥削的无偿劳动,还是赋权用户呢?[14]其实二者兼而有之,数字劳工的情感劳动是剥削,也是用户话语权提升的体现。
3.1 从外在劳动剥削到内在情感剥削
在数字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曾被哈贝马斯等学者喻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商业利益的工具。众多网民在商业意识形态召唤下,试图建构“平等、互动、参与”为核心的赛博空间,营造一种“想象的参与的胜利”,作为“数字劳工”推动互联网行业进步:他们一边享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一边“贡献”着代表商业网站价值的流量。数字劳动从众包到情感劳动,用户从“商品”到“数字劳工”,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它将网络用户好奇心、忠诚和消费欲望等情感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数字化资本,形成了“情感经济”。实际上,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自主性,恰似戴着镣铐跳舞,是在一个被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所拥有的小部分权力。
而且通过聚焦数字劳工的情感劳动,可以发现,资本不仅通过控制行为获利,也逐渐深入“数字劳工”的意识形态和情感,情感也被异化成为价值工具。吴鼎铭等人指出,网民情感在新型产业增值模式中被商品化与劳动化,从而导致精神价值与理性交往的社会整体性缺失[15]。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个人的一言一行、一颦一蹙都将可能被转化为线上数据,沦为资本增值的重要一环。
3.2 参与式文化下的赋权
情感劳动终究还是一种主体性的生产,在劳动时间、地点、工具、内容上具有自主选择性,数字劳动者可以个性化地进行自我表达。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会获得满足和认同感。早在传统媒体时代,亨利·詹金斯就提出参与性文化的概念,其认为受众是有主动性的,他们通过阅读观看媒介内容,然后参与到内容的改造或创造过程中去,形成自己的一种文化。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情感宣泄、故事的分享都是基于主观意识完成的,也是用户参与文化创造、情感抒发、寻求认同感、强化社交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为了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人类本质[16]。
因此在采取批判性态度来看待情感劳动的异化现象时,也应该看到情感劳动对产业发展的正面影响、对用户关系的改善。因此,情感劳动的剥削维度与传统的劳动剥削、资本剥削的单向过程并不完全相同,而是一种剥削与赋权动态交织的过程。
4 结语
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互联网技术既带来了自由,也衍生了新的奴役机制,但是任何人和制度都无法完全抵抗用户劳工化趋势,但是在微观层面上,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显得极为重要,应适当参与消费性活动,重塑公共空间的积极公民身份,避免让自身情感为资本奴役和驱使。
参考文献
[1]Toffler,A.The Third Wave[M].London Pan Books.1980:281-283.
[2]Terranova T.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Social Text,2000,18(2):33-58.
[3]Fuchs C.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M].New York,Routledge,2014:34-36.
[4]吴鼎铭.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5.
[5]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108-109.
[6]Jernej Prodnik.A note on the ongoing processes of commodification:from the audience commodity to the social factory[J].triple:Communication, Capitalism&Critique.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2012,10(2):274-301.
[7]Hochschild,A.R. 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8]Michael Hardt,Foreword: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The Affective Turn. New York:Duck University Press,2007.
[9]陈璐.情感劳动与收编——关于百度贴吧K-pop粉丝集资应援的研究[J].文化研究,2018(3):123-134.
[10]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2):38-61.
[11]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娛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4):1-12.
[12]林品.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及其政治转化——从“鹿晗公布恋情”事件谈起[J].文化研究,2018(3):99-107.
[13]胡婷.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网络受众“劳工化”探究——以网易云音乐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9,5(12):16-17.
[14]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5):141-149.
[15]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6):21-25.
[16]刘芳儒.情感劳动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J].新闻界,2019(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