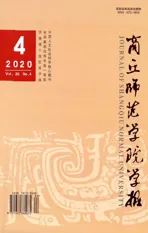“鹑火三月”索解
——殷人对春分实时观测的记载
2020-04-21贺汪泽
贺 汪 泽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31)
《甲骨文合集》[1]五册11501片(图1) 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一片刻辞 ,后经甲骨学者缀合,成《甲骨文合集补编》[2]2813片(图2),意思表达得更完整,惜其仍有二字残缺,不可识。

图1 图2
现整理于下:
这不是卜辞,而是实时观测天象的记录,应入记事刻辞类。对这条刻辞说的什么不作深入细致解读,是不知究竟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大采”。
“大采”何义?《甲骨文合集》五册12814片正:
乙卯,卜殻,贞:今日王往于敦,之日大采,雨?王不往?
《甲骨文合集补编》3643片正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乙卯,卜殻,贞:今日王往【于敦】,之日大采,雨?王不【往】?
《甲骨文合集补编》3770片:
庚辰雾,大采雨?
甲骨文有“大采”的记载,也有“小采”的记载。《甲骨文合集》七册20397片:
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延伐瞿羊,日唯启?
“延伐瞿羊,日唯启”,等雨停,天放晴时再宰羊。四条卜辞结合起来看,“大采”“小采”应是一种仪式,因这种仪式在采集现场举行,大王还要像耤耕仪式那样亲自操作一番,不可能冒雨参加,故要卜天气好坏。采礼,本从采集为生活主要来源时代延续下来的风俗,当狩猎、农耕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后,采集业退居次要地位,但作为一种不忘大自然恩赐的纪念活动,还是延续下来了。为什么有大采、小采的分别,还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回到“鹑火三月”这条刻辞上来。“采日”之上似缺“大”字,“大采日”与“大采”相应,言此日在“鹑火三月”,是一有异常天象的日子,值得一记。
有学者认为,“大采”“小采”为表一天早餐前、晚餐前的两个时间点。甲骨文有旦、中(午)、昃、昏(夕)四分的习惯表示法,更细的划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也与“大采日”的前缀不相应,故不取。
四个大障碍扫除了,这段刻辞就能读懂了:
夏历二月(殷历三月)这一天,黄昏时分鹑火星出现在东边天际。行大采礼时,一团灾云从西北方向袭来,云与云碰撞,发出一声巨响。隆隆的雷声过后,暴雨倾盆。看来今年不会风调雨顺了。
电闪雷鸣,是暴雨的前兆,后面补出的话是灾云造成的必然结果。夏历二月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春分。当时尚没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还只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节。该刻辞点出三月(夏历二月),不言而喻就是观测春分天象。
鸟星,或曰鹑火星,是东边天际黄昏时分出现的一颗最明亮的恒星,下面这条验辞没有点出月份,我们不可贸然判断是观测春分天象,但对理解前面这条刻辞有帮助,也引证如下:
乙巳,夕,有饮于西。(《甲骨文合集》五册11497片)
这是整板卜辞的验辞部分,前有卜辞、占辞。“鹑火星”称为“鸟星”,字形较前者简省。《尧典》也称其为“鸟”,所指为一物。以前学者将“卯鸟”连读[3]28,意会为杀鸟仪式。既然人祭仪式(伐,以戈砍头)都举行了,还来个杀鸟仪式,已无必要。施,陈设;卯,将牲肉析成几大块,放在鼎中烹煮。施、卯,都是祭的后续动作。前面的占辞已提到“有祟”,会出现虹霓(即“饮”),末尾又验证虹霓在西边天际出现,记下的也是灾异,警醒当政之王要敬天礼祖,才能逢凶化吉,求得年岁的平安。

戊寅卜:贞有饮?
前卜阳日,后卜有饮,饮而为虹,不言自明。后世称“虹”,以虫状其象形,因为蛇也是虫。蛇蠕形动物,表皮也有七彩闪光,不谓不像,然并未沿袭殷民“饮于山涧”的传统认识,作了另类的解读。上面这段甲骨文就可以这样解读:
当天傍晩,有长虹现于西天。
一年四时是天气变化的节点,提示殷民农事安排作好新的准备。殷王在春分来临之际,要举行观天活动,敬天同时还要祭祖,这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条验辞有日期:乙巳;乙日祭乙祖,是殷代常例。因未记月份,只说鸟星出现,还不足以判断是春分之祭。不过,于我们理解四节在殷代的重要性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再看看后来的史籍是如何记载的。关于鹑火星所在方位,《尧典》说: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嵎夷,东海之滨;旸谷,观日出之所,有说是日之所居。司天官来到滨海之地,在晨光熹微之际,观测日出的方位和时间点;傍晚,昼夜均分的时刻,又观测鹑火星出现的方位和时间点,由此确定春分的准确时辰。依此说,鹑火星为东方之星是没有疑义的。四方风名甲片也有相似的记载:
东方曰析风,曰协。(《甲骨文合集》五册14294片)
《尧典》说“厥民析”,甲片说“析风”“协”,都是说春分到了,开始用耒翻松土地,经过一冬的休整,又要辛苦劳作了。这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但是,《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却是另一种说法:
南宫朱鸟……柳为鸟注(喙)……七星,颈……张,素(嗉)……翼为羽翮……(括号中为《汉书》相异文字)
朱鸟即鹑火,鸟喙、颈、嗉、羽翮即鹑首、鹑火、鹑尾;所谓柳、七星、张、翼正是南宫朱雀七宿(东井、舆鬼、柳、星、张、翼、轸)中的四个星团。

《尧典》东方观鹑火,定春分日;南方观火星,定夏至日;西方观昴星,定秋分日;北方观虚星,定冬至日。四星配以四时,明明白白,都能从星次、星宿中找到依据,只是当时缺乏系统的记载(1)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天文篇,罗列二十八宿次序依《汉书·律历志》,不与《尚书·尧典》《史记·天官书》东、南、西、北的次序同。,尚处于完善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弄错一个时区,就会有大幅度的偏移。历代的《尚书·尧典》注释文字,总想弥合两者的分歧,以致怀疑甲骨文四方风名记载是否有错讹。如何解开这个疙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古人一直以为恒星是不动的。人生不满百,一个天文学家终其一生,光凭肉眼,没有精密仪器校准,发现不了恒星的位置有什么变化。甲骨文记载的天文现象,经过一千多年,与司马迁观测的天文现象对比,还是不是一样呢?原来症结在这里!
恒星不是不动,而是动得很慢。都是实时观测,殷人沿袭夏人的观念,一直认定鹑火星在东方,没有发现有偏移;历史车轮转到了汉武帝时代,全面修订历法,认认真真重新实时实地观测,这就是《史记·天官书》记载鹑火星(朱雀)在南方的根由。这种偏移现象晋代虞喜已经发现,当时称之为“岁差”,发现太阳循黄道向西退行,每50年移动一度,虽精确度有待提高,然有了岁差概念,谜底也就揭开了。
不过,跨一个时区(十二月均分),大约要2160年;跨一季,则有六千余年。从公元前104年往前推,跨一月,进到了夏初;跨一季,则在八千年前,进到了母系氏族公社时代[4]34。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从汉武帝年间至盘庚迁殷才一千二三百年,偏移还不到一个时区,如何有了东、南之别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东,有正东,还有偏东;南,也有正南,还有偏南。两个相邻的方位,容易出现模糊的判断。也许殷时已经偏南了,因为传统上一直认为鹑火在东方,实时观测也就沿袭不改了。而汉武时期天文学已有很大的进步,发觉传统记载已严重脱离实际,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所以作了纠正。反正有了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弄清了这条刻辞的原委,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以确切的事实证实殷代已有对春分的实时观测,与四方风名的记载互相印证,见证了殷人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第二,告诫我们对晚出的史籍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如果盲目地以《史记》《汉书》去订正甲骨四方风名及《尚书·尧典》的记载,就会凿枘不入,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2)《尚书正义》言:“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依《史记》《汉书》,将东方改为南方。张道勤《尚书直解》在注释“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时写道:“星鸟在天方位,指日落星明时,恰置南方天幕之正中”;称“日永星火”之“星火”为鹑火,“昏后日落见时火星居南方天幕的正中确定中夏时刻”;称“星虚”“指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星”;称“星昴”为“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星”。这种释义勉强牵合《尧典》与《史记》《汉书》之间的岁差,造成混乱。现代注释普遍采取这种模式。笔者有家藏1879年刊刻的《五经备旨》,其中《尧典》眉批:“尧典中星月令不同者,天道三十年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这条批注证明康熙年间(此刻本有康熙御案)学者已运用岁差知识解释《尧典》记载不与《史记》《汉书》同的原因,只是未精确测定变之速率罢了。。
第三,“鹑火三月”的记载不是孤立的一例,由此对甲骨文其他天文现象的记载,如日月蚀、彗星等,增强了信任度,不只为古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而且也为殷代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一批可靠的支撑点。
第四,从鹑火星由东向南偏移现象的记载,可以倒推古代中国观察天象指导农业生产已有六至八千年的历史。天文现象是最准确的年代坐标,古代中国在六千年以前进入农耕社会,已经不是传说,而得到天文年代学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