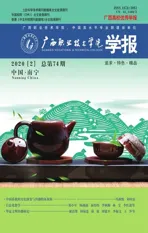稷下学宫时期齐国的舆论营造
2020-03-15王笋
王 笋
(淄博职业学院动漫艺术系,山东 淄博,255314)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重要命题,认为公元前600 年至公元前300 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很多非凡的事都在此期间发生,并影响当今世界。[1]在这一时期几乎同时出现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院,这两个高等学府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分别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和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自由宽松的舆论氛围。
稷下学宫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位于当时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历经齐桓公午、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齐王建六代,前后历时约一百五十年。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各个学派。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子、田骈、慎子、申子、彭蒙、鲁连子、荀子等,都曾作为稷下先生在此讲学或教化齐民。在此期间,稷下之士或独立完成了《宋子》《田子》《捷子》等学术著作,或参与编撰了《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等著作。在那段时期,齐国通过王、士、民三级在齐地营造了整体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作为齐国乃至当时东方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的兴盛促成了当时有名的“百家争鸣”盛况的产生,为齐国奋发图强、建立霸业夯实了理论基础。稷下学宫见证了田氏代齐后齐国的兴衰,见证了古代中国人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1 舆论学视角下的研究对象
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属于舶来品。1762 年,法国著名学者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公众”和“意见”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舆论。[2]中国学者刘建明在《舆论学概论》中认为,舆论的“狭义概念是指某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多数人对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的多种意见,各种意见的综合或纷争称作舆论。”[3]陈力丹教授在其《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意见当同时具备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问题、舆论自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时,则该意见可视为一种舆论。[4]谢清果教授认为华夏舆论研究主要可包含三个面向:一是舆论的传播主体,即公众的言论发声,就古代中国舆论环境而言,需要尤为关注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二是舆论的接收方,其中往往指社会上层建筑;三是基于社会整体结构功能变迁,考察古典社会制度与舆论之间的关系。[5]
在《说文解字》中“舆”指“车舆也”,作“车厢”解,《道德经》中“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中的“舆”即为此意。“舆”常常又与赶车、造车之人相联系,如《周礼·考工记·舆人》中“舆人之车”中的“舆人”就指造车之人。后“舆”渐作“众、多”之意,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听舆人之诵”中的“舆人”就指“众人”。“舆论”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此处“舆论”即为“众人之论”的意思,其义与现代的“公共意见”比较接近。从“舆论”一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演变可以看出,舆论是民意的“晴雨表”,具有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舆论主体角度,分析稷下学宫时期齐国舆论营造的背景、流变及影响。
2 稷下学宫时期齐国舆论营造的背景分析
2.1 西周舆论的延续
周代商后,通过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构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天者,百神之所最尊也。”[6]“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始终,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惰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7]周天子将君权通过“神”“圣”“王”合流,将王权舆论“王化”[8],构建了自上而下的王权,在“民”中树立了统治者的权威形象。在营造“王”化舆论的过程中,“言谏”占据重要位置。言谏制度在周朝形成,谏官的工作职责一是“廷诤”,二是“上封事”,并享有言者无罪的“特权”,具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9]的职业道德。言谏制度为稷下之士在齐国的舆论营造中发挥中坚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周朝通过“礼乐”制度巩固王权。礼用于对社会等级、道德伦理及个人行为进行制度规范,分层次对社会与个人进行外在约束。乐用于教化个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周朝以“礼乐”为准绳,教育人们形成自觉的受礼意识,营造符合当时社会的舆论氛围。
周朝民众主要通过歌谣、谚语等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时的乡人、国人可在乡校、国人大会等场合公开发表言论,亦可即兴创作歌谣。为了了解民意,周朝实行采诗观风制度,采诗官把收集到的歌谣进行整理之后,交由乐官谱乐,再呈给天子、诸侯,供他们观察民情、决策参考。《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觐之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周朝采诗观风制度诞生的杰出作品是《诗经》。古人将劳动、生活中的感悟、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社会政治的态度等,通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等个人意见,以朗朗上口的语言口口相传并被收录到《诗经》中。作为周朝社会风情的画卷,《诗经》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民情和口语时代的中华文明。稷下诸子在说理论证时也常引用《诗经》,用以增强说服力。
2.2 诸侯割据的影响
周灭商后,因其国都镐京远在西北,不利于天子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及统治商代后裔,周天子便开始大规模分封诸侯,被封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同时有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力、维护周室安全等责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周天子对其渐失约束力,诸侯间开始争霸,最终形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局面。在诸侯争霸过程中,礼乐制度崩塌,传统价值观逐渐崩溃,各种新思想不断产生,形成了不同流派。各流派间相互诘难、争鸣,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逐渐形成。
2.3 齐国前期的积淀
姜尚协助周武王灭商后被封至齐国,是齐国的第一位齐王。姜尚在位期间“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使齐国一跃成为经济强盛、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修政,因俗,简礼”充分展现了姜子牙对舆论的重视。春秋第一个霸王齐桓公姜小白在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曹操《短歌行·周西伯昌》)。齐桓公是一个非常重视“兼听”的君主,他能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并听从管仲的建议,以“尊王攘夷”的口号引导舆论,实现春秋霸业,使齐国出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10]、商贾归齐如流水的局面,齐国都城临淄一跃成为当时东方文明的中心。管仲对齐桓公的称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思想对稷下学宫时期的诸子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稷下学宫中的“管仲学派”。主流学术观点认为《管子》就是“管仲学派”托名“管仲”而著的一部论文集。贤相晏婴先后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晏婴主政期间,坚持任人唯贤,不私于亲;诛不避贵,赏不避贱;进一步发展渔盐碱业;减轻百姓负担;搞活流通,增强国力;弛严刑苛法,尚仁治并辅以法。晏婴的思想对稷下诸子的影响也非常大,学界认为《晏子春秋》也是稷下诸子合作的产物。春秋时期的姜齐为之后的田齐奠定了政治、经济和舆论基础,为稷下学宫的建立与诸子争鸣创造了良好条件。
3 稷下学宫时期齐国的舆论营造
稷下学宫时期齐国的舆论营造延续前期自上而下的形式,呈现出王、士、民三级的传播流向:舆论为王权服务,齐王对王权的态度决定了齐国的舆论氛围,直接影响了稷下学宫的兴衰;士在君王与民众间搭建桥梁,上谏齐王,下教化齐民,是诸子争鸣的直接践行者;齐国民众在齐国的舆论营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3.1 王:舆论营造的掌控者
“在任何组织中,确定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11]。“稷下学宫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齐国统治者的政权目的而诞生的”,[12]田齐第三位齐王田午向天下招揽贤士,创建稷下学宫;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鼎盛;齐湣王、齐襄王时期,稷下学宫出现萧条、衰败迹象;至齐王建死,齐国灭,稷下学宫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3.1.1 立黄老之学,强调王权的正统
黄老之学的确立与田齐政权有着特殊的关系。田氏代齐,于“礼”不符,容易引起世人的诟病。齐威王为巩固田氏政权,大兴“稷下学宫”,并钦定“黄老之学”为主导学说。其原因在于:首先,黄帝是田氏的始祖,因此田氏是可以享有王权的,作为黄帝后裔的田氏取代炎帝后裔的姜氏属于正当传承,田氏的政权具有“天赋”的“神化”特征。其次陈国的公子完是齐国田氏的先祖,老子李耳也来自于陈国,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高度契合于齐威王的执政理念,田齐接受老子的思想就使得齐政权具有“圣化”特征。再次,作为一位重视进谏、广开言路的开明君王,齐威王通过重用邹忌、淳于髡等稷下先生,让他们引导稷下学宫的学术争鸣,以推动教化齐民的进程,这体现了王权“王化”的特征。综上所述,黄老之学为“田氏代齐”找到了合法性依据,稷下学宫的发展及学宫内诸子争鸣其实是齐威王政权“神化”“圣化”“王化”的结果,为田齐王权稳固提供了正向舆论。
3.1.2 纳谏言,强化治国理政
言谏文化与制度贯穿于中国封建统治史,“本质上属于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3]。纳谏作为齐王听取民意最常用的方式,是齐王治国理政的有效行政手段之一。《战国策》记载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很好地证明了纳谏对齐王治国的影响。齐威王通过采纳邹忌的谏言,不但使民意能够进耳,而且个人的政绩亦“闻达”于诸侯,实现了舆论传播的无限扩大。
齐王对纳谏所持的态度与个人的政治作为是密切相关的。齐威王初政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群臣莫敢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其曰:“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明白其用意,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此后造就了“一鸣惊人”的政治霸业,使齐国再一次称霸诸侯。齐宣王在位期间通过人才金政政策招揽天下学士到齐国稷下学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稷下学宫进入了鼎盛时期。反观齐湣王的失败与他拒听谏言、不重民意的舆论观有直接关系。他在纳谏理政上,表现出“亲佞远贤”的倾向,重用苏代,一再拒绝诸多稷下先生的极力谏言,最终造成君臣不和、百姓离心的局面,使稷下先生们带着失望、愤懑与不舍离开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在齐湣王时期出现了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萧条,齐国也进入了快速衰败期。齐王建不听即墨大夫的谏言反听陈驰的奸言,“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战国策·齐策六》),齐国灭。
3.1.3 齐王性格影响舆论的营造
齐国的政治权力集中于齐王,因此齐国政策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舆论的氛围也与王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齐威王格局大,处事客观公正,善于从全局谋划,能够广开言路,对不同身份、阶级人士的谏言都能听进,且不偏信(如对诋毁即墨大夫一事,齐威王亲自派人调查,最终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同时“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在齐威王营造的宽松舆论氛围下,群贤毕至,诸子争鸣,稷下先生们能充分施展个人政治才能与表达个人学术主张。齐宣王时期的舆论氛围仍较宽松,但分析齐宣王的事迹不难发现,齐宣王喜好大场面(喜三百人吹竽)、注重实用性(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这些性格特点使他不惜重金聘请大量稷下先生至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规模达到鼎盛。另外从他与孟子的几次对话中又可看出,齐宣王虽有大的政治抱负,但又不想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特点造成了齐国虽有大量稷下学士,但他们并未得以“人”尽其用。齐湣王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偏信佞臣、穷兵黩武欲争霸天下,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最终造成了臣伤、诸子离、民心尽失的结果。
3.2 士:舆论上达下联的中坚力量
周朝将贵族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又分上、中、下三等,士有食田。后来礼崩乐坏,士失去了食田和特权。至战国时期,“士”成为对有才略,有胆识或品格高尚者的尊称,从封荫的爵位变成可凭借个人修为获得的称誉。在东周之前,世人的教育主要以“学在王宫”为主,但随着礼崩乐坏,“士”阶层开始出现,士逐渐担负起文化教育的大任,成为连接君王与平民的中介和桥梁。他们或政治敏锐、巧言善辩、率兵杀敌,成为朝臣重臣,如苏秦、田单等;或为贵族门客,为贵族出谋划策,如冯谖、毛遂;或隐于世,复出后力挽狂澜,如鲁仲连、聂政;更有立言授徒,以思想影响于世者,如孟子、荀子、庄子等。“‘士’是政治上活跃的一个社会阶层,是形成所谓‘百家’的根本来源。”[14]田齐时期,士在齐国兴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或进入齐王室,辅佐齐王的统治,或在稷下学宫展开争鸣,最终促成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东方文明舆论场的建立。
3.2.1 教化民众:士的主要社会职能
先秦时期,生产力落后,物质资源和教育资源都十分匮乏,教育为统治阶级垄断,为阶级统治服务,“教育即政治,政治即教育”[15]。春秋之前,“学在王官”“学在官府”是主要的教育形式,“吏”承担主要的教育职能;随着“礼崩乐坏”“学在王官”的教育垄断态势逐渐被打破,致使一部分“官吏”流至各诸侯国。在这场流动中,官吏们慢慢将个人的政治抱负、文化修养等投入教育之中。教化下移使“吏”向“士”转变,士担起了教化民众的大任,同时成为当时舆论的主体。士的教化过程呈现出两个流向:一是将符合王权统治的思想向民传达。例如在稷下学宫三次担任“祭酒”(即学宫之长)的荀子,虽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但却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观念形成了自己天道自然、天行有常、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荀子的天道理论不在于自然主义偏向,更在于凸现“天人相分”。他继而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荀子的天道思想与稷下学宫倡导的“黄老之学”相符合,适应了齐王“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另一个流向是将个人、民众的意见等通过谏言、立说等方式上达给王。例如邹忌以五音喻事,向齐威王进言个人主张。邹忌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2.2 向上进谏:士最常用的舆论上达方式
士向王进谏,为统治者提供决策前的意见与决策后的意见反馈,这是士人表达个人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最常用的方式。君王通过他们的进谏,实现了王权的内部调节与自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士人通过进谏,获得加官进爵,实现了由“士”到“吏”的回归。邹忌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委任为相国;孙膑以兵法见长,被任命为军师;淳于髡以博学善辩著称,被拜为政卿大夫。一部分士通过谏言受到齐王的重视,如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的士人,耗巨资招天下各派文人、学士到齐国进行讲学。当时,驺衍、田骈、环渊等七十六人都被赐给府宅,官拜上大夫,不具体治事但可自由言政。
3.2.3 百家争鸣:士自由言论的集中表现
齐国舆论营造的典型表现就是以稷下学宫作为舆论场而展开的百家争鸣。“进入稷下学宫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稷下学宫就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百家争鸣就是在稷下学宫中进行的。”[16]当时道、儒、法、兵、名、农、阴阳等诸子都在稷下学宫争论、著书,阐述各自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以《管子》为例,该书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结果。《管子》内容庞杂,《心术》《白心》《宙合》等篇体现了黄老之学,《四时》《五行》《水地》等篇则体现了阴阳家的思想,《兵法》《七法》《制分》等篇则带有明显的兵家思想,儒、法、墨、纵横等其它学派的思想亦在不同篇章有所展现。分析《管子》,会发现该书体现了与当时社会状况相吻合的朴素的舆论观。《管子·桓公问第五十六》明确提出了咨议制度:“(对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为啧室之事也。”[17]“无仪法程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间。蜚蓬之间,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蜚蓬之间,不在所宾。”[18]“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与任大。”[19]体现了对谣言、蜚语的批评。三做祭酒的荀子非常重民,他提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20],这一思想消解了战国末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固有界限,为国家争取民意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导了民众的舆论风向。
3.3 民:对社会现状的个人态度表达
3.3.1 齐民个人意见对齐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齐国舆论环境宽松,许多底层的劳动者得以公开谏言。当时不但男性民众(如贯珠者)可进谏,地位相对低下的女性也可公开表达个人意见。。《列女传·辩通》中记载了无盐女钟离春对齐宣王身边危险的分析:“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雠,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齐宣王最终迎娶无盐女为后。齐威王听了姬妾虞姬谏言,开始励精图治;齐湣王也被宿瘤女才学吸引,娶宿瘤女为妻。由此看出,在当时宽松的舆论氛围下,齐民的个人谏言对齐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3.2 齐国歌谣、谚语体现民众对齐国世事的态度
林语堂认为中国古代的歌谣具有舆论的功能:歌谣除了具有讽刺社会的特点,还总与中国的宗教迷信混合在一起,赋予歌谣神谕特质以及占卜未来的功能,表现出一种幽默的风格。[21]张艳丽在《先秦时期齐国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一文中做了进一步分析:齐国的歌谣具有政治讽刺、政治颂扬、政治表达、社会调控的功能。[22]从宣湣王时期表达孤独凄凉情绪的《雉朝飞》(年五十,无妻,求薪于野,见雉雄雌相随而飞)(晋崔豹《古今注·音乐》)、田单攻打狄地时产生的《攻狄谣》(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西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六》)、齐王建投降秦国时产生的《松柏歌》(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西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六》)等民谣可管窥齐国歌谣的上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