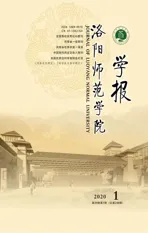二程家风与理学思想初探
2020-03-03侯瑞华
侯瑞华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目前从哲学角度对二程理学进行的论述与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和深入了,但从二程生活的家庭习惯与观念风尚出发来反观其理学,则似乎仍有继续探究与讨论的必要。二程作为理学大师,其家风自然与理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理学影响下的优良家风,无疑又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继承。本文即从二程家风的角度切入,试对二程家风与其理学思想作初步的探讨。
一、儒学背景下的家风与个体
在讨论二程家风之前,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儒学背景中的家风与个体的关系。对传统儒学而言,君子往往不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从而使个体人格实现一种典范性的意义,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是也。这种自身道德修养的外在转换,既是对君子品格的前提性强调,如《大学》中的“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又是儒家传统理论中由“内圣”至“外王”的自然展开,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通过典范性意义的实现,就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师”和“教”。所以儒者往往以师的面貌出现:有学统意义上的弟子师、政统意义上的帝王师,更有道统意义上的与“天地君亲”相并列的“师”。儒家重“学以成人”,则学不可无师; 又因儒家将家庭伦理关系外推至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使得师与父在伦理关系上获得相同地位,从而师不单单有着可效法的典范性,同时还有着伦理上的权威性。这种师父合一使得历来对儒者作为师的身份十分重视,而往往忽视了儒者父的角色。实际从父的角度出发,我们才可以看到示范意义背后一个更加真实的人格。“师”对应的是弟子,是学生; “父”则对应的是子女,是家人。学生面对老师,获得的是知识、义理,是学术层面的逐步深入的认知; 子女面对父母,获得的是言传、身教,是家风层面的潜移默化的濡染。这种示范对象的不同,自然会使儒家理论呈现出不同的或是更加原始性的面貌。而“师”与“父”的统一,更体现着理论的说教在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转换。
二程作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哲学思想上即他们作为“师”的地位已被后人反复申说。然而二程并非“生而知之”,他们的成长与思想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家风的影响; 而且他们除了作为“师”还有作为“父”的一面,理学思想使得家风薪火相传,也会影响他们的子女乃至更多后代。
二、父母家风对二程的深刻影响
如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起首叙述的那样,程家祖先历来多为仕宦出身。高祖程羽官至兵部侍郎,还曾被朝廷赠予“太子少师”,子孙亦显宦。二程之父程珦即因祖上恩荫得官,因而程家可谓典型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如此绵延久历,就在无形中酝酿成一种良好的氛围。“程氏居永宁之博野,土风浑厚,世以忠廉孝谨闻。少师贵重于朝,始赐第京师,为开封人。世风不衰,子孙多好善。”[1]495-496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 二程的父母以言传身教所营造出的良好家风,自然使得二程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
二程的父亲程珦自小便受到家风的熏陶,因为他的父亲便“事父兄谨敬过人,责子弟甚严”,并且在程珦才十余岁的时候“则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称意旨,公恐惧若无所容”。[1]647这种恐惧一方面来自父亲的严格督责,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足见程珦乃是一个非常孝顺、有仁义之心的人。“开府终于黄陂,公年始冠,诸父继亡,聚属甚众,无田园可依,遂寓居黄陂。劳身苦志,奉养诸母,教抚弟妹。”[1]647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程珦仍能尽心尽力做好对长辈的奉养与对晚辈的抚育,其一言一行所散发的人格力量岂能不对自己的子女产生影响?并且他面对朝廷的升调,一再推拒,“至长弟与从弟皆得官娶妇,二妹既嫁,乃复赴调”[1]647。而且在之后“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1]338。这种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君子之风,更给二程兄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他们所屡次提及,更为他们所效法遵行。
在程颐的记忆中,父亲的两件小事情始终令他记忆尤深。父亲“一岁丧母,祖母崔夫人抚爱异于他孙,尝以漆钵贮钱与之,公终身藏其钵,命子孙宝之”[1]650。虽然只是一个小时候的漆钵,然而其中承载的却是浓浓的慈爱之情。父亲命子孙宝之,则是希望把这样的家风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开府喜饮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尝不思亲。颐自垂髫至白首,不记其曾偶忘也”[1]650。这种发自肺腑的爱亲之情,乃是真正的仁心流露,抵得上千千万万高头讲章和道德说教。而这种对亲人极深挚、极诚恳的感情,无疑使子女得到真正的教育。程颐自言“自垂髫至白首,不记其曾偶忘也”,就是最好的证据。所有这些仁孝的家风,对二程理学强调“仁心”自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程理学从本体上揭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16,由这个大本大源出发,则能与理体合为一,因而可以做到“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1]17。这正是所谓超越生死,生顺死安。二程这种在理论上的阐述实则有其生活实践层面的直观体验。二程之父可以说就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年八十,丧长子,亲旧以其慈爱素厚,忧不能堪; 公以理自处,无过哀也”[1]652。并且他对死亡的态度更是处之泰然,对身前身后的荣辱褒贬亦淡然视之。“年七十,则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后十五年终寿。”[1]646在自撰墓志里特别交代子孙: “葬日,切不用干求时贤,制撰铭志。既无事实可纪,不免虚词溢美,徒累不德尔。”[1]646二程父亲这种超然的气度胸襟与二程理学“生顺死安”的意蕴,共同表现了二程家风中的君子人格。
二程的父亲爱打坐而不爱动,“居常默坐,人问:‘静坐既久,宁无闷乎?’公笑曰:‘吾无闷也。’”[1]652“尝从二子游寿安山,为诗曰:‘藏拙归来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关。洛阳山水寻须遍,更有何人似我闲。’”[1]652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程颢的那些带有浓厚理学意蕴的诗句,如“阴曀消除六幕宽,嬉游何事我心闲”,又如“心闲不为管弦乐,道胜岂因名利荣”等,两者具有非常一致的内涵与意韵。如二程理学中的“口头禅”即有“心要在腔子里”,心安则心定,身与心才自然会闲。所谓“然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1]31,如此方能在终日打坐中亦不觉得沉闷无趣,即便出游也是无事而心闲。“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1]8这里的无事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1]1263的精神状态。父亲的这种精神意趣,从游的二子当然能够心领神会,因为这正是二程家风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相比父亲,二程之母更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二程的母亲侯氏出阁前即“好读书史,博知古今”[1]653。二程的外祖母“素有风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其作为女儿“涕泣扶侍,常连夕不寐”[1]653。可以说在学识与人品上都堪称一时的典范。尤其她能读书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成长背景无疑使得二程之母在以后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上远远高于一般人的认识。比如当孩子“才数岁,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抱扶,恐其惊啼,夫人未尝不呵责曰:汝若安徐,宁至踣乎?”[1]654一般人对孩子跌倒往往疼爱不已,二程之母却能教育孩子,使之在跌倒摔疼这件事上懂得道理。这种做法远比督责有效,还能让小孩子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懂得更深刻的意义。看似一件小事,然而程颐却念念不忘,在母亲的家传中特别拈出此事,足见母亲的教育对二程兄弟的影响。
二程理学将“理”看作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谓“理便是天道”[1]290。从规律性上出发,则自然引申出理性看待问题的精神: “圣人致公,心尽万物之理,各当其分。圣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二程之母在对待孩子摔倒的问题上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精神。既不是过分溺爱,又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恰如其分地在训诫中传授理性看待问题的精神。儒学中又历来强调“反求诸己”,二程的理学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如《周易程氏传》卷三所言: “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而母亲“汝若安徐,宁至踣乎”的训诫,实际就是一种“反求诸己”的要求。从理学体系上着眼,则“反求诸己”既是求理明道的重要方法,又是人生修养的必由之路。像对“诚”和“主敬”的强调,也即是这一思想的自然延伸。程颐对此事的念念不忘,则说明母亲的教诲,在他们对“反求诸己”的儒学精神的体认与发展上无疑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与二程的父亲一样,二程之母也非常孝顺仁爱,其“事舅姑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德容之盛,内外亲戚无不敬爱”[1]653。“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就连小臧获也视如儿女。程颐曾这样回忆母亲道:“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1]654二程兄弟是仅存的二男,母亲又特别慈爱,可以想见二程小时候的成长必定是相当幸福的。但母亲对二程并没有流于溺爱,而是从平时走路吃饭到读书做人,无不予以谆谆教诲,以至程颐深情地回忆:“故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1]654程颐的这番自述,足以表明程家家风与二程理学的密切关系。正是父母的言行表率与日常督责,让二程兄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仁爱孝顺、循理而行、反求诸己等儒家精神的熏陶与濡染,从而获得最生动具体的体认。
三、家风是二程理学思想的生动体现
如前文所述“师”与“父”的统一,儒者的哲学理论与其生活实践是相一致的。理论上提出“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二程,在生活中也当然有种种相应的行为。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乃是儒者之大耻。我们且看《宋元学案》中对二程为人的概括:
先生资性过人,而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2]539(大程)
衣虽布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致养其父,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党八十余口。[2]591(小程)
此外还有大量门人弟子的回忆追念,都足以说明他们是说到做到的纯粹儒者,而非欺世盗名的虚伪君子。程颢的蔼然和气与程颐的克己孝亲,既是从父母仁爱孝顺的家风中获得熏陶习染,又因自身的理学思想而达到道德自觉。程颢为了方便奉养父亲,曾求闲官若干载,“嫁女娶妇,皆先孤遗而后及己子。食无重肉,衣无兼副。女长过期,至无资以遣”[1]330。程颐“致养其父,细事必亲”,自己衣布素、食简俭。他们的仁爱孝顺与前文所述其父其母的仁爱孝顺岂不正是一脉相传?他们的勤俭自勉、安贫乐道,正如程颐所言:“故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如二程之母即“安于贫约,服用俭素,观亲族间纷华相尚,如无所见”[1]654。这样的以身作则与谆谆教诲、安贫乐道的家风自然深深影响了二程兄弟。此外,二程理学中对孝者安亲十分强调,如“至诚一心,尽父子之道,大义也; 不忘本宗,尽其恩义,至情也”[1]516。而他们对自己的理念思想的践行,也为其家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其家风能够更好地发挥影响。
四、家风在二程子女身上的延续
中国人历来是重“身教”胜过“言教”,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家庭中更是如此,长辈的一言一动,无不对晚辈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正是家风的重要作用。从二程对其子女的教养,我们可以看到二程家风的延续。
程颢次子端悫,聪明敏锐,生性淳厚,乃被二程兄弟视为“尝意是儿当世吾兄弟之学”[1]495,程颢称其“坐立必庄谨,不妄瞻视,未尝有戏慢之色”[1]495。不难推想程颢之子能够有如此的行为举止,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必定也受到父辈严格的教育以及浓厚家风的影响。如二程提出并践行的“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 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返归内心、求仁主敬,自然是明道所必由,然而外在的举止行为同样会影响到内心修养。其家庭注重子女一言一动皆有规矩,从而营造一种严肃活泼的氛围。
程颢有一女十分贤良,却因为一直没有找到足以相配的夫家而始终未嫁,后来因母亲去世哀毁过度而亡。对于程颢的这个女儿,“众人皆以未得所归为恨”,而作为叔叔的程颐却不这么看: “颐与其父以圣贤为师,所为尚恐不当其意,苟未遇贤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没世。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1]641。足见在二程的家风中,并不是专重所谓的世俗伦理道德,而是有着更高的更真实的道德自觉。后世往往讥讽理学是“以理杀人”,然而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其家风与流为说教的纲常名教绝然不同。
五、结语
程家家风在数代人的敦厚自修中逐渐形成。二程的父母既是这种家风的继承者,同时又以身作则,注重子女的教育培养,从而使优良家风进一步及于二程兄弟,对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二程理学思想的发展,同时又为其家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道德自觉。从家风的角度出
发,我们看到二程理学在形而上的哲思之外,也深深根植于日用常行,它是活泼泼的,而不是压抑和沉闷的。这种孝亲敬人、反求诸己、安贫乐道的优良家风,也十分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