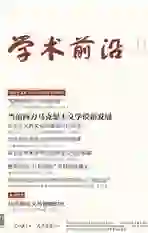结构性溢出: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溢出论”
2020-01-19吴冠军
【摘要】从马克思到阿甘本,其理论存在一条马克思主义“溢出论”的发展线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出商品的“怪异结构”,当代的阿甘本进一步提出该“怪异结构”实则是从古至今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状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已被一般化到所有领域之中,抵达了该结构的“纯粹形式”。依循马克思主义“溢出论”所提供的思想视角,进一步深入考察儒教社会的超稳定性之谜与共享经济的革命性潜能可以发现,前者构成一个政治神学-政治哲学的考察,而后者则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人类学的考察。
【关键词】结构性溢出 马克思 阿甘本 宗教 儒教社会 共享经济
【中图分类号】A81/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1.006
思考“结构性溢出”:从马克思到阿甘本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对商品进行了整整三节篇幅的深入分析后,写下了如下这句话:
第一眼看上去,一个商品似乎就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东西,极易理解。对它的分析却显示,在现实中它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精细。[1]
对于马克思而言,商品的“怪异”之处便在于:在其世俗的“平凡性”之上,还具有着溢出性的形而上学-神学向度,这就形成了一种以隐秘溢出为特征的结构。而马克思的批判,便正是落在那内在于商品,但第一眼不容易看到的怪异的“结构性溢出”上。
具体而言,商品的“怪异结构”就体现为如下这种内在固有状况。商品的价值,就其世俗的平凡性层面而言,就是它具有某种“使用价值”——某个特殊的对象可满足某一特殊的需求。某件“十分平凡的东西”之所以是“商品”而不是无价值的事物,正在于它是“一个在我们之外的对象,一个通过其属性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满足人类之所需的事物”。[2]然而,嵌入在商品中那怪异的“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精细”,恰恰使得“使用价值”结构性地被逾越。而正是那个逾越的溢出性部分,构成了商品实际在市场上的价格(即“交换价值”)。马克思把商品本身的价值(使用价值),称为“价值的实体”(the substance of value),而把逾越价值实体的那个溢出性部分,称为“价值的巨量”(the magnitude of value,现有中文译本多简单将其译成“价值量”,使得那層“多”的意思被完全取消了)。正是这“多”出来的溢出性价值,是资本主义繁荣的秘密:它使得消费形态从为了事物的使用功能而消费,逐渐转变为拜物教式的消费。“多”出来的那份神秘“巨量”,最终使得商品变成“物神”(fetish)。商品的“溢出性结构”,使得资本主义系统不再是一个纯然“内在性”(immanence)的世俗秩序,而隐秘上升到“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形而上学-神学层面,也正是后者,是资本主义系统长久繁荣的密钥。
我们看到,马克思对商品的结构给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批判性诊断,这一诊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母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产品在市场中被转换成了“商品”,这就在它内部产生出了一个怪异的结构——在前市场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产品)之外,隐秘地多出一个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作为商品)。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恰恰是这溢出性的“交换价值”,变成了事物的核心属性。你想要某个东西不是出于其功用,而是出于其价格。举例而言,你想要拥有一款爱马仕包,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使用价值,能装多少东西,结实不结实,而是在于它的交换价值——几万元的包,直接就让几千元的包自惭形秽(更准确地说,让背包人自惭形秽)。于是,人们和物品的自然关系就转变为一种狂热的情感,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由此,物品变成物神。古代社会中的“神”至少不在凡间,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凡间的物品就直接变成被疯狂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个世界到底变得更理性,还是更蒙昧?
当代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i?ek),直接以“淫秽”(obscene)一词,来描述内嵌在商品里的这种“结构性溢出”。他结合拉康主义精神分析提出对商品结构的如下批判:“一个产品,根据其定义,从来不会交付其(幻想性的)承诺;换言之,最终极的‘真正的产品,将是不需要任何补充的产品,将是单纯地、完整地交付它所承诺之内容的产品——‘你将获得你付钱的东西,既不更多、也不更少。”[3]商品的淫秽之处便在于:它的溢出性“补充”(supplement),使得一个产品本身的价值实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幻想”(fantasy)。而应对商品的这种结构性状况,在齐泽克看来,便是直接去斩断那溢出性的淫秽补充。[4]
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晚近著述,把由马克思所开启、但并未受到后世马克思主义学者重视的“溢出论”,做出了学理上的进一步推进。阿甘本紧紧追踪马克思所诊断出的那份溢出性的“神学的精细”,并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今天,宣称我们实际上从未离开宗教阴影的笼罩,换言之,我们从未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阿甘本接着马克思的诊断提出:那份作为溢出性补充的“神学的精细”,将最终掏空物品的使用价值,使之只留下一个空白的形式。换言之,资本主义系统最终产生的,是使用的绝对不可能性。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那些被献祭给神的事物,实际上就是被从人的世界中移除出去,不再能被人所使用。而所谓“宗教”,就是关于祭祀的一套文化实践——“宗教可以以如下方式来定义——它将诸种事物、场所、动物或人民从共通使用(common use)中移除、并将它们转移到一个分隔的领域”。[5]这个“分隔领域”,就是世俗秩序的“神学补充”。在阿甘本看来,只要在任何人类社会中察觉出这样的“分隔”,那么必定“在其中包含和保有一个纯然宗教性的内核”[6],不管该社会自我标榜为“现代”还是“后现代”。从这一分析性视角出发,阿甘本着重确认了马克思当年的诊断,并对分隔性结构进行强调:“在商品中,分隔就固有在每个物体之形式中,将它分裂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将它转变为一个无法把握的拜物教对象。”[7]
阿甘本并未止步于对马克思论题的再确认,而是进一步推进对宗教(“神学的精细”)的分析性研究并指出:宗教通过祭祀仪式而构建的“神圣”之域,实质上只是通过“排除”的方式,在共同体内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特权空间——那些被排除出去的事物“现在根据某些决定性的规则,只对某些人开放”。[8]从对宗教的分析再返回来考察资本主义系统,阿甘本提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有权”(property)概念,也恰恰就是一种隐秘的“神圣”之域——某物被分隔进一个特权空间,只能少数人(该物之“所有者”)有权使用,他人皆不能使用。
同齐泽克聚焦于没有淫秽补充的“真正的产品”相类似,阿甘本聚焦于摆脱了溢出性“价值巨量”的纯粹“使用”。“对于人的生活,只有使用才是绝对必需,也因此,绝对不能放弃。”[9]阿甘本提出的核心论点是:“使用”同“占有”(possession)相对,并且它使得“所有权”的真正本质暴露了出来——财产所有权什么也不是,它是这样一个机制,将人们本来的共通使用转移到一个分隔的领域,而在那里,使用被转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权利”。[10]资本主义让消费变得疯狂、让商品变成“物神”的方式,便恰恰是让你占有,而不是让你使用。在今天“买买买”的时代,我们已能看得很清晰:一个人真正需要用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当你下单抢购耐克新款时,并不会去想一想即便一周七天天天换鞋,自己穿得完鞋柜中已有的鞋么?“买买买”,绝不是“使用”逻辑的产物,而恰恰是“占有”逻辑的产物——正是在后一种逻辑下,你才会不断扩充你的鞋柜,并且永无止境。某物一定要是你的,你才感到踏实。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人与物的关系,就应该是占有和被占有吗?
经由“所有权”这个话语装置加持后的占有,其“霸占”的属性便被转换成“神圣”的属性——它把事物的使用转移到一个分隔出来的“神圣”领域。“所有权”或者说“拥有的权利”(right of ownership),便正是对事物“神圣化”操作的现代形态。经过该操作,事物便形成一个分隔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占有,实则就是人为搞出一个排他性,就像祭祀仪式将某些事物人为地嵌上一个排他性的标识。真正考虑使用的人,其实占有并不那么重要,自己用完了别人可以用。所以,占有实则是使用的反面,占有就是拒绝使用:我用不用你别管,反正你不能用。
阿甘本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原初分析之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商品系统中的“交换价值”,实则便是“所有权”的一个附生产品。换句话说,“交换价值”从来不是内生于事物本身,它就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只有在占有的基础上,交换价值才得以成立,并一步步地盖过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系统只重交换,不重使用——市场里的交换,以占有为前提,而使用则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在阿甘本看来,只要“所有权”的框架得以确立,事物的交换价值就会渐次取代使用价值,交换、消费与商品拜物教,最终会彻底取代共通使用。就所有权被设定为神圣不可侵犯而言,资本主义现代性,实际上恰恰内嵌溢出性的“神学的精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话语形容“财产权/所有权”的语辞,同“前现代”宗教形容神的语辞完全一致——“至高的”(sovereign)、“神圣的”(sacred)……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在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如下著名论述:资本主义就是宗教。而当代的阿甘本则接着这个论述提出:资本主义作为宗教,不只是因为它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将新教信仰世俗化,而更是因为它“将那定义宗教的分隔结构一般化到所有领域之中”。[11]本来是经由祭祀进行分隔操作,而现在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操作取而代之:在一个单一但多平台、永不停歇的分隔过程中,该操作“攻击”所有事物、所有场所、所有人的活动,从而将它们与自身相分隔。“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宗教实现了分隔的纯粹形式,以至于抵达这样一个点,在那里一切都已遭到分隔。”[12]也就是说,较之古典社会,资本主义现代性才是最大限度地将宗教这种被分隔出来的“结构性溢出”扩展至其极致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当年从商品上所诊断出的“怪异结构”,实则恰恰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一般化属性,并且它恰恰把“前现代”社会中宗教所分隔出来的那个溢出性位置,嵌入社会的一切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神圣化,同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实则具有全然相同的结构。祭祀将某动物或人的一部分(如内脏或肉体)分隔出来,赋予其神圣之属性;而资本主义将某物(如爱马仕包)之“价格”(交换价值)单独分隔出来,使之同该物的使用不再相关。可见,神圣属性与交换价值一样:它们被分隔出来,并上升为定义某事物的根本属性。同信仰者最关心某物是否是圣物一样,今天世俗化了的人们首先关心某物多少钱、“价格”多少(从此处可见,交换价值已彻底取代使用价值,成为定义某物之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宗教,在后神学时代恰恰抵达它的更为成熟与隐蔽的形态——商品拜物教。祭祀仪式使得祭祀物品“属神”,不再能够被人所使用;而在資本主义秩序中由“物神”所组成的“神圣”之域处,我们同样遭遇使用(共通使用、自由使用)的绝对不可能性。[13]
于是,我们不得不服膺马克思当年那个著名的“反达尔文主义”论断: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换言之,要深入地批判地考察一个对象,不是先去看它的初级形态(猴子),恰恰相反,要去看它的“成熟”形态(人类)。细致研究资本主义秩序里那种实现了“分隔的纯粹形式”的商品拜物教,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前现代”的宗教到底是什么。
政治神学-政治哲学分析:从战争到儒教社会
我们可以接着马克思—(本雅明—)阿甘本的论题,继续将对“结构性溢出”的考察做进一步的分析性拓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往回看和向前看,以此深入考察儒教社会与共享经济,前者构成一个政治神学-政治哲学的考察,后者则是政治经济学-政治人类学的考察。
从文明史的尺度上而言,宗教(包括商品拜物教在内的人类社会任何一种宗教形式)实则正是人类社会(宗教视角下的“凡间”、“尘世秩序”)的一个淫秽补充。“神圣”,就是对“尘世”(the profane)的结构性溢出:它超越了后者的界域,但并不毁灭或取代后者,反而构成了后者的根基。“神圣”的这种奠基性地位,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考察到。有的宗教里直接是神创造世界或者创造人类(如上帝、女娲、普罗米修斯……),有的宗教则提供人间秩序的保护神。
宗教这个淫秽溢出,便导致人类社会形成一个“怪异结构”:人类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生产的日常世界(内在性),它还有一种至高的“神圣”之域——神、狂欢与至高统治者的世界(超越性)。这一“怪异结构”,便导致了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哲学结果——它使得“主权者/至高者”(the sovereign)这个怪异位置得以产生。共同体中那些不直接参与劳动与生产的居高位者,通过掌握祭祀同“神圣”之域接通,从而成为尘世秩序里的主权者。换言之,居高位者在共同体中所占据的位置,因为内嵌于人类社会的那个“怪异结构”,而具有了本体论-神学根据(onto-theological ground)。他们在尘世法(profane law)中,又在尘世法外。
就尘世法而言,任何人类的共同体秩序,都有关于不能随便杀人的禁令。中国古话“杀人偿命”“人命关天”流传至今且耳熟能详,恰恰映射出了内在于人类共同体的“怪异结构”。“杀人偿命”是尘世法的律令,而“人命关天”则恰恰指向那结构性越出尘世法的神学补充——正是当人“命”关“天”(超越性)时,掌握祭祀的主权者才拥有那溢出尘世法处决人“命”的至高权力。对内,这种至高权力具象为把人标识为可无罪杀死的“神圣人/牲人”(homo sacer)的权力(杀之无须偿命)。阿甘本的代表性著作《神圣人》便系统性地分析了这种法外权力。[14]对外,这种至高权力则具象为发动战争的权力。主权者,就是拥有发动战争之大权的居高位者,可以让无数人在法外状态互相杀戮,短时间内耗尽生命。于是,我们看到,“杀人偿命”与“人命关天”这两句从古至今被高频引用的话,恰恰互相抵牾却又互相交融,进而形成一个“怪异结构”,在其中淫秽溢出被结构性地固化下来。正是在这种“怪异结构”中,以构建并维护日常秩序(尘世法秩序)、保护老百姓(从古时臣民到今时人民)为己任的主权者,恰恰能毫无违和地拥有将他们送上战场的生杀予夺大权。[15]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键性的洞察:和交换价值的结构性位置一样,战争亦属于那溢出性的淫秽补充——这个在人类社会中十分平凡的现象,实则同样“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精细”。此处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关于杀人的禁令(尘世法),战争就会成为不可能与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杀人禁忌的动物,就从未把相互之间的争斗,发展为有组织的战争。人类的“文明”首先发展出不能杀人的禁令,然后,战争就构成对该禁令的间歇性逾越(对尘世法的溢出)。战争不可能是常态、日常秩序,而只可能是常态的例外、对秩序的溢出,如同肾上腺素的迸发,它是过剩能量的消耗。故此,尽管战争状态有时会长时期存在,像中国的三国至南北朝、宋王朝和辽、金、元时期,但即便如诸葛丞相般肾上腺素飙升地五出祁山,也得在主要时间停下来从事生产、建设。战争只可能是日常秩序的溢出性补充,而在其中,我们有组织地杀人。
这就是发动战争者为什么老是要宣称“天命”,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或者“复兴汉室”“保卫天子”。因为通过这个方式,战争的实际发动者便让自己上升到了——至少暂时性地——主权者位置。“人命关天”这句表述人命无比重要的话,其所隐秘承载的淫秽信息就是:只要关了“天”了,那就有理由让人大量去死。也正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帝将自身称作“天子”,只有他们能主持祭天,而他们中最牛或自认为最牛的那几位,更是到泰山封禅——这样你才是至高者,上通“神圣”之域。欧洲历史上,有着比东方更为大量的上通“神圣”的战争——无数大大小小以宗教名义发动的战争。光是“十字军东征”就曾每隔数十年爆发一次,以“神圣”的名义来烧杀抢掠。这些宗教战争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神圣的”和“淫秽的”实际上从来是平滑交融、毫不见外的。
根据阿甘本对宗教的界定(制造分隔性结构),仅一个人或一群人内心里信仰神,构不成宗教。宗教一定包含一种分隔机制,把世界中的一部分东西移除出去,使其不再属于人的世界。祭祀,就是一种对这种分隔进行维持和管理的机制:通过各种仪式、程序,祭祀掌握着所有事物从尘世到神圣、从尘世法领域到神法领域的通道。于是,实际上宗教不是去联合人与神,而恰恰是去确保它们保持有所区分。这就意味着,宗教的对立面实则不是对神的不信仰或无动于衷,而是对尘世与神圣之“分隔”的忽视——例如,在对待事物或使用事物上,忽视“神圣”与“污浊”的属性之别。
“神圣化”这个过程,并不是不可逆的。被祭祀仪式“神圣化”了的事物,同样也可以被“污浊化”(profanation),以使之返回尘世领域。污浊化的一种最简单形式,就是人的“接触”:牺牲品乃至牺牲品的一个部分,一旦在祭祀过程中被人触碰后,就不再具有属神的性质。在宗教文化史上我们可以考察到:人们经常有意使用这种“污浊化”的接触,将猪牛羊这样的祭品的肝脏、心、肺等内脏供奉给神,而使其他部分“返回尘世”,且可以供人食用。今天,在江浙地区的清明祭祀习俗中,我们还能发现这种“污浊化”的操作。人们在家里祭拜完先人后,将供奉品(如酒菜、水果等)拿回厨房转一圈后再端出来,便可供人食用(笔者很多亲友家里都保持这个习俗)。“到厨房转一圈”,便是一个最典型的“污浊化”操作。[16]这种似乎毫不起眼的“人的一碰”,或者“回厨房转一圈”,从阿甘本主义分析视角出发,恰恰很值得深究。它们举重若轻地取消了包含一整套复杂仪式的神圣化操作,使遭到“分隔”并從人世间被排除出去的事物,一举“祛魅”,从而重新回到尘世。高高在上的“天子”,也同样能被去神圣化、污浊化。这就是为什么皇帝必须坐在高位上、住在宫殿里,就是为了保持其自身不被人轻易“接触”。
现在我们可以说:和商品结构一样,人类共同体具有一个怪异的结构性格局,那就是法律秩序及其溢出性补充。法律,结构性地具有它的淫秽溢出。作为法律之例外的“神圣”之域,实质上就是通过“排除”而在共同体内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特权空间。该空间以“神圣”的名义,反过来为并没有本体论根基的法律(尘世法)秩序提供一个“绝对”基础。一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那溢出性的“价值的巨量”,恰恰是使资本主义秩序持久繁荣的基础。淫秽的“结构性溢出”,恰恰是秩序本身结构性的必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溢出论”的根本命题。[17]然而,这个构成日常秩序之“绝对”基础的“神圣”之域,却是彻底人为构建出来的一种淫秽溢出。本文在第一节已经分析过,那些经由祭祀仪式被从人类秩序中分隔出去的人或物(神圣人、神圣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到另一个“领域”去,而是现在只对某些人——上通“神圣”之域的居高位者——开放。这些人(譬如“天子”)所占据的位置,正是内在于日常秩序的结构性溢出点——他们构成了共同体内的一个“至高的例外”。故此,中国皇帝通过儒家士大夫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而欧洲中世纪国王则通过天主教教宗来给自己“加冕”——两者实质上皆是确认自身至高者地位的政治神学装置。
经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进入如下这个自晚清以降在学界被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从古典文本本身出发,“儒教”的“教”实是教学、教化的教,而非神学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当我们根据当代马克思主义“溢出论”分析视角来理解宗教时,可以发现,汉代以降一直作为中国历代王朝之“王官学”的儒家,同样包含强烈的宗教向度。实际上,任何有“神圣”之域的文化里都有宗教。宗教使得在高位者成为主权者、至高无上者——“天子”之上就是“天”了,自然是至高的了。然而,如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权”一样,“神圣”之域从来就是被人为创制出来的。上古商周之际的“绝地天通”[18],实质就是把“神圣”之域垄断在少数高位者手里的政治神学操作。
古典儒家思想,在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层面上,实则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强大的话语装置。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天子”一方面和“父亲”同构,连各级官员都是当地老百姓的“父亲”。同时也承认“先王制法”,先王就是父亲祖先,《荀子》甚至允许“法后王”。[19]但另一方面“王”上通于“天”,承接“天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20]《史记·五帝本纪》专门写道:“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21]我们看到:“天”是被牢牢抓在包括皇帝和儒家士大夫集团在内的少数居高位者手里。
从结构性分析视角来看,儒家政治话语诚然“其至矣乎”[22]——“父亲”(尘世秩序)和“神圣”(对世俗“平凡性”的溢出)都牢牢握在手里,共同体内的个体如何能逃出其结构性笼罩?背离“父亲”是不孝,背离“天子”更是大逆不道。社会上所有规范,都有“父命”“天纲”两重加持,还怕你不从?是以,北宋王安石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3]时,他的“变法”自是无法持久,因为他把“父亲”和“天”都掀掉了,这就导致其所变之“法”丧失了根据。换言之,“变法”无法自我转变成日常秩序,而只能是一种充满肾上腺素的暂时性越界。所以,这就是“儒教”政治话语结构的强悍之处:民众可以“无法无天”大搞一通,但这种搞法命中注定只能是暂时性的,属于奢侈性折腾。法国思想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曾深入分析过这种充满肾上腺素的奢侈性折腾:从古代的“夸富宴”到节日庆典,其核心都是溢出性的过度、奢侈和浪费,它们是对日常秩序的暂时逾越,用来消耗掉过剩的能量、积蓄。但夸富宴取代不了量入为出的一日三餐,节日庆典也取代不了日常生产的秩序。
是以,儒教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借用金观涛、刘青峰术语),就缘于它在前秦典籍中就已经强有力地把“怪异结构”予以正当化,并卓有成效地将日常秩序及其溢出(“神学补充”)糅合到同一个话语结构中,进而以此牢牢掌握住结构的“上下”两端。在这个话语结构中,“天下为公”[24]和“天子”这个例外能够毫无违和的共存。儒教在中国“大一统”帝国格局形成的肇始期,便被提升为“王官学”,实际上有着政治哲学-政治神学根据;反过来,也正是儒教的被“独尊”,有力地使得“大一统”格局得以成型并持久存在。晚近倡导“天下体系”“天下的当代性”并以此“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学者们,很遗憾地恰恰没有触及“天下”秩序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内核。“天下”秩序的稳定性,实则建立在儒教社会对“怪异结构”的强大固化与正当化上。赵汀阳提出“天下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无外世界”[25],然而“天”恰恰就构成了该世界的溢出性的“外”。而“天下”本身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而非战争频发、“无法无天”事件频发的——世界,恰恰正是以这个淫秽溢出作为结构性的必需。
政治经济学-政治人类学分析:从人类祭品到共享经济
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現代化”“现代性”的巨量论述截然相反,以阿甘本为代表的溢出论者的一个重要洞见就是:我们从未现代。[26]所谓的“前现代”社会中的支配性结构,在二十一世纪社会中不止还存在,而且更为稳固,成为更为一般化的存在。诚然,现代社会中,宗教似乎被世俗化所“祛魅”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过去几百年的世俗化,实则并没有真正祛除宗教所导致的“怪异结构”,没有真正铲除溢出性的“神圣”之域。世俗化仅仅让主权者的“神圣”依据被改变,但却并没有触碰结构性的权力装置——主权者所通之域。此域从神圣的“天”(上帝、诸神)转变成神圣的“人民”(人民主权)。
施米特(Carl Schmitt)曾有一句著名论述:“关于国家的现代理论的所有重要概念,全部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27]而阿甘本接着说道:“神学概念的政治世俗化什么也没干,只是用领土性的君主制取代了天上的君主制,而让其权力完全无损。”[28]现代社会里,主权者继续“至高”,继续上通“神圣”。现代的主权者既在人类共同体(作为尘世法的司法秩序)之内,同时又在人类共同体之外:他们在法律之外,来宣称一切都在法律之内。现代社会的法律保护“人权”,却能在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总体战争”(total war)中大规模地杀人。而主权者,恰恰就是能发动战争的那个人。
当然,现在主权者不再声称他们自己“神圣”,不再称自己是“天子”或“天皇”。现在“神圣”的,必须是“人权”“人民主权”。[29]但是阿甘本的著作,正是旨在让我们警惕“神圣人”这个美好说法背面的诅咒:法律总会被淫秽地溢出,总会有人被祭祀,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所有人更污浊(黑人、妇女、移民、难民、农民工、低端人口、病毒感染者,等等,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变化下去)。故此阿甘本激进地提出,神圣生命(sacred life)就是赤裸生命(naked life)。[30]在阿甘本这里,“赤裸”不仅仅指向淫秽(对法律的淫秽溢出),更增加了一层血腥:“赤裸”意味着像祭品那样可以被杀死而没有法律后果。主权者所握有的那溢出性的至高权力,就是去决断谁成为人类祭品。而问题恰恰在于,从古至今的人类共同体,正是皆以这样的方式被建立,“从共同体中被排斥出去的东西,在现实中,正是整个共同体生活建立其上的基石。”[31]对法律秩序的淫秽溢出,反而是秩序的基石,使秩序更稳固。
可见,世俗化,并没有改变人类共同体“怪异结构”里的权力结构,也并未阻止该结构的自我永恒化。[32]人类社会的“古今之变”中,唯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世俗仪式和节日取代了原来的宗教仪式与节日。我们看到,古代的祭天变成了现代的国庆;民族-国家、人民、财产权(人权)等等,变成了新的“神圣”。现代的主权者,可以以新的“神圣”名义要求共同体内的个体去死,连语辞都没有改,即要求人去“牺牲”(sacrifice)。在今天,“壮烈牺牲”是很高的荣誉,而在古罗马,人类祭品(human sacrifice)的地位也很高。巴塔耶通过人类学研究发现,人类祭品在被献祭前,都得到相当尊贵的对待。那是因为,他们是代替整个共同体去死。人类祭品高于日常秩序,他们是神圣的。如下这个问题很值得追问:作为祭品的人和作为奴隶的人,哪个更惨?如果问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肯定很多人情愿做奴隶也不要做祭品,因为至少还能活。然而,古代罗马人的选择却是恰恰相反:一个自由人如果在被献祭和被奴役之间被迫选择,那他/她情愿选择做活祭也不要做奴隶——虽然死,但地位却比奴隶高很多(亦即,以“神圣人”身份去死)。反映古罗马社会的影视剧(如《角斗士》《斯巴达克斯》)使现代观众们多有不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做角斗士?那是因为:他们地位比奴隶高很多,他们高于日常秩序,他们是生产之外的“奢侈品”。角斗士的死,是作为人类奉献给诸神的祭品。换言之,他们通过自身的死亡,实则也极其短暂地(一次性地)上通“神圣”之域,暂时性地分享了至高者所占据的那个位置——在人类共同体的“怪异结构”中,该位置是整个共同体日常秩序的基础。
而奴隶,实则是日常生产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同人类祭品恰恰处于全然对立的结构性位置上。内在于奴隶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效益主义,是故金字塔能“奇迹”般地出现在完全不具备技术条件的古埃及。此一底层逻辑,便使得奴隶能够被隐秘地(变相地)世俗化:尽管奴隶违反政治现代性,即人权理念,但符合经济现代性,即效益理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之所以人们会谈奴隶色变,正是在于它把人对象化(不再是“主体”),使之成为工具的一部分。现代性基本的政治哲学框架(如康德所提出的“人是目的”),使奴隶的存在无法被证成。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恰恰揭示出:无法在政治层面证成的事物,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恰恰能够在经济层面被允许、甚至被一般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一个关键洞见正是落于人的“物化”上:表面上看你是人不是对象,但你的“权利”仍然使你实质上不得不出卖劳力,把自己变成工具、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进而给资本家制造溢出性的“剩余价值”。所以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平等,因为对奴隶们、农奴们的“解放”一定是假的。于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则正是以政治现代性批判经济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始终无法处理如下悖论,即,自愿做奴隶。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政治哲学代表人物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曾坦言:“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33]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实际上古代社会的奴隶(日常生产秩序)与人类祭品(该秩序的溢出性补充)以及两者所构成的“怪异结构”被全幅完整地延续和保存下来,并且被进一步地一般化。
既然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今天,仍然未能铲除那结构性内嵌于它自身的淫秽性的“神学溢出”,那么,我们是否就只能命定般地接受这种“怪异结构”,并进一步接受将该结构“一般化到所有领域之中”的资本主义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的最成熟状态?显然,对该结构完全未予关注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右翼思想家認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标识了“历史的终结”。[34]然而,以阿甘本为代表的溢出论学者,尽管在分析中揭示出那从古至今始终贯穿各种人类社会的“怪异结构”,却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顽强地拒绝接受这样的社会结构性状况,而坚持解放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述及,阿甘本把这种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已被一般化的“结构性溢出”,视作“神圣化”操作的产物。而他应治“怪异结构”的解放性方案,便正是对它进行“去神圣化”的操作。换句话说,解放性的实践,就是去实践“污浊化”(如前文所论及的对祭品毫不起眼的“人的一碰”抑或“回厨房转一圈”)。在本体论层面上,那些所谓“神圣的事物”自身内在并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而反过来,那些所谓“污浊的事物”自身内在也不存在任何受污染的东西。此处的关键是,如果没有“神圣化”操作,也根本不会存在“污浊化”。尽管“污浊化”会被人们普遍感受为不是一个好词,但这种感受恰恰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渴望“神圣”,恰恰是因为“神圣”之域(超越性、“形而上学微妙与神学精细”)在日常秩序(内在性、“平凡性”)中的结构性存在。是以,污浊化绝非降低事物的价值,相反,它是真正解放性的实践,因为这一实践“污浊”掉那自我标识为“神圣”的淫秽的溢出性空间,从而使其获得释放。对阿甘本而言,“污浊化,就是将已经被移到神圣领域的事物,返回到共通使用中”。[35]齐泽克建议捍卫真正的纯粹产品,而阿甘本则进一步提出,只有污浊化的实践,才能有效达成对纯粹产品的捍卫,才能铲除掉附加其上的溢出性的神学补充。“那些返回到人们共通使用的事物,是纯粹的、污浊的,它们从诸种神圣的名称中解放了出来。”[36]
接续马克思主义-阿甘本主义的分析性诊断,笔者旨在进一步提出如下论题:晚近因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产业创新所诞生的共享经济(如共享单车、共享雨伞等等),便正是以污浊化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有效侵蚀了那结构牢固的资本主义秩序。前文已经分析,资本主义秩序中的神圣化装置,便是“所有权”:“所有权”构建了一个神圣空间,事物被这个话语装置强行嵌上了排他性的“神圣”属性(“权利”),而不再能够在日常世界中被共通使用。正是在“所有权”这个装置下,事物才能被商品化(产生“交换价值”),最终一步步转变成彻底无法被使用的“物神”。
共享经济并没有直接冲击“所有权”这个装置(被共享的单车等仍然有其所有权归属),但是它却恰恰以污浊化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使用的共通化。换言之,它并没有直接尝试瓦解以“占有”为内核的“所有权”框架,但却挑战了“占有”这个观念。它在实践层面告诉人们,你不用占有,却可以过得更有效率;而在共同体层面上,事物也可以得到更优配置。我们看到,共享经济并没有绕道政治现代性(平等、自由、团结)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直接在经济现代性的层面上,展示了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操作所压制的事物之共通使用的效益主义潜能。在这个意义上,共享经济实则展示出,现代性可以不需要设置溢出性的“神圣”空间,在对事物“十分平凡”的共通使用中就能实现繁荣(“共通”一词本身就包含平凡、普通之意)。换言之,事物可以近似纯粹地保持其“十分平凡”的状态,而不再需要具有“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精细”。共享单车和早就发明出来的单车没有任何物质性的不同,但就如同祭品“回厨房转一圈”般,同一辆单车现已变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事物。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机械锁变成可通过APP定位、解锁、付费的智能锁外,共享单车较之既有单车的唯一内核性区别,就是使用代替占有,并成为人与它发生关系的方式。当你拿着APP软件找到附近的一辆共享单车后,不会想到去拿把防盗车锁出来宣示“主权”(“所有权”),而是想到真正地使用它。这才是共享经济带来的真正深远的革命。
当一辆单车可以被许许多多人“接触”,无疑它的“神圣”属性(只能被“拥有者”使用)被污浊化了。这样的产品,不再具有或极大地被削弱了“交换价值”。然而,恰恰正是这种被污浊化的产品,才是近乎纯粹的,因为它只剩下那十分平凡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它就是因被使用而非被交换而被生产出来。经过这般污浊化操作的产品,就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一个十分怪异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神学的精细”——它是没有溢出的单纯直接,甚至不是所见即所“得”意义上的单纯直接,而是所见即所“用”意义上的单纯直接。它传递给每一个看到它的人的信息就是:如果你不想使用我,那就无视我。
共享产品(共享单车、共享雨伞乃至未来可以去设想的共享钻戒、共享女士手袋,等等),结构性地无法上升到“神圣”之域、上升成为“物神”。对于巴塔耶而言,任何的奢侈品,就和宗教仪式上的圣品一样,都十分的淫秽,那是因为: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没有真正使用价值的、纯粹旨在消耗非生产性过剩能量的淫秽物。而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同样一只爱马仕包,当它以共享手袋的形态存在时,它是无法成为原先那种淫秽的“物神”的——当许许多多人都可以以共享方式背上它、使用它,它就彻底被污浊化了。故此,共享经济能够在既有资本主义秩序中生长出来,本身便意味着:当下的资本主义秩序并没有标识着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这种实质上颠覆资本主义隐秘结构的新事物,却竟是就这样在短短几年之内遍布于大街小巷。但也正是因为其内核处的激进性,可以想见:共享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会充满颠簸,甚至步步艰难。
由共享经济所重新复苏的对事物的共通使用,实际上,尚未能涵盖污浊化实践的全部旨趣。在共通使用后面,阿甘本更是进一步提出对事物的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是不按照设定好的方式使用,而是自己建立和事物的关系。阿甘本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小孩子玩玩具。很多时候,小孩子根本不按照玩具说明书的玩法来玩,大人跟他说不是这样玩的,他根本不予理会,而自己玩得很开心。实际上,对于任何事物而言,小孩子比大人更关心怎么“用”它,而且以各种创造性方式来“用”它,而不是像“物神”一样崇拜它和占有它。如果大人看到孩子以某种创造性方式——创造即意味着彻底污浊——使用爱马仕包,恐怕立即要昏倒,但孩子却玩得很开心,丝毫不会觉得这个爱马仕包跟其他玩具要分个贵贱上下。故此,如阿甘本所言,“从神圣到尘世的通道,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对神圣的一种全然不恰当的使用(或者说,重新使用)来产生,那就是,嬉戏”。[37]在小孩子手里,事物不但彻底摆脱了它们的交换价值,还远远越出了它们被设定的使用价值。自由使用意味着,所有事物都有被转变为玩具的潜能,意味着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结构性地投入新的使用。它所通向的,是阿甘本所说的“任意的创造”(whatever creation)。
一旦从十分平凡的对事物的共通使用进一步迈进到更加平凡的自由使用(小孩子都会),那么,所有商品(如爱马仕包)便都会被彻底地污浊化、彻底地打回原形:附加在它身上的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符号”(如品牌)与德波(Guy Debord)所说的“盛景”就都马上消褪了。[38]商品被还原成了没有任何“神圣”属性甚至没有任何符号性-幻想性的十分平凡的事物。自由使用较之共通使用更为激进之处便在于,它是一种彻底“没有目的”的实践,彻底抛开了效益主义逻辑,从而指向了人同事物的一种非效益主义关联。[39]而正是自由使用,才使人类不断发展出关于事物的新的使用。新的使用并不是更“真”或更“自然”,它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的基础作为依据或保障。污浊化绝非旨在恢复事物的前商品化的“自然使用”。这意味着,力图铲除神学补充(“神圣”之域)的污浊化实践,拒绝再次坠入形而上学补充(“自然”之域)的溢出性陷阱。所谓“自然使用”,实则是把事物固化在某一特定领域,将其绑定到一个目的上,从而使我们陷入工具性的主体—对象关系中。而这种固化与绑定尽管以“自然”名义出现,实是在根本上倚借某种形而上学的“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借用罗尔斯术语)来维持。[40]关于新的使用,人类学实则提供给我们很多具体的分析素材。譬如,人类学的考察能让我们看到:今天人类社会中很多游戏(如球类游戏、棋类游戏、运气游戏乃至陀螺、公仔娃娃、赛舟、登山,等等),都能在古代找到对应的宗教性实践的源头。在政治人类学的视野下,我们便可以提出如下论题:当代这些游戏,便正是祛除原先宗教實践的“神圣”属性而纯然保留其仪式的产物,亦即,它们是将原有仪式污浊化、挖去原本“目的”后产生出来的对它的全新使用。[41]
共通使用同自由使用尽管具有旨向上的重要差别,但两者实则仍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小孩子对玩具并没有什么“我的”“你的”的概念,拿来就一起玩,好玩才最重要,这才是通向以平等、自由、团结为理念性基础的现代共同体(相对于以“神圣”之域为基础的“前现代”共同体)的起点。自由使用,其内核是一种“无-法的使用”“没有权利的使用”;而建立在共通使用基础上的自由使用,则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使用,阿甘本本人直接称其为“共产主义的使用”,并将其视作“正在到来的共同体”的标志性特征。[42]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观察到,正是家长老师们在不断教给孩子,这是“我的”还是“你的”玩具。“占有”逻辑一旦出现,就使得玩失去趣味了(凭什么玩我的玩具,玩你的好了,我的玩旧了玩坏了算谁的……)。这样的逻辑一旦产生,每个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藏在自家抽屉里就好了,还拿出来一起玩干嘛?可见,占有逻辑一出来,使用就要马上退位,人跟人之间的联结也立即变味,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立即被“异化”。孩子眼里的世界,从此就是“你的”和“我的”的世界,而不是共同创造、共同实践、一起使事情变得好玩、变得有意思的世界。而在阿甘本看来,消费不会使你幸福,一起玩一起创造,才是幸福的根源。
资本主义之神圣化操作下的交换、消费、占有,永远无法带来幸福生活(eudaimonia)。幸福生活是“一个绝对尘世的‘充裕生活,它抵达了自身力量和自我可沟通性的完美”。[43]一个人占有了100个爱马仕包,也不会幸福,因为他/她还会想要101个——这就是占有而非使用的逻辑结果。无法抵达幸福,这便是内嵌于商品中的“无能”:事物不再能被自由使用、被共通使用,而只能被消费、被交换、被占有。今天的共享经济,至少在那密不透缝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迅猛并尖锐地标识出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在共享过程被污浊化的产品,不再能够被交换、被占有,而只能被使用,并且是被共通地而非排他地使用(尽管还不能被自由地使用)。于是,在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历史终结处,共享经济恰恰刺出了标识幸福可能性的平凡但激进的全新开端(New Beginning)。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ZDA017、2018ECNU-QKT012)
注释
[1][2]Marx, K., Capital, a New Abridgement, edited by D. McLell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2, 3.
[3]?i?ek, S.,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 edited by C. Mass,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p. 146.
[4]关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路向的学理研究,请参见吴冠军:《现代性的“真诚性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被忽视的理论贡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5][6][7][10][11][12][28][35][36][37]Agamben, G., Profanations, trans. by Jeff Fort,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pp. 74, 74, 81, 83, 81, 81, 77, 82, 73, 75.
[8][31]Agamben, G.,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trans. by Karen Pinkus and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05.
[9]Agamben, G.,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trans. by Adam Kotsk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 3.1.
[13]吴冠军:《关于“使用”的哲学反思——阿甘本哲学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面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14][意]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15]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霍布斯、康德、施米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重疏》,《同济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6]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17]吴冠军:《重思“结构性不诚”——从当代欧陆思想到先秦中国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吴冠军:《猿熟马驯为哪般:对〈西游记〉的拉康主义-阿甘本主义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18]《尚书·吕刑》。
[19]《荀子·儒效》。
[20]《书·盘庚上》。
[21]《史记·五帝本纪》。
[22]《礼记·中庸》。
[23]《宋史·王安石传》。
[24]《礼记·礼运》。
[25]赵汀阳写道:“人类共在的必要条件、人类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的关键条件,就是天下无外,即世界的内部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只有内部性而不再有外部性的无外世界。天下体系将成为一种无外的监护制度而维护世界的普遍秩序。”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26]这句宣称本身并非来自阿甘本,而是来自当代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by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Schmitt C.,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trans. by George Schwab,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36.
[29]哈贝马斯将“人權”与“人民主权”视作为现代性的两个根本性“支点”,分别代表自由主义传统与共和主义传统,而他本人的工作,则是致力于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对垒的夹缝中构建一条“程序主义”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完全没有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结构性溢出”的理论聚焦。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30]Agamben G., Homer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
[32]从词源学考察“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secular”来自拉丁词“saeculum”,指“生命长度”或“这个世纪”,它并不直接和神圣、宗教、诸神相关,只是在古典教会的语言里,把这个世纪(扩展为这个世界)和天上的永恒世界相对。
[33][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8页。
[34]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同时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38]吴冠军:《德波的盛景社会与拉康的想像秩序:两条批判性进路》,《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39]阿甘本本人所使用的术语就是“没有目的的手段”。Agamben G.,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40]吴冠军:《从精神分析视角重新解读西方“古典性”——关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路向的再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41]在我们的感受里,诗人和小孩子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这正是因为,诗的源头本身也同样是一种古代宗教性实践。后来的诗人则是抛去了诗的“神圣”属性而只保留了其形式,并同嬉戏的小孩子一样,时常对它进行自由使用、“任意的创造”。
[42]Agamben G., 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by Patricia Dal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7; Agamben G.,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43]Agamben G.,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 114-115.
责 编/桂 琰(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