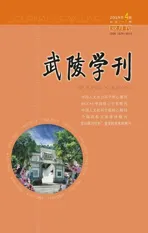左翼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的经验
——东京大学铃木将久教授访谈
2019-12-24刘成才铃木将久
刘成才,[日]铃木将久
(1.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2.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东京113-0033)
铃木将久(すずきまさひさ),196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87年考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93年留学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语中国文学博士毕业;历任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现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上海现代主义、竹内好与东亚现代经验,以及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中日知识交流。主要著作与编著有《上海现代主义》《竹内好文选》《当中国深入世界:东亚视角下的“中国崛起”》《竹内好的中国观》《如何形成“亚洲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茅盾》《如何理解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等,翻译有《竹内好的悖论》(孙歌著)、《世纪之交的“现代化”想象》(王晓明著)、《中国革命与亚细亚论》(贺照田著)、《毛泽东与中国》(钱理群著)、《谁都不知的香港现代思想史》(罗永生著)、《黑夜中漫游的灵魂:灰娃“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刘志荣著)等,被认为是中日知识界重新发现竹内好思想的主要推动者和日本第四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在中日知识界与文学研究界享有较高声誉。
本文作者刘成才于2018年10月11日在东京大学文学部铃木将久教授研究室与其进行了访谈,内容如下。
刘:铃木教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我阅读您的文章始于2005年,一次偶然机会在学校图书馆看到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读到您的文章《竹内好的中国观》,读后非常受启发,开始渐渐留意竹内好和您的文章。但之前读到的主要是您的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如《“国民文学论”与中国人民文学的问题》《竹内好的中国观》《竹内好与〈鲁迅〉》《如何形成“亚洲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茅盾》《钻研文化、赢得尊严:吕途“新工人”论述引发的思考》等,到一桥大学访学后,集中阅读了您的日语论文,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您的研究,所以才冒昧地请求对您进行学术访谈。
铃木:你辛苦了!非常惭愧,我的几篇小文和一点微不足道的研究劳你花费时间阅读。我非常乐意接受你的访谈,愿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同中国的学者深入交流。
刘:我把您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上海现代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现代性、竹内好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经验、日本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性与困境,我们今天的访谈就从这三个方面开始,如何?
铃木:好的。
一、上海现代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现代性
刘:我们先从您的求学经历开始吧,这可能更有助于理解您的学术渊源与学术道路。您是1987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当时怎么会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铃木:我当时就读的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入学时是文科III类,在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教养学部的课程类似于中国大学里的通识教育课程,大学一、二年级时不分专业,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学术素养,到三年级时,才慢慢地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专业,我选择的是文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在东京大学的本乡校区,但专业区分也不是很明显。1991年,我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修读修士课程,类似于中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导师是藤井省三老师,藤井老师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学者,我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专业,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对中国的好奇,希望更深入地了解现代中国,而现代文学当然是深入了解现代中国最有效的途径。要说明的是,日本学界没有“当代”这一概念,有的是“近代”(きんだい)的概念,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没有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区分,学者没有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区别,不然的话,我极有可能会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专攻,因为通过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中国更为直接。
刘:我注意到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多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您的导师藤井老师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您为什么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从鲁迅研究开始呢?
铃木:我倒是没怎么想这个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吧。一是藤井老师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学生研究专攻的选择也主要根据学生个人的兴趣,不会强求学生和自己的研究专攻相一致。而且,藤井老师本人的研究专攻也很多,他不仅仅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研究台湾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华语圈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村上春树在华语圈的传播,同时还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翻译了鲁迅作品、台湾作家作品、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包括莫言的小说,对莫言小说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所以,做藤井老师的学生非常幸福,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专攻。二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鲁迅研究太难了。由于语言的原因,我当时读鲁迅的很多作品感觉很困难,要想在两年的修士课程期间写出一篇很好的鲁迅研究修士论文是很难的,而且,在日本从事鲁迅研究的著名学者太多了,像大家熟识的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等,都是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他们已经取得了那么高的学术成就,后辈学生如果再想在鲁迅研究上有所突破,非常困难。三是我从本科时起就对现代主义非常有兴趣,虽然鲁迅的作品中也包含现代主义的因素,但总体上来说不是很多,所以才没有选择鲁迅研究当做自己的研究专攻。
刘:您的修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研究的重点都是上海的现代主义,而且到现在也一直在关注上海现代主义,您当初为何会重点关注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
铃木: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对中国比较好奇,对中国当时的状况关注比较多。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而要想深入了解中国的现代,我认为必须了解中国在最初是如何接受“现代”这一来自西方的概念的,往回追溯,自然就关注到了1930年代起在上海出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我当时喜欢读日本著名思想家沟口熊三先生的书,特别是读过他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等著作后,对沟口熊三先生从中国内部而不是从西方的冲击来研究中国的现代非常感兴趣,关注到上海的现代主义后,就想着从上海来探讨现代主义是如何从中国内部发生、发展的。
刘:上海的现代派文学,在1949—1990年的中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中国学界对上海现代派文学的关注,大致起于1990年代以后,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吴福辉先生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您对上海现代主义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铃木:1993年修读修士课程的时候,我开始研究上海的现代主义,关注重点是现代主义在上海的起始、演变、发展,以及最终走向这一完整过程。现代主义在上海最初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与接受的,当初的作家与理论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时着重点在什么地方,上海的现代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变化,其最终走向是什么,并最终以一种什么状态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中,这是我一直在研究中想要探究清楚的。
刘:您在《上海现代主义》一书中,把茅盾的《子夜》当做上海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研究,这一点比较新颖。因为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茅盾的《子夜》都被当做现实主义的或者写实主义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品,而且其写作意图是为了回应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也与茅盾秉承的“文学表现人生”创作主张相吻合,瞿秋白的评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为《子夜》的创作手法奠定了基调。长时间以来,很少有学者把《子夜》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子夜》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的?
铃木:我对茅盾的关注比较早,早在1994年,我就发表过《上海的媒体空间——读〈子夜〉》一文,论述《子夜》以及茅盾作品的现代主义,相关的文章还有《“上海事变”的影——茅盾〈林家铺子〉的方法》《异乡日本的茅盾与〈谜〉》《茅盾——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坛》《茅盾——异乡日本见〈虹〉》《一九二八年茅盾在东京》《抗日战争时期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以及2018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茅盾》等多篇文章。在《上海现代主义》一书中,我认为《子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现代主义的,主要从交流的危机、视线的功能、电话作为交流的空间,以及阅读的构筑等几个方面论述《子夜》对当时上海都市生活的表现。《子夜》是与那个时代的都市生活相对应的文本,《子夜》文本结构的错综复杂正是处于西方列强压倒性文化影响中心的半殖民地都市上海的表象,所以《子夜》是现代主义文学,而且这种现代主义的尝试不是茅盾一人的独创,当时的很多作家与理论家有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与探索。
刘:您在《上海现代主义》中把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当做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铃木:瞿秋白是我重点关注的革命家与理论家,我写过几篇文章论述他的翻译理论。与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理论,试图通过翻译改变中国人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同,作为革命家,瞿秋白认为应根本地推翻文言文的地位,创造下等人的新的语言,因为文言文巩固了高等人的统治,而翻译只要遵守“口头上说得出来”的准则就能够创造新的语言,帮助形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瞿秋白对理想语言的构想、对“文”的功能的转换、对交流乌托邦的构思等理论的设想与努力,为我们思考在上海半殖民地条件下,文化人如何开展自己的活动、如何形成推动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这一现代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刘:您在《1930年代左翼文艺思想与现代主义》等文章中,把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思想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1930年代左翼文艺思想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铃木:1930年代左翼文艺思想的现代主义体现,除了刚才提到的瞿秋白的语言革命理论外,更重要的还有胡风的理论建构。关于胡风的文艺理论,是我继《上海现代主义》之后的主要思考之一,承继《上海现代主义》的研究,我写过《胡风文艺思想与〈七月〉的实践》《民族与启蒙:在民族形式讨论中的胡风》《胡风文艺理论的形成及其问题》《胡风文艺理论初探》等文章。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胡风在“五四”传统的延长线上思考民族形式问题,针对讨论中排斥外国文艺的观点,主张世界革命文学与中国的民族现实相结合才形成“五四”传统并成为发挥全能作用的价值观念,强调作家的“主观力量”。胡风也重视农民语言,但又认为农民语言有“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必须经过知识分子“主观力量”的启蒙。胡风思考的是建立民族意识的时代课题,这在当时是最具现代性的。
刘: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如何,在后来的文学中又是如何存在的?
铃木:最具关键性的事件当然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现代主义的自然发展进程,但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完全被阻断了。战后路易士在台湾的现代诗歌创作直接推动了台湾现代主义的发展,战后香港都市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大陆毛泽东对文艺要表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理论设想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直到1980年代北岛的《波动》等作家的作品,都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刘:您现在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铃木:我现在研究的重点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这几年一直在写相关研究文章,最近要结集成专著出版。同时还研究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建国前后的思想转变,以及东亚视角下的中国“新工人”论述等。
二、竹内好与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经验
刘:您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竹内好的研究,主编过《竹内好选集》,写过《竹内好的中国观》《竹内好与〈鲁迅〉》《竹内好与中国:何谓“认识中国”》《如何形成“亚洲主义”:读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与〈亚洲主义的展望〉》等重要文章,在中日学界,您被认为是重新发现了竹内好思想的代表性学者,您对竹内好的关注最初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考虑?
铃木:研究竹内好,其实是我研究上海现代主义的自然延伸。刚才提到,我把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理解为中国现代主义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左翼文学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到了新的层面,如何认识1949年后的人民中国,人民中国的现代对东亚国家的现代具有什么样的经验借鉴,这些问题自然就进入到了我的阅读与理论思考视野。对于这些问题,竹内好在1950年代就曾经有过深入的思考,要深入理解这些问题,重新回到竹内好的思考是最直接的途径,于是,我开始慢慢地进入到竹内好的理论思考之中。
刘: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现在也依然存在这种状况,中国学界对竹内好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他的鲁迅研究,甚至造成现在很多年轻学者对竹内好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个鲁迅研究学者,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铃木: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成就太突出了吧,所以中日两国学界都把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称为“竹内鲁迅”。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竹内好的思想太丰富与驳杂,我们今天还不具备全面处理竹内好思想的理论准备,比如竹内好对人民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对国民文学的提倡,以及竹内好在日本“安保运动”中的诸多理论思考等,由于当今时代缺乏竹内好当时的现实背景,所以理解起来也就更需要理论储备与对现实的关怀,这也许是竹内好思想被简化的主要原因。
刘: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已经被学界研究得很深入,在中国更有“竹内鲁迅”之说,您认为竹内好鲁迅研究最核心的,或者说竹内好最迫切的理论意图是什么?
铃木:竹内好是在战争的不幸当中与鲁迅“相遇”的,对竹内好来说,这种不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还是日本那个时代的不幸,所以竹内好才会把《鲁迅》当做自己的“遗书”。战争中的竹内好通过主体介入思考真实中国,但却因找不到有效回应和介入方式而充满绝望感,他与鲁迅“相遇”,探索的是鲁迅“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的根源是“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试图从鲁迅文学里寻求摆脱自己困境的出路,并回应当时中日关系的现实情况。竹内好的这种理论追求,在我看来,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为缺少的品质。
刘: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开启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为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树立了标杆,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丸山升、伊藤虎丸、北冈正子、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诸多学者,在您看来,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并思考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意义在哪儿?
铃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对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影响很大,也出现了被命名为“丸山鲁迅”“伊藤鲁迅”“丸尾鲁迅”“藤井鲁迅”等诸多说法,但还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对我最具有思想的冲击力。战后日本最直接的思想课题是如何反省战争,随着竹内好等学者的努力,鲁迅在日本语境中慢慢变成文化偶像,竹内好自己也成为启蒙知识分子,但这反而大大削弱了鲁迅思想的冲击力,后来的日本中国研究者已经很难理解竹内好当年遭遇的困境,鲁迅的重要性也好像降低了。我们今天再阅读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关系其实并不融洽,冷战时代被意识形态的对立压下来的诸多问题,慢慢地浮现在两国关系之中。面对这些复杂纠葛,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几乎无能为力。因此,竹内好当时的精神挣扎以及他的《鲁迅》,对现在的日本有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示范与启发意义。而如何面对同时代的中国、如何思考包括两岸问题在内的东亚格局,这些竹内好当年思考过的问题,在今天反而变得日益紧迫起来。所以,我常常会想,面对今天这样的现实,如果竹内好还在的话,他会怎样思考?
刘:除了鲁迅之外,竹内好还关注并研究了哪些中国现代作家?
铃木:竹内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远不局限于鲁迅研究,只要浏览一下《竹内好全集》的目录部分,就会发现竹内好关注的中国现代作家有蔡元培、胡适、叶绍钧、茅盾、林语堂、曹禺、赵树理、周而复、陶晶孙等,除了关注这些现代作家,竹内好还关注“五四”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抗战文学、抵抗文学、人民文学等文学现象,研究对象非常多。虽然他的鲁迅研究影响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但“竹内鲁迅”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竹内好丰富而庞杂的思想是一种简化。
刘: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之外,赵树理是竹内好关注较多的作家,您在《竹内好“国民文学论”与中国人民文学的问题》中也曾谈到,竹内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度评价赵树理作品的同时,倡导了日本国民文学。竹内好提倡日本国民文学,为什么会选择赵树理的文学?
铃木:竹内好1950年代在日本提倡国民文学,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两个大事件使日本成了反共军事基地,此后,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让美军获得长期驻扎日本的合法权利。日本学界在这一时期集中探讨民族独立问题,竹内好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倡日本国民文学的。我要更正你提到的一点是,竹内好不仅仅讨论日本的国民文学,他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也就是说,他对日本国民文学的提倡,是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刘:竹内好的赵树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铃木:竹内好关注赵树理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赵树理文学大众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竹内好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文体,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与民族主义运动三个时期,赵树理是在继承现代文学传统基础上的飞跃。二是赵树理写到了来自老百姓的民族意识,看到了农民身上体现的个别性与民族意识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两点,竹内好认为赵树理文学超越了现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新纪元。
刘:除了赵树理,我发现竹内好对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评价也很高,这与他对赵树理关注的重点是否一致?
铃木:不仅是竹内好,1950年代的很多日本学者对中国那时的文学评价都很高,如饭塚朗、小野忍、岛田正雄、三好一、冈崎俊夫、鹿地亘、小峰王亲、洲之内徹、今村与志雄、桧山久雄等学者,当时翻译出版的中国1950年代文学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六十年的变迁》《东升的太阳》《麦田人民公社史》等。在日本被美军占领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当时的日本文学缺少负有责任感的政治意识,欣赏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责任感与拯救民族意识,希望以赵树理与1950年代中国文学为榜样,重塑日本国民文学理念。
刘: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中,赵树理的文学是作为失败的文学受到批判的,批判的焦点是对政治的迎合;在2000年以来的赵树理研究中,赵树理文学作为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典范重新被发现,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您认为转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铃木:我留意到对赵树理现代性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教授。这种转变的背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2000年以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功为东亚/亚洲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资以借鉴的经验,这种与以欧美为首的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另一种现代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需要研究者给以理论的回应与思考,而对赵树理文学现代性的阐释,则是最好的理论切入点。
刘: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中提出了与日本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又提出亚洲现代性的复数问题,中国知识界自1990年代末提出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与竹内好在理论上有没有相似性?
铃木:竹内好在1950年代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非常集中,一些代表性的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如《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作为方法的亚洲》《现代中国论》《日本与亚洲》《亚洲主义的展望》等。由于时代的原因,竹内好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在1950年代没有引起日本学界足够的重视,甚至被日本学界忽视了,但2000年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又为重新发现竹内好思想提供了时代背景,所以竹内好才会在中国流行。中国知识界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强调,以及贺桂梅老师对赵树理现代性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与竹内好的思考具有一致性,或者说,是竹内好思考的理论延伸。
刘: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很难被秉承现代性立场的文学史所接纳,有人理解为这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与“大众化”“民族化”的矛盾,您如何理解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史的这一悖论性?
铃木:“大众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是中国文学与知识界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现代的方向问题,所以才不难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会开展有关“民族形式”的广泛讨论,讨论遍及延安、重庆、成都、晋察冀边区,并涉及到知识界与学术界,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时代知识界的命运,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史上的核心事件。我在《民族与启蒙:在民族形式讨论中的胡风》一文中详细探讨过这一问题。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这一矛盾又显得异常明显,赵树理与现代文学史的这一悖论,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但文学可以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最终如何解决,要看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三、日本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性与困境
刘:是不是由于对竹内好思想的研究,所以您才会格外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关注当代中国的知识状况?
铃木: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作为日本学者,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竹内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他对亚洲现代性的思考,自然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当然,在此之上,我更希望了解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知识分子是如何思考自己国家的现代性的,这种思考与竹内好的思考有着何种对应,与日本学者的思考有什么异同。
刘:您关注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哪些?
铃木:从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起,就与中国很多著名学者保持联系,比如钱理群老师、王晓明老师、汪晖老师、孙歌老师、贺照田老师、蔡翔老师等,一直关注他们的研究,当然,也受到他们研究成果的启发,得到他们的很多帮助。这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是孙歌老师,她对竹内好的研究,对丸山真男的研究,对沟口熊三的研究,对我帮助很大,孙歌老师本人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多的批评与帮助,我曾把她的《竹内好的悖论》《冷战初期的“民族”与“民主”》翻译成日文出版。与贺照田老师也经常保持联系,他对东亚现代性的思考对我启发很多,我也把他的很多文章翻译成日文,如《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现代史研究与中国现在的思想与政治》《中国革命与亚洲论》《在困惑中搏求,在不安中承担》《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等。当然,我希望能与更多的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上的交流,为推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做力所能及的努力。
刘:您和这些老师思考的一个共同点是东亚现代性或者亚洲现代性,类似的思考与研究,除了中国与日本的学者,东亚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哪些学者?
铃木:在我的了解中,除了中国大陆与日本的学者,对东亚/亚洲现代性进行思考与研究成就较为突出的,还有韩国的白永瑞、白乐晴、李南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魏月萍,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陈光兴,台湾大学的徐进钰,香港岭南大学的罗永生,以及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帕沙·查特吉等,他们都是研究成就非常突出的著名学者。
刘: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总体上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关注比较少,很多人一提起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多谈及的还是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等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学者了解得较少,当下日本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也在变弱,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铃木: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那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太优秀了,后来的学者几乎都要受到他们研究成果的影响,很难超越他们。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从竹内好在1934年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发展到现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学者是竹内好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包括武田泰淳、增田涉、冈崎俊夫等人,还包括小野忍、饭塚朗、岛田正雄、鹿地亘等人,这一代学者均有过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对中国文学及社会有着切身的体验,他们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个人的精神困境,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第二代学者以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北冈正子、岸阳子、釜屋修、松井博光、饭仓照平等学者为代表,他们主要受第一代学者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竹内好的影响较大,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加上受日本战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时代因素的影响,对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有强烈追求,有着非常浓重的现实关怀意识。这一代学者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实证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学科进入日本当代大学体制的贡献居功至伟。第三代学者主要以藤井省三、坂井洋史、长崛佑造、工藤贵正、加藤三由纪、近藤直子、饭塚容、千野拓政等为代表,他们多是第二代学者的学生,他们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体制化,成为一门专门的知识,他们不再像第一代、第二代学者那样需要挑战既有的学术格局,这种体制化与知识化,当然也开始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慢慢地远离中国的社会现实。当然,你访学的导师坂井洋史先生一直非常关注中国,与中国学者交流比较密切,学术研究的范围也很宽,从文学到语言,再到音乐,进而深入到中国思想的内部,在这一代学者的研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第四代学者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与我年龄相似或更年轻,有代表性的如小川利康、伊藤德也、秋吉收、松村志乃、大东和重、谷川毅、滨田麻矢、櫻庭ゆみ子等,这一代学者多是在体制内工作,把中国现代文学当做专门知识研究,和中国社会现实联系不太密切,当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相对也小很多。
刘:在日本与中国学界,都有学者批评竹内好的中国研究更多地带有理想化的色彩,甚至有学者批判他有意地误导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说他介绍的中国几乎都是错误的,你如何理解对竹内好的这一批判?
铃木:中国学界我不太清楚,在日本学界是有很多人批评竹内好的中国研究,竹内好的中国研究中也的确存在着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知识,我认为,这种批判本身反映了日本学界的学术态度,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竹内好那一代学者的中国研究多少带有对中国和毛泽东崇拜与憧憬的情绪,这种研究态度突破了战前日本学界对中国缺少必要同情与理解的学术传统,在当时中日没有正式邦交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的理解难免理想化。但这种批评是基于历史的后见之明,忽略了竹内好思想特有的针对性和张力。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提到自己研究中国的契机是被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吸引,想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来探索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了站在客观的立场研究跟自己分离开来的外国,也就是说,他与中国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分割的关系。这种研究态度与日本学界模仿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态度产生了错位,对竹内好的批判显示了当今日本社会对“认识中国”的态度,今天重读竹内好,纠结的不应该是竹内好的中国研究客观与否,而应该是直面竹内好面对中国的独特认知态度,以及把他的中国认知与对日本的思考深刻关联起来的思想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仅不应批判竹内好,而应该深入思考在今天的现实处境中如何有效地继承竹内好。
刘:阅读欧美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章,总有一种隔的感觉,一看就感觉是外国学者的文章,而阅读竹内好与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这些学者的文章,以及您的很多文章,则没有这种感觉,非常自然,很容易会当做中国学者的文章,您认为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铃木:很惭愧,我的文章当不起这么评论,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学者的文章读起来确有这种感觉。我想,这主要因为他们的研究起源于一种问题意识,首先是为了思考日本自己的问题,然后进入到中国研究中去思考日本及研究者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这种研究就把个体与整个时代有机地联系起来,读他们的研究文章,不仅仅是阅读他们个体的思考,更是对整个时代的阅读,所以读起来会感觉到亲切,会感觉到自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会很容易产生一种代入感。
刘:现在年轻一代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和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这一辈学者的研究路径与切入点是否一样?
铃木:我对日本学界现在的中国研究不是太乐观。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这一辈学者的中国研究所面临的可以说是时代问题,是整个日本都在思考的,所以他们处理的是时代的大问题,虽然也注重细节的考证。现在的日本学者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很少关注中国问题,这可能和日本选择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有关,日本主要向以欧美为首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学习,很多学者主要的理论努力是如何学习与处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对中国的经验是忽略的。即使是中国的研究学者,由于大多处于大学等体制之内,关于中国的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对他们来说,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巴金、莫言等作家,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如莎士比亚、欧美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等,都是一样的,与个人的内心困境,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无关,只是一种体制化的客观知识,当然,也很难说与个人的情感有多少关联。
刘:在这种学术体制内,东亚学者该如何理解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
铃木:我在《日本谋求“问题化”的难度》一文中曾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老师的观点,“努力深入历史和现实,努力把现有知识生产脉络和理论思潮脉络之外影响和制约我们的历史现实因素问题化,使其得以被我们凛然面对”。我多年前批评的日本知识界“伪科学”传统盛行的历史与现实现在很难说有较大的改观,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大多数日本人依然存有冷战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与时代的错位是包括中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韩国、日本的知识界共同面对的困境。贺照田曾经提出应从“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状态”出发,我非常赞同,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经验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更是中国老百姓生活感觉上的社会主义,已有的研究多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验,而更重要的或许是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社会,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意义。当然,这是一种理论挑战,所以我认为东亚的协同在全球化时代非常重要,知识分子理应为此做出自己独特的探索与理论思考。
刘: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是否只是您的研究对象?您对中国的情感如何?
铃木: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怀念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的那段时光,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到中国常住一段时间,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和中国的很多学者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友谊,研究中得到他们的很多帮助。我也经常受邀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不喜欢日本的媒体和一些学者一直关注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和很多学者一样,对当下的中国也会有一种危机感,一个正在崛起的、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自然会形成一种危机感,我思考的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该如何解决、克服由于对中国的简单化理解和想象而造成的具体而真实的危机感。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战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同的历史经验,看清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研究,当然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刘:我在书店看到您翻译的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最近由みすず书房出版,书名翻译成《中国はここにある》,书名为什么没有直译?
铃木:一方面是因为如果直译成“中国在梁庄”的话,日本读者对“梁庄”这个地名不太容易理解,可能会影响对这部书的阅读;另一方面,基于对梁鸿老师这本书的理解,我更愿意把“梁庄”看做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梁庄里很多普通人的命运是中国在现代的象征。所以,翻译成“中国はここにある”,可能较好地表达了这本书的内容,日本读者一看到书名,会对书的内容有个直观的了解。
刘:为什么会选择翻译出版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
铃木:一是因为梁鸿老师的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很大;二是因为这本书对中国现代困境的表现,与我对中国现代的关注以及对东亚现代的思考相关,梁鸿老师的这本书逼迫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中国/东亚/亚洲”的现代,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现代道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更愿意回到竹内好的思考轨迹上去,再去经历竹内好当年直面的精神与思想困境。
刘:多谢铃木老师的访谈,更要感谢您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
铃木:惭愧惭愧,和中国很多学者的研究相比,我的研究显得微不足道,希望有机会能够同更多的中国学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