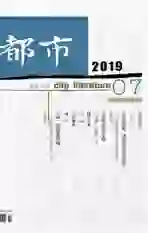去针孔里捕捉一头大象
2019-09-10成向阳
成向阳
一
此刻,我们聚集在此处谈诗的这个环境非常符合我对诗的判断与想象。人很少,也不专心,来来去去,玩着手机。这可能充分说明,诗,恰是一种特别弱势同时特别易于被干涉、被忽略、被随时打扰的文体。但我也发现,我们聚集的这张桌子的正中间,那一小截闪烁着微弱光亮的红烛。从一开始点燃直到现在,无论周围如何变化,无论人们怎样来来往往,它始终那样淡淡地亮着,悠悠地闪烁着、无惧无畏地照耀着。其实我们聚集的这个房间并不需要它,你们看我们头顶有多少大功率的灯盏,但这一小截似乎无用的红烛依然照耀,在一大片雪亮之中给我们的精神以幽淡、朦胧的一小块投影。
我觉得这一截红烛和它的光,正是今日诗歌之本身。
二
但诗并不可谈。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谈诗就像去针孔里捕捉一头大象。
当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开始一起谈诗,诗早已悄悄溜走,是诗以外的东西在嘴唇与嘴唇之间飞来飞去。诗是否只可意会是个问题,而将诗诉诸谈论已是低级。最高级的诗学已只是学问而非诗本身,且因高级而难得一见。
而最低级的诗学是一种荷尔蒙排泄工具,其终极目的是抵达陌生的身体。这似乎较为常见,比如一个意欲泡妞的人与妞之间。
三
一个谈论者的智能短板在对诗的谈论中显现无遗。
对诗的认识、判断与赏鉴,最能体现一个文学从业者的基本审美常识以及对语言的理解与把握程度。诗并不来自于轻薄而总是充满倾诉欲的嘴唇,而来自于浑厚的、振动的却又很难轻易打开的胸腔;诗不是对语言的铺排、炫耀与耗费,而是对语言最终的清洗与再造。写一首诗,要有冰雪天划最后一根火柴时的小心翼翼,而将一个词带进诗歌,要有将最后一颗子弹推入枪膛时的坚决,那是你最后的、仅有的力量的最后一次抛掷,很多时候它的目的地不是世界之外的任何对象,而是抵达你自身。而这仍然不够,于是需要停顿,需要贴着词与词的缝隙呼吸与审视,然后或将它们推翻重来,或将继续携带巨大的惶恐不安与世界、与具体生活的本质裸身相见。
四
诗是词语构筑物。诗不只是词语。诗在词语止步之处产生。但诗首先还是词语,被词语拒于关外的人怎么可以看见诗?
诗要求你成为第一个在那个词上留下痕迹的人。
像一只小鹿在原始的雪地上。
五
诗有大象而无常形。
但一切合格的诗歌一旦成形都势必产生“流动”。
诗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物,虽然它一瞬间被定格在那里像一幅以词语凝固的世界之相,一只词语塑造的蝴蝶,但它又必定携带着惊人的速度和加速度,它必定能以比它表面体积大一万倍的质量穿透阅读者之心并携带新鲜的体温远远飞出去。
像一颗灼热的子弹、像一滴冰凉的水在被穿透者体内裂变并在持续裂变中奔向下一个。
六
一个诗人的体内隐藏一个核反应堆、一个兵工厂、一个巧克力蛋糕店。
一个跳舞的人先要解放身体,一个写诗的人先要解放语言。当语言在诗人的体内获得解放,就有了核反应堆、兵工厂和巧克力蛋糕店。
诗的蝴蝶,从这三座语言建筑物上面同时升起。
七
诗在对万物的宽容相待中日益严格。诗在万物之上采撷诗意并持续提纯它的苦味。
诗对进入它之中的一切诗的东西都宽容相待;同时也对混入它中间的非诗的东西具有天生严峻的排斥力。
一首诗以梯状架在天地之间。那通天的梯子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远离黑暗,在抵达天堂之门的下一格,在仰视者眼中,诗的出口状如一个针孔。
一个倒置的巨大的深刻的漏斗中,谈诗的人啊,你坐在哪一颗微尘之上。
八
要允许一个人在诗中呼唤玫瑰,也要允许另一个人在诗中发出扣扳机的声响。但一定得是美的。
诗是一次美的救援。当诗之美抵达被围困者、被窒息者,稍有理智的谈论者闭上了朝天的嘴巴,开始深呼吸。
但诗不是美盲症者的解药,好诗美得无可救药。
九
诗是漂亮到极致的婴儿。
但几乎没有一个诗的谈论者能用自己生产的文本来验证所谈论之诗。
当一个谈论者向另一个提出终极检视的要求,那另一个就像自惭的母亲或者不育的女子那样闭嘴并保持了愠怒。
难道说,对诗的谈论是对诗的反动?
十
那些没读懂的诗为什么总是显得故弄玄虚?在诗分行的梯子上攀登的你为什么总像踩着一个一个骗局摔得头破血流?在你和那个悄悄写诗(制造骗局)的人之间究竟隔着几颗石头、几条河流、几维空间?
之于读诗,所谓读懂,就是向写诗者生存背景、思维逻辑和语言经验的靠近、融合与超越,并反身握手言和。
之于读诗,所谓不想看,就是那写诗者的生存背景、思维逻辑和语言经验对你已了无生趣,不如立判其死刑。但所有死刑判决都显得可疑,需要极端审慎。
之于读诗,所谓意义,就是一次一次接一次地持续建构自己思维逻辑和语言经验的免疫力,并对不同的生存背景产生认同、悦纳或悲悯。
十一
世界很大,但没有谈不死的一首诗。
来,加把劲儿,让我们谈死下一首。
十二
之于写诗的人,那种二尺距离之内的自照、自怜、自恋与自慰并不是诗。
这作用于表层的自我抚摸,一不涉及灵魂,二不涉及美。它只带来轻微的皮肉之癢。甚至不痒。
在北京香山公园门口盯视一群庄严肃穆的中年人时,我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自我观照,紧紧缩在一起,利用一台自拍杆前端绑架的手机。他们的表情、皮肉之下欲动的灵魂,和背后琉璃瓦遮盖的门楼子一样,是睡着的。
诗,永远不能是一根铝合金自拍杆。冷冰冰的,得意洋洋的。
十三
之于写诗的人,被边缘化是一种恰如其分。从舞台正中间被一步一步挤压到边边角角、甚至挤下舞台、甚至与舞台咔嚓一声产生断裂,可能正是一首、一批好诗的出处。
在舞台的正中心,那一小块喧闹浪潮形成的漩涡里,写诗的人唱的恐怕永远是别人的歌。
与被边缘化相比,被庸俗化或许才是一个诗人随时需要警惕之事。而庸俗化,就是送你到那喧闹舞台的正中央,一边吃奶油蛋糕,一边说胡话。
十四
之于写诗的人,应该把自己和自己的诗变得更小,小到一只针鼻里并穿过那针鼻。
写诗者之小,是不被时代的炒炉所膨化,不成为一颗滚烫的爆米花把自己飞溅在广场的人群里。
而诗之小,是诗要保持诗自身该有的体积与温度,不企图自我放大与自我升温。尤其是在诗歌思想与诗歌语言的层面上,诗的指向对象应该更狭窄,只对神灵、对自己、对有限可数的读者,喃喃而语。
大众化不该是诗的归宿,写大众化的诗不该是写诗者的本业。
十五
唐诗也不能被拿来作为诗歌大众化的证明。
唐诗在唐朝不如唐诗在当代更加大众化。说唐诗在唐朝是小的,这从唐朝识字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便可看出。从直到宋元才出现唐诗选本便可看出,从直到清初才出现《全唐诗》、直到清代中期才出现《唐诗三百首》便可看出。
在唐朝,诗在诗人圈子之内产生,但可能并不向诗人圈子之外溢出。
说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这是宋朝人惠洪在说白居易(的诗学追求),不是在说老妪(的读诗行动)。
诗仍在唐朝老妪的生活之外。
事实上,能有空去解诗的老妪也是绝对少数。
她或许是少数诗人的少数母亲。
十六
鲜有诗歌大众化的证明,连余秀华女士也不能。虽然余秀华女士的一夜走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众基于“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而对诗人生活的窥私欲。
但这无损余秀华女士的诗歌品质。大众开始关注并围绕诗歌热烈欢呼鼓舞也并非坏事。最起码,它改善了余秀华女士在人间摇摇晃晃的物质生活,让她顺利拿到了一张离婚证。
十七
当然,也许,诗歌的大众化也并非全不可能。当诗成为一种宗教,当伟大的诗人成为国家之神。
诗歌便有了它广泛、虔诚而狂热的信徒。
普希金之光笼罩下的俄罗斯便是如此。那里的母亲把圣经和普希金诗歌一起朗诵给睡前的儿童。
但,这似乎与诗歌的大众化仍有距离,或者完全是两回事。
它们一个是宗教化的大众向诗之神靠拢,一个是闹剧化的诗向大众之娱乐需要妥协。似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将这二者完全贴合在一起。
十八
而在一个诗歌师承资源如此庞杂而不清晰的中国当代,一个写诗者判断另一个写诗者的诗究竟是不是诗真的很难。这种难度,约等于使用最新款苹果笔记本的人费力去思考那款286究竟是不是电脑。
而286可能也正想着同样的问题。
十九
一个研究雪茄的海归90后诗人教我抽雪茄。告诉我,徐志摩创造了“雪茄”这个词。
所谓“烟灰白如雪,烟叶卷如茄”。从Sikar到雪茄,是诗的创造。
我告诉一个研究雪茄的海归90后诗人,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样去写诗。
你看雪茄一直在我们周围的时间里燃烧。你看时间一直在雪茄点燃的尽头漫过。
思维、语言和诗也是。它一点都不饶恕写诗者的懒惰。
二十
一个要回加拿大的用汉语写诗的女诗人最后问我,究竟什么樣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一个诗人。
夜深了。我没有回答。
这真是一个和夜晚一样深刻而可怕的问题。
一个写诗的人,需要用所有白天之后的所有时间去回答与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