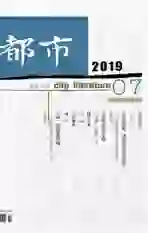来看我的戴胜鸟
2019-09-10玄武
玄武
自在如小鸟
清晨见一个辞去职务潜心写作的朋友发帖,说布拉格的鸟鸣,四点多就开始。我于是想中国南北方鸟鸣之别。北方清晨能听到的鸟鸣少,麻雀的聒噪盖过一切。偶或有斑鸠咕咕的叫声,然后是鸦科。乌鸦的叫声,像曳一根长长的大棒子划过天空,有时忍不住看天,仿佛怀疑它的叫声把天空划了一道伤。喜鹊的叫声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尾鹊飞动时空灵,发音却也是一口北方方言,又直又愣又冲,像扑上去就是尖嘴巴一叼。
南方的鸟鸣千回百转,委婉得很。奇怪同样一个小舌头,怎地它们弄出那么多娇媚之声。怪不得江南之地吴侬软语,想必万物,果然是相通的。
我见到一只不认识的鸟,黑乎乎的,也不好看。起初它站在路上,见我过来,并不飞走,而是小碎步跑到一棵矮灌木下———它迈小碎步真是帅呆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流畅,几乎不见迈腿,不像乌鸦那样一跳一跳。我油然想到戏曲里的花旦舞着长袖,脚在长裙里快快地走,满台上行云流水一般地转。
它站在灌木下等我走过去,然后它还要接着干什么。但是我不走,要看它,拍它。我走近去,它不飞,绕着灌木转圈躲,反正就是不想让我看到它。我加快脚步,像小孩子玩捉人,忽然反方向追它,它扑棱着飞起来了,哈,似乎是叫了一声,像在骂我:
干什么呀你这个人,讨厌不讨厌?
它不飞远,落在枝头偏头看。我不理它,假装看别处。五六分钟时间,它落到地面上。现在是它好奇了:
这个人站在这里不走,它在干什么?
我感觉它在我背后,偏着黑色的小脑袋看我。
它已经安然了,不觉得我的存在是威胁。它在地上行云流水地走动,一点也不用翅膀。我看它挪来挪去,从树荫里站到了阳光下,有车过来的声音,它又往回躲一躲,仍在光中。它是要晒太阳啊。
另一只鸟儿飞来,落在草地里。我走过去,相距五六米。它根本不管我。屁股对着我撅得高高的,一翘一翘。头埋在草里。它吃嫩草,或草籽,或里面的小虫子。
鸟兽屁股对着你,专心做它的事,是完全不戒备的意思。中间它抬头扭过来看了我一下,小眼睛乌黑,阳光下一闪一闪。它唧的叫一声,继续埋头吃。我觉得它是对我说:
耶!好吃着呢。反正你又不吃。
它心目中与我之间的安全距离,大概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安全距离相仿。我走近到一米多点时,它头也不回哗啦啦飞起来了。我很是赞叹。它飞行的样子,很有一只鹰的气势!
它飞过我头顶,我才清晰地望到它的喙,呈嫩黄色。
虽然它们个头不小,却只是几只当年的雏鸟。它们好奇,单纯,有小孩一样的童心,愿意跟我交流,愿意跟我玩一会儿。那些老鸟就油腻得很了,已经养成许多下意识的习惯,比如提防和机心,比如说假话———假装出表示有某一种需求的叫声,比如匆忙奔波———不会有沉下来望世界的心。老鸟像内心混浊看不出颜色的油腻男女。
学狗叫的野鸭子
黄昏时分,水边驯狗的老头。这么冷的天让狗下水叼棒子,如是者三,还挑选人多的地方炫耀。
我承认他狗驯得好,但难以接受他的残忍,和残忍的虚荣。
狗第五次下水时,实在看不下去,我起身离开了。
芦苇边,不小心拍到奇怪场景。这么冷的天,两只野鸭子全然不顾,在冰水中爱爱。
夜晚水边散步,忽然听到小狗的吠叫,———低沉有点沙哑,凶狠,是威胁又是警示。
黑乎乎的不辨,下意识看脚下,恐被咬。我怕小型犬,它们不讲狗理。但没有。初听声音是在水上,望去水面茫茫,不见有可落脚处,于是担心是哪只小狗被淹。
又叫了几声,很近,竟然是在我头顶。我吃惊极了。
抬头,苍黑的空中,有更黑的影子盘旋,望见时已在水面上。难道是它?暗中难识,有鹰翔之态。
水面露出的芦苇断掉的杆之间,有野鸭子的叫声,是在远去。我望不到它们。那叫声也是短促的低沉的嘎嘎声,我能识别出那是在警告同类:“小心,有个两条腿的家伙来了。”
再看空中,那盘旋的鸟儿不见了。纳闷是什么鸟,难道和野鸭一伙?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鸟儿又出现了。展开翅膀很大,飞行不快,可知不是鹰类。它又发出一声短促的狗吠,就像小狗看到人离去、危险解除时的吼吼声,音低。然后,它发出了嘎嘎的鸭子鸣叫声!
是的。是一只很大的野鸭,承担夜间警戒任务。鸭中斥候。
野鸭子能发出狗叫声,我生平第一次遇到。
一只麻雀,两三只麻雀
一只小麻雀,在栅栏上,与我视线平行稍低,随我步行的方向蹦蹦跳跳。我看它,它是出窝不久的雀,在阴翳的天空下依然黄灿灿,每一根羽毛都新崭崭。
我并不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打量它,它随我步行的方向一蹦一蹦。觉察到我的目光,它害羞了,扑棱着飞起来,却是从我眼前横飞而过,不高于我头顶。它那么傲娇,肚皮下细细的小爪子,在我眼前一晃。距我不过一尺,哈,它几乎是擦我眼皮飞过去。
世界多么生动。我这么一直写下去,是写不完的。我一边写事情一边发生。世界聚汇如海,从笔尖的小隙挤压而出。
能够被世界的生动拥簇,一颗心随时随它荡动,随鸟儿飞舞,随花朵开放,随豹子杀戮,随大狗奔跑,随小童哭笑交加,随老者哀伤,随少女怀春,随义士愤怒,随狐狸眼珠子一转,是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两三只麻雀,从我脚下掠起。它们灰黄地翻动着,贴着地面,不高飞,一点向上的势头都没,再落入低低的草丛。我并没有看它们,心里想着什么,还以为是风搅动,卷起了地下去年的落叶。
在时间中,生命的性质会模糊。园柳变鸣禽,落叶变麻雀,我也会站成一棵树,伸开臂膀栖满飞鸟。我也会流成一条河,随意将浑身的水滴溅起。
我认为那些写下来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句子,就是最好的文学,无论长短,哪怕只有一句。一句就够,就成立。它们还冒着刻打時微小的崩开的火花。
一句即可以像劈开海水的力量,显露出水底多少年前淹没的城郭,以及淹没的河流———那像人最深处被搅动的、清晰地显露出来的记忆。甚至,会是人的原始记忆,祖辈世代遗传的记忆。
为什么要敷衍成章,弄成期刊上刀子切豆腐一般整齐的一块一块,五千字,八千字,一万字?期刊削足适履,作者稀释成性,由有然矣。多出那一句的,都是废品。是废物。
你会说大家都如此。大家,完全不能代表什么。而且可能相反。这许多年,大家一起做并以大家都这样来安慰自己的愚蠢的事,难道还少么。
女孩子的鸟
小时候得到一只鸟,忘记是怎么来的,反正它是属于我的。我把它两只爪子捆着,它飞,却飞不远,逃不掉。那么一直是我的。
后来它飞起来,一头撞到门上。撞死了……
我给我的鸟下葬,在树下挖了个坑,把我的鸟埋到土里,弄了一个隆起的土堆,是我的鸟的坟。我用纸片做了一个墓碑,在上面写:啄木鸟之墓。
我不知道鸟的名字。那时候我唯一知道的鸟名,就是啄木鸟。
总下雨。一下雨我就惦记我的鸟儿的墓。雨停了我就去看。纸墓碑被雨水打得不见了,土堆也平了。找不到我的鸟儿的墓在哪里。
我就挖土,终于找见它。我把我的鸟儿挖出来,它浑身是土,嘴巴上也是泥。不会动,不会飞,真的死了。
我再把它埋到土里。每过一阵,就刨出来看看。
有一天,再刨出来,它终于没有了。它不再是鸟,是细细的小骨头。
关关之声
空气中到处是鸟儿求偶的鸣叫声。它们相互嬉闹,追逐,召唤,飞到并不茂密的树叶间快乐地交欢,一边发出忘我的尖叫和呻吟。甚至能听到它们极度销魂时小翅膀抖动的声音。这些呆鸟,它们怎么可以判断我不懂?
坐在树下,我难免有点难为情。它们这么诱惑我,不顾忌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触,还把腹部细小的软羽,嘲弄般地扔到我头上来。
它们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有点纳闷。已经有小小的各色鸟儿,笨笨地在隐蔽处学习飞行术。我注意到一只雏黄鹂鸟,往一根苇草上落。它没掌握好平衡,扑棱着小翅膀跌下去。它下坠的动作好狼狈啊。不知吓着了,还是觉得丢了脸,还是跌疼了,我听到它的叫声持续了好长时间。看不到它,它就在那里一直哭。两只稍大的鸟急匆匆飞过去,几乎是在那根苇草边擦翅直接落下,消失在草丛里。它们的飞行轨迹堪称完美,就像用铁丝折成了一个直角。
应是小鸟的父母。小鸟儿得了安慰,或者得了一只虫子哄,不哭了,安静了。树下来了俩老头,在谈论六味地黄丸的事。
我离开,没有等到鸟重新起飞。手机写到这里,一个雪白的大鸟在眼睛余光里掠过。抬头来得及捕捉到它消失在远处。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词汇是:惊鸿一瞥。这就是惊鸿一瞥。
如果此时你的心静若止水,你又正巧看到了它,那么它就像在池塘里投进了一块石头,水面要荡动一阵了。
嫩燕子
燕子回来了。很嫩的小燕子,说话慢慢的,飞得也慢,只在高空笨笨地翻着小翅膀,像麻雀。
大燕子是上下翻飞,翕乎往来。丢下一连串呢喃,看见它飞走消失了,才来得及听到它的话。大燕子发声是干脆利落,不像小燕子带着粘音。
来看我的戴胜鸟
两只戴胜鸟,飞在我身后不足五米远的栅栏上,看我蹲着干什么。不太惧生,反倒有点欺生。我回头时,一只还偏一下脑袋,头上的羽冠更神气,那意思像说:
嘿,没带相机吧?就是让你拍不着。
我往起一站,它们眼花缭乱得不见了。空气中振动的气流久久未散开,我在其中,等它们翅膀打开的气流,轻轻地一股一股绕过我头顶,脖子,脸,耳朵,把我手中的香烟升起的烟雾弄得凌乱。
又一次写到麻雀
麻雀是高度警觉的小鸟———它算鸟吗?过于普通,遍地都是。
观察到黄昏时麻雀的栖落和飞行,都是成对的。两对麻雀,面对四个方向。那是刚刚落下,严阵以待,合作监视环境。稳定下来后,变成每一对监视一个方向。
有一对飞走了。剩下的一对麻雀立刻变成背对背,各朝一个方向。
有个美国人著一书《鸟的故事》,董继平兄翻译,他近年译了许多美国自然文学的著作。那是一册真正堪称讲述鸟类生活的书,不像国内书胡乱吹牛,名不符实。比如讲到麻雀的智力活动———有只雄麻雀捡到一根好看的羽毛,衔回窝里,得意得叽叽喳喳飞高飞低叫。像个农民发了财满村炫耀。它邻居一只母雀,羡慕得不行,它一飞走就飞进去偷出来。但并不衔回自己窝,而是飞到树上找浓密树叶藏起来。
一会儿雄雀回窝,羽毛不见了。气得暴跳如雷。它首先飞到邻居母雀窝里,看看羽毛在不在。木有。于是蹿高飞低叽叽喳喳,那是骂了,像个泼妇骂大街。
那只母雀在附近树上,假装没事人看热闹。
等那只雄雀安静了,又飞走了。母雀飞到藏羽毛处,衔着返回自己窝里。它多么开心啊!于是蹿高飞低,叽叽喳喳。那不是炫耀,是按捺不住的开心。
这作者花了多少时间,精力,来研究一只鸟儿的活动。麻雀———这么普通的简直不能称鸟的鸟儿———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我们鄙俗,愚蠢,几代人也只有单调的表象化的知识,只知道它们叽叽喳喳。
灵之雀
一大片、一大片又一大片的梨花,高高低低沿路边延伸开去。有时树遮住了,或遇崖忽然不见,心里急切,像少年望见倾慕已久的女子在眼前消失。赶紧看路那边,啊,她在那边更妩媚。赶紧前行,啊,前面还是她亭亭站立。多么幸运的女子,在少年心目中,美得像十万亩梨花开放!
我的心荡动不息,我的心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扑棱着飞起来,飞得也不高,不快,还不知落向哪里。我一辈子了不知麻雀叫声里的情绪,我猜几乎所有国人都不知道。但这次我确定,这是一群惊喜的麻雀发出的叫声。
好的,我的灵就是那雀,它轻轻站在梨树之巅,这棵,那棵,还有那棵,一排排过去。我的灵要像雀一样小,轻,风微微吹起它的羽毛,它不会压坏哪怕一瓣梨花。我行车很远了,我的灵还在那漫野的梨花之巅的枝条上荡动,這只雀,那只,一大群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