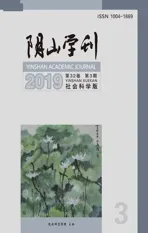神灵慰藉下的苦难命运
——评刘庆的《唇典》
2019-03-02乔霞
乔 霞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刘庆自19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2017年,刘庆出版长篇巨制小说《唇典》,次年荣获第七届“红楼梦奖”,这部小说亦是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唇典》述说萨满传人满斗的家族故事,展现东北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命运。主人公满斗是一位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拒绝成为萨满的命运,其身世充满传奇色彩,郎乌春是其名义上的父亲,众人却认为是公鸡玷污其母所生,其生父实是穿白色衣服的工程师李白衣,也是后来的大匪首王良。满斗的母亲柳枝独自一人抚育满斗,命运坎坷而悲凉。满斗所爱的花瓶姑娘最终成了其生父的爱人,也即满斗的继母。暮年的满斗最终成为了一名萨满,他希冀通过种植灵魂树来寻找丢失的灵性。《唇典》是一部讲述神灵慰藉下的苦难命运的故事,当命运的苦难早已得到暗示却依旧无法改变、无法结束时,东北人民凭借对萨满与神灵的信仰和敬畏,完成了与苦难的和解并获得救赎。
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1]书写苦难的作家有很多,但刘庆笔下的苦难揭示了苦难时代东北人民还未知的一些存在和力量,讲述了萨满的伟大与神秘,书写了苦难的宿命性与普遍性。本文以萨满、苦难为切入点,通过对满斗、郎乌春与柳枝等人物形象的分析,窥视萨满背后所包含的、为东北人民所信仰和敬畏的神性,思考永无终结且既定而不可对抗的苦难命运,探索刘庆书写苦难、救赎苦难的方式,以及言说苦难背后的深刻意义与价值。
一、苦难的书写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慕诺说道:“苦难证明我们的存在,苦难证明那些我们所爱的的确存在,并且苦难证明上帝也存在也同样受苦。”[2]人类的命运总是伴有苦难,文学讲述人的故事,因此苦难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书写苦难亦始终是作家执着的追求。刘庆笔下的苦难具有可预见性且具有宿命性,具体表现为东北人民虽然通过萨满知晓苦难的存在,但却无从改变苦难的命运,亦无法与之对抗。刘庆笔下的苦难还拥有普遍性,苦难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唇典》中的每一个人物各自有各自的苦难,且无法逃脱。
(一)苦难的可预见性与宿命性
萨满在《唇典》中占据大量篇幅,刘庆也正是凭借对萨满文化的描写实现了对苦难的书写。刘庆笔下的苦难具有可预见性且具有宿命性。萨满通过“跳神”的方式与神灵相通,掌握了人类生命形态中神秘的一面,因此萨满其实提前向东北人民揭示了即将面对的苦难命运,但苦难依旧无法改变。当郎乌春听着青衫妇人讲的奇怪故事时,东北人民的苦难在萨满的通神中显现。博额德音姆萨满说道:“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东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3]14大萨满预言了东北人民即将面对的战争与灾难,但即使大萨满预言了白瓦镇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人民的苦难,苦难依旧无法改变,亦无法与之对抗。
郎乌春命运的最大转折处是他当上灯官老爷那一晚,当灯官老爷和灯官娘娘乘着轿子来到亚洲火磨公司门口时,白瓦镇最大的一场胡匪抢劫事件发生了,这使得郎乌春心爱的姑娘柳枝最终下嫁于他,但也是这一晚让柳枝失去了清白之身,郎乌春内心无法接受柳枝腹中的他人之子。“郎乌春的心里说不出的别扭,他这会儿才知道,接受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新娘是多么艰难,即使抢在他前面玷污姑娘清白的是一只该死的公鸡。”[3]63于是,当韩玉阶“拉队伍”时,郎乌春积极响应,参加了首善乡保乡队,由此也踏上了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郎乌春的苦难体现在其长期徘徊于各色组织与队伍之间而难以寻找到自己准确的人生定位。他反复游走于各种组织之间,职位更替频繁,生活颠沛流离,但却没有一次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他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暮年的郎乌春回忆道:“这些年的日子真像梦一样,谜一样。一闭上眼睛,欲望、逃避、背叛、眼泪、子弹、疯狂、银元、理想、狗屎、革命、迷茫、痛苦、叮叮当当、稀里哗啦、倾泻而下。而命运和不测的下一个章节又已掀开,露出羊肠一样的盘根错节。”[3]397郎乌春最大的苦难是他作为一名英雄但最终被迫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挽救五个伤员的性命,他不得已垂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当郎乌春想要再次看“姑娘表演”而未看到时,他意外地从博额德音姆萨满那里得知了自己将来的命运。萨满说道:“谁的心里藏着镜子/谁的心里生长刀剑/谁的眼睛能看清黑夜/谁的骨头不再洁白/谁的鲜血不再纯洁”[3]15;“大红冠子的公鸡扇着翅膀,站在院子里的姑娘挥着手帕。去吧,一个雷会击中你的头顶,你会用雪水和血水洗脸,你的命运就要改变。”[3]15郎乌春不幸的婚姻与颠沛的从军生涯都在萨满口中得以预见,命运的转轮神奇地按照萨满所说的行进,郎乌春的苦难无法改变且越加深刻。当郎乌春无意间再回忆起当初萨满所说的话时,他终于有所顿悟,但即便如此,他仍旧无法改变这苦难的命运。
(二)苦难的普遍性
《唇典》中的苦难书写还体现在苦难无可逃避,具有普遍性。柳枝、满斗、苏念、蛾子以及其他人都逃脱不了苦难。柳枝的苦难在于白瓦镇遭胡匪抢劫的那一夜失身,漂亮的柳枝一夜间跌入谷底,此后的人生愈加悲惨。柳枝虽最终嫁给郎乌春,但这场婚姻的“完满”却是以五亩地的交易来达成的。婚后的柳枝被丢在马滴达独自生养满斗,为了保护孩子,她与恶狼勇斗,之后又抚育丈夫郎乌春与其他女人的孩子。柳枝终于不再是那个备受保护的少女,她可以熟练地做各种农活,为了平整出一块生长庄稼的土地,她用力用镐头耙地,“潮湿的黑土里爬满了大个蚂蚁,土腥中涌动着胖大的截虫、一团一团的蚯蚓,一条小而细的白蛇从冬眠中醒来。放在六七年前,她不知跳起来惊叫多少次了,会哭得一塌糊涂。可是现在,这些再平常不过”[3]98。
满斗的苦难在于他一生都在拒绝成为萨满,但夜视以及看见他人梦境、预测未来的能力却始终伴随、扰乱着他,甚至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危险,他最终还是无法拒绝命运的安排。花瓶姑娘亦是饱受苦难,其父母双亡,弟弟也离她而去,她迫于生活需要而成为供人娱乐的花瓶姑娘。满斗真诚的爱与追随似乎给花瓶姑娘的苦难命运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最终她为了活命不得不嫁与土匪王良。
蛾子的苦难更为深刻和震撼,当苦难的蛾子摇身一变成为斗争大会的主要领导人物时,她的残暴、凶狠、无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所经历的苦难,这些苦难化成一把锋利的刀,直插人的心脏。蛾子成长在一个缺爱,甚至是无爱的环境下,她的一生充满了悲惨与痛苦。蛾子自幼满受煎熬与委屈,既不受养母疼爱又遭兄长满斗的欺辱,她的生母丢弃了她,父亲从来没有给过她一丝温暖,她的生存简直是一场奇迹。蛾子最大的苦难在于她后来的剧变,也是这剧变造成其生命的终结。在那段灰色的岁月中,蛾子发明“坐疙针柜”“扔腚墩”等残酷的逼问手法,她身上体现出的人性转变是深刻且震撼的,她的暗恋陶玉成更是其生命中苦难的催化剂,也是其生命中最大的绝望。
《唇典》中的每一个人都苦难地活着,而这苦难早已注定且无法反抗。但如果书写苦难仅仅是为了展现毫无意义的毁灭性力量,那苦难自身就失去了意义。赋予苦难以意义的实际是悲剧性的洞察与深度思考苦难的救赎与超越,刘庆正是洞察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命运,书写了苦难所具有的超越作用进而展现出了生命力量的韧性。
二、苦难的救赎
《唇典》中的苦难因无从摆脱与反抗而使得人物命运充满无奈与悲凉,可是作者没有一味宣扬这种极致的苦难,而是通过萨满文化这一介质给予苦难以人道主义式的宽慰与救赎。《圣经》强调人类需要懂得感恩,信仰上帝,由此获得救赎。[4]《唇典》中,刘庆将这种信仰化成了对萨满文化的敬畏与尊崇,也因此传达了信仰救赎苦难的理念。面对苦难,刘庆并非仅仅停留在痛苦、恐惧、绝望等基本生存感受上,而是试图洞察苦难,给予苦难以不同方式的救赎。《唇典》中的郎乌春与满斗选择了逃避苦难,试图以此来实现救赎,但最终仍是陷入苦难。柳枝等人信仰萨满文化,她们以信仰的力量给予生命以勇气与信心。这种信仰支配了人物的日常行为并内在地改变了其思维方式,由此苦难得以消解,苦难实现了真正地救赎。
(一)逃避苦难
生活于无尽苦难中的东北人民为了获得救赎,尝试用长久的逃离姿态来实现这一目标,但逃离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救赎。满斗为了获得救赎选择逃离出走,但他始终无法获得救赎,最终成为了一名萨满。当大萨满李良决定将满斗收为徒弟,满斗说道:“老实说,我对记住这些祀神没有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师父李良的法术。”[3]159面对师父李良的教导与传授,满斗选择逃避,李良也承认满斗不愿意担起族人的责任。满斗看见祖先神的法衣时,李良萨满的灵魂告诉他赶紧跪下磕头,满斗并没有下跪,他哭得像一个满脸鼻涕的丫头,李良萨满叹息地说道:“孩子,你注定成为一名萨满,你逃不出你的命运。”[3]250满斗依旧选择奔跑、逃离,尝试对成为萨满的苦难进行救赎。此后,满斗成为了一名军人,也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认为他的逃离姿态获得了苦难的救赎,却未曾料到暮年的他最终成为了世界上最后一位萨满,而当他直面自己萨满的身份时,满斗的苦难终于得到了救赎。
同样选择逃避苦难的还有郎乌春,郎乌春从不曾正视和接受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当妻子柳枝怀着他人的孩子嫁与他时,他不能接受自己将要面临的不幸,即使他真心爱妻子柳枝,但他却不能与这样的苦难达成和解,于是他选择逃离。他甘愿跟从韩玉阶的号令,开始了迷茫的军旅之途。逃离并不能获得救赎,因此当苦难再次接踵而至时,他又一次选择奔波逃离于各色组织之间,却未曾想到这加重了他的苦难。暮年的郎乌春想起自己混乱颠簸的生活,自己的命运早已被揭晓,但却不自知。最终在柳枝的照顾下,他接受了自己的苦难,至此他与妻子柳枝最终实现了圆满,苦难得到了救赎。在试图救赎苦难的过程中,萨满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刘庆构造的神、人与萨满三者并存的世界,实际隐含了作者对于消解苦难,获得苦难救赎的深层次思考。
(二)消解苦难
“消解苦难,即是于苦难处转身,这种转身并不是对苦难的妥协,而是通过受难个体对苦难的隐忍、消化、遮盖甚至遗忘,把苦难淡化甚至放置于虚无之中。”[5]刘庆借助萨满文化实现了对苦难的消解,也完成了对苦难的救赎。作者反复强调的萨满文化其实是强调存在一种信仰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唇典》中,这种信仰以萨满文化的外衣进行了包装。刘庆构建的神、人、萨满三者并存的世界些许继承了许地山的创作理念,许地山在处理苦难时常从宗教中汲取养分,借宗教达观地看待苦难,甚至享受苦难。刘庆则是将宗教信仰转变成了对萨满文化的尊崇,借此实现消解苦难的目的。与许地山不同的是,刘庆在萨满文化的外衣背后更多地是张扬生命的力量,许地山则更多强调宗教的力量。
柳枝苦难的消解与李良萨满有很大关联,正是在李良萨满的援助下,柳枝直面了生命中的苦难,实现了苦难的救赎。柳枝年幼时问李良萨满是做什么的,李良说道:“萨满就是生命的向导,可靠的护神”[3]83,并承诺柳枝会保护她,也会保护其他人。柳枝遭他人玷污,企图放弃生命时,李良萨满给予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当柳枝决定不顾孩子自寻短见时,李良萨满给她唱了一段神歌。柳枝受到神歌的打动,感喟母爱伟大,决意活下去。命运的苦难在萨满出现时得以缓解,尽管往后的生命还将继续着各种苦难。李良萨满说道:“泉水伤心的时候会呜咽,欢快的时候浪花洁白,泉水比我们更知道生命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流过了就流过了,每一刻都是过去,每一刻都是开始。你不必为河床的肮脏负责,因为,你没有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有承受和承担,承受你不想也会来的一切,承担你必须承担的责任。”[3]86萨满告诉人们,我们应对万物存有敬意,我们的苦难只能承担。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当命运既定如此的时候,我们不必埋怨,我们可试图与这偌大的世界和解。在历史长河之中,人是极其渺小的一点,生命何其卑微,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刘庆巧妙地将基督教中的原罪论与萨满文化相融合。“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的弃儿,都受过伤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伤害过别人。生命是祖先神和我们的父母共同创造的奇迹,祖先神在另一个世界做苦力,只为我们能来这个风雨雷电交织的世上。我们总感到身心俱疲,有时丧失活下去的勇气。”[3]86由此,人类与苦难的命运达成和解。萨满借李良之口讲述生命的意义、时间的力量,也劝慰苦难的人们与命运和解、与苦难和解、与怨恨和解。在和解与消融背后,命运的轨道得以延伸,萨满的信仰得以延续。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萨满描述较多,她笔下的萨满具有解救苦难的作用。当鄂温克族人遭遇困难时,萨满能够帮助族人转危为安,苦难的命运得以被解救。刘庆则执着于思考消解、救赎苦难的方式,在刘庆眼中,苦难是无法摆脱亦无法解救的。在言说无尽的苦难与尝试给出苦难救赎方式的背后,刘庆更多思考的是苦难本身所固有的意义以及信仰所具有的力量。
三、言说苦难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应当以沉思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而不是沉醉于日常生活的安逸表象中,作家勇于揭示苦难的行为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没有苦难的生活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因为只有经过苦难的熬制,在苦难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才值得人们珍视。”[6]刘庆描述东北人民苦难命运的背后饱含着对传统的留恋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东北人民在苦难的深度体验中,生命韧性得到了张扬,传统道德得到了彰显。《唇典》中,现代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而来,人们与传统告别势在必行,但刘庆展示的传统价值与虔诚信仰无疑是对现实人生最真诚的慰藉。
(一)生命韧性的张扬
苦难的体验伴随着恐惧与不安,受难需要极强的勇气,因此坚韧地活着便是一种尊严。《唇典》中的东北人民在苦难中依旧选择活着展现了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坚韧力量,这对于当代社会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嘲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对苦难避之不及,享乐成为极致追求,生命的价值亦被忽视,而刘庆再一次勇敢书写苦难,张扬了生命的韧性。反观“80后”青春文学作家,如春树、韩寒等,尽管惹眼吸睛,但他们不能勇敢面对苦难亦恐惧书写苦难,热衷对青春享乐的无限怀念与赞颂,其文本即使稍稍触及到苦难也立即以滥交、绝望、自杀等加以遮蔽与掩盖。然而,生命的价值在苦难中才能够得以最大展示,因此有一批类似刘庆的作家,执着于苦难的书写,努力彰显生命的力量。
《唇典》中,坚韧不屈是柳枝高贵的精神品质,活着成为她对待苦难最好的方式,郎乌春亦是如此。柳枝与郎乌春将要死去时,刘庆并没有在文章中渲染浓烈的悲伤氛围,而是着重表现生命的韧性与力量。当郎乌春写信给柳枝告诉她自己明天就能抓住王良时,郎乌春死亡的讯息比信早一步到达,柳枝亦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她并不惊慌失措,她依旧坚韧,不向死亡屈服。文中道:“柳枝不用人搀扶自己从炕上坐起来,她让素珍给她端来一盆水,她洗脸洗得多仔细呀,连耳朵眼都洗了五遍,比当年结婚时洗得还要干净。她从来没像今天这么轻松过,病好像好了。”[3]424在柳枝与郎乌春两人逝世后,文章丝毫没有展露悲伤,而是充满温情与希望地写道:“太阳高挂天空,河谷撒下白色的炫目光芒。空气中散发着早春的寒凉,河堤上融化的雪水和舒展枝条的树木都在宣告,冬天的严寒已经过去。”[3]427“开江了,河谷孕育着新的生机,新的苦难,新的希望,新的社会。”[3]427柳枝与郎乌春的苦难得到了超越,生命的力量足以打败对死亡的恐惧。余华的《活着》亦是通过刻画福贵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形象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在一个接一个苦难的背后实际融入的是余华对人性、对生命的思索,刘庆继承了这样的写作传统。
(二)传统价值的彰显
刘庆书写了东北人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与挣扎的现状,东北人民在接受了苦难的洗礼后最终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坚守传统价值,坚守善良温情的本质,坚守内心真诚的信仰。在现代文明无情地冲击下,刘庆注目于书写乡土苦难,他在《唇典》中充沛地传达了其对传统的无限留恋,作品背后更是展现出其所渴望的善良温和、虔诚信仰等传统价值。
《唇典》中,苦难虽无法改变,但刘庆一直试图以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去驱赶苦难带来的阴霾。郎乌春迫于无奈,为了救五个弟兄的生命而不得不投降时,他内心的痛苦达到了极致,但他曾经爱过恨过的女人柳枝最终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当郎乌春后悔自己没有战死,没有被鬼子打死,苟且活下来时,柳枝回应道:“别这样说,那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要是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3]387两个曾经彼此记恨的人,在一瞬间达成了和解,善良与温情成为苦难中的一抹亮色。“他们第一次心甘情愿地躺在一起,他们一边听江水的咆哮,一边想象着未来。这时候,他们发现过去并不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彼此的怨恨不知何时已经消失。”[3]387郎乌春与柳枝两人给彼此造成的痛苦太多且沉重,但乡土世界所坚守的传统道义与良善使得两人最终成为彼此坚实的依靠。苦难彰显了乡民内心坚守的传统价值。
刘庆在《唇典》中还强调了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借助萨满文化得以充分地展现。东北人民虔诚地信仰萨满文化,“没有人不相信李良萨满,虽然他的讲述不可思议。但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李良萨满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一个大火烧过的萨满。”[3]43虽然萨满文化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刘庆讲述萨满文化的背后其实是试图重建一种精神信仰,这种信仰代表了传统价值观中对万物存有的敬畏与善意,以及对生命、自然的尊重。面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精神信仰危机不断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了,人与家族精神的关系割裂了,人和自然不再和谐,失去精神故乡的人们将彻底流离失所。”[3]465在没有精神信仰的现实面前,刘庆书写苦难,彰显信仰价值具有悲剧性意义,也展现了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思考。东北人民心存信仰,对万物生灵怀有一颗尊重的心,在苦难的体验中,强大的精神信仰成为东北人民最终的精神归宿。在失去萨满的年代中里,满斗最终成为最后一名萨满。他种植灵魂树,从萨满李良开始,再到亲人、长辈、朋友,甚至是儿时曾伤害自己的狼,满斗尊重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并渴望与他们的灵魂相约。满斗说:“每棵树都有灵魂附体,虽然他们不会走,不会飞,但他们个个有魂,能听懂你的话,看懂你的事。”[3]460树承担了寄托灵魂的功能,树自身也作为生命而被尊重着。在这种强大的精神信仰下,每一个生命都归于安息,每一个灵魂都得到抚慰。
四、结 语
《唇典》以宏大的场景与广阔的历史维度完成了对苦难的书写,在神灵(萨满)的慰藉下最终实现了对苦难的救赎。在缺乏信仰的年代,刘庆传承书写苦难的写作传统,执着描写苦难的精神具有非凡的意义。《唇典》不仅对刘庆个人是一场文学创作上的突破,对当代文学苦难主题写作的丰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唇典》中有关萨满的描写是其文本中的一抹亮色,展现了刘庆对苦难别致的思考与理解方式,萨满背后所蕴含的信仰价值对当今社会亦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