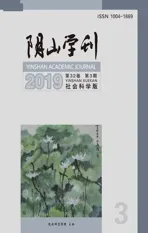“神实主义”视野下的乡土文学
——以阎连科短篇小说为考察
2019-03-02邓淦元
邓 淦 元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1)
阎连科,一位有着土地原生色彩的作家,其创作一开始就与其日常生活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前期著名的“四个系列”(包括“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军营系列”“耙耧系列”),无论他怎么处理都与其“衣胞地”血脉相连,仰仗土地成了他创作的精神纽带。此时的阎连科是紧随着现实主义思潮的步伐,即便相对于同时期的寻根、新写实、先锋等流派作家而言,显得慢半拍,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一直都在摸索着如何建构土地书写。但如学术界所言,从《坚硬如水》开始,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直至2003年长篇小说《受活》的出版,无疑成了他写作上的分水岭。《受活》之所以成为转折点,与那篇“代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有关[1],这可谓是他第一次公开对现实主义进行猛烈批判。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阎连科要批判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仔细去想,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内心的深疼,不能不体察到,那些在现实主义大旗下蜂拥而至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纸张:虚伪、张狂、浅浮、庸俗、概念而且教条。时至今日,文学已经被庸俗的现实主义所窒息;被现实主义掐住了成长的喉咙。”[2]在中国已有百年演变的现实主义晃眼间成了文学的“墓地”,已然无法支撑他的创作路径。在其文学实践和文学探讨中,阎连科逐步找到了自我信奉的创作理念——源于“真实的内心”而非“真实的生活”的现实主义,即“神实主义”。
如此一次“倒戈”,绝非偶然或是一时之冲动,毕竟他一直都把现实、真实地反映养育自己的黄土地视为创作使命。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其创作必然是其文论思想演变的最直接反映者,或是酝酿或是呈现,文本与文论之间有着无法隔断的联系。据可考证的资料统计,截至目前,阎连科创作长篇小说20篇(公开发表19篇,未发表作品为《山乡血火》),中篇小说55篇,短篇小说53篇。于创作反响而言,其长篇小说可谓是每出一部必是回响袅袅,中篇小说也是频出好评或是议题满满,相较之,短篇小说却常常被人忽视,这正是“在一个作家身上产生的文体不平衡现象”[3]。但在作者本人看来短篇有着其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短篇最高的境界不一定就是韵味、精巧那一类,可能是‘随性’——是随作家之心,吻作家之性”[4]。换而言之,其短篇创作所呈现出的历时性是作者的选择。此外,若对其创作进行宏观解剖,不难发现其长、中、短篇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从主题题材划分,都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军营生活,一类是乡土生活,从创作转型看,也符合前后连贯性。那么以其短篇小说为研究样本,便足以考察阎连科“神实主义”下的乡土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趣味。
一、以“神实”观照现实
早在2010年,阎连科在访谈中论述到:“文学是经过九十年代的各种借鉴、融合之后到了二十一世纪,‘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路’来。”[5]502011年其文学随笔《发现小说》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神实主义”,并对之进行了理论性的阐释。针对前人走过的两条乡土文学道路,阎连科进行了简要的划分,一是始于陶渊明,后继于李渔、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赞歌式书写,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启蒙式书写。毫无疑问,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一开始进行创作的时候,这两种乡土文学书写经验对自己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时代在变,作家的个人思考、个人创作也在不断的深化,这两条道路已然无法满足当下乡土书写的需求,必须以一种崭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去诠释中国这片土地,及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整个民族,可以说“神实主义”是阎连科以自身文学实践、生活考察探索出来的乡土文学“第三条道路”的创作理论与方法,也是延续乡土文学命脉的新路径。
对于“神实主义”,阎连科曾作了系统的论述:“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和渠道。”[6]181-182要理解“神实主义”中的“神”,就要追溯其对现实主义中“实”的长期思考——他认为现实主义包括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和灵魂现实主义三大类,其中世相现实主义是力求描绘社会和个人的命运,如《边城》《围城》和张爱玲的作品,生命现实主义则是要超越人物生命长度而延绵至今,成为给予人们警示的镜子,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典例,最后灵魂现实主义是小说能对灵魂进行深刻的发问与挖掘,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最高层次,代表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般定型的现实主义无疑会限制作家的创作,使之无法进入更为深层的真实而徒留于真实之面,可另一方面,若现代主义过于抽象则又会拉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因此,“神实主义”便应运而生,阎连科企图借助神话、寓言、传说等现代主义元素打破真实之面,走进现实主义更为深层的精神内核——被真实遮掩的真实。
这种叙事的倾向,追其源流,早在“耙楼天歌”系列便开始出现。1995年发表在《北方文学》杂志上的《生死老小》本只是一个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娃不慎从树上掉下来,血肉模糊一团,同村的老人带孩子去医院抢救却碍于治疗费而无法马上救治,老人决心要向同村人挨家挨户地求助,但可悲的是生育在同一片土地的人们都残忍地拒绝援助,老人为了救孩子不惜乞讨、卖菜、跪求医生,最终自己为孩子输血至死……但里面增添了一个携带着凶兆预言的角色“乌鸦”,其并非一开始就登场,而是在老人被村里人拒绝的那一刻孤立无援而又对土地生命质疑的瞬间,这便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而忧愁的雾霾。这部短篇一改作者往常对农民抗争自然等无畏精神的歌颂,而走向了对乡土文明、人性的怀疑与警觉。这样一种打破现实的真实追逐,一直延续并愈发彰显。其后出现的《小村与乌鸦》《三棒槌》《黑猪毛,白猪毛》等作品,无不于荒诞的神秘中渗透着对现实的进一步追问,去寻找那被遮蔽和遗忘的本质所在。或正如孙郁所说:“阎连科看重的恰是来自现实,又远离现实的神秘精神体验。当现实词语无力或者思想表述受挫的时候,隐语、神话、宗教寓言便成了现实的另类摹仿。”[7]这样的叙事,恰是阎连科对这片土地爱的信仰与痛的怀疑的书写探索。
二、“神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乡土来源
事实上,当代每一位乡土文学作家都无法避免地会受到五四以来中国乡土书写两条路子的影响。鲁迅所开辟的“为人生”的乡土写作路子,受到了后辈的积极追捧,先有“乡土写实派”的兴起,后有当代的韩少功、刘震云、李洱等作家的脉络延续——用现代的眼光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借助理性批判主义去抨击存活于土壤中乃至渗透根部的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从而实现对愚昧国民性的揭露与人性的唤醒。另一方面,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则是走向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乡村是美好的象征,村民更是淳朴、纯粹人性的保留者,田园牧歌是其诗情画意最好的点缀。这一讴歌式的乡村书写,并未止于现代而延续至当下,像张炜的《柏慧》、贾平凹的《土门》、迟子建的“北极村”系列等。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两条路子都有着其自身弊端,前者是把乡村的本与宗都放置在否定、批判的位置,在其产生初期确实随了社会思想解放的大潮,给予人们警醒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的进步与解放,这种一成不变的批判方向是否还适用呢?而后者则是给乡土建造起了桃花源式的美好,令人向往,可于社会而言又似乎遥不可及。换而言之,两条路子所建立起来的,或是愚昧落后的农村或是美好诗意的湘西,其实都只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抒写,是以知识分子的精英视角去为农民代言。农民即便是乡土世界的主角,但却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和表达,话语权的沉默最后也换来了农民主体地位的沉没,而真正的乡土往往沦为被遮蔽的境地。
诚然,早期的阎连科也是如此,且更倾向于鲁迅式的批判农民劣根性、揭露乡土复杂权力结构的叙事模式,例如《爷呀》(1989年)、《限》(1996年)、《小镇蝴蝶铁翅膀》(1999年)等。可阎连科有别于前辈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是实打实的初中毕业,在他看来,土地与其说是一种书写对象,还不如说是一种生之交换,“那片土地养育了我,它把我培育成一个作家,它要求的回报就是要我去表达它、叙述它”[5]20。所以,他的笔墨之中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批评之余又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且时刻饱含着对启蒙话语若隐若现的警觉。这便也注定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实践创作的不断深化,两条传统的书写道路无法满足阎连科对乡土“真实”的挖掘与反映。他试图突破前人的框架束缚,寻找“第三种写作”,以此走进一个具有更为广阔意境的乡土世界,去探寻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可再细细溯源,便不难发现,“神实主义”从萌芽到酝酿再到发酵成型,有着其不可分割的生命体验源泉——自小就在乡村成长起来的阎连科,中国传统民风民俗便是他耳濡目染的环境,那块土地给予他的不只是生命,还有的是非启蒙性质的沉重与压抑。以火葬和土葬为例,因为传统和文化,村里人们只会选择土葬,当亲人死了,全家人就忍着痛苦,偷偷把死者埋在遥远的山上,到了痛苦实在忍不住了,晚上一家人就跑到无人能听见的山上痛哭一场,然后又佯装无事地、默默地回到家里……这里面不只是土葬和火葬之间固有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暗含着文明对人性的巨大压迫,由此也衍生了无数怪诞陆离的事情,这也就是阎连科以乡土生活和民族文化为起点,企图透视整体社会、整个人性的复杂、诡异和意义。从这一层面上看,前面论述的两条道路都无法达到这般的社会、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寻求突破,是阎连科唯一的选择。
此外,西方现代派文学是阎连科实践神实主义的重要思路与方法之一。其中尤以拉美文学影响最为深刻,如他所言“特别喜欢拉美小说,是拉美小说推倒了我与乡村生活的某种隔墙。”[8]无疑,阎连科在后期的乡土书写中极力借助“魔力”,来推倒隔墙——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鼻祖加西亚·马尔克斯,神交之中,阎连科无疑与马尔克斯有着惺惺相惜之感,大概便是因为两人都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一位‘土’作家”。马尔克斯把现实与魔幻手法结合起来,带来的不只是耳目一新的震撼,还有的是魔幻异化背后所暴露的拉美民族艰辛沉重的历史进程及现实真相,于无声中也给予了阎连科新的乡土创作思考——他依然保持着对乡土社会高度的关注,但在如何刻画真实乡土上做出了调整,除了乡间传说习俗所带来的荒诞与意料之外,还让土地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戛然而止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局中无情地被暴露出来,于是,“一个更为宏观的乡土中国以及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特性也随之被挖掘、被呈现”[9]。此时,其乡土书写仍以最熟悉的家乡为背景,人物塑造、方言应用都具有明显的中原特色,但地域所指已呈现泛化的特征,是乡土中国的象征,以透露着作者对乡土中国生存意象的思考与追问。像《小安的新闻》(2008年)中改革开放让小安的村里人都看上电视,甚至以家里拥有一台电视为荣,小安从一开始买电视所表现出来的“为村里人吐一口”的意志,到逐户去比较各家如特色农作物般的电视,再到想要上电视,其中的乡村心态很值得玩味。可小安对上电视的执着程度近乎痴迷,是要“把做一次新闻里的任务当做事业了,就如农民种地把丰收做了人生目标样”[10]11。为了上电视爬上树梢飞翔着观看村里形势,最后徒留着自己的牌位和遗像,新闻太大了,也没法播……小说里有着人之常情却也又饱含着人性欲望追求的荒诞性,这样的“魔力”介入非但没有拉开作品与乡土现实的距离,反而让他后期的乡土创作有了超越现实束缚的张力,进一步还原真实乡土,并深入到民族生存本质的探寻中。
三、“神实主义”的乡土文本实践
21世纪以来,阎连科对“神实主义”的思考与实践愈发深刻,民间无疑是其创作的源泉,神话、宗教、寓言大量地融入叙事之中,西方流派则又为他的写作带来了鲜活的动力,情节上趋于夸张、荒诞,透过这些看似荒谬的外表实现了对乡土书写的解构与重构,慢慢展露了本质的真实。这便是乡土写作第三条路产生的原因,也即是阎连科与前人书写的最大区别——作品已不拘泥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大量渗透着现代主义对“存在”的追问与探求,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思考与人所处境地的不断拷问。正如学者谢有顺所说:“现在的乡土文学不再只是关于制度、文化或现象的探讨,而有了更为内在的精神主题,从文化关怀到存在关怀,从写文化的乡愁到写存在的乡愁,这个‘存在’的主题是现代主义的,也是先锋的。”[11]在学习、消化、过滤西方现代流派的基础上,他结合自身特有的乡土经验,曲化、荒诞式的技法,刻画着乡土的人与事,藉此回到民族文明、国人生存问题的根部,去关切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以追寻现实的“真实”。
早在1998年《农民军人》这部短篇作品,阎连科就开启了文本内涵的革新,准确地说,是对以前乡土叙事的一次诀别——先锋小说式的意义模糊与暖昧不清笼罩期间,西方现代存在式思考与乡土特色的书写方式开始交汇。故事发生在熟悉的耙耧山脉上,前马家峪和后马家峪是对立的邻村。主人公马林,是前马家峪的光荣,做过团长领着一个团在南线战争中打出过国界,如今回村里当农民。岁月往前走着,耙耧人也染上了城里人无事不相往来的习惯,人与人之间冷漠而不相干。一次探访马林,烧砖瓦的土包引起了前马家峪村民对后马家峪的不满,两村之战一触即发。前马家峪把战胜的希望都落在马林身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刨坟成了他们逼马林“出山”的最后手段。可就在这迫在眉睫的瞬间,马林献出自己一根胳膊去跟后马家峪谈判,最后用血把土包一分为二,平息了这样一场斗争。设计微妙的是,马林虽是主角,但文中所涉笔墨并不多,即便是最后的保卫之举,都是通过一个孩娃之口讲述,事实上,马林的高大英雄形象或说是传说,都是通过村民塑造的,一方面是村民间的讨论,另一方面是村民所作所为的对比烘托。这样的叙述实则暗示了该小说真正的主角是那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村民。当土包如“血腥气红豆浆样浓”[10]210的瞬间,既标志着乡土战争的和解,也是给予两个村村民当头一棒——冷漠、猜疑、争夺,是村的气息,阎连科则企图用军人的义气当头、勤劳勇敢去浇灭这一戾气,但结果也是显然的,一分为二的土包仍是二,两个村恢复平静,却不代表着因有千百年前血脉联系而再次联结在一起。这场无硝烟的战争已然折射出阎连科对乡土深层次里的人性思考与批判。
这样的“真实”探寻与实践从未停止。2002年阎连科发表了短篇《三棒槌》,这是一桩刑事案,源于本能的冲动,石根子似乎煽动起并不清醒的自觉,怒发冲冠,对长年霸占自己妻子、欺辱自己到牙齿的李蟒,决绝地做了“一次性”的“了断”,为此石根子愿意付出生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在长期被羞辱状态下的男人成长史,火山式的爆发只是他挽回男人尊严的举动。但若顺着“第三条路”思考,将文本放置在当下中国农村现实之中,则又会呈现出更多复杂的、新旧杂陈的关系与结构。当暴发户何李蟒在抢占了别人家的媳妇时,还敢当众辱骂:“你要敢在我面前吐口唾沫,我给你一千块钱;你要敢在我面前举起棒糙,我给你一万块钱;你要敢在我头上砸一下,我给你盖一栋楼房。”[10]129里面所要显示的远远不止于文字间的人物,而是由此引起人们对新的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中国乡村民间结构的复活与异化的关注。那又是为何法官、乡人、石根子的媳妇都对他抱有期待,怀揣着“敬意和男人们的自豪”[10]132有组织地为他收尸呢?这便是阎连科最想要表达的,通过一层层地剥开迷雾,就是为了还原社会冲突、失衡的状态,又以石根子死后祭奠他的白花茫茫一片为结尾,言已尽而意无穷——冲突、失衡仍未得到缓和……同年发表的《黑猪毛,白猪毛》可谓是其续篇,不在于角色的延续而在于乡土理念、乡土探索的延续,是对乡村显型社会结构的诠释。它的核心语义在于,“在现代社会形态渗透于乡土生活的时候,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乡土宗法势力却仍有市场。”[12]镇长撞死人了,竟是一件献媚的大好事,村民都争先恐后为镇长顶罪,特别是对于穷途末路者而言,“这好的机会,别人烧香都求不到”[10]83。这便在悄无声息中透露出了乡村政治的异化,官本位和权力意识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思维之中,成了其自然的行为准则,但人们并非纯粹地膜拜权力,而是在做交易,企图借此从中获益。小说结尾可谓戏剧化,“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做镇长的干儿子就完啦——”[10]91可这实际上又是刘根宝们顶罪后另一走向的结局。两个结局是相互冲突,又遥相呼应,进一步展现了阶级分歧、权力异化、人性扭曲的乡村基层现实与现代理性之间碰撞摩擦而产生的悲剧色彩。
这也是阎连科面对愈发边缘化、碎片化的乡土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的创作手法。[9]书写模式的进化速度远远不及时代更迭,当下的乡土也就跟鲁迅、沈从文时期的乡土大相径庭,若仍延续旧路,又该如何才能触碰到乡村随时代而衍生出来的窘境与矛盾呢?因此,包括阎连科在内的不少乡土作家都做出了挣脱与调整,只是阎连科把具体的文论方法进行了提炼与界定,形成了“神实主义”。“当代的作家有这种冲动的很多,他们感到现实主义的方式无法满足精神伸展的渴求,于是借助于民间文学与神学,在寓言、歌谣里寻找突围之路。这个思路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于一些作家那里。他们以为是一种技巧,很少以理论的方式言之。对于作家来说,真幻之间、虚实之间、明暗之间,是没有界限的。”[7]学者孙郁指出了神实主义的乡土实践在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中都能找到相关的痕迹。例如莫言《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原型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母亲“女娲”,《红高粱家族》以大量的民间传说贯穿全书,《生死疲劳》更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年为一甲子来展现生命的轮回……可以说,莫言也是以民间传说、民俗风尚为窥孔,在一步步地推到固有的现实主义模式下的乡土而走向更为真实的乡土世界。不止莫言,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神实主义”的实践痕迹。作品《老生》在结构、叙事视角和内容上都深受《山海经》的影响。书中的“唱师”本就是一个非常理的存在,于阴阳之间游走,借唱师之口,以诡秘莫测的唱词说尽历史长河中的血腥、惨烈与无情。还有张炜的《九月寓言》、周大新的《伏牛》等,都不是纯粹的启蒙式批评或是诗意描绘,而是以荒诞、神话、传奇、寓言的方式去叙述乡土。
“第三条道路”以看似曲笔的书写为略显停滞、落后的乡土描写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乡土呈现的真实性也为这一创作方式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四、小 结
第三条道路,并非是一种脱离中华民族之“根”的探索,相反是以阎连科为首的中国当代作家对乡土书写进行解构与重建,审视时代变迁下乡土中国的复杂性与可变性,由此引发出对民族生产方式与人类精神发展问题的揭示与追问。王富仁称之为“第三种写作”:“他们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给人以新的感受,提供一种新的范例,即离开西方范本,回归自己,又离开自我的子宫,来展开一个荒凉的世界,感受到外界的寒冷,也感受到自己生存的危机,由此产生了第三种文化和话语。”[13]诚然,不管是王富仁所言的“第三种写作”,还是阎连科的“第三条道路”,都是这批乡土作家借助本土经验与西方现代技法的交融,实现对乡土中国的“真实性”、叩问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轨道的进一步披露与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