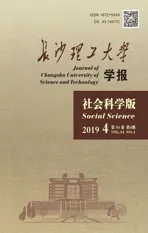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国家”层面的STS
2019-02-15吕乃基
吕乃基
(东南大学 STS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1189 )
任何主体,如个人、社会组织、学科的学派等等,都有自己的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以及处于相应的语境之中。语境对主体及其活动方式产生或潜移默化或直截了当的影响。如果说在以往的岁月,主体主要感受到的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小环境的影响,那么在当今世界,主体无不较之以往越来越感受到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影响。无论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最终都是经由“国家”的折射而影响到具体的主体。于是,作为语境,“国家”位于人类与小环境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对各类主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科技哲学的STS,有必要用以往作为语境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一、语境的历史、逻辑与相对性
语境[1],是当今学界广泛使用的词汇,大意为一句话的上下文、前因后果以及时空背景,时间上在什么时代,空间上在什么场合等。通常,语境这一概念用于言者(说或写)与闻者(听或读)之间的沟通,闻者尽可能由与言者共同的语境来理解言者之言的含义,再按自己的背景转译其含义。在强调实践优位的今日,语境不仅是“语言”之“境”,也是“行为”之“境”。
(一)语境:历史与层次
任何人的言行举止都受到特定语境的影响。个人言行所处的微观语境千变万化,本文仅在宏观层面加以讨论。
在传统社会,影响个人言行的语境,包括家庭、村落、庄园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在现代社会,个人所处的语境是家庭、由契约安排的工作关系、与陌生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及与自然界和机器之类“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等的关系。当今社会,个人所处的语境还要顾及人类和地球。
语境衬托个人之言行,提供理解个人言行的框架,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之言行。反过来,个人或以对语境的坚守构成对他人之语境,束缚他人之言行;或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语境的束缚,形成新的语境。科技,特别是媒体技术,对语境的影响至关重要,互联网极大的改变和扩展了语境。“媒介即信息”[2]。
一般来说,个人言行处于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三个相对稳定的层次及其叠加的语境之中,以及处于各种临时多变的语境之中。在全球化、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面前,在上述语境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人类命运作为新的语境。
作为个体的主体,自衣食住行、言语举止,直至灵魂深处等,无时无处不是处于“国家”语境的深刻影响之中。而无论个体是强烈地感受到了,还是没有感受到,“国家”语境的客观存在都是一种实在。全球化中国家之间的纷争进一步凸现了“国家语境”在“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国家-人类”语境中的权重。
(二)主体及其语境——语境的相对性
主体——言者与闻者(后文主要涉及言者)——及其所处的语境之间构成了一组互相限定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哪座山唱哪首歌”,形象地说明了语境与主体的关系。
其一,无论是哪个主体,说与不说,说什么,语境总在。语境在空间上是总体性的存在,在时间上是持续性的存在,在主客体关系上是(准)客观性的存在。
其二,语境在总体上和潜移默化中规范、约束、引导言者之言,这是语境“客观”的一面;但这种“客观”只是在“准”的意义上,因为主体以其主动的言和行,坚守或突破语境的束缚,建构新的语境。
在大多数情况下,语境与主体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张力。不过,在主体顾及“底线”和具有相应道德修养的情况下,言者一般并不觉察到语境的存在。语境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境”,几近于“时间”概念;“感觉不到”,这是言者及其语境关系的最高境界:彼此相吻合。由此可以提出一个衡量言者及其语境关系的指标:吻合度。笔者将另文述及。
二、科技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科技哲学界的不同语境
科技界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这一研究当然不可能脱离“国家语境”,但大多不会去以“国家”本身及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国家”只是作为科技界研究和创新的语境而存在着。科技界的不同个人、团队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与“国家语境”之“吻合度”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一般地并不妨碍研究结果的相对客观性。这主要是由于科技界研究对象——自然界的客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同行评议,因而科技人员必须在研究中排除主观性和情感的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国家语境”不仅是语境,而且往往成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研究者是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能动的参与者。同时,该领域中的有些研究者,既可能因其处于“权威”地位,也可能因其参与有关制度的制定,因而可能通过影响语境而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局面。由于语境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研究者。所谓“有意”,意为语境的背后,存在着“表达”或“体现”自己诉求的活生生的人群和利益集团;而“无意”,意为语境一旦作为研究对象,就要求研究者撇清与对象的关系。这种情形,可能造成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领域的内部分化,乃至对立。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不仅是认识,而且是实践。研究者总是试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他人和社会,以学者之“言”固守或改变某种具体的语境。
科学技术哲学界对语境的感受,大致处于科技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之间。科技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科学技术。在整体层面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涉及认识过程和价值判断,涉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必然较之科技界更多关注社会。比如,在比较研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不同国家的国情,于是作为语境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能同时成为研究对象。不过,较之人文社会科学直接以“国家语境”为研究对象,科学技术哲学只是涉及而已。在现实中,科技哲学界的研究者们,往往不将“国家语境”作为研究对象,或只是因研究需要,间或涉及,或者干脆越过国家层面直接跳到最高层次,站在人类命运的顶峰讨论科技哲学。如此久而久之,作为“总语境”的“国家”,便在科技哲学研究的“对象域”中悄然隐去。
但是,这种在科技哲学研究中对“国家”的选择性的无视,往往可能妨碍着对科学技术整体之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一端,科技哲学所涉及的科技政策之研究,如果缺失“国家”维度,不仅解决不了一个个具体问题,而且具体问题间还会彼此纠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家语境”的关注,是解决科技哲学中的一些相对低层次问题,如科技政策问题等的根本之途。在另一端,科技哲学在“人类命运”与“终极关怀”等层面研究作为整体的科学技术,如果无视国家维度,那么这种研究可能只是失去“地基”的“空中楼阁”,因为“人类命运”在现实中离不开国家,“终极关怀”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语境”,实际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技界的所有研究,包括影响着研究选题、研究途径和研究结论,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在这种情形下,以科学技术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如果无视“国家”维度,深入推进对整体的科学技术之研究的可能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国家”层面的STS,是科技哲学界义不容辞的研究领域。
三、国家层面STS研究的多重考量
(一)基于空间的考量:横向与纵向
横向,在同一层面考察全球化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一,重建全球产业链,还是规则[3]优先?2008年,全球产业链随金融危机而发生断裂,是重构全球产业链,还是“逆全球化”。世界各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其二,我国具有“完整产业链”似乎已是“共识”。然而,在“高质量发展”层面,我国的产业链是否还有“短板”?
其三,大国博弈中,如何考量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进而言之,全球化之进退,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哪些领域可以,哪些不可以?这就涉及到“纵向”的STS。
纵向,“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构成类似量子阶梯的层次关系,以及对应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在全球化中,国家之间在四个层次之一、多个,或全方位相互联系,互通有无。国家之间横向的沟通,最终落实在纵向的一个或多个层次。
可以借鉴科技哲学关于量子阶梯的相对成熟的理论。
其一,上向与下向因果关系,强调层次间的相互作用。借鉴到纵向的STS,亦即强调“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彼此间之间的必然联系,低层次是高层次的基础,高层次制约和引领低层次。
其二,在阶梯中由下而上发生的变化。低层次刚性与偏重共性,高层次柔性与侧重个性。在“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的系列中,技术刚性,从芯片、根服务器,到5 G,各国各行各业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经济次之,GDP、温饱必不可少,满足衣食住行;不过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颇多差异。政治与社会治理,虽有共同之处,但更强调特色。价值观则进一步多样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摆脱上向因果关系,摆脱低层次的制约。阶梯中由下而上的规律性变化,为全球化中的“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切割和相对独立的运行提供依据。
“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系列,涉及“功能”上的层次,功能落实到什么样的主体,个人、企业、社会组织,还是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主体是国家还是企业?还是国家与企业形成“双主体”?一方面,如果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的博弈,“国家”间将如何相处,世界将会怎样?另一方面,企业是否也需要具备外交能力[4]?等等。
对于科技哲学界来说,最擅长同时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是位于“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底层,以及处于全球化背景中的技术。“自力更生”与“全球产业链”的边界在哪里[5]? 如果“物竞天择”,那么,主宰生物界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于多大程度上依然有效?人类社会又在哪些方面超越生物界?在“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的阶梯中,“物竞”,是技术、GDP、政治体制、价值观,还是这些方面的某种组合?而“天择”中的“天”,又应如何理解?
(二)基于时间的考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宏观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无论是否愿意,在全球化中“走到一起来了”。20世纪末,在原有国际贸易的基础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产业链瓦解,使各国开始反思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得失,评估全球化态势,甚至出现在国家层面的逆全球化。逆全球化不可取。坚守全球化并改善某些规则,提升标准,方是正途。但坚守全球化所需要改善的“规则”,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三)基于虚实考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个虚拟世界正在出现,并且在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一步,向虚拟世界“移民”。向虚拟世界传输、存贮信息和知识,以及可以随时提取,以摆脱现实社会中时间和空间的羁绊,摆脱特定主体的牵连,摆脱上下文、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就是语境的束缚,屏蔽掉现实世界的随机涨落,让知识和规律说话。虚拟世界的运行建立于严格的规则——编程的基础上。由编程向虚拟世界“移”的就是“规则”。
从现实到虚拟,从中心、干预、嵌入、意会,到去中心化、非嵌入和编码;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重构。虚拟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的映射、投射,而是选择性重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从第一步由实到虚,到第二步以虚驭实。
就“虚实”而言,作为“国家”层面的STS,旨在探索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背景下的国际关系。所谓“革命”的核心是虚拟世界的“球籍”。随着越来越多的现实世界移到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权重越来越大。如果个人和社会组织不想或不善于迁移到互联网所构造的操作系统中,将在虚拟世界自我边缘化而无法在现实世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影响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社会关系不断由现实世界迁移到虚拟世界,乃至以后者为重,人在现实世界的地位就可能会受到动摇。没法移到虚拟世界的现实世界,有可能在虚拟世界被开除“球籍”,回过头来没法在现实世界与他人交往。
既然是一场“革命”,自然会有阻力。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需要以及乐意移到虚拟世界。
一项最新的进展是量子计算机。迄今为止,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是“if……,else……”,非此即彼;是否可以期待有新的计算机语言,譬如“全球脑”,将遵循模糊(fuzzy)逻辑。概念是这样,行为是那样;有时这样,有时那样;从而为诸如“一方面,另一方面”等亦此亦彼的事项的“编程”提供可能。
现实世界已争斗不断。人们同时担忧,虚拟世界是否也有“国籍”之争,甚或发生“互联网大脑”的分裂,赵汀阳表达了对这一前景的担忧[6]。为此,有人提出,需要有“互联网宪章”。
以上只是给出国家层面STS在时空和虚实维度的初步提纲,每一个维度都需要展开和深究,在这些维度之外也还有其他视角。
四、国家层面STS的方法论初探:科技哲学关注“国家语境”的优势
由科技哲学的视角探讨作为语境的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以下优势。
其一,整体性与超越性。科技哲学以科学技术之整体为研究对象。尽管科技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等,尽管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也可分别作进一步区分,比如自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相对区分“物理哲学”“生物哲学”“信息哲学”等,但这些区分,不同于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技术中的学科门类,依然持着整体性视野。以整体性视野,关注“国家”层面的STS,利于研究的全局观和战略视野。研究视野的整体性,必然带来研究主体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往往突出表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较少有过多的“纠缠”,使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更为显著。
其二,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长期发展与积淀,形成了“现成”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的分析框架。比如,由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理解社会,科技哲学不仅有马克思的“两条道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等分析“手段”,而且还有复杂性科学之“利器”。这些视角和框架起到了科学方法论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不仅是方法,其本身是一门学科,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观。
其三,共识性的科技史基础。科学技术哲学的许多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科技史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属于史学,但与科技史相比,二者具有的区别主要有:一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曲折繁复,科技史虽也有反复和分岔,但毕竟线索相对清晰,可以成为研究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稳定参照系。二是历史学的解释往往多变。比如,一些“历史事实”往往难辨真伪,甚至成为任人随意打扮的“婢女”,不同研究者的立场也往往各异。“历史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汇入了各个时代的“当代史”。科技史固然也有类似问题,但科技史的史实明了,背后还有自然界做证,容不得科技史学家的多变解释。事实上,具有共识性的科技史,作为“国家”层面的STS之研究前提,可以为这一研究之新观点的提出,奠定坚实和共同的基础。
其四,科技哲学历来具有STS研究传统。目前,科技哲学界需要做的当是,将STS个别具体的研究对象扩展、提升到国家层面,以及由宏大的人类命运和终极关怀层面的研究,下沉到“国家”层面。
固然,科技哲学研究国家层面的STS具有各种优势,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新的领域。一方面,科技哲学原有的概念体系在进入新的领域之时,有待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扩展和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
五、结语
科技哲学可以区分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STS等分支,各自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更小的分支,同时发生分支之间的融合。例如物理学哲学,既可以认为是自然哲学的分支,同时又含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STS。由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到STS,对于社会的涉及逐步加深而接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主观色彩增强,观点也愈益多样化,甚至彼此对立。
对于国家层面的STS,科技哲学的各分支可以有分有合。相应于“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阶梯,科技哲学的各分支,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关注全球化中国家之间在技术层面的竞争与合作,由技术哲学中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进入经济和政治层面,以及涉及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背景上的国际关系。科学哲学或可致力于对各种标准和规则的研究,STS则统揽全局。
科技哲学自有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内涵,不过,在全球化风云际会之时,关注国家层面的STS,科技哲学界的参与,既义不容辞,也当仁不让,并将反过来拓展和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