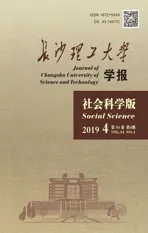从观念、实体到关系的近代中国科学价值转移
2019-02-15杨文定
杨文定
(中共崇左市委党校,广西 崇左 532200)
一、问题的提出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支持的远洋航行打开了世界近代化的潘多拉魔盒。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近代化进程,凭借科学技术的力量从地理大发现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推动科学步入人类信仰和实践的神坛。工业革命完成后,西方科学以非常途径布道四海八方,吸纳信徒,扩张势力范围,中国亦成其重要发展对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享用欧洲圣殿传来的科学餐宴,以沉重代价获得科学价值的深度体验和别样认知。然而,其在中国的进路却又并非线性演进。科学价值的探讨,关涉科学知识的普适性与地方性,其在中国的研究,乃至科学哲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皆需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1]。中国的实际是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基础、动力和最终归宿[2]。关于近代中国科学的探讨,以深究落后的原因见长,其或深受李约瑟问题影响,或是出于对中国近代史有爱之深恨之切的缘由。以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为标界,探讨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以及近代中国科学的价值观演进[3],确有宏大叙事鉴古思今之效。但就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对更多尚未深入的历史细节,连同逻辑推演和哲学反观,皆有可细琢之处。本文选取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这个时段,即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孕育阶段,以期透过期间的事件及其在社会背景中的表达事象,就科学的价值转移(侧重其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作一脉络性的粗浅诠释。
二、科学的价值在近代中国转移的历程与路径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科学价值在中国的转移经历了从观念的认知、实体的践行到科学隐喻多重价值与关系的反思。基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的认知与诠释,近代中国呈现的科学价值转移图景:在激荡的社会洪流中历经器物、制度、观念的变革路径,彰显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深度体验,其隐含的是科学观念、实体到关系的非线性演进与融合。
(一)科学价值的表征
科学价值的表征基于对自然世界和客观现象的科学探索和认知[4]。鸦片战争前夕,魏源、林则徐等开明士大夫已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彰显出晚清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对国家与现实社会的关怀与认知。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推动传统价值的考量转向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魏源从制夷战略上得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尤其强调“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5],同时主张学习“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此外,魏氏等大力主张开设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积极仿制西式船舰。这种以科学态度向西方学习、认识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姿态,直面冲撞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认识论。随着战败后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种科学认识的转向急速发展成为社会思潮,加剧统治阶层内部分化,使众多社会力量受其感召,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农民运动顺势而起,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始以自强、求富探寻强国御辱之路。科学的价值,由西方向东方、由传统向近代转移,正是这种科学的认识与解释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化。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6]。这种发展希望,以世界视野的史地观念在中国深得时代发展的召唤。中国人近代的地理观念更替尤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代表,个体的作为若只是个案的例证,大量外国新地理著述的引入和众多同时代学人同类著述的涌现,或许更能说明向科学的价值转移的大趋势。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南洋东来的地理学欧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7],却可以对19世纪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译者绘制的地理学知识大量传入中国加以论证。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8],1837年迁移至新加坡,出刊至1838年。其专辟“地理”栏目,介绍世界区域地理知识,宣传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前后,有众多外国传教士在华出版近代地理科学著作,如祎理哲在华的《地球图说》《地球说略》,慕维廉的《地理全志》等[9]。晚清士大夫关心时局与国家疆域,姚莹的《康輶纪行》详记川藏与列强的关系;徐继畲在西方地理学直接影响下,以弃“夷”的平等国家观念著有《瀛环志略》[10],理论上应成为后人处理国家关系的一把标杆。暂且不论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后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显见其传播及影响力尚小,然作者的变局论在晚清可谓开时代先河,尚有启后世之功[11],足显其见识确实相当卓远。以认识和解译世界的地理科学为先导,关心时局动态,主张学习西方技艺寻求强国御辱之道,真实描绘了近代中国被迫开启国门阶段科学价值的转移图景。
(二)科学的工具性价值
科学的工具性价值以改造世界为第一追求。科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又往往以社会运动为突出表现,例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封建士大夫发起的自强运动。
农民阶级以宗教信仰构建理想社会,亦借重某种暗合科学的表达事象,努力改造现实。这种认识源于“科学价值必须被认为是延伸到包含人文科学、法律和人类的种种宗教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12]。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并非为了科学。然而,我们也并不能以科学来解构宗教,从而否认上帝的存在[13],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其在实践过程中,隐含的部分科学价值。在内忧外患时局下,洪秀全吸取基督教部分教义、仪式,结合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思想及民间思想学说交糅融合,这种改造的态度一反科举的八股作风,强调信仰自由与得救,可谓变相的天赋人权实证范例。宗教与科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往往杂合在一起,并非一直完全分隔,这种杂合却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以重现。宗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我们不如以“理念”解读或许有更为别样的认知。在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甚至自创教以来,都不是以其宗教的理念引导民众入教或组织教徒开展政治斗争的,恰恰是利用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发。在正史和地方史志中,有大量关于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地区尖锐的阶级矛盾的记载,如:
广西桂平县“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
——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
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
——(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
晚清道光年间,广西地方钱粮由“卯铺”包收,“此辈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种种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
——(民国)《邕宁县志》卷十四,页五。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言“而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加之摈斥,司讳匿不报,至盗或有遂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14]。可见,富豪兼并,政治贪污连同巨额赔款,连年灾荒催生了农民运动[15]。同时,又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物质利益驱动,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又将农民的小农思想发挥到极致,吸引农民成为教徒。可见“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撤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16]太平天国后期洪仁轩《资政新篇》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不是农民运动实践的产物,也不是太平天国的运动纲领,确实也显见个体对现实的科学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勇气和努力。
当我们看到晚清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洋务派与顽固派,并以对立的视角来看待科学价值的转移会有另一番景象。19世纪60至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以图自强求富,这是科学的工具价值改造世界的集中体现。这种由认识与解释向功利价值的转移,并非缺失了之前的科学认识与解释,而是兼而有之,并侧重于改造的功能。这场及时雨对于摧枯拉朽的晚清来说,确实来得太过猛烈,已至于外敌压境时,清廷仍无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缺乏以科学大器正面御之的信心和勇气。再且上帝赋予技术天然的保密性传统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洋务运动引进技术后的种种无奈,尤其中国封建王朝的行政也同样具有悠久的保密传统。这两种传统的交融,铸就了无奈的后果。洋务派三十来年的科技兴国的战略以甲午海战中国败北而告终。
科学毕竟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没有认识上的解放,那是不太可能正确运用这把利剑为已所用。这或许更有益于我们加深对科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理解[17],同时更兼有历史实证的体验。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并未因洋务派的没落而让位于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反而因忠君爱国、务实进取的洋务运动一再以实体的科学为极欲之所归望,将科学大旗隐匿其间,成为实业救国的先导,却也注定其固本求新的败局。倘若不以进步/倒退单一论之,而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审度这个科学价值的转移过程,人自然是科学理性与科学伦理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目标。
(三)科学的目的性价值
目的并非等同于价值,科学的目的性价值转移更是如此,透过康梁政治改良与新文化运动,更显现近代科学的各种价值认识的深化和融合。尽管我们不必争辩和强调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的利弊与结果,却不得不承认“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18]。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要求,这时“中体西用”的理论成为妨碍西学在中国发展的羁绊。这其中隐藏的正是封建这一制度和社会的根源和最大障碍[18]。然而,当科学并未以实体根植于本土,就成为一种文化信念或社会意识风靡本土,那一切非科学的甚至并不能以科学定位和评判的文化或传统,都得将承受割股之痛。对这种“痛”的治疗办法,就是康梁提出的改良封建王朝主张。
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的维新运动,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如同昙花一现,确也是先进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伟大尝试,这是科学的文化价值在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成为清末启迪人们思维的一次较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康梁等改良志士力图模仿英国民主宪的政治道路,由向西方学习“器物”上升到学习“政治”的高度,以期强国御辱,不失明智之举。19世纪后半期,虽然强盛的英国已渐显出落日英雄的窘相,但功利价值的目的性结果最终还是以维新派的东施效颦而告终。学习西方,由一种意识和态度仅仅演变为一种笨拙的技能,无论是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都无法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反倒是加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至灭亡。这种分化,甚至在新阶级里出现了“保皇与革命”的政治对立取向。科学、民主、革命思想在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精英阶层最终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事件的考察基于运动或许是较好的冠名词。虽然我们不必像库恩那般考据革命概念的变迁[19](P51-77),这也许是因为革命太过于刺耳,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是不轻易使用革命字眼的。但是在近代的中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领域的事件却又是频繁使用的。
因此而认为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西方近代科学在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移植(体制化建设),实为太晚。康梁维新主张、政治意识的英式道路确实不能以成败易其主而湮其名。留学回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热心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与其说是“在中国移植体制化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教育活动,触及社会文化的深层,使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冲突成为严肃的文化问题”[20],倒不如说,这正是科学的各种价值认识的深化和融合。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倍受关注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以科学理论武装思想和头脑。从科学信念来讲,新文化运动催生了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种思想学说,并且坚信科学信念可以资治兴国,其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和新的探索。此前,人类在较长时期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都具有人文的特征而不是科学特征[21]。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未曾断传,以洋务运动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之科学价值观之,虽不能认为以往的论断都是科学的,就如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却也断然不能以科学价值的标准一统了之。而以科学的态度来论,也正是直至新文化运动,科学才作为一种信念,成为“砸破精神枷锁,扩大自由度的工具”[22]。这种工具价值铸就了科学价值的大融合时代。科学不再是富贵阶层的独享餐,而成了普通大众都乐于为之奋斗的信念。这种科学的价值,并非运动的初衷能给予解答,恰恰是后人经过了解与考察后,才还原了那些运动带来的客观价值和影响。
三、近代科学价值转移带来的反思
虽然我们不需深究近代科学价值为何会转移,也不必过多重复前人对结论做的具体分析,姑且列出一些分析思路以探讨这类问题资以借鉴。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清朝统治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导致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各种宏伟计划均告失败。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可谓是封建社会制度。其实,在探讨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功绩也正在这里[23]。基于其前后的事件与人物为科学技术引进和科学的价值转移所做的努力,我们皆可从这一思路得出更贴近历史的认识。因为我们懂得,确实应充分利用历史证据“在历史对革命的感知与史学家对革命的感知之间,必须明确加以区分”[19](P前言1)。这样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实证的结合,对于问题的深入是极为有效的。
中国的近代化,正是世界近代化的缩影。近代科学的价值转移在中国兼具一般和特殊的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也正是人类迈进科学的和革命的新时代,激励更多的人探索和发现新现象新事物,并且追问“科学到底是什么”等相关问题[24]。伴随这一问题而来的,是科学的价值在实践中的探索。这种探索,正是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也是从因果性到目的性的转化,从真理性到功利性的转化,从一元性到多样性的转化[25]。或许科学关心的是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技术才关心功利价值。但是,鸦片战争轰开中国大门后,近代科学的价值被大量引入中国,正是以技术物的形式得以呈现的。近代以来的科学与技术,透过以上三个转化的思维视角,我们可以更明晰地看到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科学的工具价值,是物化技术的反映,科学的理性价值又是对工具,即物化技术的深度反思。何况,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26]。这种精神贯通科学技术这一体两面,对于我们了解科学的价值转移会呈现更为立体的全面的历史图景。
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科学的价值转移,我们都会对预期结果产生一种莫明的高估。因为已有人反思科学史研究同历史的融合度与文化发展的程度成正比[27]。这或许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大叙事通常充满了过高的希望、梦想和幻觉[28]。当然,这也并非不利于问题分析的展开,只是会在不知觉中忽略很多关键的细节和更多生动的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如果以“从人到人”的人类学主线来审视,我们就可以由“走近”历史到“走进”历史。一切的人类文化,乃至科学的价值都是人类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既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虽然科学无法给予我们任何真理(因为真理是永恒的,然而科学及其知识却是在证伪中得以接续),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原则[29]。我们基于“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一直在努力做一些接近客观真理的建构,倒也不失为有益的探索。人的进步才是最根本的进步,人的进步又以思想解放为根本。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思想自由,自由正是实践探索的不竭动力。
有人认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活动,它考虑传统的论述与能克服的严重困难[30]。这种考虑正是基于人与人性的反思。只有当人性的价值及意义在科学中得到展现时,科学及科学事业才富含人性的光芒,才能窥见科学源起中的人性空间[31]。从而当科学价值基于人类思维演进史的探讨,这种哲学视域下的人与人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的堆叠,也就能更深入科学的价值认识。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无政府主义是科学的本质所在,其在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较之讲求规则与秩序,更具人本主义,且更有激励进步的作用[32]。这种基于批判大传统来认识科学的价值,正是对人的自我的尊重,对自由的一种崇敬,但也往往容易导致对人的概念及价值的误判[33]。
科学的价值,往往强调科学“主体”并非强调“人”[34]。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得深究隐藏在科学主体后面起关键性作用的又是什么?不是科学物化的技术或工具等实体,也不是科学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等的关系,而就是人本身。从而,我们更应该透过科学的价值,看到人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只是人的价值中的其中一小部分,并非全部。要实现科学的价值,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且这种人的活动,只有当社会在实践中产生了对科学的需要,并且具备利用科学的一定能力时,科学对社会的价值才得以形成和实现[35]。此种为科学主体需要而对科学价值进行的客体考察,其本身就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价值的统一体。通过主体的外在价值的分析可见,不论科学的解释价值,工具价值还是目的价值,也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价值,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工具,其价值不仅对实现别的价值有用,它本身也是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从近代科学的价值转移来看,不论是由传统“观念”的科学到“实体”的科学,由“实体”的科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系”的科学,与其说是科学的价值由认识到实践,由传统到科学直至理性,倒不如说是人对科学的价值所做的转移,也是近代中国人自身的转移。这种人的转移,也就是由势力的个体性到群体性,由阶层的派别化到组织化的过程,是人的认识由“观念-实体-关系”的过程。
倘若对科学的目的和方法之反省,缺乏对科学问题的特点、性质之反思,缺乏对科学解释之思考,缺乏对科学解答可靠性和检验性之反思,那我们也就已放弃科学之所以成其为科学之核心内容。不论是反省、质问、思考、反思还是就“谁对科学做了那些事”而言,都是物有所指,即人。科学只有以技术为中介,且要经过复杂的转化链条,才有可能变为生产力。技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体现和外化[36]。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依然是人。马克思视科学为历史之有力杠杆和最具价值的革命力量[37]。因此,透过近代中国科学的价值转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时期科学的价值经历了从工具到目的,从认识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线性进路到非线性融合,从功利到理性,从实体到关系与观念,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思潮的曲折转向、急剧变迁、整体趋于融合的演进历程。作用于科学这个杠杆及历史发展过程的亦是人。人的认识的转移与深化,正是表现为科学的价值转移,且二者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