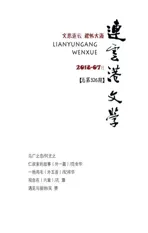观自在(六章)
2018-11-13孔灏
孔灏
爱上春梦婆
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成年人每晚做梦约4—6次,做梦时长可达1小时,每个梦之间大约相距一个半小时。这样,如果一个正常人以八九十岁为寿,他的一生做梦大约会有15万个,合计4年时间。而且,由于梦的持续时间与梦的内容复杂程度成正比,因此,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曾经有过太多轻描淡写的梦,它们在睡眠中就被遗忘了,再也无法记起。
中国古人高度重视梦的研究,在《周礼·春官》中,就根据梦的成因,非常细致地把梦分为正梦、噩梦、思梦、寐梦、喜梦、惧梦等六种。《黄帝内经》则以临床诊病的经验作为根据,提出了“邪淫发梦”的理论,指出多梦是病,还详尽地阐述了各种梦与脏腑疾病的关系。而汉代王符的《潜夫论·梦列》和明代陈士元的《梦占逸旨》,更是通过对梦的生理、心理等内在原因和节气、环境等外在原因的分析,研究各种梦兆,并且都能写得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当然,咱们国人比较熟悉的还是诸如《周公解梦》一类的占梦之书,有学者统计,我国历代占梦书多达二十余种。
据说,不仅是咱们中国的圣人周公会解梦,那外国的圣人释迦牟尼佛也是会解梦的。有一部《阿难七梦经》,说的就是佛的表弟、也是他的弟子和侍者阿难尊者,曾有一夜连做七大噩梦,梦醒之后回忆起来,仍然忍不住“心惊毛竖”。于是,他把这些噩梦向佛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释迦牟尼佛当即为其逐一详解,道破了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佛教发展的种种艰难曲折——故事的高潮还不在这里,高潮在于:佛虽然自己为弟子解梦,却又在《长阿含·梵动经》中,将不可读诵解梦之书、不可为人解梦列为和尚们不可违犯的大戒之一。这就像孔圣人晚年自己认真研究《易经》,还叹息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专门引用“恒卦”中“九三”的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将《易经》的道理与人的德行直接联系起来。之后,却突然又明明白白地来了一句:“不占而已矣”,颇有类似。
时至今日,梦,作为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理和精神现象,它的各种功能,依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理喻。比如,古今中外的很多圣贤和奇人异士的出生,均和他母亲的梦有关:伏羲、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刘邦、禅宗六祖慧能……等等,不胜枚举。同样,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词人、散文家、书法家、哲学家苏东坡先生的母亲,也是如此。
有记载说,当年,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曾做一梦:梦到某日家中,忽然有位法师前来做客。这位法师长相奇特,身体瘦弱,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梦醒之后,程氏即怀上了苏东坡。多年以后,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江西高安做官时,与真净克文、圣寿省聪两位禅师结为好友。又某夜,苏辙与真净克文、圣寿省聪两位禅师都做了相同的梦:在梦里,三个人结伴,共同迎接五祖师戒禅师。结果第二天早上,苏东坡来了。于是,三个人非常惊异,分别说出了自己在前一天晚上的梦中之事。苏东坡一听,很认真地说: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倒是真的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是个僧人,在陕西一带往来参学。那真净克文禅师一听之后,更加惊异,说:五祖师戒禅师确实是陕西人啊!并且,这位禅师也确实是一只眼睛有残疾。接着,大家又详细地推演了一番:这一年,戒禅师已圆寂五十年,而苏东坡当年正好是四十九岁。于是,大家得出了结论:苏东坡的前身就是五祖师戒禅师。这种说法,为相当多的高僧大德所认可。比如,佛教界的莲宗十三祖、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并曾培养出弘一大师等佛门龙象的印光祖师就曾开示说:“五祖戒,后身为苏东坡”。再后来,看王守仁与金山寺僧的故事,读那首“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也是如逢故人,不由会心一笑。
当然,真要完完全全地领会古人之心,哪里又是那么容易的事?!即以苏东坡为例,那么好的人品,那么高的才华,那么洒脱旷达的生活态度,那么忠君报国的本愿初心,也往往不能够被自己同时代的各色人等所理解,甚至横遭牢狱之灾,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发配流放至偏远蛮荒之地。但是,作为“五祖戒,后身”的苏东坡,同样亦如古德所说:既然是人生如梦、镜花水月,那么,梦中的老虎,又有何可怕之处呢?南宋赵德麒《侯鲭录》卷七上说:“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间。有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就在现在的海南岛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罪臣”苏东坡同学顶着个不知是葫芦还是椰子做的帽子,乐呵呵地在田里面且歌且行。有位七十岁的老奶奶,对小苏同学说:看你苏大学士现在的这副模样,再回忆起当年的富贵荣华,就像是昨夜的一场春梦吧。小苏同学听了,很认真地连连点头道:是呵是呵,确实如此。于是,乡亲们就把这位老奶奶称作“春梦婆”了。要说“春梦婆”这个人和这个称呼,想来,一定是苏东坡喜欢的。比如,他自己在《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中,先是记述自己的一次酒后出游:于半醒半醉之际在竹刺与藤梢中迷路,一路寻问之后,好不容易看到牛屎才寻得归途;然后,又在黎家三位小朋友的口吹葱叶声中,寻到了类似于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舞雩台上吹吹风般的放松和愉悦;最后,他还是要强调自己:“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和那位名叫“春梦婆”的老奶奶,可真是有缘得很呢!种种日常之间,他们总是有着种种相处、种种遇合,如此,自然也会有着种种的快乐尽在其中吧?如此,如果再允许我们虚构,允许我们调侃,就说是苏东坡“爱”上了“春梦婆”,似也可以聊备一说吧?
从苏东坡和“春梦婆”的故事,说到孔子孔圣人,好像还得补充几句。众所周知,孔子他老人家是反对学生做“白日梦”的。《论语·公冶长》上记载: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这家伙大白天睡觉。孔子气得要命,说:“烂木头没法雕刻,粪土墙没法涂抹!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老人家越说越气,又讲:“本来吧,我对人的态度,是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可是现在呢,我对人的态度,是听了他说的话却必须要观察他的行为。这,就是由于宰予的事而改变。”
不过,对于夜晚做梦,孔子应该还是认同的。比如,他老人家又说过:我啊,应该是太老了吧?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从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孔子自省到:自己,一定是老了,所以,才太久太久没有与古圣先贤在精神上有所遇合了。这话,其实和《华严经》上的一段话有共通之处:所以我知一切佛与我心,悉皆如梦;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我心,悉皆如幻。所见诸佛,皆由自心。
从苏东坡往上再推一千五百年,老苏家还有一外国亲戚叫作苏格拉底的,也是位大哲学家。这位哲学家说过:死亡,犹如无梦相扰的安眠。这样看来,不仅仅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而且,如梦的人生中,还必须有梦!所以,人有梦,而且是春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乐事啊……
出来吃盏茶
风雪之夜读《西厢》,直读到春风满室,冰雪含香!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好!好是好,确实是好!不过——前两句说的事儿想要实现完全没可能,后一句说的事儿想要实现也是非常不容易。又不过——虽然如此,还是好!还是看了喜欢。
那张生初见莺莺时,道:“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凡人、凡事,太过美好,总是显得太过突然或者说是太过出人意料。如果需要给出一个容易让人接受的、合理的解释,归之于宿命,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至于说,宿命之所指向,又为什么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则可以说“因果”,可以说“前定”,可以说“上帝不掷骰子”,也可以,干脆什么都不说。
当然,什么都不说,还是一种“说”,老子把这种“说”叫作:“行不言之教”。同样,圣贤所说别无二致,到了儒家那里,孔老夫子也照样要说“予欲无言”。因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都不说话,我,又有何可说呢?
老百姓中间也有句俗语,叫作“会说叫人笑,不会说叫人跳”。这同样是劝人,如果“说”得不好,且不如不“说”。到得《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时,那张君瑞月夜会莺莺,有“呀,刘阮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嫩蕊娇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两句。金圣叹评:“《西厢》最淫,是此两句。”那么,老金的点评,是说这两句说得不好吗?依我愚见,这两句说事,既直白香艳,又隐约深致,有人有景,有情有境,直把那“红罗帐里不胜情”的具体过程,说得“也是极好的”!所以,当年的金圣叹为《西厢记》被列为禁书一事打抱不平说:“人说《西厢》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有?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是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依金圣叹之为人,把他说这段话的场景换算成现在的模式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那愤青老金抱着个膀子、乜斜着眼睛说:《西厢记》就特么说了那么件事,就被说成是本淫书。也不想想,世界之大,那件事何时何地不在发生?是不是因为天地之间总有那件事,这天这地也就变成淫天淫地了呢?再仔细想想,那些“正人君子”的老爸老妈如果没做那么件事,又哪里轮到那些混账王八蛋到这世上装正经啊?!
也是!当年,温柔敦厚如孔子者,谈论《诗经》首篇《关雎》时,就直接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定性。这才是真正知天道知人道、懂世情懂感情的圣人呵!后来,孔子他老人家还专门说了一句话来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来理解《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一本《诗经》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叫作:坦率,真诚,别乱想!
《孟子·万章下》中列出了四种圣人的典型,其中,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也”。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圣人。孟子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孟子从“事”上看,应当正是参看了上述孔子之谈《诗经》;从“理”上看,则应当是参看了《易经·系辞传》:“变通者,趣时者也。”实际上,一部《易经》说“变通”,在“德行”的前提之下,无非是强调了“时”、“位”二字。身处何“位”?当为何“事”?需要何种步骤?应以何种措施?端看一“时”字也。“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不可不重也”,其用广矣,善莫大焉!
这道理,听起来似乎很“大”,其实尽在生活日用里。中国民间的青年男女两相爱悦,就深得了一个“时”字的精妙之义。“隔山隔水隔条冲,一难相见二难逢。久不相见心莫冷,花到春天自然红”,这个“时”,是在你心中,在我心中;“打鱼不怕风浪高,撑船不怕船头摇。有心同哥过大海,海底有针妹也捞”,这个“时”,是你若不弃,我必相从;“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时”,是天地同春,你侬我侬;“说山挡不住云彩树挡不住风,说神仙老也挡不住个人想人。宁教那皇上的江山乱,也不能叫咱俩的关系断”,这个“时”,是“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个为表妹写过“错、错、错”、“莫、莫、莫”的南宋诗人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也记录了一首当时的民歌:
“辰、沅、靖各州之蛮,男女未嫁娶时,相聚踏唱,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
这首歌,写得“美”而“有趣”。所谓“美”,自然是“美”在知慕少艾的情怀,再配上“小娘子”和“叶底花”的对举,既是人从花喻,又是情景交融,字里行间都透着那么一种天人合一、天作之合的情韵。所谓“有趣”,却是着落在上述语境之中的“无事”二字。本来,“无事”之人,殊为难得。如宋人王炎词《临江仙·思忆故园花又发》中有句:“拂衣归去好,无事即神仙”,或,又有后世之读书人撰联为:“有书真富贵,无事即神仙”。但是,无论是词中还是联中的“无事”,都是真正地无“正事”而有“闲事”;而那少年口中的“无事”,却是典型的有“正事”而无“闲事”!这其中的拿捏和轻重,因了少年散淡疏狂的口气和别有深意的用心,就形成了一种“形而上”或者是“形而下”的“向度”,至于这“向度”是有“力”还是无“力”,则全凭当事者一心之运用了。这就好比唐代诗人杜荀鹤《赠质上人》诗:“枿坐云游出世尘,兼无瓶钵可随身。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逢人不说人间事的无事之人,终究是,还在人间!同样,那本来无“事”的小姑娘,真的出来吃了盏茶,可不就是有了“事”了?
所以,郑板桥有一首《竹枝词》也写:“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这当然是另一种情形了:那本来无“事”的小姑娘,对着小帅哥说,等你没事的时候,且来喝杯茶吧!我的家门前有一树紫荆花,好找得很呢!又,《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王熙凤打趣林黛玉的话,还是说:“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如此看来,恰好印证了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
有人分析,“茶”之一字,正是“艹”、“木”、“人”三字之合体。故,可以用“茶”字,来暗喻“草木之人”。但这“草木之人”,也有两个“向度”:比如,被赵州和尚安排“吃茶去”的那个人。那是讲的“禅茶一味”,重点,是要强调人的修行。然而在生活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被青年男女邀请去“吃盏茶”的人。那是讲的“有事无事”,重点,是要强调人的感情。
但是,人的“修行”和人的“感情”,又哪里会是两件事呢?有高僧说:“闻佛语,如闻冤家语”。如此,这位高僧也好比,是为我们泡了一杯茶。这老和尚!他且坐在我们的对面,看着那杯茶,看着我们,再不说一句话。
蝴蝶与歌声
现代诗中,时有把蝴蝶比做飞舞的花朵之喻。按庄子的逻辑,这蝴蝶或者也会不会想道:是我这蝴蝶做梦,静止下来,停在枝上变成花朵?还是那花朵做梦,飞将起来,舞在空中变成了我蝴蝶?
庄子和天地亲,所以天地也和他亲。俗语所谓“相亲相爱”,无非是说:亲和爱,总是要相互的才好。反言之,仇和恨,也同样是相互的。这样,才会有因果历历,报应不爽。释迦牟尼成佛后,仍有“三不能”,那第一个“不能”,就是定业不能逃。话说佛陀的祖国迦毘罗城,曾遭敌国侵略。敌国国王琉璃大王率大军计划攻下城后,杀尽释迦佛的族人。佛陀闻讯后,曾三次坐在大军经过的路上。按古印度习俗,大军出征的路上遇到僧人,必须退兵。这琉璃大王只好按常理出牌,鸣金收兵。也因此,琉璃大王心中的仇恨之火,愈燃愈烈。到了第四次,佛陀虽然挡在路中,琉璃大王却再也不讲规矩,指挥大军长驱直入,杀入城内。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有位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运用神通之力把释迦族的至亲五百人装到钵里,让钵盂像飞艇一样从天上飞到城外。等目犍连喜滋滋地打开钵盂想要放出这五百人时,发现他们已全部都化作了脓血。佛陀告诉他,认吧!这一切,都有前因:在N世以前,琉璃大王是在水里的一条鱼王,率领鱼鳖虾蟹在河里生活。河边的村民都喜欢吃水产品,他们把所有的水族都吃完后,把鱼王也捕了上来。当时,全村的人都分吃了这条大鱼,只有一个小孩没有吃鱼,但是他因为好奇用棍子在大鱼的头上打了三下。这个小孩就是佛陀的前世,全村的吃鱼人都是释迦佛族人的前世,这条鱼王就是琉璃大王的前世。所以,释迦牟尼成佛之后,也非但救不了他的族人,还因为曾打过鱼头三棍,得了头痛三天的果报——定业难逃呵,只因:因果不昧!
把蝴蝶和歌声放在一起说,又当有另一层意思。20世纪80年代,乔羽老爷子写过一首歌《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据说,这是老爷子耗时最长的一首歌词,从起心动念到构思完成,用了整整25年时间。早在1963年初夏的一天,乔羽在家中打开窗户,忽然飞进一只蝴蝶。它在屋里绕了几圈,又从窗口飞出,老爷子目送着它消失在远方之后,豁然有悟,却又不知所出。直到1987年提笔咏叹友谊时,才重新开启了心底的记忆,成就了这首经典好歌。当然,这个“你”,未必只是指蝴蝶或爱人,它也可以是代指漫漫长路,也可以是代指迢迢岁月。于是,蝴蝶和歌声,也好比说的是天地山川锦瑟年华的背景下,我们为世界和时光所感动,继之,再把自己的生命融会于感动过我们的世界和时光之中。
陶渊明论音乐,有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弦乐不如管乐?管乐又不如人声?老陶答:“渐近自然”。这四个字说得真是好!对人而言,以丝以竹做乐器,当然不如用自己的肉嗓子做乐器更自然。恐怕,这话就是让庄子听了,也会颔首称是!因为,说起庄子的歌声,那本也名闻千古、惊世骇俗。《庄子·至乐》上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的妻子逝世,他的老朋友惠子听说之后赶紧前往庄家吊唁。可是当他到庄家的时候,见庄子正岔开两腿,像个簸箕似地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着歌。这种场景之下的这种歌声,本来难得听闻、本来令人不忍,可你若是能够想道:这庄子不过是只蝴蝶在梦中变过来的,那,你又何奇何怪之有呢?
庄子与天地万物皆亲,所以,就不会独亲其亲之“生”,而不亲其亲之“死”。由这位道教的祖师爷先开了头,后世之学人,自然是茅塞顿开、纷至沓来。像那李白,本是道教的行者,老庄的粉丝,故写起敬亭山时,也端的气定神闲,清虚冲淡!那《独坐敬亭山》说的是:“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与鸟亲,所以,那众鸟飞尽,他为之欢喜;他与云亲,所以,那孤云独去,他也被感染了闲适;他与山亲,所以,他与山如如不动,相互观照,两下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李白这“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固然是道人情怀,不过,也并不妨碍儒者的英雄所见略同。在李白去世十年后出生的又一位李姓文学家、哲学家,唐代大儒李翱,虽一生崇儒排佛,作《复性书》三篇论述“性命之源”等问题,为后来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却在《赠药山高僧惟俨之二》诗中写道:“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撇开知人论世不说,他应该真是把那药山惟俨禅师,也当作了孤峰顶上的石头或者飞鸟了。
20世纪80年代,听小虎队唱《蝴蝶飞呀》:“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忽然想起乔羽老爷子写《思念》,他老人家那二十五年的时光堆积起来,也不知,又为谁,造了一座敬亭山?
狸首之班然
古时候,有个名叫原壤的人,他的老母亲去世之后,他的老相识孔子孔圣人来帮助他办理丧事。这中间,原壤突然敲击着棺木说:“我啊,已经很久没有唱歌抒怀了。”于是自顾自地唱了起来:“貍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这棺木的花纹,像是狸猫的头一样色彩斑斓啊。拿斧子的手,也像是女子的手一样有一种舒缓、也有一种柔软。孔子很难受,假装没有听见,走到了旁边。旁边随从孔子的人问:老师,您就不可以让他不要唱歌吗?孔子回答说:我知道,没有失去的亲人才是亲人,没有失去的老相识才是老相识。
故事见于《孔子家语》,也见于《礼记》。原壤唱的歌,是上古时代行射礼的过程中,诸侯唱来作为发矢节度的礼乐。《礼记》这本书,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分别是“三礼”、“五经”和“十三经”之一,宋代以后,更是位居“三礼”之首。读《礼记》“檀弓”篇,每读到这里,我也很难受:为原壤,为孔子,也为那个跟随孔子的人。
说起原壤,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如果按照联想记忆法,提起孔子因为原壤而讲的那句名言“老而不死是为贼”,大家可能就容易记住他了。《论语·宪问》上说: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以一种蹲着两脚不坐不起的无礼姿态,来等待孔子到来。孔子见了,就训斥原壤:你啊,小时候,就不守逊悌之礼。长大了,又毫无著述来教导后辈。现在,又老而不死的混日子,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祸害吧!孔子一边说着,一边还用手中所持的住杖叩击原壤的脚胫。
孔子这人,其实最讲原则。人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用善行回报恶行,这种作为乍听之下,确乎有点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孔子非常冷静地反问说这话的人:假如要用善行回报恶行,那么,你用什么回报善行?所以,孔子认为:应该用公平来回报恶行,用善行来回报善行。又,《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这是孔子在直接说,乡里之中那种不分是非、处处讨好的所谓“老好人”,实际上是败坏道德的人。至于每每被无知之徒用以攻击孔子不讲原则的所谓“中庸之道”,其实讲得正是要“择善固执”,选择那真正合适和正确的,坚持到底!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来看孔子与原壤的相处,看原壤的从小到大都吊儿郎当不正干,看他在母亲死了之后还敲着棺材唱歌的疑似禽兽之行,从古到今的儒者们,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得通:这疾恶如仇的圣人孔子,为什么竟然容忍自己的老相识原壤如此作为?如果已经“忠告而善导之”了,既“不可”,何不“止之”——这“止之”,当然不是停止忠告和劝导,那是干脆绝交算了嘛!
但是,孔子对于原壤,既有责骂,又有怜惜,既有失望,更有理解。他老人家说了:“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照我看,这话的意思或者可有三种理解:其一,原壤和他的母亲感情很深,母亲身体的死亡,并不代表母亲形象在他心中的死亡。所以,他的唱歌与眼前之人、之事俱无关联,那只是自己的一种兴之所至罢了;其二,原壤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是,我孔丘作为他的故人,还是要尽到故人的责任呵;其三,原壤所唱“貍首之班然”歌,本是母亲之所教唱,如今母亲去世了,他唱此歌,正是深切悼念他的老母啊。
董桥曾经说过,再动人的男欢女爱都是私事,别人听了肉麻。还真是!所以,对于这两个老男人之间的友谊故事,宋朝的朱熹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母死而歌,盖老氏之流,自放于礼法之外者。”原壤这家伙,应该是老子道家一派的人物,他把自己彻底地放逐于礼法之外,当然不必以常理观之!这样,孔子出于一种学术尊重,自然也应该充分地理解原壤、谅解原壤。何况,那原壤,毕竟是孔子的故人呢?
实际上,儒家在讲原则的同时,从来不否认对于情感的珍惜和注重。且不再说圣人孔子,即后来的亚圣孟子也同样遇到过学生所提出来的类似问题。那时,孟子的学生桃应假设说:在舜当天子的时候,如果其父瞽叟杀了人,此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皋陶应该怎么办?孟子说:皋陶当然应该把瞽叟抓起来法办!桃应又问:那么,舜不可以利用他天子的身份和职权去阻止这件事情吗?孟子回答说:作为天子的舜,怎么可以阻挠司法公正呢?桃应打破砂锅问到底说:那么,作为人子的舜到底应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作为孝子的舜,假如有机会的话,当然会把天下看得连一只破鞋子都不如,偷偷地背着自己的父亲瞽叟逃到天涯海角去,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甚至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天子这回事儿。
后世儒者,每于这种极端的事例面前,时露吞吞吐吐之象。大概这种事情,在他们的内心看来,多多少少会有点难受、难办吧?我想,这应该是读书读死了的缘故。面对这样的问题,老庄一派的道家人物,确实更加通透洒脱,干净利落。比如庄子在《逍遥游》中就讲:“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你读书少,自然不了解咱们读书人的事;你的寿限又短,更不了解我们这些年寿长的啦。你和我,差距太大啦,不跟你说……
但是,要说到真正地通透到底,恐怕还得说是释家。唐代布袋和尚的《插秧歌》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那一方水田之中,青秧与蓝天相互映衬,色彩斑斓、煞是好看,也像是狸猫头上的花纹一样:恰恰,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恰恰,有那么一点心心念念。
孟子不高兴
孟子脾气大。而且,不是一般地大!
《孟子》首章首节,就看见他老人家在发脾气。话说,这是孟子初次与梁惠王见面,梁惠王就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梁惠王这人,本没什么能力和建树,却偏偏是个好大喜功之人,历史上著名的“孙庞斗智”之惨败于马陵道的庞涓,正是他重用的心腹爱将。其时,他刚刚经历了三次败仗,太子被敌国俘虏,上将被敌人斩杀,自己国内财政空虚、民怨沸腾。可他见到孟子时,似全不以之前的败迹为耻,倒还是一副居高临下、老三老四的样子和口吻。脾气大的人本就敏感,何况是面对如此德不配位之所谓“人君”!孟子当即开骂:我特么听到人家唯“利”是图就烦!为国君者,有了仁义还不够吗?做国君的想着怎么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做重臣的想着怎么样有利于我的封地?各级公务员和老百姓都在想着怎么样有利于我自己的小家?上上下下,皆为着一个“利”字你争我抢,当真是“仁义放一边,利益最当先”,你的君主之位岂不是大大地危险?但是,如果反过来看,讲“仁义”的人不会抛弃父母,讲“仁义”的人也不会不顾君王。所以,你只需强调仁义就行了,何必唯“利”是言呢?
也真是,让孟子他老人家不高兴的事儿太多了——就说这梁惠王吧,在孟子的教诲之下总算是有所进步,懂得谦虚地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了,也听到孟子著名的“仁者无敌”论了……结果,还没等到有所作为之时,却突然又一命呜呼了!他那继位的宝贝儿子梁襄王,用孟子的话说,更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远看吧,也不像个人君的样子;接近之后有所了解呢,根本就是个无知无畏的货!而且,告诉他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一统天下后,这位梁襄王竟然问孟子:有谁,愿意跟随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与无知无畏同行的,总是少不了无耻!
孟子真是不高兴啊!
其实,孟子的高兴指数并不高。他自己说过,君子有三种快乐,就是给个皇帝也不换:“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朱熹认为:这三种快乐啊,像父母健康长寿、兄弟平安无事的快乐,要靠天意;像能够遇到品学兼优之青年才俊来教育他的快乐,有待人和;只有那俯仰之间对天对地都无所惭愧地快乐,可凭一己之力能做到!可是,要让一个人面对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毫无愧疚,为什么总是那么难呢?
所以,孟子不高兴!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最后,他干脆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骂人,骂得直白,骂得深刻,也骂得悲哀,骂得痛彻……
当年,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如果有人对一位仁者说,井里面掉进去另一位仁者,这位仁者会照着跳下去吗?后来,孟子的学生问孟子:对于以至孝闻名的天子舜而言,如果他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又会怎么办?圣人和亚圣的这些学生们,他们都曾经历了些什么呵,才会这样想、这样问?
禅门之人,时有以儒释禅者。但他们多以孔子章句相标举,少有以孟子之说为例的。为什么?孟老夫子火气太大了!不过,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义玄禅师,常以大声呵斥来接引弟子的方式,却是大大地因袭了孟老夫子“不高兴”之风。《五灯会元》记载:
师谓僧曰:“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杆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这临济义玄禅师的喝来喝去,亦如孟子的骂来骂去,有时斩断疑情,有时震碎妄想,有时只是用来试试尘世和人心的深浅,有时就是那么纯粹的一喝、纯粹的一种宣泄而已!但是,真要到了直面世界直面生命之时,峻烈的禅风里自有一种儒者的担当。还是这临济义玄禅师,临终之时,举目四望,对弟子们说:“假如有人问起,佛道究竟是什么?你们要如何回答?”他的弟子惠然禅师马上就学着临济禅师一向教导学人的方法,大喝一声!临济禅师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谁能想象,我想要指给你们的佛之知见,以后却要在这些大喝一声的人那里断绝了。真是让人好不伤心啊!”说完,坐在法座上端然圆寂。那位惠然禅师非常不解地说道:“老师平时对来求道者都是大喝一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学着老师也大喝一声呢?”临济禅师忽然又活回来,说:“我吃饭,并不能让你们也肚子饱;我死了,你们也同样不能代替。”惠然禅师急忙跪叩说道:“老师!请原谅,请不要离开我们,再给我们更多地教诲。”这临济禅师大喝一声,说道:“我才不给你们模仿!”说完,他真的就此入灭了。
临济禅师去世的故事,也当好有一比——好比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那怎么办?”孟子答:“把他逮起来就是了。”桃应问:“难道舜不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皋陶是在尽职尽责。”桃应再问:“那么,舜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会把天子之位像破鞋子一样抛弃掉,再偷偷地背负父亲逃走,沿着海滨住下来,终身逍遥,快乐地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说到底,孟子固然常常不高兴,但究其初衷,不过是想让太多的人都能明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或者说,他不高兴,只为能让天下人,都高兴!
夜夜抱佛眠
读《齐物论》,想象庄子其人,想象他就是那个南郭子綦:就那么萧然,就那么懒散,就那么满脸都是浑不懔地坐在你的对面……
真的,就“过尽千帆皆不是”了吗?
“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我说偃啊,你这个问题不是问得很好嘛!可是,可是现在我把“我”丢了,你知道不?
《说文解字》释“我”,“从戈”,本意为一种长柄的进攻性武器。执了这“我”,可壁垒森严,可略地攻坚,可恃强凌弱行一己之私,可假正义之名逼人就范……因了这种种特性,“我”,渐由武器演变成第一人称代词。庄子有大智慧,他把“吾”和“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多么盼望:有多少人想要强大这个“我”,就真能有更多更多的人,想要丢弃这个“我”!
唐伯虎写过一个《伯虎自赞》:“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老唐自然深谙佛理,却同时也是庄子的知音。他知道,从根本上说,那个“你”才是“真我”;那个“我”,不过是沉重的一百多斤肉和附在上面的各种妄想执着所聚合的“假我”。
当年佛教进入中国时,翻译佛经的人,多为对儒、道两家都极为精通之学者。所以,儒道释之间在很多的概念和内涵方面,本就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中国维摩禅祖师,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与达摩、志公并称“梁代三大士”的傅翕傅大士,有一首著名的偈子:“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知佛去处,只这语声是。”他抱的“佛”是谁?就是这个“真我”呀!
但是,身处于万丈红尘和喧嚣物欲之中的我们,又有多少时候能够真正地丢掉那个“假我”呢?这人说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人说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人说道,“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最后,这人说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谁是辛弃疾的青山呵?谁又是,那个见到青山的、辛弃疾的“我”?
“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辛弃疾探究的“我”,轻如月色、如云影、如鹤鸣、亦轻如罗大佑“轻飘飘的旧时光”。但是,却都决然不是。或者,只在一低头一闪念间,会有一次猝不及防地相见?那一年,辛弃疾被削职,闲居于江西上饶带湖附近。这天,他在博山附近的雨岩游玩。正临溪而行时,蓦地发现:“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他知道,自己认清那个“我”了。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个人面对流水,面对上善的德行或者远去的时光,总是应该会更容易回头更容易看清楚自己吧!《洞山良价禅师语录》载:“(良价禅师)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云: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
禅宗二祖慧可付法给三祖僧璨后,即前往邺都,随形就化,便宜说法。而且,不管是歌楼瓦舍,还是酒肆屠门,不管是引车卖浆之徒,还是学富五车之士,都能观机逗教,以致四众皈依。有人就问二祖:“您是个出家修行佛道的人,本应严守出家人的戒律,怎么可以出入这些不干不净的地方、结交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呢?”二祖回答道:“我自调心,何关汝事!”禅门中人,具正眼者,不管是临水照影,还是出入红尘,若论勘一“我”字,果然都是“不二法门”!
又,就文字而论,当一个人去掉了自己身上本是古代杀器的“我”,剩下的那个“真我”,岂不正是个慈悲之我、智慧之我?所以,辛弃疾的《重午日戏书》云:“青山吞吐古今月,绿树低昂朝暮风。万事有为应有尽,此身无我自无穷。”这是他对福建任上再次被弹劾罢免的态度,这也是他对天地宇宙和世道人心的超越性参悟。细细品来,有一种旷达在,也有一种孤单在。
真的是孤单吗?好像,又不尽然!对于深刻的感受而言,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是不是都会有一种不舍又有一种不甘,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情不愿?比如傅大士的“夜夜抱佛眠”。本来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又何必去多想,那不知是谁的、一笑而过?